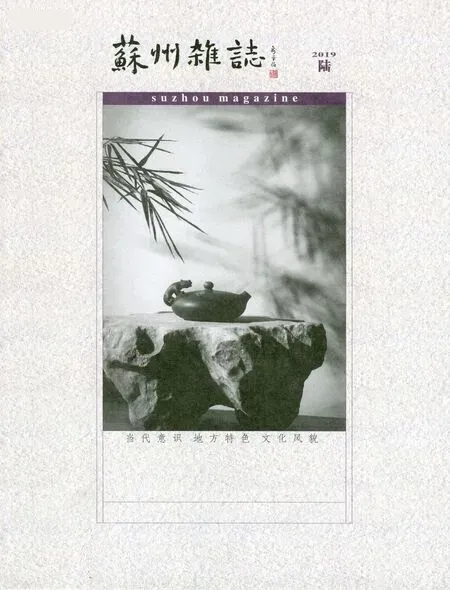我要用余下的全部生命,來尋找你
——痛悼文瑜
范小青

陶文瑜近影 攝影:薛亦然
我不能寫,心底里的痛,是寫不出來的。
可是我要寫,文瑜在等我,我想,他希望我跟他說說話。就像過去了的無數個日子一樣,他的電話來了,先說一說要說的事情,或者甚至根本就沒有什么正經事要說,就是想說說話了。然后他開始調侃我幾下,我出了小說集,他說是女巴爾扎克,我離開《蘇州雜志》到南京工作,他一直說我是改嫁的母親,兩頭放不下,等等。
當然我也不是省油的燈,也不好惹,我會回敬他的,我特別喜歡跟文瑜繞嘴皮子,用蘇州話,如果蘇州話不足以表達了,就用蘇州普通話,甚至用網絡語言,反正是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如果在嘴皮子上勝了他,那是多么有成就感啊。
或者,他怕我在開會,就發個微信來,多半是他截屏朋友圈的一段內容,他的一幅字,或者一首詩,有多少人點贊,他會毫不謙虛地問我,我阿牛?
我嘲笑說,牛。
如果我沒有及時回復,他就不管我開不開會了,電話就追過來了,范老師,你看了沒有?
我說,我在開會。他說,哦,那你等會看一看,我牛得不得了。
別以為這就是我和文瑜的全部日常,我們也有生氣翻白眼的時候,不過多半是我惹他生了氣。有一次他籌劃著他的隆重的書畫展,問我時間,某個周六行不行?我一算,這個周六正在開一個漫長的會議,我說不行。那就定下一個周六,我又算了一下,下一個周六應該散會了。于是那一次的陶文瑜書畫作品展就定的那一個周六了。
結果,我闖禍了。我沒有料到這一次會議比往年多了兩天,到周六沒有散會,我心中還偷偷希望,希望他激動于書畫大展,把我忘了。哪能呢,電話已經到了, 我趕緊“哎呀”了一聲,憋出十分討好的聲音對他說,今年會期長,會還沒散呢。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他的聲音頓時僵掉了,冷冰冰地說,那就這樣吧。電話就斷了。
我這人,做了壞事不自知,所以我并沒有以為他生氣了,當他在朋友圈里顯擺書畫展成果的時候,我肯定是要上前湊熱鬧的,結果沒有受到搭理,碰了個冷臉。然后我又私信他,再表祝賀,他禮節性地回復了恐怕是他和我的無數通信中最簡短最干巴巴的、也是從來沒有用過的兩個字:謝謝!

范小青和陶文瑜早年參加文學活動
再麻木如我,終于知道到他生氣了。有好長時間不理我了。萬一在什么場面躲避不開,碰到了,他那臉就漲紅了,真是十分的尷尬,十分的好玩。我在心里偷偷地笑。
沒事沒事,不會長的,但是我得先討好他一下,這一點我完全做得到,分分鐘都做得到,因為我的生活和生命中不能沒有文瑜的存在。
于是我們又和好如初了。繼續我們的日常的不算太多的電來電去、信來信去,偶爾呼朋喚友去吃個飯,偶爾鄉間去采個風,跟他摜蛋的時候,把我氣得噴血,他一邊學,一邊就把我們打個三比〇。因為實在奈何不了他,我就稱他為“阿爹上身”,因為他說過,他的爺爺,是喜歡賭的。
有文瑜的日子,我的心一直是踏實的,雖然我母親走得早,我父親也在十年前離開了我們,但是我的心不空,我的心是完整完美的。
來日方長。
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會想到“老”,就知道要老去了。但我不怕。我不怕老,不怕老了無聊,不怕老了寂寞,因為有文瑜在。我們可以到蘇州雜志社的院子里或者其他的任何地方,坐坐,喝茶,三兩好友,像從前的許多日子一樣,下雨的話,我們坐在走廊里,看雨,談風花雪月,談家長里短,或者談小說詩歌,或者東拉西扯,老不正經,這都是我為自己以后的日子所作的想象。

雜志社小院
文瑜在我心中,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個世界上我最依戀的人,他像我們的父母一樣愛著我們,給我們溫暖。12 月4 日,小海對我說,昨夜我仿佛成了孤兒。
是的小海,我也成了孤兒,好多人都成了孤兒。
沒有來日了。
文瑜和我哥小天是摯友,他倆情深嘴兇,斗嘴是他們交往中的常事、樂事、不可缺少之事,經常斗得不可開交,胡言亂語,互相討便宜。我父親還在的時候,有一次他們竟然讓我父親作評判,好我個父親,不假思索,就指著文瑜說,你,是他(小天)的精神父親。
小天一跳八丈高,大喊,我才是他的精神父親。
哥啊,你若不要這個精神父親,我要。
哥哥啊,你知道,我知道,你我兄妹,今生能與文瑜相遇,是多么的幸運和開心,讓我們寡淡的人生,變得那么有意思有意義。
只是如今,留下的只有悲痛和空。意思在哪里、意義在哪里啊?
從前有一次文瑜突發奇想,跟我父親說,我這輩子沒有大哥,我認你作大哥吧。我父親即刻回答,不,還是我認你作大哥吧。一個老頑童,一個小頑童,就這樣讓歡聲笑語不斷地在我家回蕩。
已經記不太清文瑜和小天最早是怎么結識的,牢牢記得的是,我在自己的房間,埋頭寫作,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在另一個房間下棋,忽然之間,就聽得“嘩啦”一聲巨響,兩人中的不知是誰,憤怒地掀翻了棋盤,摔門而去。
不要緊,不要緊,過不了一天,甚至過不了半天,一兩個小時以后,他們又在一起下棋斗嘴了。
幾十年來,文瑜就是這樣,把他的所有的好,善良,天真,厚道,智慧,幽默,才華,溫暖,體貼,一切的好,帶到了我的家。漸漸的,讓我們越來越離不開他。
就在昨天,我知道了最后的晚餐是在12月7 日的晚上,是文瑜自己給自己安排的最后的晚餐,我的心頓時糾痛起來,有一個早就定好的活動,我需要在7 日下午出發,可是7日的晚上,我不能缺席。
我碰到難題了,那一瞬間,我忽然想應該打個電話問問文瑜,然后,猛然驚醒。
一直就是這樣的,有什么大難題小問題,打個電話問問文瑜,已經成為我的習慣。雖然我不一定會聽他的建議,因為他經常會有很餿的主意,但是我習慣了依賴他,依靠他。
可是文瑜生病了。
文瑜早就生病了,十年來,他每周要做三次透析,每次四到五個小時,其中的辛苦難受,只有他自己體會。我能夠做到的,就是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的下午和晚上,再大的事情也不打擾他,并且告訴所有能夠告訴的人,請他們也不要在那個時候打擾他,其他,還能為他做什么呢?有時候他自己反倒堅挺,做完透析還給我打電話,我說,你嗓子啞了,今天不說,休息,明天再說。
現在文瑜又生病了。生了更重的病。他,要走了。
在查出病癥的前一陣,但凡有人到雜志社去辦什么事,他幾乎見人就說,你到《蘇州雜志》來工作吧,你到《蘇州雜志》來工作吧!他這是要干什么?年初的時候他就跟張黎說,想年底出本詩集,如果我不在了,就給你寫個出版遺囑。
文瑜啊文瑜,難道冥冥之中,你已經得到什么暗示,你只是不肯告訴我們,你只是不想讓我們為你難過。
文瑜,你一定看得見,朋友圈里,都在讀你的詩,都在說你這個人。是的,你很牛,你太牛了,正如你自己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跟我們開玩笑說,你和江姐差不多,明知來日無多,還在一針一線繡紅旗。文瑜啊,聽你在電話里這么說,你讓我怎么回答你啊。我只能強行地笑出一聲,說,你就好好繡紅旗吧。文瑜開心地笑了。
文瑜,我真的沒有想到,你有如此之大的勇氣,死亡也不能奪走你的高貴,你就這樣昂首挺胸地走了過去,你也害怕,你也恐懼,但是你的高貴,戰勝了它們。
文瑜,真的真的沒有想到,我一生的摯友,調皮的文瑜,竟然如此英勇。
但是,但是,但是,如果能夠重新來過,我寧可你慫一點,不要你那么高貴,不要你那么高傲,不要你做英雄,只要你活著。
但是你不會聽我的,你就是你,你還是你,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關心著他人。
11 月29 日上午,文瑜還主動為了我的家事,給我發了截屏,說,你自聯吧(你自己聯系吧),我不行了。他真的不行了,多兩個字也寫不動了。
同一天,他給小天發信,希望小天“和自己及親人互相溫暖”,小天說,他在離開世界之前,卻是牽掛我。
治療用藥,快速地損害了他的身體,用藥的第二個月,他已經難以承受藥的打擊了,只要哪天一停藥,他的精神頭又起來了,他又要繡紅旗了。他打電話給我說,醫生吩咐每天都要吃,但是他想吃吃停停了。我怎么辦啊,我怎么回答啊,我既怕他離去,又怕他痛苦,我跟他討價還價,我說,你根據自己的情況,要不,吃五天,停兩天?他說不,我吃四天停三天。

陶文瑜畫桌
11 月28 日,他給我打電話,說,這一次真的不行了。他已經無力行走,無力起床,甚至一點也不能動彈了,病魔殘忍兇惡地將他“抽絲剝繭”。再次入院后,仍然每隔一天要送到透析室做透析,需要幾個人把他抬上擔架床,到了透析室,如果各項檢查達不到指標,不能做透析,再推回來。
如此折磨。他迅速果斷,決定放棄治療。11 月29 日那個周五,他不再做透析。
他是很清楚的,以他的身體狀況,只要停一次透析,就會出現什么情況,但是他已經決定坦然地接受。
可是文瑜,我們不知道呀,我甚至不太知道他的“放棄治療”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以為是停止使用靶向藥。即便如此,我們都覺得,還會有一段時間的。
可是已經沒有時間了。
11 月29 日下午我去了并不算太遙遠卻感覺無比遙遠的駐馬店,30 日晚上急趕回來,沒有音訊。我有不好的預感,因為時間太晚了,我沒敢給周曼珍發信。
第二天起來我趕緊問曼珍情況怎樣,曼珍說,今天早上有點迷糊,現在好一些了。

早年參加文學活動
12 月2 日上午,我正準備去醫院,手機來電了,一看是陶理的電話,我心里“格登”了一下,趕緊說,陶理啊?那邊卻是文瑜的聲音,他用兒子陶理的手機,給我打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個電話,他用非常微弱的聲音說,你今天空嗎?(我真不是人啊,我有那么忙嗎?)我說,我這幾天都在,過一會我就來看你。他說他不行了,又說了說出書的事情。然后他讓我看微信,用他自己的手機,給我發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條微信,那是一個截屏,是11 月30日晚,他發給曹后靈市長的:“我已放棄治療,就這兩天了,麻煩你關照院方認真做好我的臨終關懷。謝謝。朋友一場,就此別過。”
我看了這個信,立刻回電過去,他搶先就說,你看到了?我說看到了,我馬上過來看你——電話忽然就中斷了,我等了半天,一直沒有聲音。我的撕心裂肺的文瑜啊!
過了幾分鐘,陶理打電話給我,說爸爸電話打到一半,昏迷過去了。
我立刻趕到醫院,在病房門口看到里邊有很多人,我稍稍站立了一會沒有進去,文瑜的妹妹看到我了,趕緊出來喊我,說,現在還有點清醒,你快進來看看。
我進去,拉住他的手,他有感覺。人已經不行了,還能說話,他說,要隨時喊醫生,不要讓我痛苦。我告訴他,你安心,醫生都在這里。
這是他說的最后的一句話。
片刻之間他又昏迷了,這是12 月2 日上午,他第三次昏迷。他是在昏迷中醒來的那一點點時間里,給我打了最后的電話。
我哭了。我哭得無法停止。
一直到現在,仍然無法停止。
他沒有再醒過來。
我守到傍晚,回家后一夜心神不寧。12月3 日,起來先問陶理,情況怎樣?陶理說情況一樣,昏迷。上午我急著趕一篇稿子(該死的稿子),匆匆吃過飯急急忙忙趕到醫院。
他的呼吸已經很微弱,生命即將耗盡,我默默地坐在他的床前。過了一會,忽然聽到他重重地呼吸了一聲,我頓時心生奇想,會不會有奇跡發生了?這么想著,我看了一眼監護器,就是那一瞬間,心跳停止了。
時間永遠停留在2019 年12 月3 日下午3 時53 分。
荊歌說:失去了才知道他的重要,我們永遠沒有他了。沒有人再會對我們這么好。
小海說:今夜我仿佛成了孤兒。
費振鐘說,文瑜去世是今年最大痛事。
北北說,這個人死出骨氣和詩意了。
有多少人在為文瑜流淚,無眠,嘆息,包括無數并不認得他的人:
小菲說:我好喜歡他,字里行間都是親切,體貼,安慰,溫馨。
杜懷超說:雖無緣謀面,可哀慟,沿著這些柔軟而透明的文字之岸,潮來。
可是我只有一個字:哭。
哭文瑜。
哭永遠沒有了的文瑜,因為下輩子是不會再見的。
我一直在想,文瑜你回來吧,你回來,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你和死神搏斗的經歷。
文瑜不會回來了。
大家說他的詩好,他卻一直想出一本小說集,11 月26 日,他去世前一周,把十六篇小說發給了我,說,“沒寫好,不入法眼的,你全權做主,不行就不出了。”
文瑜,一定會出的,只要是你的心愿,我一定做到的。
“面對任何人,他是一律如常地插科打諢,消解富貴者的那份妄自尊大、道貌岸然,消解貧困者的那份窘迫局促、手足無措。”(小海語)
那些不良的世風,在文瑜的至情至性面前,是那么的猥瑣不堪。
“這詩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你沒有活到他的純凈和透徹,你沒有活到他的這份赤子深情,你沒有活出他對生死大事的舉重若輕,哪里可以寫出這等好詩來呢?!”(小海語)

陶文瑜生前辦公桌
那些裝模作樣的文字,在文瑜的詩文面前,又是多么的無趣無聊。
文瑜,雖然你不會回來了,但是你始終沒有離開,你一直就在,你永遠都在。在我們這里。
文瑜活著的時候,我沒有喊過他文瑜,要么是喊陶文瑜,要么是跟著別人喊陶老師、陶主編,要么是跟著我兒子喊他師傅。
我希望,他能看見我寫的字,如果寫得不如他意,他還會跟我生氣,不理我。他如此的熱愛生活,熱愛生命,他是舍不得離去的,但是他無懼無畏地面對了。
文瑜平日私信聊天,或者發朋友圈,不怎么多用表情,幾乎從來不用擁抱的表情,但是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用了很多擁抱的表情。他想抱住世界,抱住大家,直到他抱不住了。
文瑜,我還想看到你貌似驕傲其實厚道的笑臉,我還想聽到你得意洋洋卻又有點害羞地對我說,我阿牛?
對不起,我不能再寫下去了。我很凌亂,我語無倫次,我很痛,我撐不住了。
文瑜,我以后還會寫,再寫,再寫,一直寫。因為我還有太多太多的話要和你說,我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想跟你聊,我還有太多太多的心思要向你傾訴。
附:陶文瑜詩一首:
我要將身邊的你
打發到很遠的地方
并且
忘了你的地址
我要將所有的積蓄
換成一張車票
不久以后
所有城市
每一個路口
都有我張貼的
尋人啟事
我要用余下的
全部生命
來尋找你
這時候思念
是我的唯一行李
我要在風燭殘年
喊著你的名字
倒在異鄉的小旅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