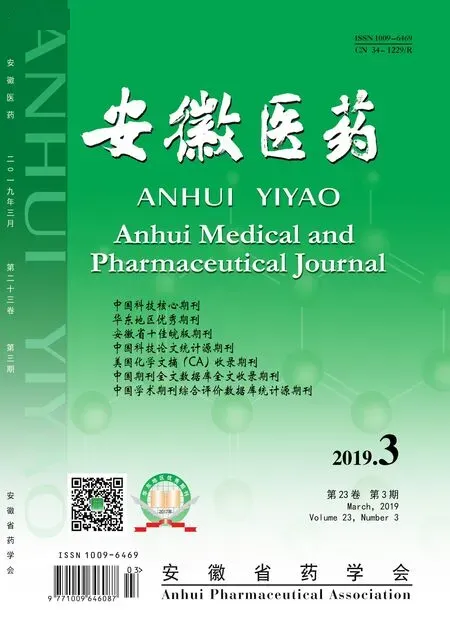外周血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血小板-淋巴細胞比值在婦科腫瘤中的研究進展
胡東東,林海月,馮文
腫瘤微環境是由腫瘤細胞、炎癥細胞、細胞外基質等共同構成的腫瘤發生發展的局部環境,可導致腫瘤細胞增殖和侵襲轉移。其中炎癥細胞包括巨噬細胞、自然殺傷細胞、淋巴細胞、中性粒細胞等。炎癥反應是機體為維持內環境穩態進行的復雜免疫反應,有大量炎性因子參與。以前研究認為炎癥與腫瘤發生發展并無關系,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眾多研究證實,在腫瘤的進展中,炎癥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慢性炎癥對腫瘤的影響最為突出,這可能是由于炎癥產生的炎性因子持續作用導致細胞增殖、炎性細胞募集活化,產生大量活性氧和蛋白酶,致使正常細胞DNA氧化損傷,最終導致腫瘤產生,因此炎性因子可作為腫瘤病情評估的標志物,所以有學者提議將炎癥作為新的腫瘤特征。中性粒細胞可改變腫瘤周圍環境,使正常細胞向腫瘤細胞轉化,并且可誘使腫瘤細胞增殖、轉移,而淋巴細胞是機體重要的免疫細胞,對腫瘤起到監視、殺滅作用,淋巴細胞減少,可增大腫瘤浸潤轉移的發生[1]。血小板也存在于腫瘤微環境中,對腫瘤細胞的增殖有促進作用,也可反映機體炎癥反應程度[2]。臨床研究揭示,NLR、PLR不僅可作為反映腫瘤病人免疫系統狀態的指標,并且也是多種腫瘤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3]。而NLR、PLR可以反映腫瘤病人病情及預后與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血小板在腫瘤發生進展中的作用密切相關。本文現就NLR 、PLR在惡性腫瘤中的作用和近年來在婦科惡性腫瘤方面的研究最新進展進行綜述。
1 NLR、PLR在腫瘤中的作用
1.1中性粒細胞與腫瘤中性粒細胞是機體白細胞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一種免疫細胞,自骨髓入血后可隨血流移動至病變部位。研究發現在腫瘤增殖活躍的部位聚集了大量中性粒細胞,中性粒細胞因其免疫特性,在腫瘤微環境中會發生表型改變和功能重塑,之后釋放的細胞毒性介質、蛋白酶及其他因子可導致機體正常細胞向腫瘤細胞轉化[4]。中性粒細胞還可下調腫瘤細胞中E鈣黏蛋白(e-cadherin,E-cad)的表達,促進癌細胞的遷移和侵襲[5]。研究還發現中性粒細胞通過釋放活化型基質金屬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eptidase 9 ,MMP-9)或者促使腫瘤細胞表達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促進新生血管生成,在腫瘤模型實驗中利用藥物抑制中性粒細胞向腫瘤組織部位運動,可顯著抑制腫瘤新生血管的形成,明顯降低腫瘤細胞的血管外滲活動[6]。在腫瘤微環境中重塑后的中性粒細胞還具有類似髓源抑制細胞的功能,可產生精氨酸酶1(arginase 1),減少細胞外精氨酸合成,抑制T淋巴細胞的增殖,另外在腫瘤無限制增殖造成的局部低氧環境可以導致免疫抑制性中性粒細胞增多,可抑制自然殺傷細胞的功能導致腫瘤發生轉移[7]。
1.2淋巴細胞與腫瘤在對腫瘤的細胞免疫中淋巴細胞起著重要作用。淋巴細胞對腫瘤細胞的免疫反應根據主要功能細胞不同分為兩個類別,分別為T淋巴細胞介導的細胞免疫和B淋巴細胞介導的體液免疫。其中以T淋巴細胞為主,T淋巴細胞可直接殺滅腫瘤細胞,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與擴散。但是隨著腫瘤進程的發展,一些腫瘤因子可抑制T淋巴細胞的生成,影響T淋巴細胞殺傷能力,最終導致細胞免疫水平降低。T淋巴細胞具有細胞免疫和免疫調節雙重功能,又可分為CD4+和CD8+兩個主要亞群。CD4+細胞又被稱為輔助性T細胞,可以調節其他T淋巴細胞的免疫反應,并且通過輔助B細胞分泌抗體參與體液免疫;CD8+細胞是一種細胞毒反應細胞,可以直接殺傷細胞,因此在T淋巴細胞反應模式中,CD4+和CD8+淋巴細胞可反映機體免疫能力的高低強弱。腫瘤病人外周血淋巴細胞數量減少和功能缺陷可導致病人免疫功能下降。檢測外周血淋巴細胞水平,可直接反映病人體內的免疫水平及腫瘤發生發展情況,因此淋巴細胞已經被認為是一種有效診斷篩查腫瘤并預測腫瘤預后轉歸的指標。
1.3血小板與腫瘤在1872年就有報道血小板增多與惡性腫瘤存在關聯。Levin 研究發現約38%無法手術治療的晚期惡性腫瘤病人存在血小板增多,并且血小板增多可增加血栓發生風險[8]。Gasic 在小鼠腫瘤轉移模型的研究中發現,使用抗血小板抗體降低血小板計數可減少腫瘤轉移的發生,在輸注含血小板成分的血漿后這種現象發生逆轉[9]。后續研究表明血小板功能異常也能降低轉移發生,在灰色血小板綜合征中,由于缺乏ɑ顆粒,轉移率降低了80%。由于腫瘤部位持續炎癥和組織重塑可釋放VEGF和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diphosphate,ADP)等刺激巨核細胞分化,腫瘤與正常組織相互作用也可產生大量炎癥因子如白介素-6(interleukin 6,IL-6),激發巨核細胞分裂形成血小板,導致血小板增多,并可誘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小板中含有大量生物活性生長因子和細胞因子,在正常傷口愈合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在腫瘤中卻是有害的,因為血小板釋放的炎癥介質如VEGF、IL、MMP以及抗凋亡因子等,可導致腫瘤增殖轉移,并且誘發更多的炎癥細胞參與這一過程,釋放過量的炎癥介質造成正常細胞損傷、基因突變等,促進正常細胞惡性轉化、腫瘤細胞增殖、轉移等[10]。
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和血小板在腫瘤中會隨著病程的進展而變化,所以研究NLR、PLR不僅可以反映機體炎癥反應程度,也可以反映機體抗腫瘤作用強弱,NLR、PLR比值增大說明機體炎癥反應增加,對腫瘤免疫能力減弱,易發生腫瘤浸潤、轉移,最終導致較差的病人預后。
2 NLR、PLR在婦科腫瘤中的研究進展
2.1外陰癌全球每年外陰癌發病人數約10萬人,其中90%的病人病理類型為外陰鱗癌。早期外陰癌手術治療后預后較好,5年生存率可達90%。然而仍有一部分病人術后會發生復發,現階段除了淋巴結轉移可作為病人預后的預測因素,尚無其他標志物用于外陰癌的臨床管理。熊巍在對外陰鱗癌NLR表達的診斷價值研究發現NLR可以作為外陰鱗癌與外陰上皮內瘤變的術前診斷生物學指標,而最佳界限值為2.01[11]。在另一項對外陰鱗癌的回顧性研究結果顯示淋巴結陽性的病人術前外周血NLR和PLR明顯高于淋巴結陰性者,這提示術前外周血NLR和PLR與淋巴結受累情況可能存在關系[12]。
2.2宮頸癌宮頸癌是常見的婦科惡性腫瘤,每年約有50萬新發病例和27.5萬死亡病例,其中約1/3的宮頸癌病人死于腫瘤復發。研究表明NLR、PLR和腫瘤病理特征相關,但由于研究設計、樣本大小和病人的差異,導致爭議的存在。楊軍文在對76例宮頸癌的研究中發現NLR與宮頸浸潤深度、淋巴結情況、病理級別及FIGO期別相關,單因素分析顯示NLR是影響預后因素,與腫瘤無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DFS)有關[13]。在一項NLR與宮頸癌臨床病理特征及預后關系的meta分析中發現NLR可預測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和DFS,NLR與腫瘤直徑、臨床期別、淋巴結轉移顯著相關,但考慮 meta 分析的局限性,需要進一步的大樣本研究,以更好地了解 NLR在宮頸癌的預后價值。在NLR與宮頸癌放化療效果的研究方面,周文毓對宮頸癌新輔助化療前NLR進行研究發現NLR可預測新輔助化療療效,預測療效最佳值為2.0,在病人預后評估中高NLR組病人的OS和DFS均顯著低于低NLR組[14]。在NLR與宮頸癌放療及同步放化療療效及預后關系研究中發現NLR與放療療效相關,高NLR是影響OS的獨立危險因素,高NLR組1年、3年OS低于低NLR組[15]。Wang等[16]對515例宮頸癌病人進行研究發現,隨著腫瘤進展,NLR和PLR持續性升高,NLR升高與淋巴結轉移和宮頸間質浸潤深度相關,而PLR僅與淋巴結轉移相關。在早期宮頸癌的預后研究提示PLR與腫瘤預后并無相關性[17]。
2.3子宮內膜癌子宮內膜癌在我國婦科惡性腫瘤中其發病率僅次于宮頸癌。根據子宮內膜癌分子特征及發病機制不同分為雌激素依賴型(I型)和非雌激素依賴型(II型),其中以I型最為常見。病人在腫瘤早期因陰道流血等典型癥狀就診而被確診,大部分I型病人有較好的預后,II 型的病人的預后較差。然而大概20%的I型病人也具有不良預后,尋找客觀準確的生物標志物用以危險分層,指導治療管理是必要的。在一項對161例子宮異常出血或子宮內膜增厚的病人NLR和PLR的研究發現:子宮內膜癌病人NLR明顯高于子宮內膜增生的病人和健康人群,PLR在三組中無明顯差異[18]。在另一項子宮內膜癌與NLR的研究發現,子宮內膜癌術前高NLR組和低 NLR組病人在腫瘤分期、病理分級、淋巴結轉移、肌層浸潤深度及腫瘤大小方面有明顯差異,高NLR是病人術后復發及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19],故子宮內膜癌病人術前NLR值可能對子宮內膜癌預后預測有一定價值。在對 733例子宮內膜癌病人臨床病理及5年隨訪資料進行研究發現,術前NLR、PLR水平在子宮內膜癌病人中均具有獨立的預后價值,并且NLR和PLR水平與病理級別存在密切關系[20]。此外有研究表明術前NLR和PLR可以確定子宮內膜癌病人宮頸間質受累的危險性,關注術前NLR、PLR水平可以幫助挑選那些應該特別關注是否累及宮頸基質的病人。
2.4子宮肉瘤子宮肉瘤是臨床上較罕見的婦科惡性腫瘤,常被誤診為子宮肌瘤或子宮腺肌癥等良性疾病,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靈敏度和特異度較佳的檢測指標,雖然有研究表明血清CA125可作為子宮肉瘤的術前診斷指標,但仍有爭議。在一項比較NLR和CA125對子宮肉瘤的診斷價值研究中,采用ROC曲線得出NLR、CA125最佳界值為2.12和27.5,研究結果顯示在子宮肉瘤術前診斷中,NLR診斷水平明顯高于CA125[21]。在一項子宮肉瘤術前NLR診斷效能的研究顯示NLR在子宮肉瘤術前診斷敏感度低于白細胞計數和中性粒細胞計數,但是其特異性在三者中最高,因此術前NLR檢測可以作為子宮肉瘤術前輔助檢測指標[22]。而PLR與子宮肉瘤的相關性研究目前國內外未見有報道。
2.5卵巢癌卵巢癌是婦科惡性腫瘤死亡率最高的腫瘤[23],每年死于卵巢癌的病人約有14萬例。卵巢癌病人通常存在全身炎癥反應,中性粒細胞、血小板計數較正常人偏高。王鑫、張虹[24]研究發現NLR對卵巢癌診斷的靈敏度和特異度較高,并且NLR和CA-125聯合檢測可明顯提高上皮源性卵巢癌早期診斷的靈敏度和特異度。近年來研究提示NLR具有鑒別CAl25陰性的卵巢癌的能力,在預測卵巢癌病人PFS和OS方面優于CAl25[25]。Feng等[26]對875例接受手術治療但沒有進行化療的晚期漿液性卵巢癌病人的研究發現NLR對PFS有較高的預測價值,但對OS的預測價值不大。而另外一項對165例初治卵巢癌病人的的研究發現術前NLR水平與腫瘤期別、惡性腹水、CAl25水平、減瘤手術效果及血紅蛋白水平等有關,在預后方面,高NLR組的PFS和OS明顯小于低NLR組,多因素分析提示NLR是卵巢癌病人PFS、0S的獨立預后因素[27]。在卵巢癌化療方面高NLR組病人對劑量-密集輔助化療藥物敏感性較低,而低NLR組病人則較敏感,提示NLR對選擇化療藥物有一定參考價值[28]。
在卵巢癌病人中發生血小板增多的比例高達38%,血小板增多與期別、淋巴結轉移以及是否進行根治性手術相關,血小板增多的卵巢癌病人PFS和OS明顯縮短,所以血小板增多是上皮性卵巢癌病人術后復發或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29]。卵巢癌病人預后與期別和能否進行最佳的減瘤手術密切相關,病人免疫功能也可以影響卵巢癌病人的預后,腫瘤浸潤部位的T淋巴細胞和B淋巴細胞增高可延長卵巢癌病人PFS,卵巢癌病人常表現為淋巴細胞計數降低,進而影響治療效果和預后[30]。所以PLR逐漸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PLR不僅與癌癥病人血栓形成和全身炎癥狀態密切相關,術前PLR升高的卵巢癌病人與PLR正常者相比預后更差,PLR高于300的病人中位生存期為14.5月,明顯低于PLR小于300的37.4月,Cox’s多因素分析顯示PLR與卵巢癌期別及術后殘留病灶都可作為評價卵巢癌病人的預后指標,所以PLR升高的卵巢癌病人病情較重,預后較差[31]。另有研究報道卵巢癌病人中PLR比NLR更具PFS和OS預測價值[24]。
3 總結
綜上所述,NLR、PLR作為全身炎癥反應的重要生物學標志物,其值升高在包括婦科腫瘤在內的多種腫瘤發生發展及預后評估中存在重要價值,但目前有關研究是一些小樣本的回顧性研究,并且研究結果存在沖突之處,另外NLR和PLR的最佳界值在同一腫瘤的不同報道中仍有所不同,因此目前仍需要依靠系統性的、多中心的前瞻性大規模研究對進一步了解NLR和PLR在腫瘤中的應用價值意義,從而為臨床上腫瘤的診斷、治療和預后提供一種經濟、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