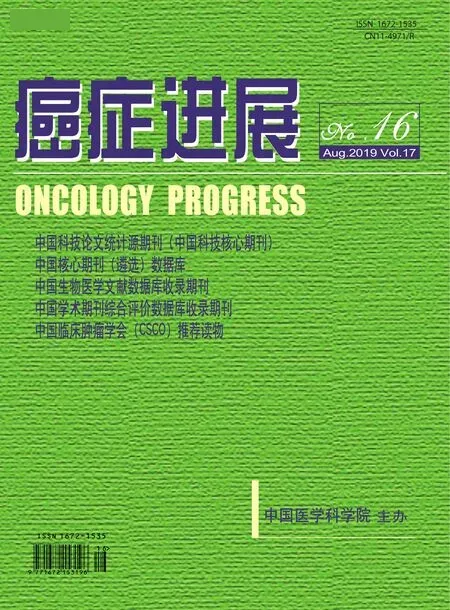血管免疫母細胞性T細胞淋巴瘤的臨床特點及治療進展△
錢景榮,李文輝
哈爾濱醫(y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檢驗科,哈爾濱150081
血管免疫母細胞性T細胞淋巴瘤(angioimmunoblastic T-cell lymphoma,AITL)是一種罕見的外周T細胞淋巴瘤(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PTCL)亞型,僅占非霍奇金淋巴瘤的1%~2%,歐洲的發(fā)病率(28.7%)高于亞洲(17.9%)[1-2]。目前,尚不清楚AITL是否存在種族傾向,但AITL好發(fā)于老年患者,且沒有性別差異,其特征性表現為淋巴結結構破壞伴高內皮血管及濾泡樹突狀細胞增生,臨床侵襲性較強,診斷時往往已處于疾病進展期,常規(guī)化療療效不佳,預后極差[1],尚無標準的治療方案,也沒有共識的生物學標志物對AITL患者的療效和預后進行定期評估。隨著對AITL細胞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不斷深入研究發(fā)現,AITL可特異性表達濾泡輔助性T細胞(follicular T helper cell,TFH)表面的免疫表型,發(fā)生ras同系物家族成員A(ras homolog family member A,RHOA)G17V突變、表觀遺傳調節(jié)因子基因突變和T細胞受體(T-cell receptor,TCR)信號通路相關基因突變,采用造血干細胞移植和新型免疫分子藥物治療AITL,臨床反應率較好,可明顯改善患者預后。本文就AITL的病因、細胞遺傳學、組織病理學、免疫表型、臨床特征、治療策略及預后因子等方面進行綜述。
1 AITL病因
1.1 惡性TFH細胞起源
AITL起源于TFH,基因表達譜分析證實,TFH細胞與AITL細胞具有相似性[3],TFH細胞的特征保留在AITL腫瘤細胞中,從而解釋了AITL的主要病理學和生物學特征,包括B細胞增殖、濾泡樹突狀細胞網狀增生及免疫功能異常,其中TFH細胞可表達CXC趨化因子配體(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CXCL)發(fā)揮B細胞募集、激活和分化等作用。
1.2 腫瘤微環(huán)境
在AITL中,腫瘤細胞及其周圍的免疫細胞等各種細胞,附近區(qū)域內的細胞間質、微血管及浸潤其中的生物分子等可共同構成復雜的腫瘤微環(huán)境。TFH細胞釋放的不同細胞因子可參與多種生物學過程,如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家族成員IL-8可參與血管生成過程,IL-6、IL-18可促進炎癥的發(fā)生,IL-10可參與免疫抑制過程,IL-21、IL-10、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還可對其他T細胞亞群進行調控。此外,AITL患者的腫瘤微環(huán)境中還存在大量CXCL(CXCL2、CXCL9、CXCL13、CXCL14)和CXC趨化因子受體(C-X-C motif chemokine receptor,CXCR),如CXCR4、CXCR5、CXCR6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由CXCL13刺激B細胞釋放的淋巴毒素B可誘導濾泡樹突狀細胞的增殖。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及其受體在AITL患者腫瘤細胞、上皮細胞和樹突狀細胞中表達上調,從而促進血管生成及腫瘤進展。
1.3 感染
AITL發(fā)生與 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人類皰疹病毒(human herpesvirus,HH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細菌和真菌感染有關,且這些病毒感染可能與免疫失調有關,表明AITL患者可能存在免疫功能缺陷和細胞毒T細胞活性降低等。此外,EBV和HHV-6可通過調控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膜受體在AITL腫瘤微環(huán)境中發(fā)揮作用,促進AITL的進展,研究顯示,EBV水平升高與AITL進展和B細胞克隆密切相關,值得注意的是,EBV陽性患者有發(fā)生B細胞淋巴瘤的可能,特別是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4]。
2 細胞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
2.1 細胞遺傳學
傳統的細胞遺傳學研究表明,約75%的AITL患者伴有染色體數目和結構異常,最常見的是3q、5q、21q和X染色體三體型,以及6q常染色體缺失,基因組雜交研究發(fā)現,高達90%的AITL患者可出現染色體高頻突變,包括22q、19q和11p11~q14染色體的增加及13q缺失[5]。約80%的AITL患者存在CD4+T細胞克隆,41%的AITL患者存在B細胞克隆[6]。此外,研究顯示,約80%的AITL患者還存在TCR基因重排,大多數為TCRα/TCRβ鏈基因重排,少數為TCRγ/TCRδ鏈基因重排,10%~20%的AITL患者存在免疫球蛋白重鏈(immunoglobulin heavy locus,IGH)基因重排[7]。
2.2 突變
近年來,基因組學研究分析了誘導AITL潛在發(fā)病機制的遺傳基因譜發(fā)現,RHOAG17V突變和表觀遺傳調控因子基因[如TET甲基胞嘧啶雙加氧酶2(tet methylcytosine dioxygenase 2,TET2)、DNA甲基轉移酶3α(DNA methyltransferase 3α,DNMT3A)和異檸檬酸脫氫酶2(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2,IDH2)]突變在AITL發(fā)病機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此外,AITL患者還存在TCR等相關信號通路的基因突變,也為AITL的靶向治療提供新依據。
2.2.1RHOA突變 約70%的AITL患者存在RHOAG17V雜合錯義突變,RHOAG17V突變發(fā)生于CD4+T細胞中,可誘導TFH細胞分化,促進其增殖相關的誘導性共刺激分子(inducible costimulator,ICOS)的表達上調、磷酸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ide 3-kinase,PI3K)和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相關信號通路活化,表明RHOAG17V突變與TET2功能缺失突變共同促進了AITL發(fā)展[8]。
2.2.2 表觀遺傳調控因子突變AITL患者存在表觀遺傳調控因子突變,其中47%~83%為TET2突變,20%~30%為DNMT3A突變,20%~45%為IDH2突變,其中TET2突變在具有TFH表型T細胞淋巴瘤(AITL、濾泡性T細胞淋巴瘤和具有TFH表型的結節(jié)性外周T細胞淋巴瘤)中發(fā)生率更高[9]。研究發(fā)現,RHOA突變、TET2突變和IDH2突變具有較強的突變相關性,如在RHOA突變患者中同時也存在TET2突變,這些基因組合突變對AITL的發(fā)生發(fā)展可發(fā)揮重要協同作用[9]。
2.2.3 TCR信號通路相關基因突變 研究發(fā)現,約50%的AITL患者的TCR相關基因中存在互斥突變,其中14%為磷酯酶Cγ1(phospholipase C gamma 1,PLCG1)突變,9%~11%為CD28突變,3%~4%為FYN突變,5%為VAV1突變,7%為磷脂酰肌醇-3-激酶催化亞單位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PIK3CA)突變,6%為β-catenin突變,6%為通用轉錄因子Ⅱi(general transcription factorⅡi,GTF2I)突變,3%為胱天蛋白酶募集域11(caspase recruitment domain family member 11,CARD11)突變,雖然尚未發(fā)現這些突變與AITL患者的臨床特征或生存期有關,但發(fā)現TCR相關基因突變與早期疾病進展有關[10]。進一步研究發(fā)現,TCR信號通路過度激活可能促進腫瘤進展,而這一過程可能是由于基因融合實現,如CTLA4-CD28融合基因由CTLA4的細胞外結構域和CD28的細胞質區(qū)融合形成,該基因可將抑制信號轉化為刺激信號從而促進T細胞活化,超過50%的AITL患者中存在基因融合變異[11]。此外,PLCG1突變、PI3K突變、PDPK1突變、GTF2I錯義突變及MAPK信號通路的激活對AITL的發(fā)生發(fā)展也具有重要影響[12]。
3 組織病理學及免疫表型
3.1 組織病理學
在組織病理學方面,AITL患者的淋巴結結構被完全破壞,濾泡或生發(fā)中心消失,淋巴細胞異常增生及多形性細胞浸潤,伴有獨特的高內皮血管增生和濾泡樹突狀細胞不規(guī)則增生。此外,AITL患者的腫瘤T細胞占比較少,與霍奇金淋巴瘤的里-施細胞(Reed-Sternberg cell,R-S細胞)類似,僅占10%,多數是腫瘤細胞與反應細胞如小淋巴細胞、組織細胞、上皮樣細胞、免疫母細胞、嗜酸性粒細胞和(或)漿細胞混合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多數AITL患者的B細胞可通過原位雜交技術檢測出具有活動性EBV感染,但惡性TFH細胞則不能檢測出EBV感染[13]。
3.2 免疫表型
AITL可特征性表達TFH細胞表面的多種免疫表型,如CD3、CD4、CD10、CXCL13、CXCR5、CD154、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CD1,也稱PD-1)、ICOS、信號淋巴細胞活化分子(signaling lymphocytic activation molecule,SLAM)相關蛋白(SLAM-associated protein,SAP)、B細胞淋巴瘤/白血病-6(B cell lymphoma/leukemia-6,Bcl-6)或c-Maf等,通常伴有CD5和(或)CD7的異常缺失,部分患者存在CD30或CD20異常共表達。CD3、CD4和CD10是TFH細胞的基本免疫表型,與CD10相比,細胞質CXCL13的表達情況對診斷AITL更具有特異性;CD21和CD23的表達可特異性顯示出濾泡樹突狀細胞的不規(guī)則增生;約30%的AITL患者可表達CD30,且與治療相關;此外,流式細胞免疫表型分析儀檢測PD-1(CD279)和CD10的異常T細胞群的共同表達可輔助AITL的診斷,外周血中檢測到細胞表面sCD3-/CD4+T細胞群和CD10的表達診斷AITL的陽性預測值較高(94%)[14]。由此可見,TFH細胞表面的免疫表型有助于區(qū)分AITL良性淋巴組織增生性疾病與具有TFH細胞來源的其他PTCL亞型,可明顯提高AITL的診斷率[15]。
4 臨床特征
AITL好發(fā)于老年男性,發(fā)病年齡多為65歲(中位數),確診時通常已處于臨床晚期,約70%的患者可出現B癥狀,1/3的患者伴有肝脾腫大,多達1/5的患者可累及2個以上的結外部位,皮膚病變是最常見的結外表現,其次還包括黃斑、丘疹、斑塊或結節(jié)病變等,隨著時間推移,皮膚浸潤程度逐漸增加且逐漸出現淋巴細胞的異型性[16]。AITL早期,近70%的患者可出現淋巴瘤相關癥狀,如水腫、胸膜或腹膜積液、關節(jié)疼痛或冷凝集素綜合征等;超過65%的患者在診斷時伴有貧血,10%~40%的患者表現出Coombs試驗陽性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60%的患者合并骨髓浸潤;此外,部分AITL患者還伴有特殊的實驗室指標異常,如30%~50%的患者可出現高丙種球蛋白血癥(>12 g/dl),偶爾合并單克隆血清免疫球蛋白增多、血清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水平升高及自身免疫標志物如類風濕因子、循環(huán)免疫復合物和抗平滑肌抗體陽性[17]。
5 預后因子
目前,探討AITL的相關預后因子仍是臨床研究的熱點,AITL臨床侵襲性較強,盡管存在個體差異,但AITL患者的總體預后較差,5年生存率僅30%[1]。臨床采用國際預后指數(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評估患者預后的價值仍存在爭議。AITL預后指數(prognostic index for AITL,PIAI)對AITL患者預后評估更有意義,包括年齡>60歲、美國東部腫瘤協作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體力狀況(performance status,PS)評分>2分、累及結外部位>2個、存在B癥狀、血小板計數<150×109/L、貧血、縱隔淋巴結腫大、累及骨髓、血清β2微球蛋白(β2-microglobulin,β2-MG)>3 mg/L、血清LDH水平>200 U/L、免疫球蛋白 A(immunoglobulin A,IgA)水平>4 g/L、PD-1高表達、磷酸化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1(phosphorylated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1,p-MAPK1)高表達、沉默信息調節(jié)因子1(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SRIT1)高表達可作為評價AITL患者預后不良的因素;此外,循環(huán)血EBV DNA表達水平也是AITL的預后評估重要因子[18],基于上述預后因子構建的預后模型對AITL患者的預后進行評估似乎更有意義。
6 治療策略
6.1 一線治療
6.1.1 常規(guī)療法 目前,環(huán)磷酰胺+多柔比星+長春新堿+潑尼松(CHOP)方案仍是AITL的主要一線治療方案,盡管AITL患者對CHOP治療方案的臨床反應率較高,但由于復發(fā)率高,遠期療效較差。Vose等[19]的研究中,85%的AITL患者接受CHOP方案治療,其中18.5%的患者5年無失敗生存率(failure-free survival,FFS)僅為18%。因此,研究者不斷嘗試改善AITL的一線治療方案,包括在CHOP方案中添加活性劑、基于CHOP誘導方案與自體外周血干細胞移植(autologous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SCT)相結合。年輕的AITL患者通常采用CHOP方案聯合依托泊苷治療,療效較好,一項德國非霍奇金淋巴瘤研究(DSHNHL試驗)結果顯示,與CHOP單獨治療相比,年齡<60歲且LDH水平正常的AITL患者接受CHOP方案聯合依托泊苷治療,3年無事件生存率(event-free survival,EFS)明顯提高(70%vs51%),盡管未觀察到總體生存率的差異[20]。GOELAMS試驗納入了88例PTCL(其中17%為AITL)患者,比較CHOP方案與依托泊苷+異環(huán)磷酰胺+順鉑+多柔比星+博來霉素+長春堿/達卡巴嗪(VIP-rABVD)方案的臨床療效,結果顯示,VIP-rABVD方案在提高EFS方面不優(yōu)于CHOP方案,這兩種方案2年EFS無明顯差異[21]。
6.1.2 ASCT移植 為進一步改善基于CHOP方案的長期療效,在AITL患者首次達到緩解時對其進行ASCT鞏固治療,可能使患者受益。如一項在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進行的回顧性分析中,112例PTCL患者(其中49例AITL)接受ASCT移植,結果顯示,4年總生存率和無進展生存率分別為68%和43%[22]。由此可見,CHOP方案聯合依托泊苷治療AITL首次緩解時進行ASCT鞏固治療,可能是PTCL包括AITL患者的合理治療方案,但仍缺乏Ⅲ期臨床試驗數據的支持。
6.2 復發(fā)或難治性AITL
復發(fā)或難治性AITL患者的生存期僅有幾個月,對這類患者的治療始終是臨床難點。對于年輕的復發(fā)或難治性AITL患者,同種異體干細胞移植可能達到治愈,Le Gouill等[23]研究納入77例PTCL患者,采用異體干細胞移植治療,其中11例為AITL患者,5年總生存率為80%;當患者計劃異體干細胞移植且已確定捐贈者時,治療方案包括異環(huán)磷酰胺+卡鉑+依托泊苷(ICE方案)或地塞米松+阿糖胞苷+順鉑(DHAP方案),并在患者臨床反應率較高達到緩解時進行異體干細胞移植,但這些治療方案反應持續(xù)時間較短,病情控制時間較短[24]。大部分復發(fā)或難治性AITL患者往往由于年齡或在異體干細胞移植前出現疾病進展或未達到緩解和(或)對化療耐藥,很少適用異體干細胞移植。復發(fā)或難治性AITL患者不適合采用異體干細胞移植時,ICE或DHAP等方案的療效往往較差,迫切需要新型抗腫瘤藥物來實現較為持久的治療效果。目前,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批準用于復發(fā)或難治性PTCL(包括AITL)的3種新型藥物分別為普拉曲沙、羅米地辛和貝利司他,因為盡管總反應率較低(8%、30%和46%),但未出現明顯的不良反應,因此,患者可能通過持續(xù)治療實現持久反應[25-27]。
6.3 新型治療策略
目前,CHOP聯合新藥治療AITL已成為一種新型治療策略,已有臨床試驗對標準CHOP方案聯合利妥昔單抗、貝伐珠單抗、貝利司他或阿侖單抗方案的臨床療效進行評估,但上述聯合治療方案的臨床療效與單獨應用CHOP治療相比并未得到明顯改善。
6.3.1 組蛋白脫乙酰酶抑制劑 鑒于組蛋白脫乙酰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在AITL中具有重要的活性作用,HDAC抑制劑(伏立諾他、羅米地辛、貝利司他和西達本胺)可能會使AITL患者受益。目前,一項正在進行中的Ⅲ期臨床試驗(NCT01796002)對羅米地辛聯合CHOP方案與單獨CHOP方案治療AITL的臨床療效進行比較[28]。MSKCC進行的一項研究采用羅米地辛聯合來那度胺+卡非佐米聯合治療,共納入19例PTCL(包括7例AITL)患者,結果顯示,AITL患者的客觀反應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為87%,明顯高于其他PTCL患者的33%[29],表明HDAC抑制劑對AITL具有潛在的治療效果。
6.3.2 抗CD30抗體 超過1/3的AITL患者可表達CD30,本妥昔單抗可能是AITL的潛在有效藥物。一項Ⅰ期研究采用本妥昔單抗聯合環(huán)磷酰胺+多柔比星+潑尼松(CH-P)方案治療26例CD30陽性表達的PTCL(2例AITL)患者,結果顯示,總ORR為100%,完全緩解(complete response,CR)率為88%[30]。基于此,另一項正在進行的隨機、雙盲Ⅲ期ECHELON-2臨床試驗(NCT01777152)比較本妥昔單抗+CH-P方案與CHOP方案治療AITL的臨床療效,共納入300例AITL患者,該研究可能對AITL的治療產生重大影響。
6.3.3 去甲基化藥物TET2突變在AITL中較常見,推測去甲基化藥物可能在AITL的治療中具有潛在價值。Horwitz等[31]采用5-氮雜胞苷治療PTCL(包括12例AITL)患者,結果顯示,總ORR為53%,AITL患者的ORR為75%,CR率為42%。基于此,另外兩項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NCT03161223和NCT01998035)。
7 小結與展望
AITL不僅生物學特性較為獨特,治療策略也較為特別,單藥口服治療或強化聯合化療治療AITL的療效往往不佳,常伴有原發(fā)性疾病進展或緩解持續(xù)時間較短。目前,尚無標準的治療方案治療AITL,未來將致力于研究標準CHOP或CHOP聯合依托泊苷的新型的誘導方案與生物制劑聯合治療,以提高AITL患者CR率,使得更多患者從異體干細胞移植中獲益并延長生存時間。此外,探討AITL相關的預后因子仍是臨床的熱點領域,風險適應性的治療策略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