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對大灣區(qū)人群健康影響研究進展
杜堯東 段海來 劉暢 羅曉玲
(廣東省氣候中心,廣州 510640)
0 引言
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指出,近百年(1880—2012年)全球平均地表溫度上升了0.85 ℃[1]。氣候變暖不僅嚴重影響全球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活動,而且也帶來一系列重大的公共衛(wèi)生問題[2-3]。氣候變化可以通過各種直接、間接途徑和復雜機制影響人群健康[4-5]。目前,全世界每年有超過10萬例患者因氣候因素死亡,預計到2030年可能達到30萬例[6]。由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人群適應能力以及所處地理位置等的差異,氣候變化對不同地區(qū)人群健康的影響是不同的[7]。粵港澳大灣區(qū)位于歐亞大陸南端,瀕鄰南海,屬亞熱帶氣候,正處于對氣候變化敏感的南海季風區(qū)[8]。在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qū)的氣候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1961—2010年大灣區(qū)年平均氣溫以每10年0.30 ℃的速率顯著上升[9]。氣候變化和城市化引發(fā)的熱島效應、高溫熱浪、灰霾等對人群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影響。2003、2014年在大灣區(qū)爆發(fā)的SARS、登革熱病毒傳染病更是敲響了防控警鐘。因此,開展氣候變化對粵港澳大灣區(qū)人群健康的影響與適應對策研究,對于推進氣候變化對人群健康的脆弱性和風險評估,制定切實可行的區(qū)域公共衛(wèi)生政策,降低氣候變化不利影響,保障人群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1 氣候變化對粵港澳大灣區(qū)人群健康的影響
1.1 溫度變化的影響
1.1.1 日平均溫度
粵港澳大灣區(qū)日平均溫度與死亡之間呈“U”形關系,這說明溫度和死亡的關系是非線性的,在某一溫度閾值時死亡風險最低,日平均溫度高于或低于溫度閾值均導致人群死亡風險增加[10]。但不同城市,死亡風險最低時的溫度閾值,以及溫度每增加或降低1 ℃時,人群的死亡風險大小不一。廣州死亡風險最低的日平均溫度是26.4 ℃,當日平均氣溫高于26.4 ℃時,氣溫每升高1 ℃,廣州全死因人群死亡率累計上升1.9%;當日平均氣溫低于26.4 ℃時,氣溫每下降1 ℃,廣州全死因人群死亡率累計上升1.2%[10]。香港死亡風險最低的日平均溫度是28.2 ℃,當日平均氣溫高于28.2 ℃時,氣溫每升高1 ℃,香港全死因人群死亡率累計上升1.8%[11]。日平均溫度高于或低于溫度閾值時,不同死因的死亡風險也不一樣,因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增加更高[10]。進一步研究表明,廣州心血管事件當天的發(fā)病人數(shù)與當天的氣溫呈顯著的負相關[12]。冷熱效應健康影響時長不同。高于溫度閾值的熱效應對死亡的影響急促短暫,相對危險度一般在當天達到高峰,其影響通常持續(xù)4 d左右消失,而低于溫度閾值的冷效應緩慢持久,在第2~3天達到最大,但其影響持續(xù)的時間可長達2周或以上[10]。因此,高溫預警要早,行動要迅速,而對低溫的防范措施要延續(xù)兩周或更長時間,不應隨著低溫結束立即停止。香港的研究也表明,夏季(5—9月)與中暑有關的死亡只在日最高凈有效溫度(NET,一個結合溫度、相對濕度及風速的熱力指數(shù))超過26時出現(xiàn),當日最高凈有效溫度在26以上時,NET每增加1單位,人群中每日平均中暑死亡率增加1倍;而在冬季(11—3月),與低溫癥有關的死亡只在日最低NET在14或以下時出現(xiàn)。當日最低NET在14以下時,NET每下降1單位,低溫癥引起的死亡率增加30%[13]。
1.1.2 氣溫日較差
氣溫日較差是指同一天內最高氣溫與最低氣溫的差值。極大、極小的日較差對居民死亡率均有重要影響。日較差大,溫度在一天內的變幅大,人體因難以適應驟然增溫、降溫而引起身體不適。日較差小,溫度在一天內穩(wěn)定在人體的一個臨界高溫或低溫值上,人體熱或冷應激不能緩解,進而導致身體不適。廣州地區(qū)研究發(fā)現(xiàn),低日較差和高日較差都與人群死亡率的上升有關聯(lián),但低日較差的急性效應更明顯。在冷季(11月—次年4月),日較差對所有類型死亡的累積效應隨著滯后天數(shù)的增加而增加,高日較差的累積效應強于低日較差。在熱季(5—10月),低日較差的累積效應隨著滯后天數(shù)的增加而增加,高日較差的效應在滯后13 d時(腦血管疾病滯后6 d)時最大,之后開始下降[14]。在香港分析了日溫差與居民心腦血管病死亡率的關系,發(fā)現(xiàn)日溫差的波動在大于65歲年齡組人群中的健康效應最為顯著[15]。
20世紀50年代以來,粵港澳大灣區(qū)氣溫日較差呈顯著的減小趨勢,而且冬季減少幅度更為明顯[16],氣候變化使人們被迫改變習慣適應已經(jīng)發(fā)生和將要發(fā)生變化的氣候。未來大灣區(qū)也將處于人口快速老齡化時期,如廣東2050年老齡化程度將由目前的14.8%上升到23.7%,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是2000年的3.5倍[17],這將導致更大的脆弱人群。
1.2 熱浪的影響
熱浪是指持續(xù)性的高溫酷熱天氣。一般把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 ℃稱為高溫天氣,連續(xù)3 d及以上的高溫天氣過程稱為高溫熱浪。監(jiān)測資料顯示,1961—2010年,粵港澳大灣區(qū)日最高氣溫≥35 ℃的高溫日數(shù)以1.1 d/10 a的速率顯著增加,1998年以來高溫日數(shù)增加的速率更快,其中有6年的高溫日數(shù)大于20 d[9]。熱浪不僅易引起居民中暑死亡,還使人們出現(xiàn)失眠、疲勞、疾病加重等。2004年6月底至7月初的熱浪導致廣州市39人因高溫中暑死亡[18]。2003年夏季熱浪期間,廣州市居民中暑率、失眠率、疲勞癥狀發(fā)生率和疾病加重發(fā)生率分別為21.6%、21.6%、21%和5.0%[19],2006—2011年熱浪期間,廣州住院人數(shù)增加2.6%[20]。其中,老年人、孕婦、兒童及一些慢性病患者,由于熱調節(jié)機能較差,對熱應力更敏感,所以更易受高溫熱浪的影響[21]。廣東省北部內陸地區(qū)人群對高溫熱浪的脆弱性高于南部沿海地區(qū)[22-23]。不同時間的熱浪效應存在差別,以夏季早期的熱浪影響較為明顯,因為人群對熱的適應能力在夏季開始時比較低[24-25]。此外,壽命損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是一種衡量疾病負擔的指標,它綜合考慮死亡發(fā)生時的年齡與期望壽命。研究發(fā)現(xiàn),廣州高溫時,溫度每上升1 ℃由非意外死亡、心血管和呼吸系統(tǒng)疾病造成的YLL分別上升12.71、4.81和2.81 a[26]。
未來熱浪的影響在粵港澳大灣區(qū)可能更為嚴重。未來氣候變化將可能導致更加頻繁、更加強烈、更長持續(xù)時間的熱浪[27],從而增加熱相關疾病和死亡。由于熱島效應,大灣區(qū)城市群的熱浪不僅強烈而且持續(xù)時間長,而持續(xù)時間比瞬時最高溫度對死亡率的影響更大。大灣區(qū)熱浪的增多和增強,將會增加用于空調降溫的電力需求,這又增加了來自電廠的空氣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熱浪還常常伴隨著一段時間的空氣停滯,從而導致空氣污染和健康影響的加重。
1.3 寒潮的影響
寒潮是一種大型天氣過程,對人群健康的影響有直接導致?lián)p傷及疾病發(fā)生,也有間接作用而誘發(fā)疾病及死亡發(fā)生。在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灣區(qū)寒潮次數(shù)雖呈減少趨勢,但年際、年代際變化明顯[28],意外的強寒潮不時出現(xiàn)。20世紀90年代以來,灣區(qū)共發(fā)生了5次強寒潮,占50年代以來強寒潮次數(shù)的62.5%[8]。2008年初,一場罕見的強寒潮襲擊了我國南方地區(qū)[29],對居民健康造成了巨大影響。據(jù)估計,本次寒潮期間中國亞熱帶地區(qū)的死亡率較同期增長43.8%,造成約14.8萬人的超額死亡,而且對華南華中影響最大[30]。與2006、2007和2009年同期相比,2008年寒潮期間,廣州、南雄和臺山三個城市居民非意外死亡和呼吸系統(tǒng)疾病死亡的風險明顯增加,依次為43%、52%、35%,寒潮對人群死亡的影響一直持續(xù)到寒潮結束后4個星期。寒潮對呼吸系統(tǒng)疾病的影響最明顯,75歲以上老人是寒潮的脆弱人群[31]。
預估表明,未來我國南方地區(qū)低溫日數(shù)整體將減少,但在廣東和廣西北部部分地區(qū)連續(xù)低溫日數(shù)有增加現(xiàn)象[32]。連續(xù)低溫日數(shù)的增加可能對當?shù)鼐用竦慕】翟斐芍苯踊蜷g接影響。
1.4 空氣質量下降的影響
1.4.1 灰霾
霾天氣是指能見度小于10.0 km,排除降水、沙塵暴、揚沙、浮塵、煙霧、吹雪、雪暴等天氣現(xiàn)象造成的視程障礙,相對濕度小于80%時,判識為霾,華南地區(qū)將受到人類活動顯著影響的霾稱為灰霾[33]。1961年以來,灣區(qū)年灰霾日數(shù)以每10年6.3 d的速率顯著上升,2000年之后,平均每年的霾日數(shù)在30 d以上[9]。霾發(fā)生時,細粒子濃度升高,大量極細微的干性塵粒、煙粒、鹽粒等均勻地懸浮在空氣中,易誘發(fā)上呼吸道感染、哮喘、結膜炎、支氣管炎、眼和喉部刺激、咳嗽、呼吸困難、鼻塞流鼻涕、皮疹、心血管系統(tǒng)紊亂等癥狀,以及容易出現(xiàn)抑郁、窒悶,情緒低落,煩躁不安,直接影響到人體的生理和心理健康[34]。廣州地區(qū)的研究發(fā)現(xiàn),灰霾天時,心血管疾病門診病人量顯著增加,廣州、深圳醫(yī)院的數(shù)據(jù)顯示,灰霾中的大氣污染物(如PM10)與人群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病例數(shù)、住院數(shù)有顯著的正相關性,當空氣中PM10的濃度升高,心腦血管疾病每日死亡人數(shù)增加[35]。此外,廣州市1954—2005年的灰霾數(shù)據(jù)和肺癌死亡率的研究表明,灰霾天氣與肺癌死亡率有關,且灰霾對肺癌死亡率的滯后效應在7年后達到最強[36]。
由于灰霾影響的復雜性,科學家迄今仍不清楚氣候變化是否會加重或減輕灰霾。降雨可以清除空氣中的顆粒物,因此降雨增加可能會減輕灰霾。風場減弱可能削弱大氣污染物的輸送和擴散能力[37],臺風的登陸對污染物的擴散和清除有促進作用[38],森林火災可以增加大氣中的顆粒物,未來氣候變化可能導致東亞季風強度和區(qū)域風場減弱[39],影響我國熱帶氣旋個數(shù)的減少[40]和森林大火的增多[41],這可能會導致灣區(qū)灰霾影響的加劇。
1.4.2 臭氧
臭氧(O3)是由氧氣、氮氧化物(NOx)及揮發(fā)性有機化合物(VOCs)在陽光作用下發(fā)生光化學反應形成,是光化學煙霧的主要成分[42]。監(jiān)測資料顯示:2006—2012年,粵港澳大灣區(qū)臭氧濃度上升了13%[43]。O3能刺激眼睛、鼻和咽喉,在高水平時會增加人體感染呼吸系統(tǒng)疾病的機會,亦可令呼吸系統(tǒng)疾病(如哮喘病等)患者的病情惡化,且對心血管疾病有明顯影響。深圳市的研究發(fā)現(xiàn),O3與人群心血管疾病住院病人數(shù)有顯著的正相關性,相關系數(shù)為0.658[44]。進一步研究表明,在溫度較低(<25%分位數(shù)日均溫度)或在冷季(11月—次年4月)時,溫度與O3對廣州居民死亡率的影響具有交互作用,隨著O3濃度的增加,居民死亡的風險顯著增加(包括當日效應和累積效應)[45]。
O3生成與前體物(NOx和VOCs)呈顯著的非線性關系[46],因此氣候變化可以通過改變O3前體物濃度進而影響O3生成。未來氣候變暖將會促使生物排放更多的VOCs(揮發(fā)性有機物),可能會加重O3污染[47]。觀測研究表明,地表O3濃度與當?shù)貧鉁刂g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因此氣溫升高可能會加重O3污染[48]。
1.5 氣候敏感型疾病的影響
1.5.1 瘧疾
瘧疾在灣區(qū)原已被消滅或控制,但環(huán)境和氣候的變化、人口流動的增加導致近年來輸入性瘧疾的暴發(fā)流行,在我國南方的一些山區(qū),瘧疾向高海拔地區(qū)蔓延[49。氣候變暖將增加瘧疾傳播潛勢,延長流行季節(jié)。當溫度升高1~2 ℃時,灣區(qū)微小按蚊地區(qū)間日瘧傳播潛勢可增加0.39~0.91倍,惡性瘧傳播潛勢可增加0.60~1.40倍,當溫度上升1 ℃時,瘧疾傳播季節(jié)可延長約1個月,當溫度上升2 ℃時,傳播季節(jié)可延長約2個月[50]。氣候變暖使沿海及沿江地區(qū)遭受洪水機會增大。洪水過后,媒介孳生地擴大,濕度增高,蚊蟲密度迅速上升,壽命延長,且災民通常較集中,生活條件及防蚊條件差,致使瘧疾發(fā)病迅速上升。全球氣候變暖,夏季時間和高溫時間延長,居民露宿現(xiàn)象相應增加,造成人-蚊接觸增多,瘧疾流行程度加重[50]。
1.5.2 登革熱
由于冰凍或持續(xù)寒冷天氣會殺死成蚊、過冬的蟲卵和幼蟲,目前登革熱病毒在20°S—30°N的熱帶地區(qū)傳播。1978年以來,灣區(qū)多次局地爆發(fā)了登革熱[51]。1986年以前,位于海南省南部的三亞市已基本具備登革熱終年流行的氣溫條件,1986年以后,三亞市已完全具備登革熱終年流行的氣溫條件[52]。氣溫突變后(1997—2012年)華南地區(qū)全年適于登革熱傳播的日數(shù)、終年流行區(qū)面積分別較突變前(1961—1996年)分別增加了10 d和408 km2[53]。研究表明,全球氣溫每升高1 ℃,登革熱的潛在傳染危險將增加31‰~47‰[54]。研究表明,與1997—2012年平均值相比,2013—2040年、2041—2070年和2071—2100年華南地區(qū)全年平均適于登革熱傳播流行的日數(shù)RCP4.5情景下分別增加10、15和20 d左右,RCP8.5情景下分別增加15、25和40 d左右,終年流行區(qū)面積RCP4.5情景下分別增加3962、5436和8260 km2,RCP8.5情景下分別增加4536、8780和20680 km2[53]。
1.6 新發(fā)傳染病的影響
1.6.1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tǒng)綜合征(SARS)
廣州大氣環(huán)境因素與SARS疫情短期變化關系的研究表明,SARS疫情的短期漲落和大氣環(huán)境變化有相同的周期性,優(yōu)勢周期為3~5 d,并且SARS和大氣環(huán)境變量的漲落有顯著的相關性。廣州每日SARS新增病例數(shù)的漲落與前期氣溫要素(平均氣溫、最高氣溫、最低氣溫、氣溫日較差)呈顯著負相關,即氣溫下降、氣溫日較差減小對后期SARS病例增加有作用。風速也與SARS呈顯著正相關。SARS疫情還與前期污染物濃度變化有明顯反位相關系,但反位相關系只是冷空氣引起的,因為冷空氣到達時北風加大,可沖淡大氣污染物的濃度。這些均說明冷空氣活動有加重疫情的作用。例如,2003年,在冷空氣來臨前的1月31日廣州平均氣溫高達19℃,2月3日一股強冷空氣影響廣州,日平均氣溫降到11℃,2月8日SARS大規(guī)模爆發(fā)。冷空氣來臨時,首先溫度驟降,劇變天氣使人群免疫力下降,SARS病毒趁虛而入;其次,風力加大,有利病毒擴散;另外,冷空氣帶來雨水和寒冷,人們室內活動時間增多,增加了封閉空間中感染SARS的機會。這些環(huán)境條件使人體感染SARS病毒和發(fā)病的機會增加[55]。在香港的研究也表明,SARS暴發(fā)與氣溫參數(shù)呈負相關,與氣壓參數(shù)呈正相關,SARS暴發(fā)前后均有明顯冷空氣活動[56-58]。
1.6.2 禽流感
研究發(fā)現(xiàn),在2004年1月中旬—2月上旬禽流感高發(fā)期,廣州地區(qū)呈現(xiàn)出低溫高濕的氣候特點,低溫高濕的氣象條件對該地區(qū)禽流感的發(fā)生和傳播非常有利,而2004年2月中旬以后廣州地區(qū)氣溫回升、光照充足的氣象條件則抑制了禽流感的傳播[59]。氣候變暖可能助長禽流感。在禽流感的傳播過程中,氣候因素肯定起作用。候鳥已成為禽流感病毒的主要病媒,而候鳥的生活習性與氣候息息相關。世界衛(wèi)生組織和我國衛(wèi)生部均指出,禽流感病毒對熱和紫外線敏感。我國97%的人禽流感的個例都發(fā)生在亞熱帶季風區(qū),很可能與這一地區(qū)的氣候特點有關。禽流感病毒最適宜傳播溫度為10~20 ℃[60]。
2 研究展望與適應對策
1)開展跨學科研究
影響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氣候因素,還有其他環(huán)境因素和經(jīng)濟社會條件,隨著全球變暖的不斷加劇,不僅需要研究氣候敏感性健康結局的疾病負擔,更需要加強跨學科協(xié)作,共同開展氣候-環(huán)境-經(jīng)濟社會健康影響交互作用研究。
2)揭示氣候變化健康影響機制
目前,氣候變化對人群健康影響機制的研究還較為欠缺,因此,需借助人工氣候艙、數(shù)值模擬等手段,研究氣候變化通過何種生理病理途徑來改變和影響人體各系統(tǒng)、各器官功能,以明確氣候變化對人群健康的影響機制并進一步探究發(fā)病規(guī)律。
3)發(fā)布人群健康氣候預警
在熱浪、寒潮、灰霾等高發(fā)和氣溫變化異常季節(jié),加強人群健康氣候預警,幫助人們及時采取預防措施,避免傷害。并進一步研究未來氣候敏感性健康結局的長期變化趨勢,明確氣候變化造成災難性健康后果的閾值和出現(xiàn)時間。
4)有效保護敏感人群
根據(jù)大多數(shù)研究的結論,氣候變化的易感人群是老年人、兒童、女性、患基礎疾病和社會經(jīng)濟地位較低者。有關部門在采取防護措施時應當更具針對性,以加強對敏感人群的保護。
5)加強數(shù)據(jù)共享和部門合作
建立氣候變化人群健康數(shù)據(jù)共享平臺,加強氣象與衛(wèi)生部門的緊密合作,建立氣候變化對人群健康危害的應急預案,促進在氣候敏感性疾病的監(jiān)測預測和早期預警中獲取有針對性的氣候服務,并將其應用于衛(wèi)生規(guī)劃和和實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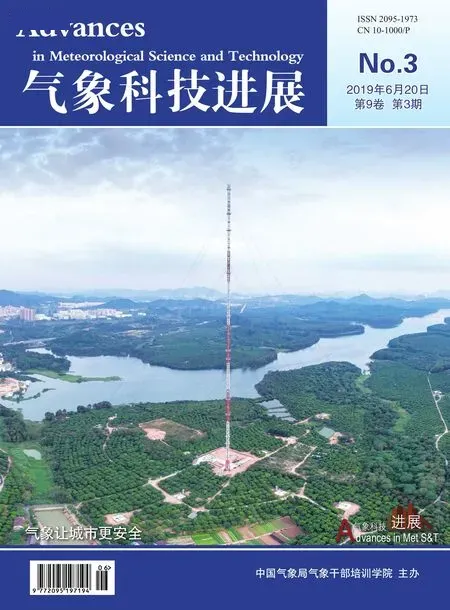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9年3期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9年3期
-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其它文章
- 讀圖
- 榜單
- 媒體掃描
- 兩岸聚力 共建華夏氣象前沿陣地
- 深圳市防雷安全管理信息系統(tǒng)的建設
- 從SCI收錄情況看大氣科學期刊發(fā)展態(tài)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