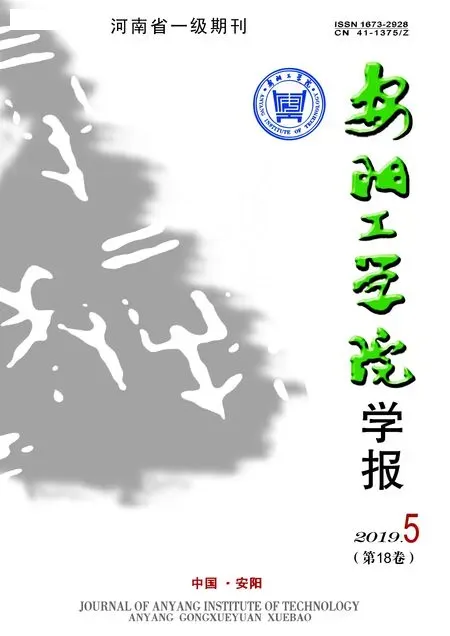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研究與改革
徐 波,王文兵
(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安徽蚌埠233030)
2006年1月施行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原《辦法》),在促進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的共同利益體的形成,公司經營管理者和核心員工積極性的調動、員工隊伍的穩定、公司治理機制的完善等方面發揮了積極效果。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由于激勵制度體系不統一、條件過于剛性、缺乏靈活性、價格倒掛等因素存在導致股權激勵實施艱難、股權激勵演變管理層尋租工具等諸多問題而飽受詬病。為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優化上市公司投資者回報機制的精神,提升股權激勵效果以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優化投資者回報能力,中國證監會于2016年7月13日發布《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新《辦法》)[1]。鑒于此,梳理與澄清我國資本市場近10年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運作狀況、效果以及存在的問題,簡評新《辦法》的重要變化,有利于指導、規范上市公司股權激勵運作,遏制上市公司管理層尋租,發揮股權激勵功能,提升長期激勵效果與上市公司績效,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股權激勵理論研究
(一)委托代理理論
Adam Smith(1937)在《國富論》經典描述了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即股份制公司的董事管理別人的錢而不是自己的,不能指望他們會像私人合伙公司的合伙者一樣時刻警覺、謹慎地經營著自己的財富[2]。為解決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委托代理關系,股權激勵是促進股東與管理者形成利益共同體的有力手段。Jensen和Meckling(1976)研究認為,通過股權激勵,讓管理者擁有公司股權,使其成為公司剩余權益的擁有者,能有效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3]。Wilson(1969)、Ross(1973)、Holmstrom(1979)以及 Grossman和 Hart(1983)等利用模型分析,系統研究了委托代理關系,因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產生委托代理關系中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股權激勵成為解決代理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的核心手段[4]。由于信息不對稱與契約不完全,為使委托人與代理人二者目標盡可能趨同,授予代理人一定數量股份或經公司部分收益以期權形式體現,將二者利益目標捆綁,縮小委托人與代理人利益目標差距,股權激勵機制順應而生。
(二)雙因素激勵理論
雙因素激勵理論(Two Factors Theory)是美國心理學家Fredrick Herzberg(1959)提出,又稱激勵保健理論。雙因素激勵理論認為人的工作動機受激勵和保健兩因素影響,其理論根據是得到滿足的激勵因素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以工作為核心的激勵因素是人在工作時發生,而保健因素缺乏時會引起人的強烈不滿,但具備保健因素時并不一定會強烈調動人的積極性。激勵因素與人的滿足感相關,而保健因素與人的不滿足感相關。在現代企業中委托人應用激勵理論設計激勵方案,一方面保證代理人的基本收入確保其基本安全感得到“保健”目標實現;另一方面給予代理人持有與投資者有同樣風險的期權收益達到“激勵”效果,促進委托人(投資者)與代理人(管理層)之間的目標趨向一致[5]。雙因素經濟論一直被視為管理層與員工持股原因的經典思想,其理論意義在于揭示了管理層與員工缺乏資本所有權而不能分享資本收益。
(三)人力資本理論
人力資本理論是由Schultz、Becker等經濟學家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提出。該理論研究認為人的知識、技能、健康、資歷以及技能的熟練程度等都屬于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物質資本收益率,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相同點是二者都具有所有權,而二者的典型區別是人力資本的所有權只屬于個人[6]。在企業契約中,人力資本主要表現為人的知識、技能以及管理能力,企業必須通過激勵機制安排才能發揮人的潛能,體現人力資本價值。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產生委托代理關系,代理人的人力資本如受到不公平對待,人力資本價值無法體現,代理人的積極性受到影響,誘生委托人與代理人目標偏離。因此,給予代理人股票期權激勵是體現代理人人力資本價值屬性的一種激勵模式,是人力資本價值補償,讓代理人共享企業的剩余價值,縮小委托人與代理人利益目標偏離度。
(四)剩余索取權理論
薩伊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是商品生產三要素,也是商品價值創造者。因此,工人得到工資、資本家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也就是按要素進行分配,馬克思稱之為“三位一體”理論[7]。隨著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發展,“兩權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逐漸代替過去那種“兩權合一”的企業制度。早在20世紀30年代,這種分離的現象被稱之為“經理革命”。代理人擁有“沒有財產的權力”逐漸強化,主要通過給予代理人購買股票優惠權高額年薪制,讓渡部分剩余索取權,其本質就是為代理人提供了一條可以憑借自己的勞動貢獻來分享企業剩余索取權的路徑。代理人分享剩余索取權,由代理人承擔部分風險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
二、股權激勵實證研究
具有“雙刃劍”效應股權激勵,是“金手銬”還是“金手表”、是利益趨同效應抑或是壕溝效應,實務與學術界對股權激勵效應爭論與探索從未停息。
(一)國外股權激勵效應的經驗證據
西方學者以委托代理、利益捆綁、不完全契約以及產權等理論為視角,對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效應進行了大量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證據。但因研究視角、樣本選取以及變量內生性等原因,至今尚無一致結論。迄今,西方學者研究股權激勵形成兩大相悖觀點,一是利益趨同效應;二是壕溝效應。Core和Guay(1999)以及 Jensen和Murphy(2004)的研究結論,均表明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與公司價值正相關[8-9]。西方學者除關注股權激勵的對公司績效的直接效應外,還重點研究了股權激勵公司的創新行為、股利政策以及投資決策對公司績效的間接影響。Defusco、Johnson和Zorn(1990)驗證了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計劃有助于促使管理層投資更高風險、更高收益的項目來提升公司績效。Wu和Tu(2007)從行為代理角度出發研究發現公司的富余資源與績效是影響股權激勵效應的兩個重要因素,當公司擁有較多的富余資源或者公司績效較好時,股票期權對研發支出具有積極的正面效應[10]。Bartoy(1998)發現,當管理層持有大量股票期權且機構投資者持股較多時,管理層更傾向于選擇股份支付而非現金的股利支付方式(即使該期權不受股利保護),該文同時發現股票期權與公司股利發放之間呈現強烈的負相關性。Bebchuk等(2003)提出了股權激勵誘生管理層尋租理論,認為股權激勵并不能有效解決反而會加劇委托代理問題[11]。Matsunaga(1995)發現當股票期權激勵的實施與公司盈利能力相關,但公司盈利能力較差時,公司更傾向于采用股票期權激勵方式以減少費用從而提高賬面盈利能力,但期權費用化會計政策推出后,這種相關性正在弱化。Feng和Tian(2009)發現股權激勵在2002年期權費用化前后發生重大變化,股票期權均值從以25%的速度上升到以17%的速度下降,股權激勵受到廣泛質疑[12]。Benjamin、Wendy和 John(2010)通過問卷調查發現,管理層權力層級與是否受聘于公司總部的等自身信息優勢安排股權激勵的行權時間,從而誘發管理層價格操縱行為[13]。除上述經驗證據外,管理層在股權激勵期間操縱會計政策進行盈余管理是股權激勵壕溝效應最主要的表現形式。Eli Bartov和Partha Mohanram(2004)研究發現公司管理層應用內部信息操縱盈余管理,股票期權在行權前公司盈利水平會有較好表現,一旦行權后公司盈利水平下降,其實質是行權后公司盈利轉回行權前公司盈利的非正常表現[14]。
從上述國外研究結論來看,股權激勵效應是化解還是誘生、是抑制還是加劇委托代理問題,因研究視角、理論基礎、樣本選擇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異,至今尚無一致結論。股權激勵在國外應用發展幾十年,其正面效用有目共睹。但股權激勵并非處處是“靈丹妙藥”,管理層推出股權激勵計劃損害股東利益屢有發生,虛高的行權比例與超低的行權價格,利用更激進的盈余管理等手段粉飾公司短期績效,將原本具有約束與激勵雙重效應的股權激勵“金手銬”演變成管理層的“金手表”。鑒于此,高質量的股權激勵契約安排的重要性凸顯。
(二)國內股權激勵效應的經驗證據
股權激勵效應在西方得到廣泛推崇,但在我國實踐中因制度背景與西方存在較大差異,國有控股、壟斷以及市場化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原因,致使我國股權激勵效應備受爭議。夏蕓等(2008)以我國滬深高科技上市公司為樣本,考量股權激勵對研發支出的影響,研究發現推出股權激勵計劃的高科技公司研發投入顯著上升[15]。呂長江等(2009)發現股權激勵具有激勵與福利雙重效應,主張通過強化公司治理優化激勵方案的優化(如激勵條件和激勵有效期的改善),來增強其激勵效果弱化其福利效果,以避免股權激勵淪為高管為自身謀福利的工具[16]。宮玉松(2012)直言不諱指出,我國近年來股權激勵制度在上市公司迅速推廣,“公司業績增長,股價上漲,投資者受益,公司高管暴富”的“多贏”表象下隱藏著大量問題,部分公司的股權激勵已被扭曲為管理層牟取暴利的工具[17]。謝德仁等(2014)研究發現,自2006年以來我國上市公司推出的股權激勵計劃的可行權條件都是業績條件,主要集中在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和凈利潤增長率兩項會計業績指標上,且要求業績水平分別集中在“10%”和“20%”上,形成了有趣的“10%、20%”現象,“10%、20%”并非推出股權激勵計劃公司盈利能力的真實期望和合理反映,而是從眾效應之結果,股權激勵計劃備案制及對股權再融資等的監管規定是從眾效應的主要誘因[18]。劉峰等(2014)對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終止實施動機進行了研究,發現終止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動機不是因為公司外部的經營環境變化、或者自身經營出現較大問題,而是公司股票在二級市場上表現不佳;不是整體激勵計劃中授予股權的數量偏少,而是激勵時對高管和核心員工的分配差異。
以股權分置改革為契機的股權激勵歷經近10年的實踐與發展,實現了激勵對象與企業共享利潤、共擔風險,減少或消除管理層短期行為,促進了公司長遠發展。但因我國資本市場的制度環境與西方發達市場存在較大差異,市場機制不完善,部分公司的股權激勵已被扭曲為公司管理層牟取暴利的尋租工具和市場買單的管理層盛宴,制度缺陷、時機選擇機會主義、門檻過低、激勵期限過短、解鎖即套現、盈余管理與利益輸送等頑疾障礙股權激勵效應,引發監管、媒體以及公眾廣泛質疑與批評。
三、股權激勵改革
與原《辦法》相比,新《辦法》在信息披露、監督管理、行權對象與條件以及股權激勵程序等方面進行細化,降低信息不對稱,遏制盈余管理與利益輸送,著力提升股權激勵效應,逐步形成公司自主決定與市場約束相結合的有效股權激勵制度。
第一,以信息披露與事后監管為抓手,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新《辦法》基于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監管理念,對上市公司實行股權激勵過程中相關信息披露的時間、內容及程序等方面進行了規定,讓投資者人了解股權激勵的目的、對象、業績條件、合規性、實施效果、實施失敗及取消等異常行為原因,以此來減少股權激勵實施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強化市場約束機制。
第二,以負面清單形式,細化實行(參與)股權激勵條件。以負面清單形式,明確了五種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情形和六種不得成為激勵對象的個人,特別是新增5%以上股東與實際控制人及其親屬不得成為激勵對象,切斷因內部人控制通過股權激勵的利益輸送鏈條。同時為進一步調動外籍管理層積極性,明確境內工作的外籍員工可成為激勵對象。
第三,放寬限制,進一步賦予公司自治和靈活決策空間。降低管理層操縱業績以滿足股權激勵的授權條件、行權條件的道德風險,新《辦法》取消公司業績指標的強制性要求(如,不低于公司歷史水平且不得為負)。給予公司更多的靈活空間,對授予價格、行權價格僅作原則性要求而不作強制性規定,鼓勵公司可以靈活確定定價方式;取消了股權激勵與其他重大事項的間隔期規定(原《辦法》為30天),明確股權激勵計劃與增發新股、并購重組、資產注入、發行債券(含可轉債)等重大事項不相互排斥;提高預留權益比例到20%(原《辦法》為10%),從而滿足公司后續發展的人才需求。
第四,細化股權激勵的規定,增強可操作性。改變原《辦法》對限制性股票過于籠統,完善對限制性股票授予價格的規定,要求限制性股票每期解除限售比例不得超過50%,未達到解除限售條件或終止股權激勵的,要求上市公司回購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既體現長期激勵效應,又促使責權利相統一;解決實踐中存在的權期時段重合問題,對于未滿足分期行權的要求,新《辦法》對分期行權提出具體要求,即后一行權期的起算日不得早于前一行權期的屆滿日,且各期行權比例不超過股票期權總額的50%,以增強長期激勵效應。
第五,強化股權激勵程序化要求,強調內部監督、事后監管與問責并舉。從董事會審議、獨立董事、監事會或財務顧問意見書、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內部公示、股東大會審議、授予權益并完成、變更與終止,新《辦法》重點強化股權激勵程序公正、透明,以期通過程序正義促進實質正義。通過強化事后監管、引入問責機制、細化監督處罰,為事后監管執法提供保障。
四、結論
此次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修訂總體原則為以“信息披露”為中心,落實“寬進嚴管”的監管理念,放松事前管制、加強事后監管,逐步形成“公司自主決定、市場約束有效”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制度。但我國資本市場與西方成熟經濟體相比還存在以下諸多問題,股權激勵并非靈丹妙藥,其長期激勵效應還有待進一步考量。一是成熟規范有效的資本市場是發揮股權激勵效應的制度環境,但我國資本市場投機氛圍濃厚,股票價格失真,制約股權激勵效應;二是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是發揮股權激勵效應的制度保證,但我國上市公司依然存在“一股獨大”以及內部人控制等情形,致使公司治理機制不健全,公司治理水平不高,抑制股權激勵效應;三是完全競爭的職業經理人市場是發揮股權激勵效應的制度基礎,但我國存在大量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管理層主要由政府行政任命,推行完全競爭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力度欠缺,股權激勵積極性不高,障礙長期激勵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