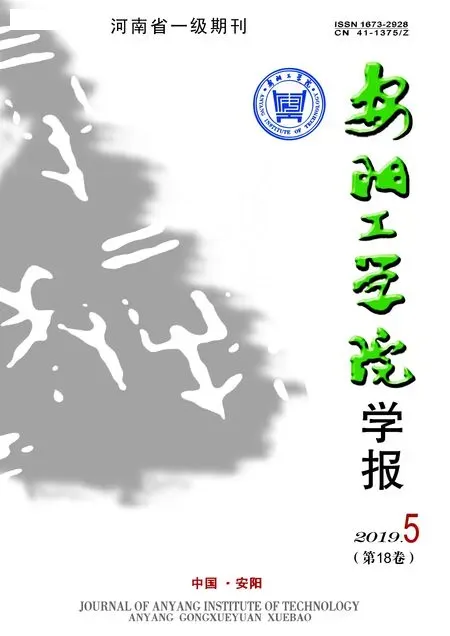晚清小說譯述風尚成因探析
李雙娟
(安陽工學院,河南安陽455000)
自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大量外國小說被譯入漢語。據不完全統計,1840年至1919年之間的翻譯小說約2567種[1]88,數量之大、影響之廣空前絕后。然而,通過研究不難發現,當時的小說翻譯不夠忠實,譯者對原作大量刪改,這種翻譯方式被后世學人稱為“譯述”。本文主要分析“譯述”作品在文學翻譯中的地位及該風尚的成因。
一、“譯述”風尚特征分析
晚清時期,為了拯救民族于危亡,眾多仁人志士紛紛拿起譯筆,希望通過翻譯引入新的思想,開啟民智。這一時期的小說翻譯不可計數。梁啟超略通日文,但他不僅身體力行,親自翻譯了《十五小豪杰》,還發表文章《譯印政治小說序》、《論譯書》,呼吁學人翻譯小說。
在小說翻譯中,眾多翻譯家不約而同地采用了相似的方法:譯述。譯者對原作內容隨意增刪,如刪除不符合中國小說形式的心理描寫,或與儒家傳統相悖的情節,“以取便觀者”;對原作中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以中國特色的詞匯代之,“凡人名皆改為中國習見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國地名”,“以免記憶之苦”,且美其名曰“小說重關目,不重名詞”[2]147。
章回體在中國文學中存在已久,晚清的小說翻譯家大多采用了這種成熟的文學形式來翻譯西洋小說,如陳獨秀和蘇曼殊翻譯的《慘世界》即采用了該形式。據郭延禮統計,1895-1926年間《新小說》、《新新小說》雜志上刊載的長篇翻譯小說共22部,而其中13部采用了章回體進行翻譯。[1]30
另外,當時雖然翻譯了大量小說,但譯者缺乏版權意識,對原作者介紹甚少,譯名不統一,隨意更改譯作題目等現象普遍。譯者署名方面也缺乏統一標準,部分譯者甚至以筆名代替真名發表譯作,如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署名為“冷紅生”等。
上述種種特點構成了晚清小說翻譯的整體風格。該翻譯風格與后世的文學翻譯截然不同,若按當前的一些標準,這些翻譯小說無法歸為翻譯文學,但作為普遍存在的現象,其成因有待我們考證。
二、“譯述”風尚成因探析
(一)對佛經翻譯的承繼
佛經的大量譯入形成了中國最早的翻譯高潮,佛經翻譯最初就有“文”“質”之爭。從“因循本旨,不加文飾”[3]22到“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3]32,從早期的字字對譯到后期的重視文采辭藻,佛經翻譯對后世文學翻譯影響巨大。晚清時期,眾多翻譯家或在譯作的序言跋語中,或在書信來往中,談及了佛經翻譯的影響。例如梁啟超曾經撰文,認為“翻譯之事,莫先于內典;翻譯之術,亦莫善于內典。今日言譯例,當法內典”[3]130。嚴復指出“夫翻譯之體,其在中國,則誠有異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書是也”[3]77而林紓的翻譯也被認為“紓之譯述西稗,可方六朝人譯佛經”[3]141。在文與質的選擇上,近代翻譯家幾乎無一例外選擇了“文”。正如梁啟超所言:“聞六朝唐諸古哲之譯佛經,往往并其篇章而前后顛倒,參伍錯綜之。善譯者固嘗如是也”,“學其語,受其義,歸而記憶其所得從而筆之”,“言譯者,當以此義為最上”。從這些言辭中,不難發現,晚清譯述風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佛經翻譯息息相關。
(二)社會文化因素影響
晚清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快速發展,封建的清王朝閉關鎖國,仍以“天朝上國”自居,但是隨著國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知識階層開始開眼看世界,洋務運動興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廣為傳播,為了開啟民智,眾多文人志士紛紛翻譯西洋小說,因為“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從而形成了“譯者百出,年以百計,與他種科學教科之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綜上年所印行者,則著作者不得一二,翻譯者十常居八九”[4]的小說翻譯高潮局面。雖然從表面上看,翻譯文學在這個時期盛行,似乎占據了文學的中心位置,根據多元系統理論,此時翻譯文學應該參與創造模式,不惜打破傳統文學規范,以實現譯文的“充分性”。“譯述”風尚下的文學翻譯恰好相反,譯者不惜對原文大加刪改,大量套用中國傳統的“章回體”等文學規范,強調譯作的可讀性。這個矛盾首先與翻譯目的有關。如前所述,晚清時期大量作品的譯介不是出于文學賞析的目的,而是為了開啟民智,教育婦孺、平民階層,翻譯作品只是“工具”。其次,雖然中國在軍事上不如人,封建文人的心目中,依然是充滿對西洋文學的鄙視和對中國文學的自滿之情的,認為“吾祖國之文學,在五洲萬國中,真可以自豪也”[3]311。因此,在進行翻譯時,他們不尊重原作,肆意篡改。
(三)譯者因素與讀者因素
正如列夫維爾所言,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譯者是在特定的時空、特定的文化中進行翻譯的。譯者的文學意識和讀者意識無不影響著其翻譯策略的選擇。晚清的譯者,從幼年始,就浸淫在“忠君愛國”、“三綱五常”等儒家思想之中,其畢生追求不外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文學翻譯中,這種儒家思想深刻影響著譯者的翻譯策略。面對列強入侵,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封建知識階層希望以小說來開啟民智,希望以文學來挽救清王朝。因此,在進行文學翻譯時,他們不是為了創造“傳世之作”,產生不朽的文學價值,而是希望能夠通過翻譯文學來激起民眾的危機意識,另外,傳統的文人對小說這種藝術形式的態度是鄙視的。小說是用來教育農夫走卒和婦孺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封建文人對翻譯小說的態度是隨意的,在翻譯時,他們所采用的工作語言也毫無意外地是自己最為熟悉的高雅語言——文言文。
雖然翻譯家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通過小說來開啟民智,認為其目標讀者是農夫走卒,事實上,“今日之購小說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2]314,這些“舊學界”小說讀者群,本身也是尊崇文言文、輕視白話文的,也是支持中國傳統文學體例的。他們內心同樣充滿了對西方文明的輕視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傲,譯者和讀者的“共謀”使得晚清小說翻譯呈現出“譯述”的風尚。
三、結論
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當文學系統在大的系統中處于幼嫩或者弱勢時,以及文學系統內部出現轉折點、危機或真空時,翻譯文學會占據其中心位置,此時會參與創造模式,不惜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而處于邊緣時,則會套用本國文學中的二級模式。體現在翻譯策略上,前者著重譯文的“充分性”,后者則強調“可接受性”[5]。晚清小說翻譯強調的就是民眾的“可接受性”。由于對小說社會功能的夸大和鼓吹,晚清時期翻譯文學在數量上一度占據了上風,但始終沒有占據中國文學系統的中心地位。譯者對文學翻譯傳統的承繼、晚清時期特定的社會文化因素、譯者和讀者的文學修養及其對小說的態度等因素決定了晚清小說翻譯的翻譯策略應該是且只能是邊譯邊述,譯述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