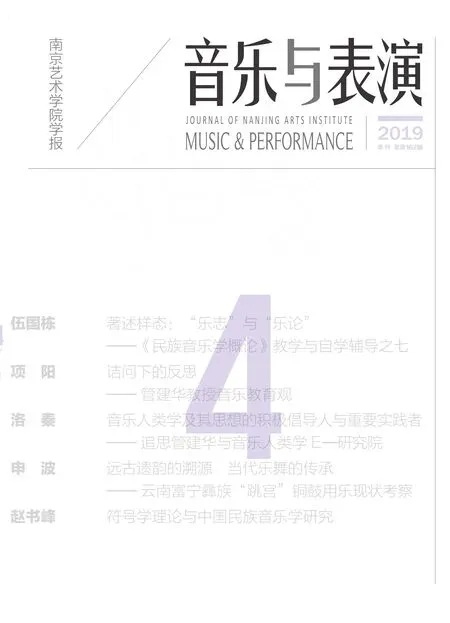音樂地理學視域下中山咸水歌生存緣由研究①
馬 達(福建師范大學 協和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楊華麗(佛山市順德區陳村鎮 青云初級中學,廣東 佛山 528313)
咸水歌是嶺南廣府的代表性民歌,是疍民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寶貴遺產,更是疍民群體的一種身份確認和精神支柱。廣東省中山市被稱為“民歌之鄉”,民間流行的歌種有咸水歌、客家山歌、鶴歌、漁鼓、白口蓮山歌、東鄉調等,其中咸水歌在市內傳承活動最為盛行,曲目豐富,至今仍保留著傳統的唱法,其音樂風格、音樂結構、語言均具有較高的藝術與文化價值。為保護和傳承中山咸水歌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山市的音樂家協會、民間藝術家協會等機構重視對咸水歌音樂的研究;為促進咸水歌人才的培養和咸水歌活動氛圍的營造,中山市政府先后在中山市內設立6 所中山咸水歌傳承基地小學,多次舉行咸水歌展演和比賽等活動,來促進中山咸水歌人才的培養和城市文化建設。可見,中山咸水歌在中山得到很好的生存和發展,已成為中山市城市文化建設的一種象征。這樣一種音樂文化現象的形成與中山地區的地理環境之間是否有關聯呢?在該地形成了怎樣的聲音景觀呢?本文通過音樂地理學的視角,由靜態地理與動態人文兩方面對中山咸水歌的生存緣由進行探討。
一、地理環境對中山咸水歌的孕育
“一種文化的產生與特定自然地理環境(含地形、地貌、氣候、水文、植被等)及特定人文地理環境(含語言、經濟、民族、民俗、宗教等)均發生聯系。”[1]中山咸水歌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在中山地區得以生存發展與中山地區的地理環境之間發生著怎樣的聯系呢?
(一)自然地理環境
俗話說:“凡有疍民處必有咸水歌”。可見,探究咸水歌的生存與發展的緣由就必然要探究咸水歌的創作和表演者——疍民群體在何處生根落戶。“中山市古稱香山,位于廣東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河網區下游,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光熱充足,雨量充沛,太陽輻射能量豐富。地形以平原為主,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平原地區河網深受南海海洋潮汐的影響,具典型河口區特色。境內河網密布,主要有13 條江河流經,內河涌有298 條,具有豐富的水資源和魚類、貝類等水生動物資源。”[2]177疍民選擇在中山這樣的地理環境落戶,是由于受到疍民長期生活環境中所形成的一種環境感知的影響。“地理學家發現,地理環境會影響著人口分布,且人們在長時間生活的環境中會形成一種環境感知,從而影響人們選擇新居住地。”[3]那么疍民為何會形成這樣一種環境感知呢?我們需追溯到疍民祖先的生活環境來探討。查閱現有的資料記載,疍民最早的祖先應是古越人,該說法已得到眾多專家學者的認同,如馮明洋《越歌:嶺南本土歌樂文化論》中對疍家人及其語其歌為古越嫡傳的說法列出三點證據佐證古越族為疍民先祖[4];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將疍民與壯、黎、瑤等族并列,稱之為“真粵人”,被視作古代越人的嫡傳后裔。[5]232古越族自古便有一種“親水”的習性,他們擇水而居,善于水上生活,熟悉海洋的潮汐、漁汛、捕魚技巧等規律,通過拾集水中貝藻、捕撈水中魚類為生,同時他們還會使用舟船,以舟為宅。漢代劉安《淮南子·原道訓》:“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民人短綣不绔,以便涉水;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6]說明了疍民祖先之一的古越人在漢代時期就已為適應環境而使用舟船了。由文獻中得知:古越族這樣一種“親水”習性、以舟為室的生活方式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后代疍民的生活方式,如宋代州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記載:“以舟為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蜑也。”[7]樂史在《太平寰宇記》卷157“新會縣條”中記載:“疍戶為新會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為活。”[8]疍民的祖先除了古越族人外,據“楊萬翔先生在《羊城舊事》的‘海闊疍家強’條目中闡述的史實,漢、晉、宋代三個時期人們因為戰亂等原因,被迫逃亡至水中而成了疍家來源之‘流’。”[9]他們備受歧視,疏離陸地,而江海的寬容和豐富資源,讓他們創造并傳承了那因水而生的傳統生活方式,對水環境形成一種環境感知。中山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正是適應了疍民對水環境的感知需求而成了新居住地。《中山市志》載:“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香山東北部沖積平原‘東沙十六沙’一帶已有疍民生活。”[2]177《中山市坦洲鎮志》記載:“坦洲原居民85%以上為‘蜑民’(疍民)。宋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先后成陸依西北向東南次第被圍墾造田,中山坦洲成陸最遲,故坦洲成為疍民最后的匯集地,來自三水、南海、順德等地的疍民陸續匯集于此,該地也成為疍民人文文化的沉淀地。”[10]1
疍民浮生于江海環境是何以能夠孕育出咸水歌的呢?疍民以舟為宅,以漁為業,會隨著漁場的變化和捕撈地點情況而遷徙,并且出海捕魚時還可能會遇到兇猛巨魚要搏斗,如屈大均所描述的:“蛋人善沒水,每持刀槊水中與巨魚斗。”[5]485上述“沒水”即“潛水”,正是反映了疍民善于潛水且常在水中與巨魚搏斗的事實。這樣惡劣的生存環境使得他們需要用高亢悠長的大聲響腔的音調來傳情達意,去傳呼、召集、相互通傳訊息,與風雨抗爭,與海浪搏斗。又因他們終年漂浮在海上,流動性大,居無定所,沒有娛樂方式,使得疍民首選人類“本能性”的抒發方式——歌唱來自娛自樂,消除疲勞,排遣孤獨感,大聲呼唱出心中的喜怒哀樂與恐懼,向往與追求。中山地區“滄海變桑田”,疍民移居于此地,在沙田[11]①沙田是嶺南沿海或河湖周圍在淤泥沙上開墾而成的農田,距離岸上居住地較遠,需駕舟前往。人們通常會在二月前往沙田結墩耕作至五月結束,七、八月再重返沙田堵水捕撈水產。參見:嶺地南文化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嶺南文化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117。上進行耕作,從事農業。他們雖遷居于陸地但依然堅守著水濱,這種演唱咸水歌的娛樂方式也未曾改變,會在耕作時演唱及空閑時舉行搭臺斗歌活動等。葉顯恩認為:“就疍民總體而言,他們的生活習俗與觀念文化,在千百年來面臨的自然和社會的生態條件的變遷,只做了適應性的調整和某些邊際性的變遷,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革。”[12]
(二)人文地理環境
疍家人千百年來與海河魚打交道,使得他們創造了與陸上居民不同,自成一派的特色疍家文化。而咸水歌正是疍民生活的一個縮影,涉及疍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別是與疍民的語言、風俗及商業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相互依存。
其一,咸水歌與疍民語言。咸水歌之所以能夠在疍民群體中廣泛流傳,不僅是因為它唱出了疍民的心聲,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其演唱的語言符合疍民自己的語言習慣有關,一唱便能產生共鳴和識別出鄉音。咸水歌的語言具有樸實自然的口語化,別具一格的襯詞喊頭,如“妹好啊哩”“有情阿妹”等,并采用依字行腔的方式演唱,凸顯其地方特色。疍民群體分布在不同地區操著不同的疍家語言,其中講粵語的疍民是我國疍民的主體,因其咸水歌歌詞中還保留有一些古越語的特征,因而有被稱為是“嶺南音樂的活化石”的說法。中山沙田地區疍民也講粵語,但因長期受中山本地方言的影響形成一定的差異,被稱作沙田話。疍民長期與水打交道,其語言上多體現與水相關的詞,凸顯在咸水歌中就是歌詞多有“魚”“蝦”“網”“珍珠”“船”等。民歌必須具有其地方特色才能稱之為民歌,而這地方特色的體現主要就是通過演唱的方言來體現。
其二,咸水歌與疍民傳統風俗。咸水歌與疍民傳統風俗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可以說是相互依存,有些風俗中還會有固定的咸水歌唱詞和唱腔,如咸水歌中的高堂歌就以婚嫁中的坐高堂儀式來命名。咸水歌對于疍民的婚姻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蛋人)常日貧乏不能自存。土人不與通婚姻,亦不與陸居”[13]59這里的“土人”指的是陸地上的人,也就是說疍民不能與陸地上的人通婚,因而導致其交往范圍狹窄,選擇渠道單一,只有在船只來往相遇時,男女疍民以演唱情歌來作為一種“姻緣線”,互訴愛慕情誼。“清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詩語》和《廣東通志》也分別有著疍民以咸水歌為媒介的婚嫁習俗的記載,即‘疍人亦喜歌唱,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過舟也’‘民家嫁女,集群婦共席,唱歌以道別,謂之歌堂’。”[10]708這種對歌形式貫穿著男女婚姻習俗的始終,不同過程唱不同內容的咸水歌,如迎親隊伍唱祝福歌,媒人唱好意頭咸水歌,親朋送禮唱送禮歌,待嫁女子唱哭嫁歌,坐高堂唱感恩親人歌等。除了婚嫁風俗外,咸水歌還在疍民祝壽、殯葬等儀式中貫穿全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其三,咸水歌與疍民商業活動。珠江三角洲地區水網密布,村鎮之間大多有小河相隔,交通不便,因而有一些疍民依靠擺渡和經營小量貨運為生計。自秦漢以后,疍民的飲食追求提升,也慢慢過渡到以糧食為主要食物,他們將捕撈的海產品駕舟去城鎮販賣來換取所需的糧食和生活日用品。“茭塘之地瀕海,凡朝墟夕市,販夫販婦,各以其所捕海鮮連筐而至。家之所有,則以錢易之;疍人之所有,則以米易之。”[14]他們販賣過程中還會隨口唱著咸水歌來吸引客戶,如:“艇仔粥,艇仔粥,爽口鮮香唔使焗。一毫幾分有一碗,好味食到耳仔煜”。[15]這是一首疍民販賣艇仔粥時演唱的咸水歌,說明咸水歌在早期疍民的商業活動中就發揮著獨特的功能。
人們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時也能孕育一方文化。咸水歌就是在這樣一種“水”環境中孕育而生,伴隨著疍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與疍民的生產勞作、風俗、經濟、語言相互依存,凸顯其獨特作用,同時也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莫日芬言,咸水歌具有“結構自如,句法不拘,土音俗語,自然入歌,曲調平穩流暢,無大起伏,清麗活潑,如行云流水,似棹舟蕩漾”[16]30的特點,以中山咸水歌《海底珍珠容易揾》為例(見譜例1)。
該歌曲是咸水歌的一類——大罾歌[17]59①咸水歌是疍家漁歌的統稱,包括多個小歌種,如咸水歌、高堂歌、大罾歌、姑妹歌等,其中“大罾歌”是流行于珠江河道口沿岸水鄉和坦洲一帶,因水鄉人喜歡在近岸的河面插罾棟(大木椿)拉大網,利用潮水漲落的時機捕捉出入海的魚類,故此這些地區流行的民歌稱為“大罾歌”(也有將“罾”寫成“繒”的)。參見:陳錦昌.中山咸水歌,中山非物質文化遺產叢書[M].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2015:59。的經典曲目,男女對唱,以獨特的、親切的、樸實的“妹呀咧”或“哥呀咧”稱謂詞為喊句,既拉近了對唱二人的關系,又表現出了疍民演唱歌曲的生活化,同時加入了“咧”這一虛詞進行運腔和特有的“啊啰噯”拖腔演唱,極大地豐富了歌曲的表現力,使得歌曲演唱更為舒展流暢、委婉動聽,韻味無窮,也更能抒發演唱者的情感。歌曲采用二拍子和三拍子的交替出現,打破了歌曲重拍和弱拍有規律的周期循環,使得整首歌曲的重音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這樣的節奏特點與疍民長期生產生活的環境有關。疍民長期浮生于江海中,以舟為室,伴隨著海浪的起伏波動而晃動,重心不穩,使得他們演唱的歌曲也自然擁有這樣一種不穩定的特性。遼闊的江海生存環境使得疍民的心胸更為寬廣,簡單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得疍民的心態更為平和,體現在他們的歌曲上便是旋律以級進平穩進行為主,少有大跳音階的起伏波動,整個曲風平緩、柔和、自由。疍民獨特的生活環境也導致他們的娛樂方式較為單一,多是與同伴對歌或“斗歌”來作為娛樂和溝通的方式。“曲調由兩句體(單樂段)結構構成,上句終止于宮音下滑至角音,下句終止于徵音下滑至角音。”(見譜例2)
這樣一種以徵調中不穩定“角”音作終止的拖腔處理形成了咸水歌曲調的一大特色。歌曲的歌詞極具地方特點,與疍民的生產生活緊密聯系。疍民生活于海上,常年與水打交道,歌詞中的珍珠、魚、蝦等都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東西,借“海底珍珠容易揾”引出“真心阿妹世上難尋”的情感表達,用“筷子一雙”表達愿“同妹拍當”的希望等,巧妙地運用起興、比擬、對比、襯托等的修辭手法來加以豐富咸水歌的演唱內容。樸實自然的歌詞語言及一些方言土語的運用,如方言“揾[wen2]”——找、“唔[m4]”——不,符合疍民自己的語言習慣,并在此基礎上依字行腔演唱,巧妙地將方言唱詞的音、韻、調與曲調旋律完美地結合起來,體現出獨特的地域性特點。
咸水歌的孕育產生與其藝術特色的形成有賴于疍民的生產生活環境,就像喬建中所認為的:“咸水歌就是海、島環境的間接產物。”[18]
二、中山咸水歌聲音景觀的流動變化
美國音樂學家謝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在《聲音景觀:探索變化中的世界的音樂》中將“聲音景觀”定義為:“一種聲音景觀,即是一種音樂文化有特色的背景、聲音與意義。”[19]中山咸水歌的產生伴隨著疍民群體的遷移和壯大而發展,形成其特有的聲音藝術風格,是疍民群體的精神支柱和身份確認,對于疍民群體來說有其重要的意義,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形成獨特的聲音景觀。薛藝兵在《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地理學方法新探》一文中向我們傳遞了“傳統音樂不是一個穩定不變的靜態的、固化的‘景觀’,而是在音樂傳統中不斷衍生變化著的動態聲音景觀”[20]的理念,也就是說音樂傳統會隨著發聲體的移動在非固定空間中展現其聲音景觀。因而,要想研究中山咸水歌在中山地區形成的聲音景觀也應當結合其發聲體(疍民)的移動,在時間(歷史變遷)和空間(地域變遷)兩個維度中探究其動態變化的緣由。
(一)時間——歷史變遷的維度
咸水歌聲音景觀的歷史變遷主要是依據其發聲體(疍民)在歷史中的進程而變化的。關于咸水歌聲音景觀的發展狀況,按照時間的延續大致可分為,從唐朝時期咸水歌開始萌芽發展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呈現上升發展趨勢,再到新中國成立帶來了咸水歌的繁榮,而后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影響而逐漸走向衰微,再到恢復搶救這樣五個發展階段。
1.萌芽階段
咸水歌具體何時產生,歷史資料尚無明確記載。查閱古籍資料,咸水歌的記載最早見于“唐初王勃的《廣州寺碑》:揚粵當唐初,北人多以商至,遂家于此。六朝以來謠俗謳歌播于樂府,炎方勝事姿勢偏聞四海。然方言猶操蠻音,以邑里猶雜疍夷故也。”[21]這里的“蠻音”指的正是咸水歌,該記載也是出現“疍民”稱謂最早的記載,由此推斷,咸水歌從唐朝時期已萌芽產生是有理可據的,也有多數學者采用咸水歌演唱的語言(粵語)的形成時期為理據來推論咸水歌在唐朝時期就已萌芽產生。“粵語是廣東漢、越兩大族群從秦始皇時期‘以謫徙民,與越雜處’開始交融,秦漢時期的中原漢語與南越語言相互交融,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進一步交融,最后到唐宋時期最終形成而獨立存在。”[16]47唐代以前疍民一直漂浮于海上,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粵語的形成使得疍民們有了語言,能夠通過語言進行溝通交流,在海上用大聲響腔的音調來隔船喊話,逐漸形成獨特的音調,咸水歌便由此萌芽產生。
2.上升階段
唐代后,封建統治制度的不斷完善,政府開始向疍民群體征稅,并納入社會戶籍管理。元代將疍民分屬于最低等的雜戶進行管理,不歸入戶籍統計,而是屬于特殊門類對待,主要負責采集珍珠,被稱作“烏蜑戶”。明代時期疍民被視為低等的賤民階層,同樂戶、娼妓、佃仆等為同類。疍民群體自唐以來一直被視為異類存在,遭受陸人的鄙視和壓迫,被限制活動區域,被剝奪教育機會,被限制與岸上人的往來等,生活溝通僅限于疍民群體內部。清朝時期的疍民戶籍開始被列入普通戶籍,允許上岸居住,但依然是屬于社會的最底層,遭受歧視,生活苦不堪言。“男女朝夕跼蹐舟中,衣不蔽體。海濱貧民,此為最苦”[13]59,正是對疍民艱苦生活的形象描述。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疍民只好借用深情、哀怨的唱腔來道出心中的苦與樂,在歌中尋找一絲安慰,給予心靈寄托和精神力量。屈大均言粵歌:“歌則清婉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5]361這不正是疍民寄情于歌中而使之感動嗎?咸水歌傳唱除了娛樂和抒發情感外還充當著一種教育的功能,即疍民長者會采用咸水歌的演唱方式,將生活常識、生產勞作知識以及名人事跡等創作成歌詞進行傳唱教育,例如《梁山伯與祝英臺》《拆蔗寮》《猜魚》等咸水歌,將生活常識、歷史故事編入歌曲中進行傳唱教育。此外,該時期咸水歌在疍民風俗活動中也充當著重要的角色,幾乎貫穿著年輕人從戀愛到整個婚禮習俗的全過程,抑或是喪禮習俗的全過程。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也記載:“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歡樂。”[5]360-361因而,自唐朝以后,隨著疍民群體的不斷壯大及歷朝歷代的變遷,咸水歌演唱幾乎涉及疍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疍民無時無刻不在唱歌。“江河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滘。”[5]360“來航去舶,櫂歌相聞。”[22]隨時隨處可聽咸水歌歌聲。
3.繁榮階段
沙田疍民從呱呱墜地到咿呀饒舌再到長大成人,歷經了無數次的對歌、斗歌活動,無不受到咸水歌的熏陶,個個均能“爆肚”(水鄉話,意為有感而發、即興而唱)演唱咸水歌。筆者采訪曾任中山縣文藝宣傳隊副隊長,參與多首咸水歌記譜和創作的黃德堯先生時,他就說:“中山咸水歌歌手們大多都是無師自通的,因為他們長期浸淫在咸水歌的海洋中長大。而且咸水歌就這么幾首曲調,也不難學。”①采訪人:楊華麗。被采訪人:黃德堯。時間:2017年9月14日17:00-18:00。地點:南朗鎮翠亨村孫中山故居園。《中山市坦洲鎮志》中也記載了坦洲地區是“家家有歌,人人能歌。每逢節慶,疍民更是喜歡斗歌,一河兩岸的男女青年,自發地成群結隊隔河對歌,越斗人越多,越斗越興奮,很多時候由晚上斗到天亮也分不出勝負。”[10]709而正是人人能唱、人人能編,使得咸水歌發展至今是經過了歷代人的改編加工,在歷史進程中積累、沉淀、篩選的集體創作成果,其具體的創作者和創作年月無法確定,而且咸水歌都是口頭傳唱,因而沒有歌曲文本資料的保存。1949 年新中國成立,人民生活得到翻天覆地的改變,國家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進行土地改革、開展大辦夜校掃盲運動等措施,讓疍民的身份地位得以真正的提高,有了屬于自己的耕地,享受到受教育的權力,讓一些歌手可以拿起筆桿將這些傳統民歌記錄下來,更是能創作順應時代發展、歌唱中國共產黨、服務于黨的工作的新民歌,并將創作的民歌手抄本進行傳播。著名的中山咸水歌民歌手何福友、梁容勝、梁三妹等都是在該時期涌現出來的,創作演唱了《共產黨恩情長》 《歌唱唱到北京城》 《釣魚仔》 《送郎一條花手巾》等曲目,這些新編咸水歌也被傳唱至今。“新民歌的傳唱帶來了群眾性民歌創作熱潮,群眾自發在坦洲鎮各村都成立了民歌隊,例如著名歌手梁三妹所在的民歌隊稱為‘同勝民歌隊’,該民歌隊還自發的組織過水上民歌大巡游,乘艇游唱民歌。”[17]111民歌隊的活動熱潮、新民歌的傳唱、民歌手的推崇,也帶來了咸水歌的傳承學習新方式——師徒傳承。例如,“著名中山咸水歌民歌手何福友,其第二代傳承人鄭石、第三代傳承人吳志輝、第四代傳承人范容好均是通過師傳的方式學習民歌的。再如著名民歌手林梨嬌也是通過師傳的方式向梁三妹學唱咸水歌。”[2]1302從以往的家族傳承的方式中增加了師徒傳承的方式來向一些著名的民歌手學習新作品、新唱法。咸水歌在民間掀起了傳唱熱潮,同時也受到了政府和國家及音樂學界等的關注。1958 年大躍進時期,在中山市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開展整治白藤湖水利工程,期間政府組織誕生了第一個民歌合唱團,用疍民熟悉的音樂來調動民工的積極性,來進行宣傳工作。此外,“1956 年3 月和1960 年6月咸水歌曾兩度唱上北京城,分別是梁容勝在全國文學藝術界第三屆代表大會文藝匯演時演唱高堂歌《共產黨恩情長》和何福友參加全國文化、教育、體育、衛生工作群英會,在周恩來總理設的國宴上演唱的《歌唱唱到北京城》,該歌曲也刊登在《北京晚報》,受到推崇。1959 年,佛山師專的老師和學生開展民歌調查工作,于1961 年出版了一部油印本民歌集。1962 年,中國唱片公司廣州分公司灌錄了一輯傳統民歌專碟并于1962 年正式出版。”[2]140-143更有咸水歌民歌手進入廣州音樂專科學校(星海音樂學院前身)教授學生唱中山咸水歌。該時期可謂咸水歌的繁榮時期,它順應著時代的發展,在政治、商業、教育各領域的活動中發揮出重要的作用,也實現了對民歌的保存和宣傳擴散,受到國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當時整個中山市都飄蕩著咸水歌的曲調。
4.衰微階段
“1964 年‘四清’運動開始,中山咸水歌被列為‘宣傳封建迷信、低級趣味’的‘毒草’而遭受禁唱。1966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山咸水歌更是遭到了全面封殺,人們在婚禮、喪禮、開基、捕撈時這些一直以來伴隨著咸水歌演唱的習慣被限制,疍民不敢隨便再唱了。”[10]642城市街道還貼滿了批判咸水歌的大字報,到處有批判咸水歌的聲音。疍民已然不能隨心抒發自己的情感,不能再唱愛情、唱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給疍民帶來了嚴重的傷害,疍民回憶“文革”時便唱道:“打殺爭斗無盡頭,岸上煙火令人愁。人民生活心更揪,祈盼社會永無憂。”“百姓聞此心滴血,神州哀悼淚盈腔。切記‘文革’慘教訓,萬千草芥沐朝陽。”[23]36該時期疍民不敢再唱咸水歌,致使咸水歌失去了生存的土地,在廣闊的大沙田上,咸水歌就這樣消聲、沉寂了。
5.恢復階段
“1970 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等五首改編的陜北民歌,發起了民歌改革的信號。廣東音樂家協會趁此機會抓住時機,號召各地區做好民歌的挖掘、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山于1971 年初率先開展咸水歌唱腔改革嘗試,打破了咸水歌多年的沉寂。”[17]113廣東省音樂家協會召開廣州語系民歌改革、坦洲召開民歌手座談會等促進咸水歌民歌的改革工作。經過多名中山咸水歌民歌手、中山市文化館工作者陳錦昌、作曲家許樹堅等人組成民歌改革小組,從咸水歌的普查與搜集再到民歌唱腔改革,以“地方特色,歌種風格與時代氣息‘三結合’的方針,確定了‘唱腔改革不離格’的原則”[17]82對咸水歌進行改革,將傳統拖腔適當延伸,在拖腔中用象聲詞代稱謂詞以及豐富歌曲節奏、曲式,來使民歌更富有表現力,創作貼近現代人民生活的歌曲。經改革創作涌現出了一批經典的新編咸水歌,如《月下輕舟泛漁歌》(陳錦昌、何福友詞,許樹堅曲)《萬眾一心跟黨走》(陳錦昌、何福友詞,許樹堅、文石耳曲)《水鄉情》(陳錦昌詞,黃德堯曲)《千船萬艇爭上游》(何福友、陳錦昌詞,許樹堅曲)等。廣東人民廣播電臺還將這些新編咸水歌編入《農村文化室》《農村俱樂部》專欄節目中進行播放、推廣,讓各地歌手們模仿演唱。何福友和梁容勝還帶領著一班民歌新秀組成民歌改革宣傳隊,到全縣各地水鄉宣傳演出,舉辦民歌演唱培訓班,派發改革民歌曲本,與當地民歌手共同演唱表演等活動。此外,陳錦昌還將搜集到的高堂歌各種句式拖腔,包括傳統的、新腔及改革腔的匯集分類組合,編成《高堂歌各句式拖腔選編》提供大家學習。1978 年,新編咸水歌《新對花》(譚大霖曲)在中央電視臺節目播放。新編咸水歌的推廣讓中山地區咸水歌活動掀起了新高潮,各地水鄉成立民歌隊,“斗歌”活動再次出現。坦洲鎮政府還聯合舉辦了中山市大型的水上歌會活動、民眾鎮開發嶺南水鄉旅游項目,成立專職咸水歌表演隊等。1993 年11 月,出版發行中山第一張《中山民歌》CD 碟,2001 年,多首咸水歌還被收錄到《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廣東卷》中。自2002 年起,中山市東升鎮勝龍小學將咸水歌作為校本課程進行傳承教育,直至今日,中山市已成立6 所中山咸水歌傳承基地小學進行咸水歌教學。中山市開展一系列工作來搶救、保護和恢復咸水歌的傳唱,但如今的咸水歌聲音景觀已與原來不同了,它已不再滲透在疍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再是疍民隨時隨地張口即唱了,而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疍民集體娛樂方式和政府組織的群眾活動來呈現。
咸水歌作為疍民群體的民間口頭非物質文化,在歷史的變遷中,隨著疍民的遷移和政治文化背景的影響,不同時期在特定的地區形成特定的聲音景觀,呈現出了五個階段不同的聲音景觀。咸水歌是疍民歷代生活的縮影,通過咸水歌聲音景觀的研究和探討,也能反映出不同時期疍民的文化。
(二)空間——地域變遷的維度
謝勒梅在其著作中將“聲音景觀”定義為包括有特色的背景、聲音和意義,其中背景包含了“音樂地域環境”的概念在內,也就是聲音景觀特定時期的特定地域。“空間維度的流動變化以時間為前提;而時間維度的流動變化則體現為空間維度的流動變化。”[20]咸水歌聲音景觀在時間的流動變化過程中呈現了五個階段的不同,在特定時期中咸水歌聲音景觀的特定地域又是怎樣呈現出一種流動變化呢?
咸水歌聲音景觀的空間流動變化以時間為前提,主要可分為兩種,即清朝以前水上生活呈現的聲音景觀和清朝以后陸上生活呈現的聲音景觀。
1.水上空間
疍民自古越族人中一部分入江海生活成為疍民,到歷朝歷代因戰亂等原因被迫流入海洋生活的疍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海上,居住于狹小的舟船上,靠捕魚為生,居無定所,將自己的生產生活定格于江河湖海中,一輩子過著漂泊的生活,再加上其社會地位低下,遭受壓迫,不能接受教育,不能與陸上人通婚等歧視規定,使得疍民經常依靠咸水歌來抒發內心的情感和進行疍民之間的交流溝通。咸水歌的內容多為疍民來航去舶過程的所思所想,捕魚勞作的辛苦表達以及相互傳達訊息,傳達愛慕以及向往和憧憬,還有在節慶日和習俗活動中展現風采。樸實的言語,連綿婉轉的語調,真摯的情感正是咸水歌的價值所在,是疍民真實生活的體現和精神寄托。咸水歌長期以來是疍民有感而發、口頭傳唱,因而早期咸水歌較少有人進行記錄保存,僅能在少有的一些文獻資料中尋得蹤跡,如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和李調元的《粵東筆記》[24]均載有咸水歌:“清河綰髻春意鬧,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滘。”[5]360樸實直白的語言道出疍民江行水宿的生活,表現出了疍民女子的豪放,獨自搖舟前往情郎的船只行歡去。清代花溪逸士的《嶺南逸史》中載有:“云在水中非冐影,水流云動非冐情。云去水流兩自在,云何負水水何縈。”“撥棹珠江二十年,慣隨流水逐嬋娟。青蘋難種君莫種,煙雨堪憐君莫憐。”[25]等四首疍民戀愛演唱的疍歌。還有清代王士禛的《池北偶談》卷十六中輯錄疍歌三首,其中一首:“疍船起離三江口,只為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26],道出了疍民撒網捕魚的生產生活及情人水上結情的場景。廣州咸水歌非遺傳承人謝棣英也搜集了幾首民間傳唱的水上生活的咸水歌,如“小艇顛簸最無常,巨浪掀船頃刻殤。隔世難見親人面,狂風卷起甚凄涼。”“低矮小艇擠海林,岸人鄙視現悲音。不怨天來不怨地,永無寧日別恨心。”[23]31、109它道出了疍民生活于狹小的艇中,備受歧視的悲慘生活,同時更是表現了疍民積極樂觀的心態,不怨天不怨地,依靠咸水歌來抒發內心抑郁之情。咸水歌同時也作為疍民商業往來叫賣的工具,如賣艇仔粥的咸水歌(前文中已介紹),還有用來教育子女生活常識、禮儀的工具,如咸水歌《拆字歌》《猜魚名》等,更是伴隨習俗活動的重要載體,李調元的《粵東筆記》中記載了疍民婚嫁過程中要演唱攔門詩歌、高堂歌、打糖梅歌等。咸水歌是疍民搖櫓過江訴真情、民俗活動添氣氛、商業活動及教育的載體工具,伴隨著疍民的漂泊而飄蕩在江海湖面的各個角落,形成獨具風格的海上聲音景觀。
2.陸上空間
雍正七年頒布法令,允許疍民上岸居住,疍民陸續開始上岸居住了,告別了疍民獨特的以水為生、以舟為宅的生活方式,結束了漂泊、居無定所的生活,也開始有了自己的耕地,從事農業生產。這樣一種從水上空間到陸上空間的變化在他們演唱的歌曲中也得到了相應的體現,即從演唱反映水上的生活和心聲的歌曲轉變為反映岸上的生活和心聲的歌曲,如咸水歌唱道:“告別艇仔上岸住,新居新戶競風流。”[23]35疍民住所大致經歷了從水上艇到岸邊窩棚、水欄、茅草房、陸上平房到最后的樓房的過程。因受環境感知的影響,疍民們在選擇新居住地時依然選擇水資源豐富的水濱地帶,主要在珠江三角洲河網交錯的沙田地帶及粵西、廣西部分沿海地區。按照地域的不同,咸水歌可分成城市咸水歌、沙田咸水歌和濱海咸水歌等類型,各以廣州、中山、北海為代表,其中又以中山沙田地區的沙田咸水歌最具代表性。疍民群體的遷移過程也是一種文化遷移擴散,他們從水上到陸地的遷移,不僅保留有捕魚相關海上作業,還有了沙田農耕作業,這些也都反應在了他們的咸水歌中,歌中出現了大量的農耕生產內容的歌詞,例如古腔高堂歌《播種歌》:“二月開田去下秧,秧地行行長又方,被人推田被人下,撒落谷種標好秧。”[17]19中山沙田地區人們在生活中隨處演唱,農閑時搭臺對唱,均是疍民咸水歌演唱的演出場所。孫帝喬對中山地區的咸水歌傳唱寫過一段這樣的感慨:“香山(中山)凡有疍家人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有人唱咸水歌。出海打魚,灘頭織網,親朋相聚,男女嫁娶時各有含義,情調婉轉動聽的咸水歌為疍家人帶來了溫暖和歡樂。”[27]咸水歌在中山地區的文化擴散還體現了咸水歌與當地其他文化的融合,例如發源于中山五桂山的百口蓮山歌,采用客家話演唱咸水歌曲調而形成的歌種,還有發源于東鄉地區的東鄉民歌中也能找到一些咸水歌曲調的影子。這些非物質文化與咸水歌共同在中山地區形成獨特的聲音景觀,使得中山成為一個民歌之鄉。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文化大革命”政治因素的影響,如今的咸水歌聲音景觀較之以往的聲音景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海上生活的疍家人們演唱著他們獨特的風土人情和心聲的咸水歌,富有濃濃的咸水“味道”。而疍民上了岸,疍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思想的轉變及外來文化的沖擊,均使得傳唱咸水歌的意識逐漸淡薄了,咸水歌也失去了一些往昔的味道。廣東地區憑借著優越的地理位置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區域,經濟生活的快節奏和文化娛樂的多元化使得人們忽視了咸水歌的存在,年輕人對咸水歌不了解更談不上喜歡。再加上疍民傳統風俗的簡化、改變和消失,人們娛樂方式的選擇多樣化及教育的發展使得咸水歌的功能作用減弱,活動空間不斷減少;人們平時生活中越來越少唱了,突然唱起咸水歌反而成了一種非常態現象,正如梁建其在《中山坦洲咸水歌芻議》一文中描述的現象:“一些婦女反映,兒女都不喜歡咸水歌,他們一唱,就惹兒女們討厭,所以就索性不唱了。”[28]種種的原因致使咸水歌演唱的人越來越少,演唱的地點、時間越來越受限,咸水歌的傳承面臨著困境。值得慶幸的是有這么一批人關注到了中山咸水歌的傳承問題并開展了對中山咸水歌的搶救、保護和改革發展工作,也成功申報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項目,逐漸受到了中山市政府、音樂研究會、文化部門等機構的重視,開展了一系列對中山咸水歌的保護與傳承工作,如端午節、春節、中秋節等節日舉行的咸水歌比賽、展演等活動;在坦洲鎮、民眾鎮、小欖鎮等咸水歌發源地設立中山咸水歌傳承基地等。咸水歌的表演場地從廣闊的海面、沙田及疍民生活區中變成了一個個絢麗多彩的舞臺和校園音樂課堂。在舞臺上,人們穿起了漂亮的演出服、拿起了話筒、配上了音樂伴奏和舞蹈,呈現出一個個精心設計編排的咸水歌舞臺作品,還有在音樂課堂上學生歡快的齊唱著一首首傳統咸水歌和新編咸水歌等,顯然,這已不是以往那種樸實動人的真情流露和隨時隨地“爆肚”演唱的聲音景觀了。此時的咸水歌已然成為沒有“咸水”的咸水歌了。隨著文化地理環境的變化,原生態的咸水歌生存空間越來越窄。這一點應引起政府文化管理有關部門的關注,如何有效地保護和正宗性地傳承、發展咸水歌是當前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
咸水歌聲音景觀在歷史變遷和地域變遷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種動態的聲音景觀變化。任何時期的聲音景觀均是在一定的地域條件下形成的,與疍民所處的地理環境,包括社會人文環境有著直接的聯系。
三、結 語
經過探討可以看出,中山咸水歌在中山地區得以生存和發展與中山地區獨特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有著密切的關聯。從地理環境的角度上看,咸水歌的創作者和表演者疍民群體從古越族祖先開始到歷朝歷代的“新生代”疍民在長期生活環境下形成“親水”的環境感知,致使其最終選擇中山這樣水資源豐富、沙田面積廣闊的自然環境中落戶發展。江海惡劣的環境、卑微的身份地位以及獨特的傳統風俗、商業行為及其語言等的人文環境共同孕育了這一非物質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又因經歷了文化遷移,從江海浮蕩遷移至沙田地區,使得咸水歌這一非物質文化在中山地區得以很好的生存和發展。從咸水歌的聲音景觀角度上看,中山地區最突出、最有特色的傳統音樂文化是中山咸水歌,被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中山地區形成特有的聲音景觀。隨著歷史和地域空間的變遷,聲音景觀呈現出一種動態變化的樣態。在歷史變遷的維度中,中山咸水歌形成了萌芽、上升、繁榮、衰微、恢復五個階段的變化發展。以歷史變遷為前提下,在地域空間維度中形成清朝以前水上生活呈現的聲音景觀和清朝以后陸上生活呈現的不同聲音景觀。咸水歌在中山地區生存和發展過程中其演唱內容和曲目得到豐富發展,也實現了對咸水歌的記錄保存,同時還對咸水歌進行了適應時代發展的唱腔改革。由于文化地理環境的改變,中山咸水歌的傳承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好在中山市政府重視咸水歌的傳承工作,在多個咸水歌發源地設立了中山咸水歌傳承基地以及舉辦的一系列咸水歌活動,努力使中山咸水歌這一古老歌種得到保護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