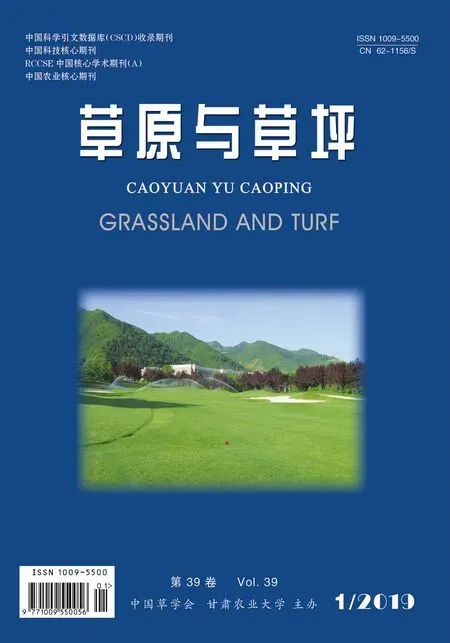模擬條件下藏羊、牦牛踐踏和降水對東祁連山高寒草甸地上植被生長的影響
潘濤濤,吳玉寶,徐長林,肖 紅,柴錦隆,魚小軍
(1.甘肅農業大學 草業學院/草業生態系統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甘肅省草業工程實驗室/中-美草地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甘肅 蘭州 730070; 2.甘肅定西市安定區香泉鎮,甘肅 定西 743015 )
祁連山地處青藏、蒙新、黃土三大高原交匯地帶,在維系西北高原氣候、水土保持、保障河西綠洲農業生產與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1-3]。高寒草甸作為該區的主要植被類型之一,不僅是當地最重要的畜牧業生產資料,還是影響周邊地區農業生產和生態安全的重要區域[4-5]。同時,牦牛和藏羊是分布在該區的重要畜種,是牧民財富的象征[6]。但其生態系統脆弱,抗干擾能力差,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下,該地區的生態系統正遭受不同程度的退化。如何提高高寒草甸牧草的產量和質量、實時合理地利用高寒草甸、修復和重建退化草甸等生產問題亟待解決。目前,已有學者對東祁連山高寒草甸牧草光合生理特征、植物抗寒性、不同退化程度及不同放牧管理模式下的植被與土壤方面做了很多研究[3-5,7-8]。
放牧普遍存在于東祁連山高寒草甸,并對高寒草甸退化產生正負反饋影響,是影響其生態系統健康與否的關鍵因子。放牧過程中家畜踐踏對草地的作用相對于家畜采食和排泄物而言,具有作用時間長、作用累加、影響草地組分及效果的特點,對草地植被、土壤的影響更為全面深刻,在草地退化和健康維護中起主導作用[9]。此外,陸晴等[10]對青藏高原1982~2013年高寒草地覆蓋時空變化及其對氣象因素響應的研究表明,降水是青藏高原東北部地區高寒草地植被生長狀況的主導因子。因此,從影響高寒草地植被生長的干擾分析,降水和放牧家畜踐踏是影響高寒草地植被生長最為敏感的2個因素。目前,已有降水和家畜踐踏復合作用下對天然草地生態系統的相關報道,但主要集中于草地土壤對二者不同梯度組合方式響應機制的研究[11-14],而草地植被生長狀況對家畜踐踏的反應并與水分之間的關系尚不明確。因此,于祁連山東段天祝高寒草甸,通過測定模擬不同強度藏羊、牦牛踐踏和不同降水梯度雙因子作用下草甸地上植被的群落高度、生殖枝數及生物量變化,探索高寒草甸植被生長狀況對模擬降水和踐踏的響應機制,闡明藏羊、牦牛踐踏對其分異影響的過程,以期為退化高寒草甸的修復及天然草地的健康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概況
試驗地位于甘肅省天祝縣抓喜秀龍鄉——甘肅農業大學天祝高山草原試驗站,地理位置N 37°40′,E 102°32′,屬高寒草甸,海拔2 960 m,氣候寒冷潮濕,屬大陸性高原季風氣候,晝夜溫差大,日照強烈,水熱同期,僅分冷熱兩季,無絕對無霜期。年均溫-0.1℃,1月最冷(均溫-18.3℃),7月份最熱(均溫12.7℃),>0℃的年積溫1 380℃;年均降水量416 mm,多為地形雨,且集中在生長期6~9月;2015、2016年年降水量分別為418.8 mm、510.1 mm(圖1);年蒸發量1 590 mm,約為年降水量的4倍;土壤類型為亞高山草甸土,土層厚度40~80 cm,土壤pH為7.26~7.38[15]。試驗區主要植被類型為嵩草草甸,群落建群種為矮生嵩草(Kobresiahumilis),優勢種為垂穗披堿草(Elymusnutans)、陰山扁蓿豆(Medicagorutheniavar.inschanica)、冷地早熟禾(Poacrymophila)、西北針茅(Stipasareptana),常見的伴生種為賴草(Leymussecalinus)、洽草(Koeleriacristata)、鵝絨委陵菜(Potentillaanserina)、高原毛茛(Ranunculusbrotherusii)、秦艽(Gentianamacrophylla)、球花蒿(Artemisiasmithii)、車前(Plantagodepressa)、蒲公英(Taraxacummongolicum)、高山紫菀(Asteralpinus)等。

圖1 試驗區月均降水量Fig.1 The monthly average precipitation at experimental site
1.2 試驗設計
選擇植被均勻、基況基本一致的天然草地(該草地夏季長期進行劃區輪牧,利用率65%~75%,放牧家畜為甘肅高山細毛羊),用鐵絲網和水泥柱圍封作為試驗區。采用雙因子裂區設計,以踐踏為主因子,降水為副因子。主區為4個水平模擬降水處理,副區為4個強度模擬踐踏處理,主副區完全隨機排列,3次重復,主區間間距為0.7 m,副區間間距為0.5 m,各踐踏小區面積為1 m×2 m[16]。
主區處理:根據天祝高寒草地不同年份6~9月每月平均降水量的實際情況(分別為70、88、87 mm和64 mm)[17-18],共設置缺水(LLP)、平水(ALP)、豐水(HLP)和自然狀況4種情況;其中,前3個水分處理每月設計量依次為40,70和110 mm,并采用活動雨棚在降水來臨前遮住自然降水,自然狀況不做控制。模擬降水于2015、2016年每年的6~9月進行,每月的降水量分10次實施,每3 d實施1次,具體噴施措施參照林慧龍[13]的方法。
副區處理:根據楊海磊等[19]在天祝縣抓喜秀龍鄉代乾村輕、中和重度放牧區開展的夏季輪牧試驗,每天8 h牦牛和藏羊行走和采食步數的統計結果換算出各試驗小區模擬踐踏的步數(藏羊輕、中、重度踐踏步數依次為27,47和67步,牦牛踐踏步數依次為36,60和80步)。設置對照不踐踏(CK)、藏羊輕度踐踏(TSLT)、藏羊中度踐踏(TSMT)、藏羊重度踐踏(TSHT)、牦牛輕度踐踏(YLT)、牦牛中度踐踏(YMT)、牦牛重度踐踏(YHT)處理。每副區在放牧季共實施3期踐踏處理,分別于2015、2016年每年6~8月的每月21~30日通過人穿自制的模擬踐踏器行走依次完成,模擬藏羊和牦牛踐踏人的體重分別為45 kg和60 kg,這與體重45 kg的藏羊和180 kg的牦牛放牧時對草地的真實踐踏效果相同[16]。
1.3 測定指標與方法
1.3.1 群落高度的測定 每期踐踏處理完,于每小區中隨機選取50 cm×50 cm的樣方3個,用卷尺測定樣方內所有植物的自然高度。群落高度為各植物高度求平均值而得。
1.3.2 總生殖枝密度及生殖枝死亡數的測定 每期踐踏處理完,在每小區中隨機選取50 cm×50 cm的樣方,計數該樣方內所有植物存活的生殖枝總數、由踐踏導致枯死的生殖枝總數,計算單位面積生殖枝數和生殖枝死亡數。3次重復。
1.3.3 地上生物量的測定 第1期模擬踐踏處理完后,在各試驗小區按對角線法隨機選取3個50 cm×50 cm的樣方,樣方內植物齊地面刈割裝入樣品袋帶回實驗室,在105℃的烘箱中殺青1 h,然后65℃下烘干至恒重,稱其質量。
1.4 數據統計與分析
用平均值和標準誤表示測定結果,采用SPSS 19.0統計軟件對所測數據統計分析,分別對同一踐踏強度不同水分處理、同一水分條件不同踐踏強度處理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并用Duncan法對各測定數據進行多重比較。采用Microsoft Excel 2007軟件繪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水分條件和踐踏對群落高度的影響
2015、2016年群落高度變化趨勢基本相同,同期模擬降水和踐踏處理下群落高度均隨水分的減少、踐踏強度的增加呈下降趨勢。同一水分處理下,相同踐踏強度藏羊踐踏處理的群落高度高于牦牛踐踏處理,且均顯著低于對照(P<0.05)。試驗第1年,第1期處理后,各水分處理之間群落高度差異不顯著(P>0.05);第3期踐踏結束后,各水分處理下不同強度牦牛踐踏后的群落高度對比相應藏羊踐踏結果無顯著差異(P>0.05)。試驗的第2年,各期踐踏處理后,豐水條件下各踐踏區的群落高度均顯著高于缺水處理(P<0.05),第3期踐踏結束后,缺水和豐水處理下各藏羊踐踏處理的群落高度均顯著高于相應牦牛踐踏處理(P<0.05);與對照相比,缺水條件下,TSLT,TSMT和TSHT下群落高度分別降低56.11%,67.78%和73.89%,YLT,YMT和YHT下群落高度分別降低65.00%,74.44%和81.67%(表1)。
自然降水條件下,同期試驗中兩年的群落高度均隨藏羊和牦牛踐踏強度的增加依次降低,且同一踐踏強度下藏羊踐踏處理的群落高度均高于牦牛踐踏處理(圖2)。相比對照,2015年TSLT,TSMT和TSHT下群落高度分別降低79.09%、84.38%和89.42%,YLT,YMT和YHT下群落高度分別降低79.81%,85.10%和90.38%;2016年藏羊踐踏的分別降低58.06%,68.28%和73.66%,而牦牛踐踏分別降低64.52%,72.04%和78.49%。

圖2 自然降水下各踐踏區群落高度Fig.2 The community height in different trampling treatments under natural precipitation注:不同小寫字母表示踐踏強度間差異顯著(P<0.05),下同

表1 模擬降水和踐踏下群落高度
注:同行不同大寫字母表示同一踐踏強度下不同水分處理間差異顯著(P<0.05),同列不同小寫字母表示同一水分處理下不同踐踏強度間差異顯著(P<0.05)。下同
2.2 不同水分條件和踐踏對總生殖枝密度的影響
2015、2016年同期模擬降水和踐踏下總生殖枝密度均隨水分的減少、踐踏強度的增加逐漸下降,同一強度藏羊踐踏處理下的總生殖枝密度均高于牦牛踐踏處理;兩年中第2期和第3期同一水分處理下各踐踏區總生殖枝密度均顯著低于對照區(P<0.05)。第3期踐踏結束后,第1年缺水和平水條件下,相同強度藏羊踐踏區生殖枝數與牦牛踐踏區無顯著差異(P>0.05),豐水條件下TSHT區總生殖枝密度顯著高于YHT(P<0.05);第2年缺水條件下TSLT總生殖枝密度顯著的高于YLT(P<0.05),平水和豐水條件下藏羊各踐踏處理的生殖枝數均顯著高于牦牛踐踏處理(P<0.05)。試驗缺水處理下重度踐踏區的生殖枝數最少,TSHT和YHT較對照第1年下降了71.85%、76.28%,第2年降低了67.53%、68.41%(表2)。
自然降水條件下,同期試驗中兩年的總生殖枝密度均隨踐踏強度的增加呈下降趨勢(圖3)(P<0.05)。相同強度藏羊踐踏處理區的總生殖枝密度高于牦牛踐踏處理。第3期處理結束后,2015年相同強度藏羊踐踏區的生殖枝數與牦牛踐踏區差異均不顯著(P>0.05),2016年僅TSHT 顯著高于YHT(P<0.05);與對照組相比,2015年TSHT和YHT下總生殖枝密度依次降低73.77%、77.63%,2016年兩者依次降低62.69%、73.94%。
2.3 不同水分和踐踏對植物生殖枝死亡數的影響
2015、2016年同期處理下植物生殖枝死亡數隨模擬降水的減少、踐踏強度的增加總體呈上升趨勢,各踐踏處理的生殖枝死亡數顯著高于對照(P<0.05),且相同強度藏羊踐踏高于牦牛踐踏。第3期處理結束后,第1年缺水處理下TSMT和TSHT下生殖枝死亡數分別顯著低于YMT 和YHT(P<0.05),第2年僅豐水處理下TSLT顯著低于YLT(P<0.05);兩年各踐踏區生殖枝死亡數均在缺水條件下達到最高,與對照相比,第1年TSLT、TSMT、TSHT、YLT、YMT、YHT分別上升3.8倍、5.8倍、8.0倍、4.7倍、7.3倍、9.2倍,第2年TSLT、TSMT、TSHT、YLT、YMT、YHT分別上升3.0倍、3.6倍、5.2倍、3.4倍、4.2倍、5.6倍。

圖3 自然降水下各踐踏區總生殖枝密度Fig.3 The density of total reproductive branches in different trampling treatments under natural precipitation

2

表3 模擬降水和踐踏下生殖枝死亡數
自然降水條件下,兩年同期處理下植物生殖枝死亡數隨踐踏強度的增加逐漸升高,且各踐踏區顯著高于對照(P<0.05);隨著處理期數的增加生殖枝死亡數也不斷上升(表4)。同一強度藏羊踐踏處理的生殖枝死亡數低于牦牛踐踏處理。第3期處理結束后,重度踐踏區兩年的生殖枝死亡數均最高,其中2016年TSHT處理顯著低于YHT處理(P<0.05);與對照相比,2015年TSHT和YHT下生殖枝死亡數分別上升8.3倍、8.8倍,2016年TSHT和YHT分別上升6.0倍、7.3倍。

表4 自然降水下各踐踏區生殖枝死亡數
2.4 不同水分條件和踐踏對地上生物量的影響
兩年模擬降水和踐踏處理下地上生物量均隨水分的減少、踐踏強度的增加逐漸降低,且各踐踏處理均顯著低于對照(P<0.05);相同強度藏羊踐踏區的地上生物量高于牦牛踐踏區;同一踐踏強度下,缺水處理的地上生物量顯著低于豐水處理(P<0.05)。缺水和豐水條件下TSMT和TSHT區兩年的地上生物量均顯著高于YMT和YHT(P<0.05),平水條件下同一強度藏羊踐踏處理兩年的地上生物量均顯著高于牦牛踐踏處理(P<0.05)(表5)。

表5 模擬降水和踐踏下地上生物量
自然降水條件下,試驗兩年的地上生物量均隨踐踏強度的增大呈直線下降趨勢(圖4),且各踐踏處理顯著低于對照(P<0.05);同一強度藏羊踐踏處理的地上生物量較牦牛踐踏處理高,且2015年TSHT下地上生物量顯著高于YHT(P<0.05)。

圖4 自然降水下各踐踏區地上生物量Fig.4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in different trampling treatments under natural precipitation
3 討論
放牧是高寒草甸的首要干擾方式,在此過程中踐踏作為最主要的行為方式影響著草地,且不同的踐踏強度及家畜種類對草地的影響存在一定差異[8,18-19]。試驗表明,隨著藏羊和牦牛踐踏強度的增加,輕、中及重度踐踏區草甸植被地上生物量逐漸下降且均顯著低于未踐踏區。說明家畜的踐踏不利于草地植被生長,且隨踐踏強度的增加抑制程度愈加明顯。可能是由于家畜踐踏首先導致草地植物的機械損傷,傷害植物正常組織和形態,抑制其生長,并導致草地冠層內部光、水、熱狀況等資源的再分配,引起冠層微氣候變化,進而影響草地植被生長發育及生殖分配[20]。柴錦隆等[12,21]對試驗各樣區土壤物理特性的研究表明,家畜踐踏對草地土壤的壓實效隨踐踏強度的增加愈加顯著,致使草地土壤的通氣導水性能降低,這種土壤特性的改變也是造成地上植被生長受到抑制的原因。這也反映出家畜踐踏過程中,草、土、畜是一個有機整體,他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降水量變異也是影響高寒草甸植被生長的主要限制因子之一。徐滿厚等[22]研究報道,適當的降水可極顯著促進高寒草甸植被生長。苗福泓[16]發現高降水量年份的高寒草甸群落高度和地上生物量均優于降水低的年份。試驗也得出相似的結果,未踐踏區,隨著模擬降水量的增加,高寒草甸植被生長指標呈現不同程度的優化趨勢。輕、中及重度踐踏區隨著水分的加大,家畜踐踏對植被生長的抑制作用不斷減弱,且充足的水分條件顯著緩解了踐踏對植被生長的抑制,說明降水量可調節家畜踐踏對植被生長的抑制程度。此外,試驗第1年,踐踏區群落高度和總生殖枝密度隨踐踏期數的增加均直線下降,次年這兩項指標均先升后降。是由于第1年家畜踐踏加速草地凋落物破碎、促進其分解、改善土壤肥力如加速了凋落物中碳、氮的釋放,在第2年生長季時一定程度地滿足了植物各物種生長所需養分的需求。
研究還表明,相同強度牦牛踐踏對植被生長的抑制作用大于藏羊踐踏。同時,柴錦隆等[12,21]的測定分析表明,同等踐踏強度下牦牛踐踏對土壤的壓實效應高于藏羊。將二者結合起來可充分解釋分別只放牧牦牛和藏羊對草地植被-土壤生態系統造成的分異影響。魚小軍[23]的研究結果表明,與單純放牧牦牛的草地相比,單純放牧綿羊更有益于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健康發展,并提出“多綿羊少牦牛”高寒草地放牧畜牧業經營管理模式,此次試驗為這一模式提供了又一例證。
4 結論
降水和家畜踐踏兩個干擾因素都是影響高寒草甸植被生長狀況的關鍵因素。水分的增大在一定程度能夠促進高寒草甸植被生長。在受不同強度的模擬降水和踐踏干擾后,各試驗樣區植被生長狀況的響應程度不同。隨著踐踏強度增加,植被生長受到的抑制作用加大;水分對這種抑制作用有調節作用,充足水分條件下顯著緩解踐踏對植被生長的抑制程度。牦牛踐踏對高寒草甸植被生長的抑制作用大于藏羊踐踏。因此,在高寒草甸放牧過程中應結合當地降水量實際情況,適當增加藏羊比例減少牦牛的比例,制定切實可行的放牧管理區劃方案,進而實現該區及相似區域草地的健康管理與永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