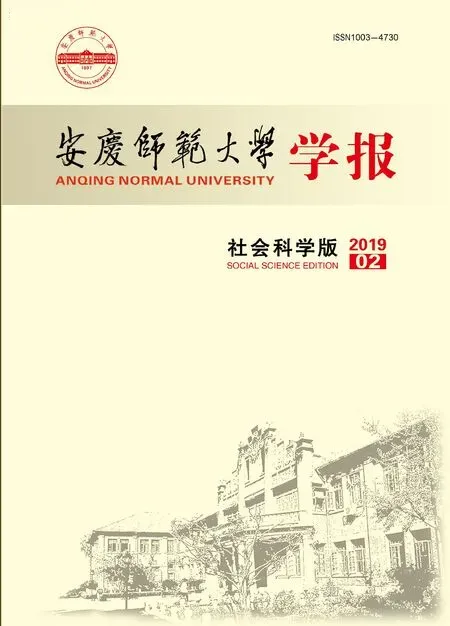近十年來“新革命史”理論研究評述
王 衛(wèi)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100089)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發(fā)展的永恒主題,也是社會發(fā)展、實踐深化、歷史前進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及時研究、提出、運用新思想、新理念、新辦法,理論就會蒼白無力,哲學社會科學就會‘肌無力’。”[1]如果說傳統(tǒng)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導致了中國革命史研究的“肌無力”,那么“新革命史”理論則為改變這一狀況帶來了勃勃生機,它將突破以往的革命史研究局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歷史進程提供一個新的解釋構架,從而實現(xiàn)歷史研究的新突破[2]。因此,本文認為,對“新革命史”理論及其建構作一番歷史的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一、傳統(tǒng)革命史范式的理論困境
范文瀾曾說:“歷史的骨干是階級斗爭,現(xiàn)代革命史就是現(xiàn)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現(xiàn)代史的劃分基本上與革命史是一致的。”胡繩也曾指出:“把人民的革命斗爭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nèi)容,就能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近代史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現(xiàn)象。”[3]由于具有極強的解釋力和理論指導功能,以革命為基本線索,將中國近代史歸納為“八大事件”“三次高潮”的革命史觀,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一直占據(jù)著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范式的主導支配地位。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大背景下,傳統(tǒng)革命史觀一家獨大的局面開始松動。1979年,汪熙發(fā)表了《論晚清的官督商辦》,從現(xiàn)代化視角重新估量洋務運動、官督商辦,重估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外國資本,由此開啟了近代史研究的新篇章。之后,黎澍發(fā)表的《1979年的中國歷史學》直接對革命史觀進行質(zhì)問:中國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這個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亂。陳旭麓則最先提出在革命敘事之外,還應注意現(xiàn)代化敘事。1980年,李時岳發(fā)表《從洋務、維新到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一文,系統(tǒng)清理過去幾十年非歷史主義對近代中國的誤讀,并提出了中國近代史演變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四階段”論。
胡繩作為革命史范式的構筑者之一,他在晚年對革命敘事方式也進行了反思。他說,長時期流行的革命敘事一家獨尊,具有孤單感,也確實存在許多不周詳不嚴密的地方;革命敘事將許多問題推向了極端,因而其價值不得不打一個折扣。過去很多年無條件頌揚革命,貶低改良,可能是不對的,至少是不完整的,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歷史,是非歷史主義[4]。
對革命史范式更直接有力的沖擊應來自于現(xiàn)代化范式的倡行。“現(xiàn)代化范式以現(xiàn)代化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以現(xiàn)代生產(chǎn)力、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綜合標志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給予新的客觀定位。”[5]依據(jù)羅榮渠的主張,現(xiàn)代化范式的目標——就是以現(xiàn)代化取代革命化,走出革命范式的“危機”。20世紀90年代,兩種范式還發(fā)生過一場激烈的論爭,雖然革命史范式的主導地位在形式上一直未受到怎樣的撼動,但是在學術研究領域,現(xiàn)代化范式還是逐步取得了事實上的統(tǒng)治地位[6]。
面對革命史范式的式微及其從學術版圖“中心”退向“邊緣”的理論困境,部分學者試圖尋求新的理論突破。1991年著名黨史學者張靜如號召“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希望黨史研究者“利用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史研究的成果,從社會生活諸方面進行分析,找出形成某個重大歷史現(xiàn)象的復雜的綜合的原因,并描述其產(chǎn)生的影響在社會生活諸領域的反映。”[7]在學術實踐上,雖然魏宏運《華北抗日根據(jù)地史》、謝忠厚《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史》、張國祥《晉綏革命根據(jù)地史》、齊武《晉冀魯豫邊區(qū)史》等論著從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變遷角度對根據(jù)地、解放區(qū)進行了側(cè)重性研究,但迄今大多數(shù)學者的研究沒有超出上述論著的水平,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思維陳舊的簡單化傾向,即沿襲著革命歷史書寫的傳統(tǒng)革命范式,更準確地說是黨派史觀的范式。而從社會史、文化史等視角下的研究亦呈現(xiàn)出了“碎化”的趨勢,有的甚至一味追新獵奇,完全失去了歷史研究的嚴肅態(tài)度[2]。
革命史觀何去何從,理論方法如何突破,范式轉(zhuǎn)換問題亟待解決。
二、“新革命史”的提出及其理論主張
近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又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如果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革命史的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革命史觀(1949年后的30年間)、去革命史觀(1980年后的近30年間)、重構革命史(2010年以來重新審視中國革命)”[8],那么,可以說“新革命史”是“重構革命史”階段的重要理論標志和研究趨向。
南開大學的李金錚教授是“新革命史”的最早倡導者。2010年,他發(fā)表《向“新革命史”轉(zhuǎn)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一文,提出了“新革命史”這一概念,強調(diào)革命史研究真正突破的關鍵在于研究思維的轉(zhuǎn)換和研究視角的創(chuàng)新[9]。2014年李金錚教授出版了《傳統(tǒng)與變遷——近代華北鄉(xiāng)村的經(jīng)濟與社會》(人民出版社)一書,該書將“新革命史”的理論方法系統(tǒng)地滲透進了具體的實踐研究中,并初步建構了“新革命史”的理論框架。2016年,李金錚教授發(fā)表了《再議“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一文,對“新革命史”理論的緣起、概念、方法以及其與傳統(tǒng)革命史范式的關系作了整體性的闡釋①事實上,早在2008年李金錚教授就已提出了“新革命史”的概念。2008年10月山西大學召開“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李金錚以《向“新革命史”轉(zhuǎn)型——國家與社會視野下的中共革命史研究》為題向會議提交了論文,首次提出了“新革命史”的概念。而2010年《向“新革命史”轉(zhuǎn)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一文的公開發(fā)表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和廣泛關注,故學界認為“新革命史”概念是2010年提出的。。
李金錚認為,由于長期以來的極端研究范式嚴重削弱了革命史研究的學術性,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蓬勃發(fā)展將中國歷史學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對中國現(xiàn)代化道路的歷史探討,由此導致了中國革命史研究備受冷落。但是,我們“無法也不可能告別革命史研究”,因為研究中共革命史對于清晰地理解中國近現(xiàn)代史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軌跡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可為人類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體實證和理論貢獻。因此,“不僅不能夠削弱中國革命史研究,而是應該重提革命史,并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但是如何邁出傳統(tǒng)革命史學之門,揚棄并超越,那就是向“新革命史”轉(zhuǎn)向。“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過程與互動:運用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理論。李金錚指出,傳統(tǒng)的革命史觀是“政策——效果”的“兩頭”模式或者“三部曲”思維,即政策制定、執(zhí)行,民眾接受、獲益,最終革命效果顯著。這一模式顯然忽視了革命(或政策貫徹落實)的重要過程,革命的艱難、曲折、復雜性被簡單化了。因此,要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視角來還原和反映中共革命與鄉(xiāng)村社會、農(nóng)民群眾之間的復雜關系。李金錚強調(diào),這種互動是自上而下的政權權力與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的排斥、融合、轉(zhuǎn)換的關系。如在考察鄉(xiāng)村社會轉(zhuǎn)型時,不僅要重視各種理論、學說、解決鄉(xiāng)村問題的相關路線、方針、政策,而且更要重視它們是如何落實于鄉(xiāng)村社會實際的,如何在鄉(xiāng)村社會中被接受、消融、轉(zhuǎn)化的。
基層與個體:強調(diào)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主體性。李金錚指出,傳統(tǒng)史觀注重宏大敘事和反映歷史的必然性,革命史敘事中很少關注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因此,“新革命史”研究要站在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立場進行深入挖掘,并突出其主體性和能動性;“新革命史”要求從人性視角、從人的情感和需求出發(fā),來考察革命的歷史進程。李金錚以解放戰(zhàn)爭時期解放區(qū)的農(nóng)民參軍為例,指出如果以傳統(tǒng)革命史觀認為的土地改革與農(nóng)民參軍之間有著緊密的必然聯(lián)系,那么解放區(qū)征兵與農(nóng)民參軍應該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但是如果從農(nóng)民個體和人性的視角來看,則不難發(fā)現(xiàn)不同個體參軍的動機絕非鐵板一塊,發(fā)動農(nóng)民參軍談何容易,而“理”“利”“力”的合力,才是促使農(nóng)民參軍的真相。
長鏡頭:革命史與大鄉(xiāng)村史相結(jié)合。李金錚認為,傳統(tǒng)革命史觀對中共革命之前的鄉(xiāng)村史——傳統(tǒng)鄉(xiāng)村缺乏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的理論、實踐與傳統(tǒng)鄉(xiāng)村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分不開的,但革命史觀只就革命史論革命史、就黨史論黨史,缺少縱向的時間維度或者歷史的慣性和連續(xù)性。因此,中共革命應被納入到大鄉(xiāng)村史的視野中來考察。所謂大鄉(xiāng)村史,就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與革命鄉(xiāng)村的結(jié)合;而大鄉(xiāng)村史視野下,革命與傳統(tǒng)在鄉(xiāng)村中的互動關系和過程是被著重強調(diào)的。李金錚以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中共民間借貸問題為例,指出:在以往革命史的表述下,根據(jù)地和解放區(qū)的減息、廢貸政策似乎是一以貫之、所向披靡的。但實際上,由于革命之前的舊有借貸關系在鄉(xiāng)村中的傳統(tǒng)慣性,中共借貸政策經(jīng)歷了一個從群眾歡呼雀躍到不滿、拒斥,再到中共政策調(diào)整與政策被認同的復雜過程,而這一過程所體現(xiàn)出的就是革命農(nóng)村與傳統(tǒng)農(nóng)村之間的張力與調(diào)適,就是革命過程在大鄉(xiāng)村視野下的生動呈現(xiàn)。
大視野:以全球視野考察中共革命。李金錚指出,傳統(tǒng)革命史中除了部分學者主要關注中共與共產(chǎn)國際、蘇聯(lián)之間的關系外,對于中共革命與其他國家、地區(qū)之間的關系互動及對中外革命的比較研究幾乎還是空白。但是,中共革命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共革命是屬于全球落后地區(qū)乃至整個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個典范。因此,要立足于全球視野,從外部對中共革命進行考察。要考察蘇聯(lián)、日本、歐美、朝鮮、越南、東南亞地區(qū)與中國革命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相互影響。同時,還要對中共革命與這些國家、地區(qū)的革命進行比較,從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中共革命的獨特性與典范性。
新視點:開拓新的研究視點。李金錚指出,傳統(tǒng)革命史觀所關注的主要集中于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等方面,這不利于解釋中共革命的豐富面向。因此,他提出要從話語、符號、象征、形象、想象、認同、身份、記憶、心態(tài)、時間、空間、儀式、生態(tài)、日常生活、慣習、節(jié)日、身體、服飾、影像、閱讀等角度,增加對中共革命史的分析,“這必將是今后革命史研究中非常令人興奮和期待的視域。”[10]
從以上幾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李金錚“新革命史”之所以“新”,就在于其視角與方法上的新,而從列舉的研究范例來看,他所倡導的“新革命史”最主要的一個特征就是對革命過程中的內(nèi)部張力——各因素之間的矛盾、互溶、轉(zhuǎn)化及其過程的強調(diào),這是對傳統(tǒng)革命史自上而下和社會史自下而上單向分析的最精彩的超越。
李金錚教授提出“新革命史”后,在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很多學者作出了回應或肯定認同。如黃正林認為,李金錚的“新革命史”觀為傳統(tǒng)革命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中共革命史研究處于兩難的境遇下,‘新革命史’的提出,不僅是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而且有助于進一步深化中共革命史的研究。”[11]常利兵指出:“李金錚在方法論層面提出了向新革命史轉(zhuǎn)型的突破,并提醒研究者要警惕濫用社會史方法導致的‘碎片化’現(xiàn)象,這是極具借鑒意義的。”[8]把增強認為,“新革命史”理念是李金錚汲取傳統(tǒng)革命史研究合理內(nèi)核基礎上,對中共革命史理論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能夠解決中共革命史研究中的諸多難題。”但同時,把增強也提出,就“新革命史”研究理念的提出和實踐來看,仍有待于進一步推進和完善,比如,對于中國革命的艱難性和復雜性,除從鄉(xiāng)村社會史層面反映,有無其他視角;如何構建多元化的研究路徑全面解決中共革命史的全部內(nèi)容[12]。
朱文通作了較為全面的評價,他說:面對中共黨史學理論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在大多數(shù)學者視為畏途而回避時,李金錚“提出并成功運用‘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引領‘新革命史’研究范式悄然興起。”他還率先垂范,率領眾多弟子一起致力于新革命史研究領域的探索,“儼然成為新革命史派的領軍人物”。朱文通指出,“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可以說就是唯物史觀理論和中共黨史、革命史研究的‘中介理論體系’之一”,它高度重視實證研究,同時運用互動理論,“依據(jù)矛盾著的事物是螺旋式上升、發(fā)展的原理,深刻地揭示其間的多層次的反復的互動關系,以及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復雜性。”朱文通贊同道:“在學科建設上,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可謂獨樹一幟,這不僅是一種學術自覺,而且還是學術自信轉(zhuǎn)化為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13]
三、學界的理論共識及研究趨向
在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范式普遍進行省思并嘗試建構替代性新范式時,“新革命史”的主張無疑在很多學者中形成了理論共識。如夏明方教授,“他站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立場上,主張超越革命與現(xiàn)代化范式,放棄目的論的預設,重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新革命史范式”[6],并提出了八個方面的構想:一是研究時限的“歷史化”。即將歷史時期的劃分與歷史視野的貫通結(jié)合起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探討和解決歷史的連續(xù)與斷裂問題。二是研究空間的“全球化”。即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史觀,把中國放在世界文明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考察。三是研究對象的“生態(tài)化”。從人的全面發(fā)展為目標的生態(tài)史觀,來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并進而重新審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四是研究主體的多元化。改變以往的兩極化思維模式,對傳統(tǒng)、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等各類問題進行多重反思。五是歷史哲學的“復雜化”。以復雜性理論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分析方法為主導的新辯證史觀,對一系列與史學研究密不可分的重大哲學問題進行再思考。六是研究目標的“相對性”,即相對真理與視閾交融為中心的敘事史觀。七是歷史資源的數(shù)據(jù)化,即通過史料發(fā)掘、整理、利用和現(xiàn)代信息技術的結(jié)合,促進歷史資源的生產(chǎn)、積累與共享,實現(xiàn)資源利用效應最大化。八是“開放史觀”,即超越本土與西學之爭,學習、借鑒一切外來理論與方法,砥礪之、轉(zhuǎn)換之。夏明方是站在一種“建設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立場上提出“新革命史范式”的,他認為革命史、現(xiàn)代化、后現(xiàn)代化三種范式都有局限,所以三者應當結(jié)合形成“新革命史范式”[14]。
王奇生的個案研究和理論方法也體現(xiàn)出了構建革命史研究的新視角。他提出,革命史研究,一是應將革命過程中形成的理論、話語、邏輯、價值本身,也作為研究的對象;二是將革命放回到20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經(jīng)濟文化變遷的大背景下考察,將革命的主體、客體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歷史場域中探討;三是在“求真”的基礎上進一步“求解”,除了過程描述更應進一步探尋革命的原理、機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
應星則從社會學研究的歷史轉(zhuǎn)向上,將中共革命史納入到社會學研究視野中。他指出,以往革命史的研究是從一極滑向另一極,而且地域社會史和革命史研究沒有得到很好對接,黨史研究和史學被分割開來。因此,從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意識切入:“需要思考中國共產(chǎn)黨獨特的政治支配性結(jié)構、精神氣質(zhì)是如何形成的,這種結(jié)構和氣質(zhì)與中國傳統(tǒng)文明是如何發(fā)生互動關系的,這種互動又是如何影響中國革命實踐的”,以及“如何著眼于從歷史的源流和傳承來分析在各種思潮風波中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文明的形態(tài)。”在研究方法上,他強調(diào):一方面要下決心做“灰暗的、細致的、耐心的文獻工作”,要舍得坐冷板凳、花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奠基在歷史研究基礎上的社會學想象力,可望給革命研究帶來一種新的沖擊力”,因此,要把社會學的思維與史學實證結(jié)合起來[15]。
在對新的理論范式進行探討和思索的同時,有的學者直接將“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運用到了具體的學術實踐研究中。如前文提到李金錚的《傳統(tǒng)與變遷:近代華北鄉(xiāng)村的經(jīng)濟與社會》(人民出版社2014年)、王奇生的《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黃道炫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qū)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肖紅松的《中共政權治理煙毒問題研究:以1937—1949年華北鄉(xiāng)村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按照李金錚的說法,“何高潮的《地主、農(nóng)民、共產(chǎn)黨:社會博弈論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臺灣學者黃金麟的《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丸田孝志的《革命的儀禮——中國共產(chǎn)黨根據(jù)地的政治動員與民俗》(日本汲古書院2013年版)、齊小林的《當兵:華北根據(jù)地農(nóng)民如何走向戰(zhàn)場》(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著作也都可被納入到“新革命史”的范疇內(nèi)。另外,帶有“新革命史”意味的學術論文也不乏陳例。很顯然,在革命史研究逐漸回暖的情況下,“新革命史”已經(jīng)成為一個具有很大學術潛力的研究方向[6]。
四、結(jié)語
夏明方說,對于“新革命史”的研究,“是否可以稱之為中國史界的新革命?至少在我看來,三十年來各路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正是這一新革命潮流當然的組成部分”。庫恩認為,“只有大量的證據(jù)表明,許多重要問題都不能在現(xiàn)有范式的范圍得到解釋時,科學共同體才會不情愿地逐漸拋棄舊有的范式”,“對于一般公認的范式的反復挑戰(zhàn)所產(chǎn)生的科學思想的危機最終由一次‘科學革命’而解決。”[16]顯然,能否已然視“新革命史”為一個范式或理論“革命”的標志,這勢必需要商榷。但是,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新革命史”是一座具有遠大前景的“富礦”,如何去開采,如何將“礦物原料”轉(zhuǎn)化為“工業(yè)成品”,仍需要學者們的艱辛挖掘和創(chuàng)造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