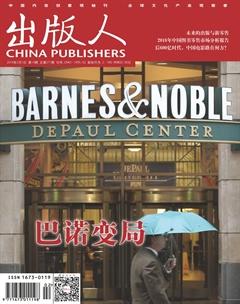“西南經驗”里的族群與國家
丁慧倩

在讀過許多大部頭的學術著作之后,《歷史人類學小叢書》這套小書對于以讀書為業的人來說,是可以重新找回閱讀樂趣的機會。說是“小書”,因為小且薄,一兩日就能從頭讀到尾。但“小書”講的大故事,一本一本講的都是中國復雜的歷史,讀的人輕松愜意、收獲滿滿,寫的人卻是積多年之功,傾情相授。
其中,溫春來教授的《身份、國家與記憶:西南經驗》一書是《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的延續。作者在新書里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將西南“夷人”的故事從王朝國家延伸到民族國家。在近代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中,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框架下沒有其他非漢族類的生存空間,他們面臨自己既非漢族也非滿、蒙、回、藏少數民族的尷尬境遇。以曲木藏堯為開始,李仕安為結束,身份各異的“夷人”在近代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型塑出一個西南民族的輪廓面貌,將自己的族類身份與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嵌在一起。作者已經實現了自己的愿望,這本書確實講了一段有溫度的歷史。帶著這份溫度回到破碎的文本記述,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這些“夷人”精英不斷創造自己身份所依憑的歷史情境和文化資源。
西南民族研究一直是民族史研究的熱點所在,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各個學科爭相在這個舞臺上展演自己對民族、歷史乃至國家的理解。這本書研究的地域在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那里是“無國家之地”(Zomia),生活于其中的居民掌握了不被統治的藝術,主動選擇逃離政權的控制;而本書的作者則認為這里一直有“國家”形態的政權存在,西南“婁素”的“國家傳統”及其與四川涼山“諾蘇”之間的關聯揭示了云、貴、川地區在歷史時期即存在著跨地域、大空間的身份認同。
如果說宋明理學發展了小宗之法,宗族倫理庶民化使家譜的編纂變得普遍,從此我們的祖先生活在一個由譜牒構建的世界里。那么今天的我們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生活在一個由族群分類構建的世界里呢?
本書沒有糾結于群體“自我指屬”(self-ascription)主觀意識對族群形成所起的作用,而是討論了西南“國家傳統”在維系身份認同方面的意義。作者指出西南的君長國早已族群化,“國家傳統”的存在是西南人群共同想象的一個重要基礎;正是“西南國家傳統的族群性”使民族主義興起之后“夷人”精英的近代民族建構成為可能。
作者將西南的君長國稱為“國家”,意在強調政權架構的存在。從普遍意義上說,小政權與大國家性質相同。中國歷史上的眾多人群都曾經有過或一直存在“國家”的形態。在王朝國家及政權的范圍內討論族群,或者反過來說在族群發展的維度上思考歷史上的“國家”,歷史學和民族學、人類學一起從族群出發,行至此處分道揚鑣,歷史學以中國的實際經驗為基礎討論人們身份建構的原因、動力、途徑和意義。在近代民族國家產生之前,族群的建構與國家的建構有怎樣的關聯?這樣與族群相關聯的“國家”與民族國家又存在哪些區別和聯系?探討這些問題,是從人的主體性角度求索中國傳統大一統格局的性質及其形成的民間基礎。
如果要追問中國的民族國家從哪里開始,又走在怎樣的一條路上,我們需要回歸歷史本源,即歷史是由一個個具有能動性的人和人群創造的。本書的寫作并不局限于展現大一統國家的多樣性,而是從實際的歷史經驗出發,在充分關注了人或者人群的主體性之后,討論族群共同體演化的復雜過程。
歷史以過去的光輝照耀未來。回到當下,或許我們還需要關注民族身份的戶籍化,以及以戶籍所代表的血系傳承為邊界的民族認同再創造。西南地區的歷史仍在延續,人們的生活在歷史鋪設的軌道上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