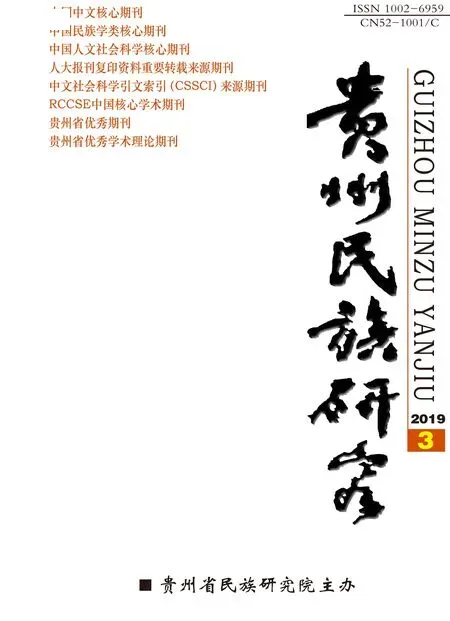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探究
王 劍
(長江師范學院 重慶民族研究院,重慶 408100)
西南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濃郁的原始族群形態為少數民族農耕文化的凝聚和傳承提供了天然屏障[1]。作為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區,西南地區至今保留著55個少數民族群眾不同程度的農耕文化足跡和30個常住民族的農耕文化要素。以神秘宗教文化為紐帶,以村寨為基本耕作單位,以原始生產為模式的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在歷史歲月的打磨下具有鮮明的階段性。一方面,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具有超凡的穩定性,比如:西藏地區以農奴制為基石的農耕文化和摩梭人原始家族式生產關系延續至“三大改造”前后;另一方面,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在歷史演變中同中原農耕文明相比具有相對的多變性,比如:獨龍族農耕文化在歷史演變中實現了“游耕”到“農耕”的轉變。此外,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又具有強烈的前瞻性,比如:獨龍江流域的獨龍族群眾“輪歇耕作”思想、基諾族群眾依據土地類型“定期輪歇”觀念等同可持續發展理念不謀而合。總之,西南少數民族“依山傍水”“仰天靠地”的農耕生產即是西南得天獨厚地理區位優勢的映射又是西南農耕文化歷史追溯的“活化石”。[2]立足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獨特性的全局透析,以民族農耕生產特征為導向,審視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進而以歷史的維度追溯農耕文化的特色與禮俗,聚焦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的典范與精髓,從而為構建民族文化共同體夯實內部機理。
一、原始混合的生產——農耕方式的漸進性分離
西南作為農耕與游耕、采集與狩獵生活方式的交匯處,在基本生活方式的選擇中并非先天性以地理環境為導向,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長期處于原始母系式社會,同“男耕女織”的中原農耕文化截然不同。[3]比如:摩梭人在“舅掌禮儀母掌財”的母系式社會中主要以狩獵和采集為主,以簡單刀耕火種的稻谷種植為輔。縱觀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基本上都經歷了不同生產方式混合的時期,一方面,部分少數民族地區長期處于原始社會,社會生產力落后,狩獵、采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始終占據著物資資源獲取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西南少數民族在不同生活方式和農耕要素的優化中實現了農耕方式的漸進性分離。首先,西南少數民族依山傍水的游牧生活習性逐漸轉變為定居式的生活,比如:納西族群眾早期處于“漁獵時代”,在圍繞玉龍山逐漸定居后,以“領主經濟”為主導的農耕方式被長期固定。其次,“谷種”在少數民族原始混合的生產過程中逐漸被發現,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農耕方式的漸進性分離奠定了基礎。比如:北盤江流域的布依族在文學作品《茫耶尋谷種》中以傳說的形式描述了布依族兒女在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期發現“稻谷種子”事跡。再者,西南少數民族在原始混合耕作方式中不斷創新改造,“刀耕火種”的簡單農耕方式逐漸向以石器農具為主導的農耕模式轉變。[4]比如:水族群眾在耕作初期通常“火耕水耨”的粗放式耕種。加之,伴隨而來的農耕社會組織的形成,極大地促進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由原始混合的生產向農耕方式的漸進性分離。再者,同中原農耕文化所不同的是,西南少數民族在不同“游耕”過程中對各種動物進行了嘗試,最終在狩獵和農耕雙重作用的影響下形成了以“牛耕”為主的農耕文化。比如:羌族“羊圖騰”習俗大致與農耕有關。此外,隨著中原封建政權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管轄和文化融合,中原農耕技術也相繼傳入西南民族地區。
二、仰天靠地的生產——農耕文化自然性的合成
“天時地利”是農耕文明賴以延續的基礎,是農耕文化不斷沉淀的引子。雖然西南少數民族在農耕方式上具有獨特采集、狩獵的混同,但是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也受自然條件和區位優勢的制約,仰天靠地生產的農耕自然性成為農耕文化獨特性生成的關鍵。換言之,仰天靠地的生產——農耕文化自然性的合成是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歷史演變的主要階段。
一是西南少數民族農耕依舊注重區位優勢的選擇。傳統農耕活動的地理依賴性是機械化農業難以媲美的,西南少數民族在農事活動不斷選擇區位優勢顯著的環境進行農耕,特別是早期在云貴高原,以游耕為主要特色農事活動成為西南少數民族仰天靠地的見證。[5]一方面,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活動兼顧水田與旱地,在土壤肥沃的田野進行農事活動成為普遍現象,比如:佤族通常在平坦開闊的地方進行粗放式的“刀耕火種”和“挖犁撒種”。
二是西南少數民族在仰天靠地的農事活動中不斷依托地理環境進行農具革新。農具革新是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歷史演變的活化石,同時也是西南少數民族農事活動不斷成熟與完善的結果。一方面,西南少數民族農具隨著歷史不斷革新,成為農耕文化歷史演變的主線;比如:云貴地區的怒族群眾在冶鐵技術尚未掌握之前,從石器時代的“石鋤”到“竹鋤”不斷在重量和長度方面改進。另一方面,在生產力水平提升的基礎上,西南少數民族在敬畏自然的前提下嘗試改造農事活動的地理環境,從而也推動了農具的革新。比如:夜郎地區的侗族先輩在水資源短缺和干旱時不斷改善簡易灌溉工具,在歷史變遷中相繼發明改善了“龍骨水車”等灌溉工具。
三是祈求風調雨順的農耕的自然性逐漸向社會性合成,成為農耕文化的重要體系。一方面,以自然崇拜為主的原始宗教形態在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中基本確立;通過原始自然崇拜達到祈求天地風調雨順、農事順利的目的。比如:早期怒族群眾信仰自然萬物,通常由“尼瑪”定期向天地禱告,祈福避災。另一方面,西南少數民族在早期農耕活動影響下的宗教活動幾乎都同農耕密切相關;比如:早期麗江一帶納西族群眾在傳統宗教東巴教儀式中有“祭天”“祭風”的宗教活動。總之,隨著仰天靠地式農事理念的弱化,祈求風調雨順的農耕的自然性逐漸向社會性合成,即祈求自然的農事習俗逐漸演變為具有鮮明社會屬性的宗教活動。
四是以自然為出發點的務農觀念的生態思維不斷孕育。[6]西南少數民族在務農中長期以地理環境為主導,不斷進行粗放式耕種,但是縱觀西南少數民族務農觀念的歷史演變,由粗放式耕種向可持續發展的樸素生態思維的讓渡成為農耕歷史演變的主旋律。一方面,隨著農耕的大幅度推廣和自然災害的瀕發,以輪耕為中心的生態農業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西南少數民族通過農耕要素的節約彰顯生態思維,比如:早期水族群眾利用梯田進行節水,成為世界范圍內原始節水農業的典范。總之,西南少數民族在仰天靠地的農事活動中不斷由粗放式耕種向精耕細作轉變,務農觀念中的生態思維也不斷顯現出來。
三、村寨與家族組織——農耕文化變與遷的紐帶
村寨與家庭組織是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歷史變遷的紐帶,特別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家族式協作耕種既可以凝聚勞動力,又可以弱化自然災害對個體農耕戶的挫傷。[7]加之,西南少數民族長期處于原始社會,以原始公社為基礎的農耕組織的變遷,成為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歷史演變的核心,富有原始氣息的公社的確立與瓦解的同時以土地為基石的勞動關系也隨之變遷。西南少數民族早期農耕組織可追溯至以母系式為中心的原始公社制,土地歸公社所有,提倡共同耕作,平均分配。[8]比如:仫佬族先輩早期組織主要以原始社會公有制為主,在進入封建社會后,土地逐漸私有,以雇傭關系為主的剝削也相繼出現。此外,佤族農村公社制作為農耕社會性的集中反映,在佤族村寨土地推行公私所有制,個體私有土地具有自由租賃等,而公社所有土地為公有制。在農事活動長期演變中以“珠米”和“普查”為主的階級雛形凸顯,以家庭為單位的“庫普萊”則同中原自給自足的小農組織相一致。此外,怒江傈僳族“伙有共耕制”也是土地公有關系的典型,但是傈僳族在以“卡”(村寨)為單位的共同耕作歷史演變中逐漸喪失原始家族紐帶,逐漸演變為行政化的組織。同原始公社相對應的氏族組織也是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歷史演變的起點,不過氏族組織在農耕社會的變遷中最終也被封建領主經濟所取代。[9]比如:金沙江流域的普米族群眾早期生產組織以氏族組織為主,在家族內部至今推崇以父系為主的家庭組織,在農耕文化演變中以氏族為單位的土地所有制也被以私有制為主的封建領主經濟形式所取代。當然,在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部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多種土地所有制并存的情況,比如:布朗族家族公有、村社公有和私人占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依舊存在,成為支撐農耕文化傳承的關鍵。總之,以家庭組織為整體,以族群等級關系為依托的社會組織的變遷成為映射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歷史演變的鏡子。
四、禮俗與宗規并舉——農耕文化社會性的凝聚
首先,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在歷史演變中,傳統禮俗始終凝聚與傳承。[10]一方面,以農耕文化為基礎的婚姻習俗和喪葬習俗在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中不斷傳承,成為少數民族農耕文化變遷原生態文化的體現。比如:哈尼族等少數民族在傳統農耕文化的影響下逐漸形成“喜而不悲”的喪葬活動。另一方面,在農耕文化的演變中西南少數民族典型的生活習俗也得以延續。比如:白族農耕文化始終具有采茶元素的因子,在白族禮俗中“三道茶”是其農耕禮俗的精髓。其次,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在歷史演變中,以農耕為主的節日習俗日益喪失原有的價值體系。比如:“添糧”本是農耕時期仫佬族群眾驅病祈福的儀式,而在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中逐漸成為宗教活動。此外,西南少數民族群眾為祈佑豐收形成了龐雜的農耕禮俗,但是隨著農耕技術的改進和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原有節日禮俗逐漸演變為群體休閑嬉戲的活動。比如:毛南族“分龍節”、苗族“燒魚節”等都從祈佑豐收的農耕禮俗轉變為休閑活動,而直接以農耕為主的農耕禮俗在歷史演變中逐漸喪失了存在的價值。比如:侗族“開秧節”在歷史演變中逐漸喪失了其生存的土壤。
再者,在家族宗規中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也被烙上了歲月的軌跡。[11]比如:摩梭人在早期農耕文化中逐漸形成了“舅掌禮儀母掌財”的家族宗規,集中反映了母系式社會農耕文化的基本特點,而延續至今的摩梭人“走婚制”也是早期母系式農耕文化的體現。此外,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逐漸融入到文體活動中。比如:白族蕩秋千源于采蕎活動時的啟迪,在歷史演變中成為體育競技活動,仫佬族體育項目“象步虎掌”則是農閑時群體娛樂的項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西南少數民族鮮為人知的農耕精神文明。當然,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常見的“插秧舞”“采茶曲”等都是農耕文化歷史變遷過程中不可磨滅的文化存在。
五、創新與多元交織——農耕文化演變的主心骨
創新與多元交織是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演變的主心骨。一方面,少數民族在長期仰天靠地的農事活動中,自然敬畏在基本生存的抉擇中被有限地突破,傳統刀耕火種的農事活動不斷被創新,修建梯田成為西南少數民族農事活動創新的基本跨越。[12]另一方面,面對天災人禍,西南少數民族在耕作類型上逐漸實現了多元化,同時不斷革新農具,侗族水碾等農具不斷改造與完善,極大地提高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農耕水平。多元是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歷史演變的關鍵,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融合了旱地和水田的農耕形式,在農耕文化的變遷中,狩獵文化、采集文化、漁獵文化始終相輔相成,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獨特農耕文化的形成和演變提供了有益的補充。同時,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在歷史演變過程中也推動了關聯文化形態的發展。
總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集狩獵、漁獵、農耕、采集為一體,在農耕中稻麥結合耕作,水田與旱地結合的自然環境中孕育了獨具特色的原始農耕文化,并在歷史演變中逐漸實現了游耕到農耕的過渡。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歷史演變的時間維度中基本同石器時代和鐵器時期的轉變相吻合。[13]就西南少數民族的農耕文化而言:農耕觀念由粗放式耕種向生態農業觀念的轉變成為西南少數民族農耕文化的精髓,而農耕禮俗的歷史演變成為農耕文化變遷的內在機理的完善,當然以農具革新為主的農耕要素的歷史演變則成為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