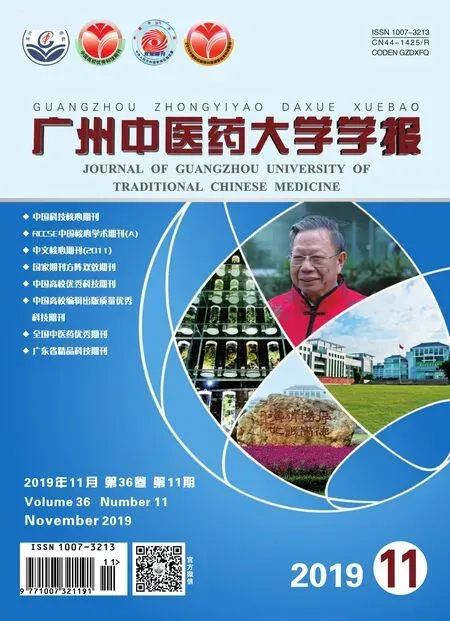潘俊輝從“腎虛證”辨治慢性咳喘性疾病經驗
黃婉怡, 潘俊輝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醫科,廣東廣州 510120)
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氣管擴張、慢性咳嗽、肺纖維化等以咳、喘為主要癥狀的慢性呼吸疾病,雖然已有比較公認的西醫診療常規,但對相當一部分患者,西藥治療效果仍不佳,容易出現反復發作或急性加重,甚至導致不可逆的呼吸功能損害。
中醫補腎療法在慢性咳喘性疾病治療中的運用較廣泛,其重要性已得到邵長榮、沈自尹、洪廣祥等名老中醫的重視[1],現代研究亦提示補腎法彌補了現代醫學在氣道局部抗炎治療的不足[2]。潘俊輝教授是第二批全國名老中醫學術繼承人,師承邱志楠教授,為“邱志楠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傳承工作室”負責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肺病臨床重點專科帶頭人。潘俊輝教授作為第六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傳承指導老師,帶領師門眾弟子,與鐘南山院士帶領的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原“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團隊長期合作,對頑咳、頑喘、頑哮等難治性慢性咳喘性疾病開展了深入的中醫學術探討及臨床實踐,不斷豐富和完善邱老“嶺南平治肺病”[3]學術體系。潘俊輝教授立足“嶺南平治肺病”學術思想,探索從“腎陽”出發尋求頑咳頑喘突破點[4-6]。
對慢性咳喘性疾病發展到后期的患者,或頑固難治的咳喘性疾病患者,若單從肺脾論治、單用培土生金之法往往力已不及。誠如清·程鐘齡《醫學心悟》所謂:“外感之喘,多出于肺,內傷之喘,未有不由于腎者”。腎藏元陰元陽,可滋養、激發及調整全身陰陽。正如明代醫家張景岳所言:“五臟之陰,非此不能滋,五臟之陽,非此不能發”。潘俊輝教授立足于“腎藏元陰元陽”,以及慢性咳喘性疾病久病易及腎的臨床規律,提出“調平腎中陰陽”之治法。以下對潘俊輝教授臨床辨治慢性咳喘性疾病“腎虛證”的經驗進行探析。
1 從細節辨析慢性咳喘中的“腎虛”
潘俊輝教授對慢性咳喘性疾病中的“腎虛”表現有非常細致的觀察和辨析。在呼吸疾病研究所就診的患者多為久病、重病、疑難病患者,病情復雜,虛實寒熱錯雜,尤其在經過現代醫學干預手段如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呼吸機、氣管插管術、胸部手術等治療后,其中醫證候的臨床特點與傳統中醫所描述的相距甚遠。故需充分利用中醫望聞問切四診的優勢,從細節中辨析其腎虛的證候,以期為處方用藥提供依據。
1.1從望診細辨“腎虛”(1)首先強調望眼神。“神藏于心,外候在目”,眼能傳神。《靈樞·大惑論》:“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患者黯然無光,眼神交流中能感覺其反應遲鈍,眼球轉動不靈,常不自覺地小幅度轉頭以輔助目光轉動;也有眼中華彩閃爍者,乍看似是眼中晶亮有光,但細看眼神空洞,不能進行有效的眼神交流,皆屬腎氣不斂,臟腑精華不能含蓄內藏,臟氣暴露,見于久病咳喘致腎氣大虛或兼有癡呆者。(2)其次望面色。患者面色黯黑,眼下眶發黑,尤其是黑色的范圍超出了下眼眶,為久病入腎,腎色外露之象。“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素問·脈要精微論》),若面色黑而尚有榮潤光澤者,腎中精氣雖傷而未衰,凡黑而晦暗枯槁者,腎精已衰或正虛而兼邪毒深重,多病重難治。(3)必查腎之外候(頭發、牙齒、腰部癥狀)。腎者其華在發,頭發早脫、早白、稀疏為腎氣不足,診察久病咳喘的患者,尤必觀察頭發情況,以了解腎虛的程度。若患者雖久病而頭發依然濃密,可知腎精未大傷。腎主骨,齒為骨之余,不合年齡的牙齒松動、脫落、干枯也是腎虛的重要征象,在小兒則為牙齒不長,例如大量或長期使用抗生素的小兒(曾治2例幼兒因肺部支原體感染使用阿奇霉素較長時間,患兒乳牙停止萌出,以六味地黃丸為基礎方治療而獲效),可見頭發不長。腰為腎之府,容易腰酸、腰痛者要注意腎虛,但長期臥床、活動不利的患者也多見腰部不適,可能是局部氣血瘀滯,未必為腎虛。(4)細查舌苔辨別腎精是否大虛。腎中陰精大虛者,見舌嫩紅無苔,或淡白無苔,舌面可見不規則的淺細裂紋;或有苔,但舌苔松腐、不均勻、易剝落(清醒的患者讓其漱口,可見舌苔變化大,掉落較多;昏迷或不配合查體的患者,用棉簽輕揩,舌苔即落),為“無根之苔”,屬腎精已傷、邪濁留滯中焦之象。還要注意,患者做氣道霧化治療、使用無創呼吸機(尤其是用口鼻面罩者),會暫時出現舌嫩紅少苔,要注意鑒別。
1.2從聞診細辨“腎虛”(1)觀察呼吸狀態。患者呼吸淺,間中需要有意地用力吸氣才能將氣吸進去,為腎不納氣的表現。(2)辨別講話聲音和方式。患者講幾句話(嚴重的講十幾個字)即需停下來,或者講長句子時至后面聲音出現變調、變悶,或者發不出聲音來,也是腎不納氣的表現。(3)聽辨咳嗽聲音。患者自覺咳嗽無力,或自覺有痰而無力咳出,讓其用力咳嗽會感到氣促;或咳嗽劇烈時,會感覺心悸、汗出,有氣脫之勢,尤其要留意。
1.3從問診細辨“腎虛”內容不一而足,為腎藏精、主水、主納氣、主生殖、主骨生髓、開竅于耳等生理功能失常的具體表現。臨床上,重點注意生長(兒科)、生殖情況(女性必須問月經)及耳鳴耳聾等表現。另外,呼吸科患者常有咯痰一癥,痰有咸味,或口中泛有咸味,為腎之口味上泛外溢,也是腎虛之象,這對于呼吸科患者很有診斷意義。
1.4從脈診細辨“腎虛”脈象貴在“有根”。以尺脈候腎氣,尺脈沉取應指有力為“有根”。若見尺脈沉細,浮大無力,尺脈短而不足位,或尺脈雖在但力量不均勻,跳動幾下之中有一下特別弱,都是腎虛的客觀征象。
2“腎不納氣”證候之病機探源
腎不納氣是腎虛而不能攝納肺氣的病證,癥見氣短、氣喘、動則喘甚而汗出,呼多吸少等表現,在呼吸疾病患者中相當常見,可見于中醫的喘證、哮病、肺脹等,現代醫學中最常見于支氣管哮喘(尤其是重癥哮喘、多年哮喘患者的急性發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尤其是肺通氣功能障礙為重度、極重度的患者)、肺源性心臟病等,也見于間質性肺炎、肺淋巴管平滑肌瘤、風濕免疫疾病累及肺部等疾病。
中醫教科書中的“腎不納氣證”被籠統地解釋為“腎氣虛”。潘俊輝教授長期診治呼吸疾病患者,對腎不納氣有細致的辨析。潘俊輝教授指出,腎不納氣從病機上可歸結為腎虛引起的清氣不能下及、腎氣不能歸元,但是治療上如何“補腎氣”,顯然不是一法一方能解決的,必須分清楚腎陰腎陽才能作出針對性的治療。
“腎主納氣”、“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根”并非單就呼吸之氣而言,其實質是腎精與臟腑之精(尤指腎中精氣)的互化互用。腎不納氣的“腎虛”,是腎中精氣的不足。腎藏元陰元陽,腎中精氣就其體而言是陰精,就其用而言是陽氣,腎中精氣實質是陰精所化的陽氣。此一陽之氣藏于陰中,務須潛藏,最忌浮越。腎中精氣是五臟六腑真元之氣的所在,腎中精元與脾生化的谷氣、肺攝取的清氣相合而化生臟之真氣。腎的生化之機旺盛,精能化氣,臟之真氣有源,肺氣才能正常宣發肅降而呼吸調順。腎中精氣旺盛,肺氣動力之源充沛,才有足夠的動力將吸入之清氣肅降歸腎,由腎攝納。
綜上,腎不納氣的病機,主要有肺腎氣虛和腎中陰虛陽浮兩類,雖然都表現為呼吸短淺、氣喘動則尤甚,治療上都遵循“陰中求陽、陽中求陰”的補腎大法,但具體的病機和治法各有側重,不宜混為一談。
2.1肺腎氣虛(陽虛)之腎不納氣肺腎氣虛的腎不納氣,乃是肺氣虛浮、不能下納,其根源主要責之腎陽。多為久患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氣管擴張等),常因肺部感染反復加重,頻繁使用抗生素而未能及時采用中醫藥固本培元,更有甚者出現肺部真菌或耐藥菌(銅綠假單胞菌、鮑曼不動桿菌等)慢性感染,病邪與藥毒交相折損正氣,久而虛損及腎,致使肺腎兩虛。此型患者除氣喘主癥之外常見呼吸短淺、咳嗽咯痰乏力、語聲低微、講話不能接續等氣虛之象。
此類腎不納氣,“腎虛”側重于氣與陽之不足,不僅腎陽不足,且肺脾陽氣也不足。治療上主要以肺腎雙補、降肺納氣為法。肺腎雙補之時同時需重視中焦脾胃之氣,因肺氣全賴脾胃化生的氣血資助,補肺實則不離培土生金,且健脾補氣也是取“補后天以養先天”之意。潘俊輝教授常用人參大補元氣,人參大補腎間生發之元氣,從命門輸注三焦而充實五臟,使氣從三焦下行歸腎,故能補虛定喘。古人常用蛤蚧納氣歸元。蛤蚧補腎丸、蛤蚧定喘丸等組方思路值得參考。因蛤蚧現為保護動物,潘俊輝教授用海龍、海馬代替,并囑此類患者可將海馬、海龍用于食療中。世有“北方人參,南方海馬”之說,《本草新編》謂海馬“入腎經命門,專善興陽……海馬不論雌雄,皆能勃興陽道”。海馬是補腎強壯的名貴藥材,性溫、味甘,入肝、腎經,能溫腎壯陽、納氣平喘。但由于海馬資源緊缺,價格昂貴,可以用相對低價的海龍,藥效也佳。《本草綱目拾遺》始載海龍,并指出“(海龍)功同海馬而倍之”。另外,對肺腎氣虛的腎不納氣,也須注意肅降肺氣,方中可合用北杏、紫蘇子等。
2.2腎中陰虛陽浮之腎不納氣腎中陰虛陽浮的腎不納氣,乃是真陰虧損、陽氣浮越,其根源主要責之腎陰。多為年老精衰、生化不及,或房勞失節、精傷太過,導致腎中精氣不足,攝納無權;現代臨床上還常見因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支氣管哮喘、間質性肺炎等)的患者,導致劫傷腎中陰精。以上都可導致腎中真陰虧虛,而使腎陽不能斂藏,氣浮于上,無力下行,出現腎不納氣。臨床除氣喘主癥之外當兼見舌紅、剝苔或無苔,尺脈虛大等真陰虧虛的表現。
此類腎不納氣,“腎虛”側重于陰精,但實則腎陽也虛,且多有虛陽外越之勢,尤其要注意。治療以補腎滋陰,納氣歸元為法。采用山茱萸、五味子固精斂氣。山茱萸味酸澀,性微溫,補益肝腎,澀精固脫。《景岳全書》謂山茱萸“能固陰補精,暖腰膝,壯陰氣”,《神農本草經讀》認為“山萸味酸收斂,斂火歸于下焦”,正是此類虛喘用山茱萸的明證。五味子味酸收斂、性溫而潤,《神農本草經》謂其“主益氣,咳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本草備要》謂其“專收斂肺氣而滋腎水”,可取得收斂五臟之氣而納于腎、調理肺氣、斂肺止咳平喘之效。若患者兼見心悸、汗出等陽氣外越征象者,潘俊輝教授常加生脈散、龍骨、牡蠣等固澀潛陽。臨證效仿潘教授用山萸肉思路,加大其量,也可取固脫之效。
綜上,“腎虛”是多種慢性咳喘性疾病,尤其是此類疾病中后期及長期西醫干預作用后的重要證候,從“腎虛”辨治是中醫取效的重要突破點。潘俊輝教授對此類患者的“腎虛”證候進行細心辨析,重視從腎、從鼓舞陽氣的角度尋求突破,尤其在疑難病的應對上,具有較高的臨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