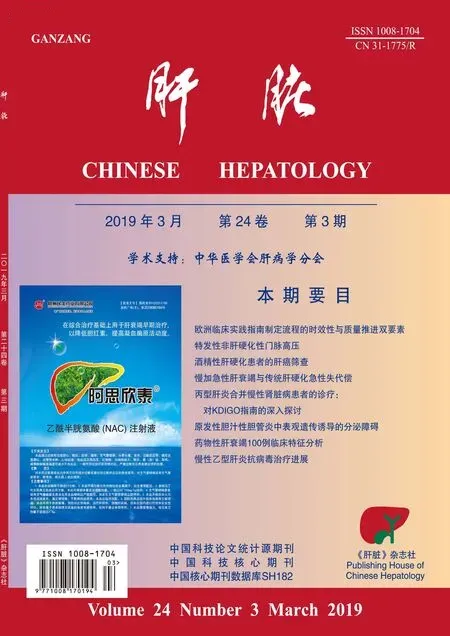慢加急性肝衰竭與傳統肝硬化急性失代償
顧聞怡 李海
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是慢性肝病基礎上的急性惡化,導致全身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其短期病死率高。目前較多研究發現ACLF主要發生在肝硬化急性失代償(AD)的患者上,而其不同于傳統肝硬化AD,最主要特點是ACLF短期和中期的預后較差。
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表現出預后的臨床異質性。 單純的靜脈曲張出血的患者、首次非出血的AD患者和發生任何第二次AD的患者,其兩年死亡率分別為20%、24%和50%~78%[1]。此外有細菌感染的患者短期預后非常差。ACLF定義的出現,就是為了將這群預后極差的患者從因傳統的肝硬化AD而住院的患者中區分出來。亞太肝病研究組織(APASL)最早定義的ACLF其30 d死亡率在25%~37%之間。而歐洲CANONIC研究中,根據新定義的ACLF和傳統肝硬化AD患者28 d及90 d死亡率有著明顯的差別(分別為28 d:34% vs 5%;90 d:51% vs 14%)[1]。北美洲終末期肝病研究聯合會(NACSELD)其更為嚴格定義下的ACLF患者,同樣比傳統AD患者有明顯更高的90 d死亡率(30 d 25%,3個月40%)[2]。
ACLF患者發病的誘因和發病機制仍存在不確定性。在誘因方面,歐美主要分為肝內誘因和肝外誘因,其診斷的患者相較于APASL診斷的患者往往有較好的肝生化標記,而APASL將ACLF定義主要限制在肝內誘因,是否要集中在肝臟特異性的標準和誘因等還是更多關注肝外器官衰竭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3]。在西方國家,ACLF發生很大程度上與3個月內的細菌感染以及過度飲酒有關,另外還有上消化道出血,而在亞洲,乙型肝炎再激活可能還是最主要的誘因。但另外也有近半數的ACLF患者并沒有顯著的誘發因素。ACLF發生的病理生理機制始終不清楚,傳統AD的患者往往有系統循環功能障礙以及系統性炎癥,但是ACLF患者相比傳統AD患者在這兩方面更為嚴重,尤其是系統性炎癥與ACLF的發生關系更為密切。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調節的免疫反應可能是導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對于已有的誘因,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闡明引起過度炎癥反應的機制。而對于沒有找到明確誘因的傳統AD和ACLF患者,腸道通透性增加導致的腸道菌群易位可能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可能還是找尋AD和ACLF患者系統性炎癥反應嚴重程度的差異[1]。
對于主要基于死亡結局定義和區分的ACLF患者和傳統肝硬化AD患者,建立預后評分系統,以根據早期判斷中短期預后來制定不同的治療方案,對于這類病程極短的患者尤為重要。目前比較多的預后評分有CLIF-C AD評分(CLIF-Consortium AD)和CLIF-C ACLF 評分(CLIF-Consortium ACLF)分別對傳統肝硬化AD患者和ACLF患者做出預后評判[1]。但是分別制定的預后模型,對于處于灰色地帶的ACLF低死亡率患者和傳統AD高死亡率的患者,他們的治療措施的選擇包括肝移植等仍帶來困難。而傳統的終末期肝病模型評分(MELD)、MELD-Na評分和Child-Pugh評分等,并沒有將全身多器官的因素考慮在內。一個比較全面的、能夠為包括ACLF患者在內的慢性肝病住院患者提供不同臨床干預方式參考的中短期預后評分,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完善。
在治療方面,目前針對ACLF的治療主要集中在消除潛在的誘因以及器官支持治療,不言而喻,肝移植對于ACLF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死亡供體肝移植可將ACLF患者移植后1年生存率增加至75%。由于肝源的缺乏,更傾向于考慮親體肝移植。雖然及時的肝移植為ACLF患者惡化逆轉的唯一措施,但是,進行肝移植的最佳時間窗仍未確定。另外,肝移植雖然能夠解決肝臟衰竭的問題,但肝移植對肝外器官衰竭的逆轉及生存率的影響尚不明確[4]。其他提高生存率的治療還包括利用血液凈化解毒系統、免疫調節治療、細胞治療和糞便微生物移植等輔助手段,這些手段可能使部分患者獲得肝移植的適應證。目前在歐洲和美國,ACLF患者比較多的還是關注在對于感染、肝腎綜合征和腎衰竭的治療,而在中國,已有研究表明骨髓來源間充質干細胞和臍帶來源間充質干細胞的治療對HBV相關ACLF能夠改善中長期結局[1]。
以上ACLF和傳統肝硬化AD的多方面的比較,總體來說必須回歸到ACLF定義設立的目的是為了設立一個嚴格的診斷標準群體,建立一個高短期病死率慢性肝病的綜合征特殊群體,亦或是能夠通過有效干預措施(如肝移植等)改善其較差的預后[3]。對于ACLF的診斷,前期大量的工作都集中在預后結局方面,ACLF的定義不應始終圍繞著預后,后期應更多關注診斷標記物,探索區分傳統肝硬化AD和ACLF的病理生理機制和標記物,特別是免疫病理相關的靶點,更好地有針對的圍繞那些潛在的靶點和通路來治療ACLF患者,預防ACLF的發生和進展,從而提高生存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