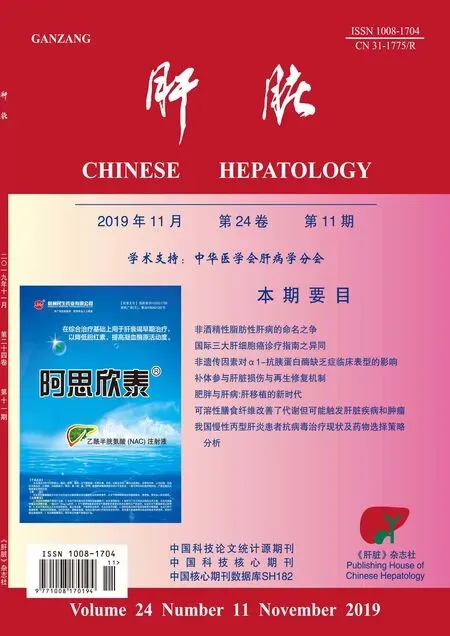可溶性膳食纖維改善了代謝但有可能觸發肝臟疾病和腫瘤
李晶
隨著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和以2型糖尿病為代表的代謝性疾病的流行,全球約有25%的人口患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而NAFLD本身有進展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硬化甚至肝細胞癌(HCC)的風險。非常遺憾的是,目前對于NAFLD尚缺乏針對性和療效確切的治療手段。生活方式干預、膳食結構調整-即低糖低脂、低能量攝入及增加以纖維素(cellulose)為代表的不可溶性膳食纖維攝入等,針對2型糖尿病和肥胖等代謝性疾病的基礎治療仍是目前針對NAFLD的最佳治療選擇。除此之外,菊糖(inulin) 和果膠(pectin)等可溶性膳食纖維由于可以通過腸道菌群作用生成短鏈脂肪酸(SCFA)進而促進腸道上皮健康,被認為是可以改善代謝綜合征的益生元,并作為代謝綜合征患者的膳食推薦。已有非常多的研究提示,膳食中增加可溶性膳食纖維可以通過影響腸道菌群組成并通過肝腸軸對NAFLD、肝臟纖維化和 HCC有保護作用[1-3]。
但近期Singh等的研究對“可溶性膳食纖維是否有百利而無一害”這一似乎已被廣為接受的觀點提出了質疑[4]。在他們的研究中,菊糖、果膠、低聚果糖(FOS) 和纖維素作為膳食補充添加于飼料中喂養已存在菌群失調的動物模型Tlr5敲除小鼠 (Tlr5KO),結果顯示,予高可溶性膳食纖維組小鼠出現了肝損傷、淤膽及HCC等情況,在高脂飲食誘導的動物模型中也觀察到了類似的現象,但出現的頻率較低、程度較輕,有約10%的試驗組小鼠發生了HCC,但高不可溶性纖維喂養組中并未觀察到上述肝損傷的情況。與現有的其他研究類似,給予高菊糖飲食的Tlr5KO小鼠肝臟脂肪變減輕、糖代謝紊亂改善,這提示以菊糖為代表的可溶性膳食纖維對于肝臟的損害獨立于其對機體的代謝改善作用。他們發現在 HCC-傾向的Tlr5KO小鼠的腸道菌群中纖維發酵細菌和變形菌豐度更高,而無菌小鼠或廣譜抗生素處理的小鼠給予高可溶性膳食纖維飲食后未發現相應的菌群改變和肝損傷,將高膳食纖維喂養的Tlr5ko小鼠腸道菌群移植給野生型小鼠或共環境飼養后菌群受者出現肝損傷表現,這些均提示可溶性膳食纖維影響肝臟病變仍有可能是通過腸道菌群所介導。在這項研究中,接受高可溶性膳食纖維飼養的Tlr5 KO小鼠或接受其腸道菌群移植的小鼠體內細菌脂多糖(LPS)和鞭毛蛋白的水平明顯增加。代謝組學結果提示,高菊糖飲食后發生HCC的Tlr5 KO小鼠盲腸中丁酸鹽水平增加,而其他可溶性膳食纖維喂養的小鼠雖未發生HCC,但其盲腸丁酸鹽也有不同水平的輕度增加,進一步研究發現高丁酸鹽飼養的小鼠也出現了肝臟淤膽、炎癥和纖維化表現,但并未觀察到進展至HCC者,作者認為基于腫瘤發生的二次打擊學說,丁酸鹽很可能僅僅是發生HCC的“第一重打擊”。 在針對通過抗生素去除產丁酸鹽菌的Tlr5 KO小鼠觀察中作者發現,抗生素干預可以有效抑制HCC的發生。在亞組分析中發現,HCC僅出現于膽汁淤積組的小鼠中,推測膽汁酸譜的改變有可能參與可溶性膳食纖維促進HCC發生的進程。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對現有的關于可溶性膳食纖維可以改善代謝綜合征的理論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質疑,面對越來越多的可溶性膳食纖維添加食品已經進入我們生活的現狀,我們是否應該冷靜而謹慎地權衡改變某一類營養素的攝入給我們帶來的獲益和潛在的風險,可溶性膳食纖維種類很多,不同的可溶性膳食纖維對代謝和菌群的改變是否應該有更嚴謹的論證?
Singh等的研究所使用的可溶性膳食纖維添加比例遠高于人類食品添加比例,如何認定可溶性膳食纖維所造成的菌群失調、肝損傷和HCC的發生、發展?什么種類、多大濃度的可溶性膳食纖維會觸發高脂飲食情況下的肝損傷和HCC發生?在這項研究中均未進一步討論。雖然這是一項對于可溶性膳食纖維,尤其是菊糖對于肝臟的負面結果研究,但我們也需要理智地認識到,高脂飲食情況下,可溶性膳食纖維、腸道菌群失調、丁酸鹽水平、腸道屏障損傷等對肝臟的影響尤其是對HCC的觸發是一個復雜過程,包括本文在內的多項研究也提示,單純的高丁酸鹽水平并不能直接觸發肝臟腫瘤,以菊糖為代表的可溶性膳食纖維觸發肝臟腫瘤的具體機制,以及目前推薦的可溶性膳食纖維攝入量對于菌群和肝臟的影響究竟如何,尚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實。
除了動物研究,也需要更多基于人群的流行病研究來觀察高可溶性膳食纖維對于脂代謝紊亂、肥胖等代謝綜合征人群的影響,高可溶性膳食纖維飲食在改善代謝性炎癥和肝臟脂質紊亂的作用之外,是否存在別的我們尚未認識到的促肝損傷作用,是這項研究給我們提出的亟需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