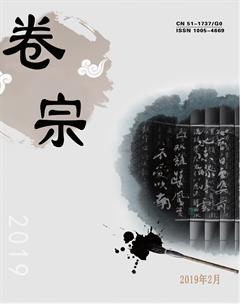《法哲學原理》中的貧困問題
摘 要: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認為相互依賴機制的失效、外部偶然因素的影響以及勞動細分和機械化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對此,他先后提出直接給予資金支持、提供就業機會、殖民擴張等應對辦法,最終傾向于以同業公會的救濟來緩解貧困,并由此過渡到國家共同體。但上述辦法都是建立在市民社會的原則之上的,即個人可以通過特殊勞動滿足特殊需要之上的,因此對貧困問題只能是緩解而非解決。
關鍵詞:貧困;市民社會;需要
市民社會的貧困問題“是他唯一一次提出了一個問題并任其懸而未決的地方。”(阿維納瑞語)因此對黑格爾貧困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首先從產生原因、規避辦法和影響三個方面對作為市民社會不可逃避的現象的貧困進行展開闡述,然后說明緩解辦法,最后引出馬克思和黑格爾在此問題上對話的可能性。
1 貧困—— 市民社會不可逃避的現象
本節的思路是:首先考察市民社會中貧困產生的原因,然后針對各個原因分別討論是否有規避的可能性,最后引出作為市民社會的不可逃避現象的后果,即賤民的產生。
1.1 貧困產生的原因
貧困產生的第一個原因與奢侈和依賴性相關。“這種解放是形式的……社會趨向于需要、手段和享受的無窮盡的殊多化和細致化……這就產生了奢侈。在同一過程中,依賴性和貧困也無限增長。”(p231)那么在何種意義上貧困的增長與奢侈的產生和依賴性的增長相關?
首先來看奢侈出現的位置。需要體系包含三個組成部分:發起者——主觀需要;中介——勞動;需要的滿足——財富。奢侈產生于第一個環節。黑格爾首先將動物與人的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手段作對比,指出“動物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法來滿足它的同樣局限的需要……但同時證實他能越出這種限制并證實他的普遍性。”(p233-234)人不滿足于動物性的需要,他還具有更多的細分的或特殊的需求,由此也要求對應的更多手段。而這種需求就是“意見”。意見表明不統一,即超出動物性需要的殊多性。與需要的殊多化相對應的是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細分而繁復”。因此,人們相互配合聯系以滿足彼此需要。在這種聯系中,1)我與他人地位平等,并且易于養成平等的需要;2)人們也存在標志自己特殊性的需要。因此需要進展到社會需要的層面,即人不再像動物一樣借助于外在偶然因素來滿足需要,而是主動地與他人建立普遍聯系以自發滿足殊多的精神需要。“人就跟他自己的、同時也是普遍的意見,以及他獨自造成的必然發生關系。”(p236)但這種社會需要的解放只是形式的,因為人們仍以需要的殊多為追求,奢侈便由此產生。
那么依賴性的增長是否與奢侈的產生相關呢?“需要和手段,作為實在的定在,就成為一種為他人的存在,而他人的需要和勞動就是大家彼此滿足的條件。”社會需要環節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就是彼此依賴的關系。這種需要始終是主觀的需要,即“趣味和用途成為判斷的標準……必須得到滿足的,終于不再是需要而是意見了。”(p234) 因為“趣味”等是主觀易變的,因此暗藏危險:當多數人的主觀興趣改變時,這種為他人存在的機制就會失效。即使反駁說這部分人還可以發展其他手段滿足新的主觀興趣,這種反駁也不成立,因為依賴機制失效是一個事實而不論“補救措施”如何。黑格爾用“貧困”一詞道出了這種被迫不得滿足的人的困境。
貧困產生的第二個原因與外部偶然因素相關。“但是分享普遍財富的可能……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礎(資本)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約,而技能本身又轉而受到資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況的制約;后者的多樣性產生了原來不平等的稟賦和體質在發展上的差異。”(p240)一個通俗的例子:一般來說農村孩子并不享有比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由此他所能受到的教育機會等后天發展就會受到影響。但對于以形式普遍性為特征的市民社會來說,并不存在因此向其傾斜的情況,這被稱之為“理念包含這精神特殊性的客觀法”(p240)。因此,市民社會中的貧困產生的第二個原因是:“偶然的、自然界的和外部關系中的各種情況”(p276)使人陷入貧困。
市民社會中貧困產生的第三個原因與勞動細分和機械化相關。“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細致化,從而也引起了生產的細致化……生產的抽象化使勞動越來越機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開,而讓機器來代替他”(p239)一方面,由于勞動細分,機器可以代替人勞動以至于工人失業而被甩出依賴機制之外;另一方面,即使工人沒有失業,在過于細化的勞動分工中工人機械化,一旦他人的主觀需求發生變化,對其有依賴關系的這部分工人也難以再次進入到新的需求體系當中。
1.2 關于產生貧困的原因的規避的討論
對于第一種——由于主觀需要的不確定性引起市民社會依賴體系的不穩定——造成貧困的原因,解決辦法是:國家限制主觀需要或者調整依賴機制。這種解決辦法并不可行。“人通過他們的需要而形成的聯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滿足需要的手段的準備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財富的積累增加了,因為這兩重普遍性可以產生最大利潤。”(p278)一方面正是這個導致貧困的原因,推動了社會財富最大效率地增長。另一方面,國家干預極有可能會危害市民社會本身的精神。
第二種“偶然的、自然界的和外部關系中的各種情況”致人貧困的情況,規避措施是要求普遍平等。黑格爾的回應是:“提出平等的要求來對抗這種法,是空洞的理智的勾當,這種理智把它這種抽象的平等和它這種應然看作實在的和合理的東西。”(p240)普遍平等的這種要求并沒有為特殊性保留位置而沒有實質意義,而黑格爾的平等應包含特殊性在內。例如殘疾者只在以市民社會成員身份參與市民社會活動時,而不是予以其他活動規則時才是被平等對待。因此,導致貧困的各種偶然的自然的因素作為特殊性已經被包含在市民社會之中了。那么第二種原因也是無法規避的。
第三種由于勞動細分和機械化引入,導致工人失業產生貧困的情況同樣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勞動細分和機械化與需求的殊多化相關。因此,第三種解決方案可能導致的危害與針對第一種原因的解決辦法的效果類似。
針對貧困產生的三種原因的規避手段失效的直接后果是賤民的產生。
1.3 賤民的產生
“貧困狀態一方面使他們對市民狀態處于嗷嗷待哺的狀態中;另一方面,由于市民社會使他們失去了自然的謀生環境(第217節),并解散了家庭——廣義的家庭就是宗族——的紐帶(第181節),使他們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喪失了社會的一切好處。”(p276)如上文所言,貧困是市民社會不可逃避的現象,因此市民社會無法解決貧困問題;轉而求助于家庭的溫情,但現在家庭倫理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市民社會中特殊性全面伸張的理念環節。于是處在貧困者就喪失了享受市民社會物質和精神利益的自由。
“當廣大群眾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為社會成員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調整的水平——之下,從而喪失了自食其力的這種正義、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時,就會產生賤民”(p278)賤民的產生是貧困范圍擴大的直接后果。簡而言之就是貧困者感到被整個社會拋棄,自我價值無處可實現的心理。如此更易滋生自暴自棄的情緒,賤民群體索性放棄信奉市民社會所提供的這種可能——福利向市民社會中的每個人敞開。較于勞動,他們更傾向于乞討;較于服從,他們更主張反動。
上述解決途徑的統統失效,原因只能來自市民社會原則本身。只要市民社會(的原則)存在,貧困就是不可消除的。貧困是市民社會的題中之義。
2 貧困的緩解
既然在市民社會中貧困無法消除,但是又有產生賤民群體的惡劣影響,因此貧困必須盡可能地得到緩解。
2.1 兩種假設
黑格爾假定了兩種緩解貧困的辦法:1)由富有的私人承擔或者用公共財產資金直接予以貧困者支持;2)給貧困者提供勞動機會。但黑格爾對此都給予了否定。因為如果直接給予資金支持有悖于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如果給予貧困者勞動機會,雖然遵循了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但會導致生產大于需求的情況,對市民社會的整體財富而言不利。
2.2 對殖民事業的否定
既然第二種方式不可行的原因在于供大于求,那么進行殖民事業以拓展國際市場可以使這種方式保留下來嗎?答案是否定的。“在近代,殖民地居民并不享有跟本國居民的同等的權利……殖民地的解放經證明對本國有莫大利益,這正同奴隸解放對主人有莫大利益一樣。”(p282)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對外侵略的不正義行為;進一步看,一旦殖民,殖民地也成為市民社會的一部分,這里的個人應該是自由市場經濟中的原子個人而平等的身份。因此,殖民擴張的辦法根本不能緩解市民社會的貧困問題。
2.3 同業公會的救濟
最后,黑格爾將緩解貧困的希望寄托在同業公會上。同業公會是這樣一種組織:共同處于市民社會的某一特定部門的工廠主或手工業者或商人為了實現這一特殊部門的福利而自愿組合而成的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并不存在特殊利益的斗爭而是作為共同體聯合起來。因此,同業公會作為其成員的普遍福利的組織是依托于它所在的特殊部門的,是實實在在的普遍性,對其成員來說也是現實的倫理的自由。
具體而言,同業公會具有“關心所屬成員,以防止特殊偶然性,并負責給予教育培養,使獲得必要能力”(p283)等的權利,因此較于市民社會,同業公會更能像家庭一樣關心成員,由此同業公會也被黑格爾看作是成員的“第二個家庭”,也是除家庭以外的“構成國家的基于市民社會的第二個倫理根源。”(p285)
“在同業公會中,家庭具有它的穩定基礎,它的生活按能力而得到了保證……(第170節)。此外,這種能力和這種生活都得到了承認,因之同業公會的成員無須證明他是某種人物。他屬于一個整體……他又有志并致力于這種整體的無私目的……因此,他在他的等級中具有他應有的尊嚴。”(p284)也就是說在同業公會中,作為追逐私利、需要通過掙得財富來無數次地證明自己尊嚴的個體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為普遍性的等級。在其中,成員之間沒有相互競爭,相反為了實現整個等級的最大化而樂于合作。因此,同業公會精神中自然地生長出了每一個成員的財富和尊嚴。所以,黑格爾說:“在同業公會中,對貧困的救濟喪失了它的偶然性,同時也不會使人感到不當的恥辱。”(p285)
顯而易見,黑格爾否定了通過直接給予資金支持、提供就業機會、殖民擴張的緩解辦法,更傾向于以同業公會的救濟來緩解貧困。
3 一種可能的討論方向
可以看出黑格爾始終在尊重市民社會的前提下來討論貧困問題,而這也是貧困問題不能解決的原因。雖然黑格爾以同業公會作為等級福利共同體的逐利方式揚棄了市民社會的成員分散的各顧各的逐利行為,但這也保留了市民社會的前提,不過減少了逐利主體的數量,增加了每個特殊部門單位值。現在的問題是:市民社會的原則必須保留嗎?《法哲學原理》重,黑格爾用國家的理念環節揚棄了市民社會;而同樣關注貧困問題的馬克思,則是用生產關系的強制性革命直擊貧困,而放棄了市民社會的自由前提。前者認為市民社會是家庭到國家的倫理的過渡環節而貧困是市民社會內涵現象,因此尊重市民社會的原則及其自由的前提;而后者不贊同這一前提,認為就是這里出現了問題,所以要直接地對其進行革命。由此,二者關于貧困問題及市民社會對話的可能性向我們敞開。
參考文獻
[1][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2][英]斯蒂芬·霍爾蓋特:《黑格爾導論——自由、真理與歷史》,丁三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3][以]阿維納瑞:《黑格爾的現代國家理論》,朱學平 王興賽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簡介
何文苑(1993-),女,重慶市人,現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