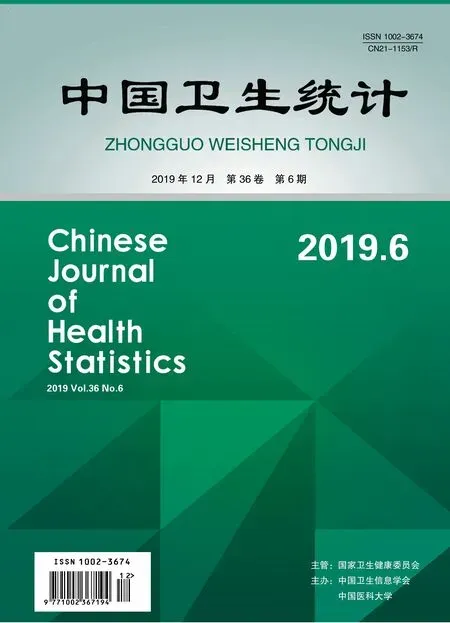基于集聚度的中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資源配置公平性研究*
杭州師范大學醫學院(310016) 王玥月 李宇陽 秦上人 孔圓峰 郁希陽 郭克強
【提 要】 目的 對我國基層醫療衛生資源配置水平進行評價,為引導基層醫療資源科學配置和布局提供參考依據。方法 基于衛生資源集聚度的評價方法,分析我國各地區基層衛生資源集聚度,包括機構、床位和衛生人員。結果 從土地面積角度分析集聚度,我國人口密集、均值地區基層醫療機構、床位以及衛生人員集聚度普遍大于1,而人口稀疏地區小于1,地理可及性較差;從人口角度分析集聚度,針對機構數與床位數,人口密集地區如江蘇、廣東、浙江的配置均不足,人口均值地區的海南、寧夏、黑龍江與人口集聚度比值小于1。針對衛生人員,人口密集地區除鄉村醫生外,基本可以滿足人口需求,人口均值地區除個別省份,如黑龍江、寧夏等,大多數地區均可滿足人口需求。人口稀疏地區鄉村醫生基本能滿足人口需求,但是衛技人員、執業醫師、注冊護士則出現不足的現象。結論 我國區域間基層醫療衛生資源不平衡依然突出,需因地制宜優化配置。密集地區與稀疏地區利用“互聯網+”共享醫療資源,稀疏地區建立合理補償機制,吸引衛生人才,密集地區優化政策環境,鼓勵社會辦醫。
衛生資源配置是衛生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保證衛生系統績效達標的重要條件,其配置公平性作為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前提,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健康利益[1]。“強基層”一直是我國醫改工作的重點,基層衛生資源合理配置是實現人人享有基本衛生服務的關鍵。本研究將基于集聚度的概念對各省的基層醫療衛生資源進行評價,分析各地居民基層就醫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資料來源與方法
1.數據來源
基層醫療機構按照衛生統計年鑒標準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衛生服務站、街道衛生院、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門診部、診所。衛生技術人員包括執業醫師、執業助理醫師和注冊護士等衛生專業人員,醫生為取得醫師執業證書的執業(助理)醫師,護士為注冊護士。人口分布和地理面積的數據來源為2013-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基層公立醫院總數與床位數以及各類衛生人員數量來源均為2013-2017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
2.研究對象
基層衛生機構資源屬于衛生物力資源,代表著主要醫療衛生服務輸出任務;床位資源是審核評級過程中常用的硬性指標,主要體現了醫療資源的輻射范圍;衛生人力資源作為衛生資源配置和衛生服務供給的重要紐帶,關系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2]。本次研究對象,包括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床位、衛生技術人員、執業(助理)醫師和注冊護士。
3.研究方法
(1)集聚度
集聚表示一定地域內某種生產要素相對于更大區域范圍內該生產要素的集中程度[3]。衛生資源集聚度(health resource agglomeration degree,HRAD)反映某一地域內以占全國 1%的土地面積上集聚的衛生資源數量的比例(%),計算公式如下:
HARDi是某省i的衛生資源集聚度,HRi是某省i的衛生資源量,Ai是某省i的土地面積,An是全國土地面積,Pn是全國總人口。
基于集聚度的概念評價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時,我們認為:
①當衛生資源集聚度大于1,即i省在占全國 1%的土地面積上集聚的衛生資源數量占全國的比重大于1%,表明衛生資源按地理配置公平性較高。
②當衛生資源集聚度與人口集聚度的比值接近于1時,即i省在占全國 1%的人口中的實際擁有的衛生資源比重與人口比重比值接近于1時,表明該地區集聚的衛生資源基本滿足集聚的人口的就醫需求,居民獲得衛生服務的可及性較好。若比值大于1,表明該地區的衛生資源相較于地區集聚的人口過剩,若比值小于1,則表明資源不足。
人口集聚度(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degree,PAD)作為反映一個地區相對于全國的人口集聚程度的指標,在本次研究里表示的是某省占全國 1%的國土面積上集聚的全國人口的比重[4],其計算公式如下:
PADi是某省i的人口集聚度,Pi是某省i的人口數量,Ai是某地區i的土地面積,An是全國土地面積,Pn是全國總人口。
結果與分析
1.基層醫療機構集聚度和床位集聚度分析
為了結果更加直觀明了便于比較,根據劉睿文等人[4]提出的觀點,將各地區按照人口集聚度的不同分為人口密集地區(PAD>2)、人口均值地區(0.5 人口密集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與床位數集聚度均大于1,說明在我國人口密集地區基層衛生機構與床位的配置公平性較高。人口均值地區的基層衛生機構的集聚度除了寧夏、云南、黑龍江,其他地區集聚度均大于1,配置公平性總體良好;床位數集聚度除了吉林、寧夏、云南、黑龍江,其他地區集聚度均大于1。所有人口稀疏地區的基層醫療機構集聚度和床位集聚度均小于1,可見這些地區居民基層就醫公平性差。 2.基層醫療機構、床位集聚度與人口集聚度比較分析 從整體上來看,人口密集地區較其他兩個地區,基層衛生機構和床位的集聚度與人口集聚度差距是最大的。其中江蘇省、廣東省、浙江省與安徽省機構數量和床位均不能達到人口分布的要求;而河北省的機構數量與湖南省、湖北省的床位數量則超出了人口分布的要求。 人口均值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床位與人口集聚度差別不是很大,說明均值地區大多數地區按人口分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床位,公平性基本可以實現。海南省與黑龍江省,機構數與床位數均不足,山西省機構數略微過剩。 人口稀疏地區,機構和床位與人口集聚度都較為接近,說明按人口分布配置機構數與床位基本可以實現,但由于機構集聚度和床位集聚度均小于1,所以即使機構集聚度與床位集聚度大于人口集聚度,這些地區居民基層就醫的公平性依舊較差。 表1 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量與床位集聚度分析 3.衛生人力資源集聚度分析 如圖1~4所示,衛技人員、執業醫師、注冊護士集聚度分析結果較為相似,人口密集地區公平性較好,人口均值地區除寧夏、云南、黑龍江三個省份公平性較差,其余地區的衛技人員、執業醫師與護士的配置公平性均較好,人口稀疏地區的衛技人員、執業醫師、注冊護士配置公平性均較差,并且與上述兩個地區差距較大。 根據鄉村醫生集聚度分析結果,鄉村醫生配置呈現不公平的地區要多于衛技人員、執業醫師與注冊護士。人口密集地區的浙江省公平性較差,人口均值地區海南、吉林、寧夏、云南、黑龍江和人口稀疏地區所有地區集聚度均小于1,公平性較差。 圖1 各地區衛技人員集聚度及其與人口集聚度比值 圖2 各地區執業(助理)醫師集聚度及其與人口集聚度比值 圖3 各地區注冊護士集聚度及其與人口集聚度比值 圖4 各地區鄉村醫生集聚度及其與人口集聚度比值 4.衛生人力與人口集聚度比較分析 將各類衛生人員集聚度除以當地人口集聚度,即可反映該類型人員配置是否能夠滿足當地人口衛生服務需求。根據圖1~4所示,大多數人口密集地區衛技人員、醫生、護士均可滿足當地人口需要,甚至出現過剩的現象,但是鄉村醫生卻出現配置不足的現象,比如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等。人口均值地區除黑龍江、寧夏、云南地區的衛技人員與鄉村醫生配置不足,其余大多數地區均可滿足人口需求。人口稀疏地區的青海和西藏,執業醫師與護士配置無法滿足人口需要,但鄉村醫生出現過剩跡象。 以往的許多研究常用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評價我國衛生資源分布的公平性,但是這兩種測算方法存在不確定性和不全面性等缺點[7]。集聚度的測評方法相當于洛倫茲曲線和泰爾指數的綜合評價,其特點是可以同時考慮人口分布和地理規模對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的影響,并且將區域的不公平性進行分解,用數字表達,計算簡便易于理解,結果清晰明了。根據集聚度研究結果可知,我國區域間基層衛生資源配置不平衡、不公平問題依舊存在。人口配置公平性優于按地理面積配置,這與楊展[8]運用基尼系數與泰爾指數對我國基層衛生資源配置進行研究的結果相似。 根據集聚度結果顯示,人口密集地區,所有基層衛生資源地理公平性均較高。但是基于人口的資源配置,江蘇、廣東、浙江均出現不足跡象。這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口密集,資源配置已基本能滿足地理需求,但是相較于人口配置依舊不足。因此基層衛生機構的工作重點應在提高服務效率,而不是一味地增加資源數量的投入。人口均值地區,基層衛生資源的公平性隨著人口集聚度的降低而遞減,在人口集聚度相對較低的寧夏、云南、黑龍江地區,出現了基層衛生機構和衛生人員配置地理公平性與人口可及性均較低的現象。寧夏、云南由于地形復雜而人口較少,從而導致基層衛生資源可及性較差。而黑龍江地區近年來由于經濟環境與薪資待遇等問題,青年人才外流嚴重,老齡化進程加快[9],實則對基層衛生資源的需求更高,更需要國家建立積極的補償機制,促進醫療資源縱向流動[10]。在人口稀疏地區,除西藏和青海,其余地區按人口分布資源配置基本滿足需求,但是地理可及性較差。人口稀疏地區地域遼闊、交通不便限制了居民對基層醫療服務的利用。盡管國家和地方政府投入較多資金,建立相應的人才戰略,但還是不能避免這些地區缺乏綜合配置措施,就業環境差、晉升空間小,人員流失大。因此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投入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在配置衛生資源時需充分了解人口分布情況,剔除無人分布地區,從而對衛生資源做出更為精準的配置。 對比基層機構床位與人員的集聚度研究結果,可發現我國基層物力資源配置公平性優于人力資源配置。物力資源配置可運用政治和經濟手段在短時間內得到提升,然而優化基層衛生人力資源的配置是長期、復雜和系統的工程,而提高落后地區的衛生人力資源的公平性更是重點和難點[11]。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人才政策,但是健康服務供給總體不足與需求不斷增長之間的矛盾依然突出[8]。根據鄉村醫生集聚度研究可知,我國的人口稀疏地區,尤其是青海和西藏地區的鄉村醫生數量遠多于執業(助理)醫師的數量。因此針對這些地方的特殊性,政府除加大衛生資源投入外,需進一步優化當地鄉村醫生隊伍。目前我國的鄉村醫生多為技術落后,學歷較低的人群,鄉村醫院診療設備簡陋陳舊,難以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的基本衛生服務需求,鄉村醫生雖不能被稱為“全科醫生”,但是他們服務對象不分性別、年紀,服務內容不分科別,服務模式與全科醫生如出一轍[9]。目前國家也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全面提高鄉村醫生技術水平,如推進鄉村全科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考試,同時深入實施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免費培養、農村基層全科醫學人才培養等措施,進一步提高人口稀疏地區基層衛生服務的利用度。 綜上所述,我國區域間基層醫療衛生資源不平衡依然突出,需因地制宜優化配置。密集地區與稀疏地區利用“互聯網+”共享醫療資源,可以實現醫療機構資源的互聯互通,優化有限的醫療資源配置。稀疏地區建立合理補償機制,吸引衛生人才。密集地區優化政策環境,鼓勵社會辦醫。




討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