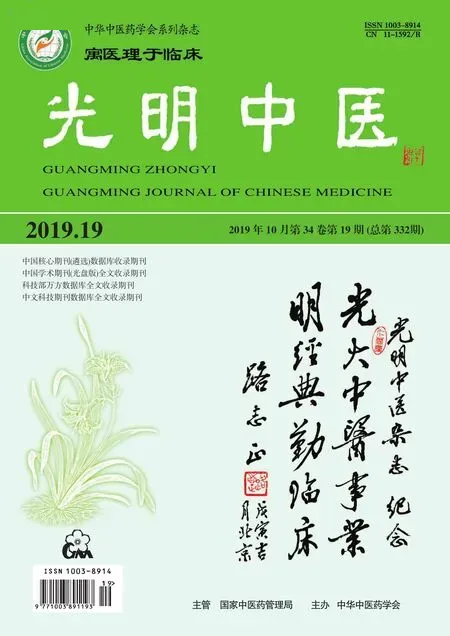李東垣“風藥健脾”治法探析
祁 勇
李東垣著述中,提出了“脾胃內傷,百病由生”的著名理論,強調脾胃在精氣升降中的重要作用,重視燮理脾胃諸法,尤擅長運用辛散升陽之“風藥”以健脾。“風藥”之稱,最早由“易水學派”張元素提出,張元素將常用藥物分為5類,即“風升生,熱浮長,濕化成,燥降收,寒沉藏”。李東垣根據“風升生”之藥物特性(意謂風藥氣溫,其性上行,猶如春氣之上升,如防風、升麻、羌活、柴胡、荊芥、麻黃、薄荷等藥,皆屬此類),將“風藥”廣泛應用于臨床脾胃病的治療,療效顯著,對后世醫家關于脾胃病的治療方法有著重要的影響[1]。
1 脾胃學說中“脾胃”特性探析
脾胃為后天之本,同居中焦,納運相得,升降相因,燥濕相濟。李東垣認為脾胃是元氣之源,元氣又為人身之本,脾胃傷則元氣衰,元氣衰則疾病生,正如《脾胃論·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中所言,“真氣又名元氣,乃先身生之精氣也,非胃氣不能滋之”[2]。
四時之氣之升降,唯長夏土氣居于中央,為之樞紐;人體氣機之升降,亦以中央脾土為主宰,行樞紐之令。如《脾胃論·天地陰陽生殺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間論》中言“蓋胃為水谷之海,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養周身,乃清氣為天者也;升已而下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為傳化糟粕,轉味而出,乃濁陰為地者也”,又“大抵脾胃虛弱,陽氣不能生長,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臟之氣不生。”可知,脾胃健運,升降得宜,才可維持機體“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腑”之正常升降運動。在此過程中,氣機生長、升發又尤為重要,李東垣認為只有脾氣升發,谷氣(水谷精微)上升,元氣才得以充沛,陰火潛藏;并以荷葉用藥之理,類比胃氣升發之機:“荷葉之體, 生于水土之下, 出于穢污之中,而不為穢污所染, 挺然獨立。其色青, 形乃空,青而象風木者也, 食藥感此氣之化, 胃氣何由不上升乎?”亦為此理。
且其言以青象風木而得以升胃氣,可見少陽春升之氣與脾胃亦關系密切。少陽之氣上升,則諸陽皆升,胃氣亦升;倘肝膽之氣不升,陽氣不升,則必致病及脾胃,即所謂“土得木而達,木賴土以培之”。
2 風藥功效特點探析
2.1 扶脾陽而復氣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以陰陽之升降變化以提挈人體機能變化之道,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云,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 云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 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基于此,李東垣推演脾胃升降之道理,提出脾胃以行清陽而上,升發運化而為用,脾胃氣虛或氣陷下不升皆為病矣。正如《脾胃論》中言:“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曰內熱。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于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寒獨留則血凝泣;血凝泣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澀,故曰寒中”,即是脾陽不升所致病者也,脾胃不升則營衛不充,元氣受損, 故治當升陽益胃,創立補中益氣湯升陽提陷。《脾胃論》中稱補中益氣湯方中升麻“引胃氣上騰而復其本位,便是行春升之令”;柴胡“引清氣,行少陽之氣上升”; 《內外傷辨惑論·飲食勞倦論》亦評論升麻柴胡兩藥為味之薄者,作引清氣上升之用: “胃中清氣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 引黃芪、人參、甘草甘溫之氣味上升……二味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清氣上升也。”黃芪、人參、甘草,以甘溫之性補脾陽,借助升麻、柴胡清輕之性,以升脾陽。配白術“降胃中熱”,當歸養血和營,陳皮理氣和胃。 此即李東垣之謂 “用辛甘之藥滋胃,當升當浮,使生長之氣旺”。
2.2 散濕邪而醒脾胃李東垣認為,倘濕濁內盛可留而為患,有礙清氣升發,多生飧泄。提出“必用升陽風藥即差”,即所謂“升陽除濕法”。縱觀歷代醫家治濕之法,“芳香化濕,苦溫燥濕,淡滲利濕”功效不容置疑;治泄之法,“淡滲、升提、燥脾、溫腎、固澀”等,亦多效于臨證。然李東垣未囿于利濕、止泄之一端,擅長以“風藥”勝濕,認為“濕乃土之氣,風乃木之氣,木能勝土,風能勝濕,乃五行相勝之理;濕盛于地,唯風能干之,亦自然之理”。淡滲之法,難以速效,更有礙于氣機,唯降而不升,對于體弱者,久用有重遏陽氣之嫌。“用淡滲之劑以除之,病雖即已,是降之又降,是復益其陰,而重竭陽氣”。故李東垣主張在健益脾胃的基礎上運用風藥,勝濕之外,更能升引下陷之清氣,且疏調氣機,外通腠理,使濕邪外出有路,而如升陽除濕防風湯中,“以風藥升陽,蒼術益胃去濕……如得通,復以升陽湯助其陽”[3]。
2.3 除郁火以平陰陽陰陽者,升降出入不已,如環無端,互根互用,陰陽相輔,化生萬物。李東垣提出陰火之理論,《脾胃論》云:“若脾之清氣不升,則陽氣郁遏日久化熱生火;若胃之濁陰不降,則濕濁流注于中焦;清濁相干、濕熱蘊結而致陰火上沖。”陰火的根本病機是脾胃氣虛,陽郁生火,濁陰不降,清濁相干,故而火浮,而非陰虛火旺之故。脾胃論中言“脾為勞倦所傷,勞則氣耗,而心火熾動,血脈沸騰,則血病,而陽氣不治,陰火乃獨炎上,而走于空竅,以至燎于周身”,指出,若脾胃氣陷,清陽不升,水濕內停于中下焦,陰火內郁,而見發熱;陰火熾盛,又可內灼耗傷津血。更有甚者,陰火升騰炎上,以至“燎于周身”。李東垣遵《黃帝內經》“火郁發之”之訓,立升陽散火法,創制升陽散火湯、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等方劑,以升麻、柴胡、葛根、防風、羌活、等味薄氣輕之風藥,輕散中焦郁熱,使陽氣伸展、清氣上浮;配伍補脾益氣,酸甘化陰或清熱燥濕藥。諸藥相合補益與升散并用,使脾陽得升而脾土自醒,氣機條暢而陰陽相濟。正如《脾胃論》中闡述:“瀉陰火以諸風藥,升發陽氣以滋肝膽之用,是令陽氣生……陽陽本根于陰,惟瀉陰中之火,味薄風藥,升發以伸陽氣,則陰氣不病,陽氣生矣”。
2.4 疏少陽以和脾胃脾胃受納水谷,為升清降濁之樞;少陽膽者,為少陽春生之氣,亦主升發,經云:“凡十一臟取決于膽也”。少陽之氣與脾胃之氣均有升發之功,互相依存,一損俱損。胃氣升發又賴于少陽膽氣疏泄,二者皆生于中焦,故李東垣稱二者起源一也。李東垣曰:“肝陽不足不舒, 風藥疏補之”,因風能瀉木,以疏泄肝膽之氣,且風藥升提疏散之性恰能遂膽之疏泄、肝之條達之性,療效遠較一般理氣之品為佳。《脾胃論·脾胃勝衰論》中,治療肝木妄行之胸脅痛,腹中急痛,用柴胡為君,防風、甘草、肉桂為臣,羌活、獨活及健脾諸藥為佐藥,亦為佐證[4]。
3 風藥健脾臨床應用探討
3.1 風藥健脾以治療克羅恩病凌發樣等[5]總結李飛教授治療炎癥性腸病的經驗,認為炎性腸病患者病機多以脾虛為主,脾虛不能輸布水液,聚而生濕,且久病入絡,多發瘀血,出現黏液膿血便。在治療中,治療總以健脾為主,脾氣健運則氣機條暢、生化有源,“健脾”在本病的治療、轉歸與愈后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健脾之法,又重視理氣行滯,加陳皮、半夏、木香、枳殼以行氣健脾,亦為“風藥健脾”的一種體現。王洮等[6]認為,風藥則可健脾以祛濕、行氣以祛瘀,不僅可以從整體上調節氣機,有助于正氣的恢復,達到扶正祛邪,且其可以直接作用于致病之邪痰濕瘀邪;風藥可激發陽氣,又可以祛濕,在炎性腸病的治療過程中發揮調節氣機、扶正氣、祛實邪等作用。認為“考慮風藥的性質功能,無論是消有形之邪的堆積,還是調無形之氣的升降,都可以嘗試配伍”,為臨床用藥提供了新思路。
3.2 風藥健脾以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林志賓等[3]學者應用升陽除濕法,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患者,取得較好療效。通過使用風藥的藥物(如蒼術、防風)以達到祛除濕邪、恢復正氣的目的,潰瘍性結腸炎基本病機為脾不升清,濕邪為患,處方重視以升麻、防風等風藥佐以健脾除濕藥物,認為潰瘍性結腸炎部分可見脾濕之象,以升陽除濕為正治之法,尤以風藥治療脾虛濕盛、氣郁血瘀型慢性潰瘍性結腸炎的療效甚為滿意。治療中,重視蒼術與防風配伍,“蒼術開濕郁之力雄壯,以升清陽;防風則為風中潤劑,與蒼術之辛燥相配,則制其燥性而加強鼓舞中陽”。意在使得陽氣升騰,脾氣來復,則濕邪可除。
3.3 風藥健脾以預防結腸癌前病變結腸癌前病變以大腸主津功能失司而致津液重吸收障礙為特征,且進一步導致氣血津液精神升降出入障礙等病變,付西等研究證實,以具有辛散宣化、升發清陽、降泄濁氣、起津潤燥之風藥,以達到升舉清陽、宣通玄府以調暢氣機, 托舉邪氣外解,升津潤腸等治療效果,從而提高病變細胞凋亡水平,促使病變細胞凋亡,從而阻斷結腸炎與結腸癌前病變之間的發展通路, 逆轉結腸黏膜上皮內瘤變[7],從而達到預防結腸癌前病變的效果。
4 結語
李東垣認為“脾胃不足之證,須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 引脾胃中陽氣行于陽道及諸經,生發陰陽之氣, 以滋春氣之和也”[2],臨證中重視調暢脾胃功能以治療內傷諸證,善用風藥升清陽助運化以健脾。通過對李東垣著述的研究,試對“風藥健脾”一說進行探析, 以期對后世體悟其中方藥運用之理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