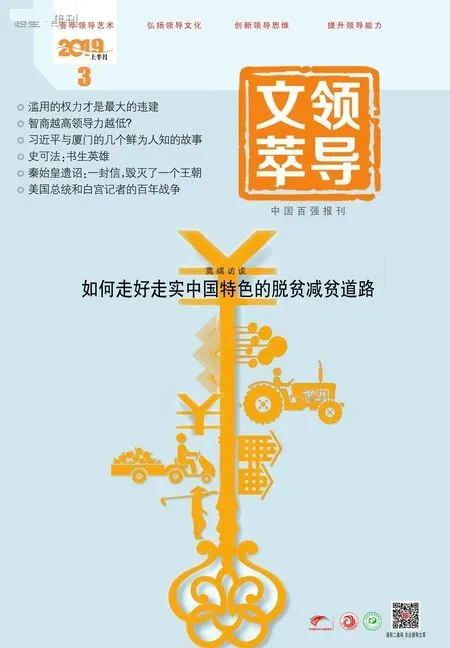史可法:書生英雄
章憲法
書生意氣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南京衙門的地位驟然上升,匡扶社稷的重任自然落到南京官員頭上。北京連兵部都沒有了,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自然由此而顯得舉足輕重,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作為兵部尚書,史可法的信息相當滯后。四月初一,崇禎帝的后事都處理完了,史可法得到的信息還是李自成逼近京師,準備率師北上勤王。直到十四日,史可法才從南下的官員那里確認崇禎帝已殉社稷。他悲痛欲絕,以頭搶地,甚至準備自盡以表明對朝廷的忠貞。
王朝的生死關頭,史可法的抉擇同樣是進退維谷——崇禎帝自殺,王朝群龍無首,又面臨清軍與民軍的雙重打擊。迅速謀立新君,做出有效的應對,才能避免王朝樹倒猢猻散。南京官員在謀立新君問題上非常敏感,正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史可法表現出的手足無措,直接導致他在弘光朝陷于政治困境。
崇禎帝朱由檢身死,三皇子均未逃出,繼位者只能是各地的藩王。以血緣關系講,崇禎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孫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最有資格當選。但桂、惠二王均在廣西,距南京太遠,且均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福王以兄弟關系繼承更為妥當。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兒——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亂逃到淮安,擁立新君,他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恰在這時,福王朱由崧從封地洛陽逃到了江南,新君人選也由此變得明朗起來。
朱由崧,明神宗朱翊鈞之孫,福王朱常洵之子,崇禎帝朱由檢堂兄,崇禎十六年襲封福王,封地洛陽。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京諸勛貴大臣議立新君。無論就近救急,還是按倫序,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朱由崧。可是,由于牽涉到黨禍問題,東林黨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東林黨人將再次受到打擊,因此一致反對立其為新君,主張擁立潞王。
究竟是立朱由崧還是立朱常淓,作為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這時的態度舉足輕重。
真實的內心里,史可法認為按倫序迎立福王是對的。于是,史可法又試圖說服東林黨人,放棄迎立潞王。
史可法給東林官員講歷史故事,目的是想讓他們不固執己見,但明顯又是兩頭不討好。猶疑糾結的史可法,親自前往浦口,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議。最后,二人達成共識: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
謀劃完了,史可法靜靜地等著好消息。
馬士英雖說也是書生出身,卻沒有一絲書呆子氣。當軍方開始動作,出手謀劃擁立福王時,馬士英果斷轉舵,成為擁立福王的領軍人物。至于史可法那邊,他連個招呼都沒打。
“定策”中的重大失誤,是史可法最終在弘光朝退出核心層的根本原因。
史可法不贊成福王朱由崧即位,當馬士英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杰發兵護送福王南下時,諸多官員要么遠迎到儀征,要么迎接到燕子磯,最近的也迎接到南京城外——這是向新主子表現的大好機會。史可法卻始終忙于督師,雖精神可嘉,但這在政壇上,不過是一種書生的可愛。
困頓時事
史可法出朝督師,實際權力并沒有減少。史可法直接控制的是所謂“四鎮”,也就是南明的軍事主力。
史可法雖然有收復失地之志,但實際上“四鎮”均在南京附近,體現的是他消極防守、保存江南一隅的真實意圖。
史可法督師江北時,正值李自成敗出北京,滿清入主京師之時,河南、河北、山東等地一度出現統治真空。滿清兵力不足,無心也無力控制如此廣大的地區,而當地明朝的殘余勢力,紛紛組織武裝自保,并盼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復失地。史可法駐守與山東接壤的江淮,在不費一兵卒即可收復大片失地時,為什么按兵不動,還向多爾袞派去“友好使團”?史可法上奏時說:“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后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滿清不過是一隊人馬“來索錢糧戶口冊”,史可法卻言“爭之非易”。在史可法的眼里,那里已經是“胡土”!
壯烈英雄
弘光元年四月十三日,清軍至泗州,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當夜渡過淮河。面對嚴峻的形勢,史可法居然驚慌失措。
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
一日三調,史可法糊涂了,把應廷吉這幫人也弄糊涂了。
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杰兩部將領已投降了清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也投降了多鐸,他們都在攻打揚州的路上。揚州城里,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當清軍初抵城下,劉肇基建議乘敵立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
不主動出擊,那就死守。揚州城西門地形較低,城外高丘能俯瞰城下,又長滿林木,諸將建議砍掉,否則對敵有利,于己不利。史可法說:這是人家的祖墳,我怎么忍心砍伐?你們認為這里不好守,我自己帶人守。
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岐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人進入揚州城。兩人的意思是劫持史可法,獻城降清。史可法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但他對二人說:“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岐鳳不好下手,率部出城,史可法就這么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出城投清。
二十四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其下城樓,史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他,但史可法不從。史可法被俘遇難,之后便是多鐸的屠城。
最后的史可法,充滿道德上的優越,與全揚州城的人共同殉難。(摘自《明朝大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