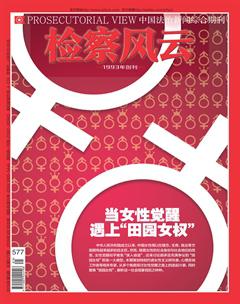不茍取
鄭海嘯
許衡字仲平,是元朝初年的理學家。有一年酷暑,他和一幫人在戶外,非常口渴。道路旁有一棵梨樹,人們都爭著摘梨吃,只有許衡一個人正襟而坐在樹下,安然如常毫不動心。有人問他為什么不摘梨吃,他說:“不是自己的東西卻去拿,是不可以的。”那人說:“現在世道這么亂,這梨樹沒有主人了。”許衡回答說:“梨沒有主人,難道我的心也沒有主人嗎?”世道越亂越要堅持自己的本心,這是對的。但無主的梨樹確實是不摘白不摘,熟透后最終還是會爛在地里的。許仲平的這種“義不茍取”在我看來未免太“道學氣”,或是他當時還不夠渴。
教育學家梅貽琦先生一生兩袖清風沒有積蓄,病后住院費和死后的殯葬費都是校友們捐助的。據他夫人韓詠華回憶:在病床旁邊有一只他從不離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開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歷年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人無不為之動容。他雖幾次出任當時教育部高層領導職務,又長期獨司數十萬美元的清華基金,卻能一生緊守原則,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沒有留下任何遺產。于是有人說:“他在母校十幾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茍取分文,在污染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為。只這一點,已是可以為萬世師表。”梅先生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能如此不茍取分文,難能可貴,但若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遵紀守法是做人的本分,畢竟社會進步了。
還有一種不茍取,即使社會再進步,能做到的人恐怕仍不會太多。1984年,法國大使館通過中國社科院外事局通知錢鍾書,法國政府欲授予其勛章,理由是他“對中法文化交流的貢獻”。錢鍾書請外事局代其堅辭:“我自忖并無這方面的貢獻,不敢冒牌。”2014年,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通知楊絳,在學院建立700周年之際,該院推選楊絳先生為榮譽院士。楊絳回復:“我很榮幸也很感謝艾克賽特學院授予我榮譽院士,但我只是曾在貴院上課的一名旁聽生,對此殊榮,實不敢當,故我不能接受。”這次當選榮譽院士的全球只有兩位,一位是西班牙王后,一位就是楊絳。學院對楊絳的拒絕非常意外。他們怕楊絳誤解學院授予她榮譽院士,是因為她是錢鍾書的遺孀,所以再三解釋,不是那么回事,是由于她對塞萬提斯研究做過重要貢獻,本身是杰出女性學者。但楊絳不為所動:“我如今一百零三歲,已走到人生邊緣的邊緣,讀書自娛,心靜如水,只求每天有一點點進步,過好每一天。榮譽、地位、特殊權利等,對我來說,已是身外之物;所以很抱歉,雖然我非常感謝你們的深情厚誼,我仍不得不辭謝貴院授予我榮譽院士的榮譽,敬求你們原諒和理解。”對于送上門的榮譽,覺得自己受之有愧(其實他們實至名歸),就堅決不要,這是何等境界!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