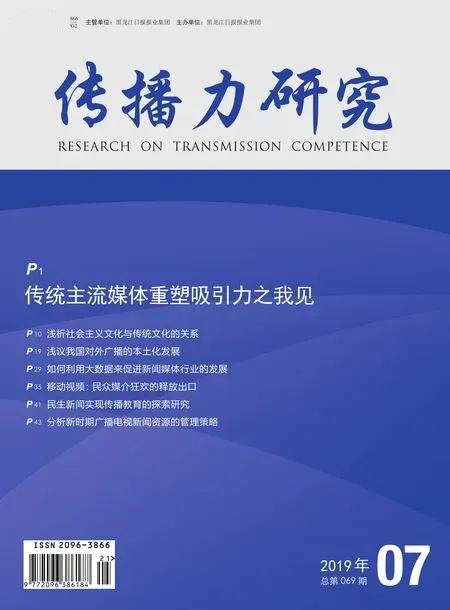傳播儀式觀視角下的廣場舞現象淺析
陳夢圓 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一、傳播儀式觀概述
詹姆斯?凱瑞將傳播這一概念分為傳播的傳遞觀和傳播的儀式觀:傳播的傳遞觀即是傳遞信息的過程;傳播的儀式觀認為,傳播是共享信息的表征,強調文化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凱瑞認為,傳播更多地只是一種儀式,而不是傳遞或運輸。
目前,“儀式”還沒有一個明晰統一的定義,而不同的學者對“儀式”的描述和側重也有所不同。涂爾干對儀式的闡釋是基于對社會生活事件過程的考察和思考,他認為,“神圣/世俗”的關系和行為被看作二元對立的基本社會分類和結構要素。而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格爾茨認為,儀式是構成民族的精神意識的重要方面。
在國內,陳力丹教授在其文章《傳播是信息的傳遞,還是一種儀式?》中深入探討了傳播的儀式觀。由此,也引發了傳播儀式觀在中國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熱潮。
二、廣場舞研究發展
廣場舞的快速發展也成功帶動了很多研究,對廣場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廣場舞健身功效、社會空間利用、社會噪音污染、社會認同等方面。
張兆曙從個體與群體的關系出發,將廣場舞看作是群體性行為,稱其是一種群體性的表達和形式化的表達,是“個性化時代的群體性興奮”。王芊霓更關注廣場舞的“污名化”。她認為,廣場舞與主流價值觀的矛盾沖突,造成了廣場舞“污名化”的現象。開薪悅和孫龍飛則認為廣場舞的“污名化”與大眾媒體的報道有密切的聯系。他們提出,為了突出社會中的沖突與矛盾,刺激受眾對相關信息的關注,媒介呈現的“廣場舞大媽”形象多以負面消極為主。
三、傳播儀式觀下的廣場舞現象
(一)儀式感的塑造與重復
儀式運用一系列象征性符號進行展示和表現,希望能夠達到意義上的一致性。2019年初,山西一小學校長帶師生跳“鬼步舞”走紅網絡。視頻中統一的服飾和統一的隊伍意味著共同的符號表達,老師和同學們分享著共同的意義空間,強調了共享的文化信仰。傳播儀式觀下的鬼步舞,不再是舞蹈舞步的簡單傳授,而是跳舞行為背后一致的文化目標和文化表征。
廣場舞是一種核心力量的固定性和形式表達的單一性為主要表現形式。以高效有序的方式開展廣場舞并使之成為一種“儀式”,便要求廣場舞具有固定的運作模式,如固定的時間、地點、不變的舞曲、簡單的舞步等,進行一種高分貝的單調重復。
(二)文化空間的共享
在傳播儀式觀的視角下,符號和象征意義都能夠在傳播的所有過程當中深刻的體現出來,這是一個不間斷的在建構和重構的過程。這一過程可以看作是文化儀式,儀式的功能讓所有參與者在廣場舞中聚集起來形成社群,分享經驗,分享屬于他們這個群體特有的文化。
廣場舞作為團體操,十分強調團體的協調統一。為了更好的組織和管理舞隊,每一個廣場舞群體都會設有管理員一職,負責隊伍的招生宣傳、隊員的團費繳納等。規范化的管理手段使得“廣場舞大媽”全面參與、深入體驗到了廣場舞群體構建的文化空間,并在這一空間基礎上建立起對該群體的群體歸屬感。
同時,廣場舞作為一種舞蹈,充當了“廣場舞大媽”之間主要的交流方式。“廣場舞大媽”實現了自我展示和自我表演,滿足了自身表達的欲望,完成了自我塑造,建立了對于自我的“同一感”,并對其他隊員也產生了認同感。在廣場舞隊員進行以上的“自我”和“他人”的非語言溝通過程中,廣場舞成為他們彼此之間互相表達和展示的最佳平臺。
(三)身份認同
凱瑞認為,傳播的儀式觀看來,傳播作用并不是提供信息,而是一種確認(conf i rmation)。也就是說,傳播的作用并不只是簡單的傳遞信息的過程,更多的應該是達到更深層次的精神交流。
從傳播的儀式觀層面理解,廣場舞對于“廣場舞大媽”最重要的意義并不在于其滿足了生理上的健身需求,而在于其滿足了一種更深層次的心理需求。“廣場舞大媽”通過自我展示和自我表演,得到了他人的認同,并在與他人的舞蹈交流中,達成了對自己身份的認同。自我與他人的互動,形成了群體認同感和歸屬感,并逐漸營造出成員間彼此認同的共同的文化空間,最終在該特定的文化空間中塑造出屬于“廣場舞大媽”特有的身份認同。
四、結語
從媒介到文化,從傳遞到儀式,詹姆斯?凱瑞關于傳播儀式觀的研究為傳播學研究領域深入探討傳播現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儀式作為意義的象征,是人類的文化存在。而文化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理解廣場舞和“廣場舞大媽”就要理解他們試圖通過廣場舞想要進行的意義表達和共享——在日益疏離的個性化時代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和與他人對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