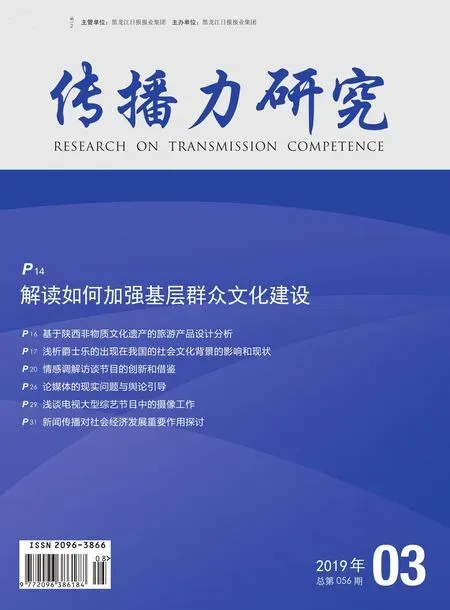談話節(jié)目的文化價值研究
黃芳芳 重慶市渝北區(qū)廣播電視臺
上個世紀,中國談話節(jié)目在工業(yè)化節(jié)目生態(tài)中隨波逐流,成為了一味效仿、創(chuàng)新乏力的俗媒文化快餐,明星訪談、娛樂訪談模仿成風(fēng),只關(guān)注形式創(chuàng)新,缺乏內(nèi)容品味,使得談話節(jié)目一度淪為偽文化價值輸出的名利場。歷經(jīng)二十七年的發(fā)展,中國談話類節(jié)目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由傳播本位到受眾本位的思想轉(zhuǎn)化,而在現(xiàn)代傳播方式中,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更是給予談話節(jié)目更大的發(fā)展空間,不僅節(jié)目思想性、風(fēng)格性得到彰顯,節(jié)目與受眾實現(xiàn)了即時、直線的交互傳輸。談話節(jié)目在比以往任何都能夠在大眾傳媒立場下,讓人們的思想得以充分表達。在多種的文化價值交融,語境交融的今天,談話節(jié)目不僅沒有消退,而且還在年輕人心中發(fā)展成為新思想、新時代的文化陣地。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價值輸出呢?文化價值是一種關(guān)系,它包含兩個方面的規(guī)定性:一方面存在著能夠滿足一種文化需要的客體。另一方面存在著某種具有文化需要的主體,當一定的主體發(fā)現(xiàn)了能夠滿足自己文化需要的對象,并通過某種方式占有這種對象時,就出現(xiàn)了文化價值關(guān)系。而文化價值的產(chǎn)生,并不局限于文化客體,也就是內(nèi)容輸出本身,而是隨著多樣的節(jié)目形態(tài)和播出形態(tài)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轉(zhuǎn)變。而談話節(jié)目的受眾也從以前的精英階層轉(zhuǎn)向了普通大眾,在這樣一個信息、輿論爆炸的時代,已經(jīng)不再會產(chǎn)生現(xiàn)象級的談話節(jié)目了,但是如何讓談話節(jié)目突出重圍,就會變成更大的挑戰(zhàn)。
一、談話節(jié)目的品牌價值
與同類型的談話節(jié)目相比,節(jié)目品質(zhì)不高、缺乏品牌特色、有效信息少等等問題,成為了制約談話節(jié)目品牌價值的最大掣肘。如何打造節(jié)目特色,如何留住主題受眾,樹立品牌價值是節(jié)目生存的前提。相對于這些問題來說,作家許知遠打造的一檔名叫《十三邀》的談話欄目很有代表性。這檔節(jié)目創(chuàng)造除了獨一無二的節(jié)目風(fēng)格,而許知遠作為這檔節(jié)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把整個節(jié)目風(fēng)格的和自身身份特征以及主持風(fēng)格貼合的非常緊密,在《十三邀》的片頭中,許知遠用內(nèi)心獨白作為開場,從一開始就為節(jié)目定下了基調(diào),我不是主持人,我不是電視人,我只是個愛發(fā)問的作家,我從作家的角度發(fā)問,這不僅僅是一段獨內(nèi)心白,而是賦予了這個節(jié)目以靈魂,節(jié)目還沒開始,品牌價值就已經(jīng)形成了,也正符合當下的大眾審美特性,即獨特性表達。
二、談話節(jié)目的獨特的文化視角
談話節(jié)目的文化視角,是它看待世界的獨特方式,什么樣的文化視角取決于該節(jié)目的姿態(tài),主要體現(xiàn)在“對談”中傳遞的信息。例如《魯豫有約一日行》是類似于真人秀與談話相結(jié)合的節(jié)目形式,它之所以這樣結(jié)合,是因為它們想呈獻給觀眾的是置身于生活或工作場景中的采訪對象,那么談話內(nèi)容不僅僅只有談,重要的在于“呈現(xiàn)”二字,而呈現(xiàn)置身于真實環(huán)境中的人物,就是這檔節(jié)目的文化視角。而《十三邀》的文化視角,則更傾向于主持人許知遠基于思想層面的探討,比如人的多面性,以及這種多面性帶來的困擾或原因,以及附加的影響,而這影響又會如何作用與反作用與個體或群體,甚至于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而每個節(jié)目的文化視角決定了它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呈獻給受眾,這正是談話節(jié)目的核心意義所在。
三、談話空間的價值取向
在談話空間中,談話場的形成對于談話節(jié)目的文化價值取向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真實有效的談話場是營造氛圍的重要因素。許知遠在《十三邀》其中的一期節(jié)目中采訪李旦,兩個不同時代的代表進行的對話,非常尷尬,對于以往來說,這種節(jié)目營造的談話場是不能夠成立的,因為談話氛圍的失敗必然導(dǎo)致節(jié)目失敗是個毋庸置疑的定律。可是在這個時代,這種尷尬的談話營造了另一種空間和意境,雖然不是刻意的迎合大眾,可卻因真實的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誰說交談就該是友好平和的?激情四射的意見碰撞更應(yīng)該值得推崇。由于許知遠身上特有的知識分子的清高和傲氣,以及他直白的發(fā)問,都成就了《十三邀》獨一無二的談空間意境。主持人和被采訪者之前的情感真實,只有在平行空間的有效交流才更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
談話節(jié)目作為主流媒體的價值理念時期,其傳播目的和效果主要呈現(xiàn)的是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以宣傳主流文化為己任。經(jīng)過多年發(fā)展至今,中國視談話節(jié)目已經(jīng)進入多元文化時代,我們不經(jīng)能夠看到提問的聲音、討論的聲音,還有更多良性的質(zhì)疑聲和眾多國籍的聲音,在這個多元的文化時代,不管西方還是東方,也不論大眾還是精英,其中的界限已經(jīng)逐漸消融,可是仍有些談話節(jié)目的文化價值理念仍然存在的分歧與矛盾,比如說一味地模仿抄襲、追求商業(yè)利益最大化、娛樂最大化等等弊端,而這個弊端是阻礙的談話節(jié)目文化價值輸出最大阻力。而談話節(jié)目的要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該如何實現(xiàn)自身的文化價值?都是基于談話節(jié)目自身的品牌、視角以及價值取向的,他不僅是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概括,更是人文精神的體現(xiàn)。而這種人文精神,是多元的意識形態(tài),是以人為本的,對整個社會、國家、人類的關(guān)懷,不僅要關(guān)注大眾也要關(guān)注個體,這才是談話節(jié)目的文化價值的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