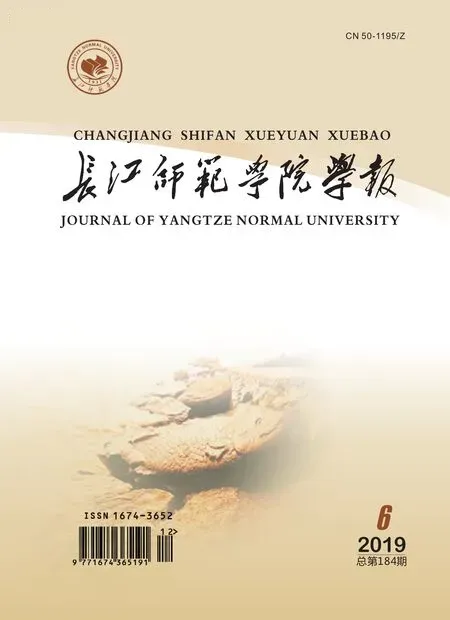春秋嘉言“敬”義發微
胡曉紅
(太原師范學院,山西晉中 030619)
“敬業”是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范疇之一,溯其淵源,當與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敬”觀念有關。從現有文獻來看,“敬”已是西周青銅器銘文、《詩》《書》中出現頻率較高的詞語與概念。春秋時期,貴族文化人的言論為當時史官記錄,并作為“嘉言善語”載錄于《國語》《左傳》中而流傳至今,即本文所謂“春秋嘉言”,其中不乏對“敬”觀念之論說。考以春秋時人的思想世界,則神祇、天命、人本等觀念側重于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而統歸于“德”行范疇的敬、忠、信、勇、仁等則更指向人的內在品性的修養;綜觀春秋時代思想研究,認識論范疇多為學者所論,對具體而微的德行范疇的縱深研究則有所不足。因此,本文擬以“敬”觀念為例,立足文本解讀,試探其豐富內涵與微義。
一、春秋嘉言“敬”義溯源
“敬”觀念不是春秋嘉言的發明,至少在西周初年,已經產生了這一觀念。西周青銅器銘文、《詩》《書》等西周文獻中,有大量“敬”字的使用。許慎《說文》解“敬”為轉注字,“敬,肅也。”段玉裁注:“肅者,持事振敬也,與此為轉注。”又進一步舉近義字以釋其意:“忠,敬也;戁,敬也;憼,敬也,恭肅也;惰,不敬也。義皆相足。”[1]434“敬,肅也。謙與敬義相成。”[1]94此釋作為字義之“敬”。若從兩周文獻語料來看,作為一種價值觀念的“敬”,其內涵已包含了敬畏、恭敬、嚴肅、認真、警戒等多層意義,那么,除了直接使用“敬”字,文獻中凡表達此一意義的其他語詞如“肅”“恭”“祗”“慎”“儆”等,皆屬于周人“敬”觀念的范疇。
青銅器銘文是目前所見的最為確定的西周原始文獻,內容多敘賞賜事,部分金文在敘事之外加告誡教導語,“敬”多出現于此類金文中。“敬”為動詞,按照動作指向區別,可以分為敬天、敬王、敬德、敬事等,對象不同,“敬”義所指側重亦有不同,對上天、周王之“敬”多敬畏、恭敬義,對德性、事務之“敬”則多敬重認真義。以西周成王時期的何尊為例,其中所載的成王誥辭中,既有敬天的表達,如回首往日云:“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眂于公室有爵于天”“廷”,馬承源引《廣韻》曰:“敬也”,釋“爵”為“恪”,“敬也”。亦有對上、對事之敬,如云:“徹令敬享哉”,其義為“通曉命令,敬事奉上”[2]21。總體來看,西周金文以“敬事”居多,如同為成王時的大保簋云:“大保克敬無譴。”[2]24意謂大保能常慎敬其事而無災譴之咎;康王時期的大盂鼎云“若敬乃正,勿廢朕令”[2]38,義為“謹慎地履行你的職責,不能違棄我的誥誡”[2]41;恭王時期的師酉簋、懿王時期師虎簋皆有“敬夙夜勿廢朕令”[2]126之句;孝王時期大克鼎“敬夙夜用事,勿廢朕令”[2]216;懿王時牧簋、孝王時師克盨皆有“敬夙夕勿廢朕令”[2]223等,此類表述多見,其義主要為認真負責地對待職務、履行王令。
《尚書》中的《周書》部分,學者普遍認為是其中最可信的西周史料,自《大誥》至《顧命》產生于武王、成王、康王時期,其時限雖短于金文,而對“敬”這一觀念的應用和闡發竟達三十余處,其內涵意義也更為詳細豐富。首先是敬畏義,常以“畏”“忌”“懼”等詞表達,或與之連言。如《無逸》篇云:“其在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3]1532。傳達的都是“敬畏”天命與人事的心態。其次是謹慎認真義,多屬于對職事之“敬”。和西周銅器銘文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對即將赴任的諸侯進行敬業的勸勉外,更多的是表達對待刑法的謹慎之義,如《康誥》反復言說對法之敬:“嗚呼!封,敬明乃罰”[3]1319;“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3]1341。《酒誥》曰:“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3]1403《立政》篇云:“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3]1657再次是敬重義,側重于對一己之“敬”,常與“德”相連。“德”是人后天通過修養而擁有的品質,《周書》中多次言“敬德”,實質上是自我看重并不斷在行為上修養德性。
《詩經》無論是作者隊伍、創作時代還是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都比金文和《尚書》廣泛,“雅頌”之詩有別于政令式的《周書》,“敬”觀念在《詩》中有獨特的闡發。《詩經》對“敬”的心理狀態有形象描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4]414“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4]420《詩經》中“敬”的對象同樣廣泛,有于天、帝、神之“敬”,如:“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4]636“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4]662“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4]718有于職事之“敬”,如“嗟嗟臣工,敬爾在公”[4]722;“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恭爾位,正直是與”[4]447。有于人之“敬”,在此意義上,《詩經》更為突出對于一己之“敬”,不泛言“敬德”,多論對自己威儀的敬慎,“敬爾威儀”之類的表述在《小雅·小宛》《大雅·民勞》《大雅·抑》《魯頌·泮水》等多首詩中頻頻出現。因為對一己威儀之“敬”,《詩經》作品發展出“敬”的審美意義,“祗祗”“肅肅”“穆穆”“翼翼”等常用來形容一種嚴肅、整飭、端莊之美。如“有言有翼,共武之服”,毛傳“翼,敬也”[4]358;“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4]495;“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惟辟公,天子穆穆”。鄭箋“肅肅,敬也”[4]734。皆是“敬”由心態而表現的外在審美。
從緣起和歷史文化演進來說,“敬”的心態最初應當和祭祀有關,主要指對昊天、上帝、神明等恭敬、敬畏意。隨著社會人事的發展,面對大邑商為小邦周所滅,周人深深反省歷史,“敬”觀念在西周得到極大的豐富,不止于神明上帝,更有對于王事、對于一己的言行舉止的敬畏、敬重、嚴肅、認真之義,成為西周上層統治者所普遍認同和倡導的重要價值觀念,也是春秋嘉言闡說“敬”觀念的基礎和源頭。
二、自律警戒的春秋嘉言之“敬”
《左傳》兼記言記事,劉知幾《史通·申左》云:“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5]391韋昭《國語解敘》亦言《國語》之作,乃是采錄前世“邦國成敗,嘉言善語”而成[6]661,《左傳》《國語》所載嘉言善語是了解春秋時期“敬”觀念的主要文獻。遍檢《左傳》《國語》所載言論,依照上文對于“敬”觀念的內涵界定,《左傳》論及此一價值范疇有五十余處,《國語》近三十處。綜觀春秋嘉言對于“敬”的論說,其內涵首先突出于指向一種普遍的警戒心態。
普遍的警戒心態來自周人敬畏天命的觀念,如前所論,這種觀念在《詩》《書》中得到反復表達,春秋時人對上天、神祇的敬畏仍然普遍地存在。公元前683年,宋國發生水災,魯莊公派使者慰問,宋閔公答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臧文仲贊曰:“言懼而名禮,其庶乎!”[7]153《國語·楚語下》載觀射父論祭祀強調“敬其粢盛”,又曰“其誰敢不齊肅恭敬于神”[6]567,“敬”在這里都是側重于對上天、神靈的恭敬、敬畏、虔誠之意。之所以敬畏天神,是以為人類的命運為上天神靈所掌控,對天、神的敬畏又常及天命,文公十五年《左傳》季文子引《詩》批評齊侯不敬畏天命:“不畏于天,將何能保?”[7]340然而“敬畏天命”的觀念本身包含了人的理性的覺醒,敬畏不是一味地畏懼和順從,而是試圖通過人對自身進行約束,從而求得上天神靈的佑護,春秋嘉言正是在這一點上發展了“敬畏天命”的觀念,大量地從警戒之心的角度闡說“敬”的內涵,“敬畏”的觀念于是逐漸從以神為本轉向以人為本。
警戒之心是獲得成功時應該保有的,宣公十二年《左傳》載晉欒書言楚人取得克庸的輝煌戰果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后”[7]393。警戒之心是面對弱小勢力也不應當放松的,僖公二十二年《左傳》載邾人出師于魯,魯僖公因其為小國而輕視邾,臧文仲引《小雅·小旻》《周頌·敬之》以敬畏之意勸諫僖公要時刻保有儆懼之心:“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7]247警戒之心在春秋嘉言中無盡蔓延,包括警戒安逸與享受、賞賜與財富、情感與欲望等。
安逸與享受是春秋嘉言所警戒的。公元前585年,晉國欲遷都,韓厥以“國饒,則民驕逸”[7]442反駁諸大夫,力主遷都新田,其主要理由即是警戒人心的驕逸;魯國臧氏代有良卿,臧僖伯、臧哀伯,皆有對魯君的諫諍良言,規勸魯隱公、桓公作為人君應當警戒安逸。楚國在春秋時期,偏居一隅而能夠入主中原稱霸諸侯,或許和楚人警戒安逸的文化觀念有關,如晉卿欒書在邲之戰前夕所論楚國國情:“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7]393這種心態在楚人言論中尤其多見,倚相《諫申公子亹老耄自安》舉例歷史名人自警故事,勸諫申公應當時刻保持對安逸的警戒,其文曰: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圣武公。子實不睿圣,于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御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6]551
以衛武公之年高,本當安享晚年,而衛武公卻要求在朝卿大夫勿忘勸諫自己,自是對安逸的儆懼心態。又藍尹亹《論修德以待吳》(《國語·楚語下》)云:
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于色,身不懷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6]578-579
這段言辭以前后兩代吳王闔閭與夫差為材料進行對比,其主旨則表達對安逸的批評與警惕。闔閭不貪于口、耳、目、身的感官享受,這是對安逸生活的自律和警戒,因而“得民”“濟志”;相反地,夫差則唯“私好”是務,放縱安樂,進而推論說,安逸必然導致失敗,不足為懼。
賞賜與財富是春秋嘉言所警戒的。賞賜代表了一種“得”,在春秋政治活動中主要包括物質與禮節名譽。面對物質與名譽,春秋嘉言所反映的觀念不是汲汲于獲取和占有,而是戒懼,即側重于反問自己:是否有資格擁有這種物質、名譽。因為在他們看來,如果占有和自己的功績、德性等不相當或不該有的賞賜,可能會給自己帶來災難。公元前672年,齊陳完因政權之亂而從陳國逃奔齊國,以“不辱高位”拒絕齊侯任其為卿的賞賜;公元前623年,衛國寧武子聘于魯,文公以大禮晏享,寧武子《論干大禮以自取戾》(《左傳》文公四年)解釋不敢接受越禮之賞;公元前562年,鄭人賄賂給晉侯一批女樂,晉侯分而賞賜魏絳,魏絳以《請以賞樂辭晉侯》(《左傳》襄公十一年)予以拒絕,皆屬此類。這些賞賜常常關乎富貴,晏子《語子尾論不欲富》(《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表達對財富的警惕;鄭國卿大夫公孫黑肱臨終之際,亦以此警戒其子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7]599富貴可能導致滅亡,因此對富貴保持警戒,可以避免災難。
情感與欲望也是春秋嘉言力主保持警戒之心的事物。情感與理性相對,《左傳》中多有記載緣于人的情感意氣而處理事情的案例,具體表現為“逞意”一詞的多次出現,“逞意”在這些語境中的基本意義就是情緒的發泄與快意。以晉國為主的戰爭中,晉齊鞌之戰的爆發和晉國卿大夫郤克因為在齊國受辱而求報復不無關系;晉楚邲之戰,荀林父和士會看到楚君已還,皆不主戰,而先縠則以晉國失霸的恥辱為由堅決主戰,最終以晉國失敗而告終;鄢陵之戰中,郤至同樣以逃避楚國為恥辱為由極力主戰,雖然晉國取得勝利,但是埋下許多后患,均是意氣用事的例子。因此一些貴族文化人看到情緒意氣對人事的影響,基于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以言論表達對感性、情緒等保持警戒的思想,范氏家族是典型代表,范武子、范文子均有對后代進行情感警戒教育的言辭,如士會《戒子書》:
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7]412
楊伯峻注解曰“喜怒合乎禮法者,曰以類”[8]774;杜預注:“易,遷怒也。”[7]412士會以引證論說情感的強大力量,不容易為禮法與理性控制,進而勉勵告誡其子士燮以敬畏和警戒之心面對。
情感和欲望相關,春秋嘉言通過對“度”的警戒表達對欲望的克制。多見于兩個方面的論說:其一戒女色不度。晉平公是晉國歷史上過度放縱女色的國君,以至生疾,《左傳》載諸侯前來慰問,秦國醫和以《論六淫致疾》的一篇言辭,從音樂和醫學的角度闡說人應當對情欲保持警惕與節制,其文曰: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7]708-709
其二是戒奢華不度。奢華的追逐本質上反映的是人的物欲膨脹,對物欲的警惕在楚人言論中多有體現。楚國創業之初時時對安逸保持戒懼,在國勢強大之際又追逐奢華,楚靈王可謂典型代表。如果說虢之會盟上公子圍以令尹身份而服飾奢華飽受非議,或者是因為違越禮制,為國君后筑章華之臺等舉動,則無疑是對奢華的瘋狂追逐,因此楚伍舉作《諫楚子示諸侯以侈》(《左傳》昭公四年)以勸止,又作《登章華臺諫楚子》(《國語·楚語上》)詳細論說,反對不顧民力的過度物欲享樂。
從敬畏天命到警惕安逸享樂、賞賜財富、情感欲望,春秋嘉言闡發了“敬”包含的普遍警戒心態之義,相對于周人敬畏天命的思想,體現出理性的增長。
三、自重不怠的春秋嘉言之“敬”
如果說以普遍的警戒之心闡說“敬”的觀念,側重于一種自覺的反省與強烈的自律意識,那么春秋嘉言大量批評怠、惰、傲等“不敬”的表現則偏向于從個體自尊自重的角度闡發“敬”觀念。
溯其上源,春秋嘉言突出“敬”的自重義當和西周“敬慎威儀”觀念相關,“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慎威儀”等說法在《詩經》中多次出現,其義為對自己言行舉止的敬重,因為詩的文體所限,沒有過多闡發。春秋嘉言繼承西周“敬慎威儀”的觀念,多次引《詩》并展開更為充分的言說,對這一觀念進行詳述。《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衛北宮文子答衛侯問威儀,先論在上位者尤其要敬重自己的威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勢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再論威儀的內涵:“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7]690春秋人所認為的威儀,表現為外在的容止、言語、行動、聲氣等方面。北宮文子所論重于理論,既論“敬慎”,又釋“威儀”,為正面論說,春秋嘉言大量的言論則是針對人的具體言行容止,通過批評“不敬”來闡發敬慎威儀的自重觀念。具體來說,“不敬”主要表現為怠、惰、傲、偷等,這些行為表現略有差異,而本質相同,即自棄,不自敬重。
春秋嘉言對于怠惰的批評十分常見,如公元前649年,周襄王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周內史看到后評論曰:
晉侯其無后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干也;敬,
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7]222
先言晉侯受瑞而惰的表現,進而論禮與敬的關系,進一步指出惰即是“不敬”,即不能夠自重。又,公元前578年,劉康公、成肅公代表周王室會同晉侯伐秦,成肅公在接受祭社后頒發的祭肉時不敬,劉康公論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7]460
劉康公認為,勤禮為敬,怠惰不僅屬于對禮的不勤,失敬更是對命的不敬。這兩則言論都是對于禮儀上怠惰、自棄的比較籠統的批評,而單襄公批評晉厲公在柯陵之會上“視遠步高”,已是從具體而微的言行容止批評不自敬重,其文曰:
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于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6]91-93
在單襄公看來,“敬”具體表現為目光、腳步、語言、視聽等細微言行方面,不合禮儀的言行是一個人內心“不敬”的表現,其根本原因是不能自重。單襄公這篇言辭的觀點或結論是晉國必亂,而大段講述的道理卻是批評對容顏舉止的不敬;在另一篇言論中,單襄公又從正面肯定晉周“立無跛”“視無環”“聽無聳”“言無遠”,進而得出推斷晉周將能夠享有晉國,無論批評還是贊美,其對敬重自身容止威儀的觀念是始終如一的。不只是周王室卿大夫有此觀念,諸侯國的卿大夫亦然。公元前531年,周卿大夫單成公和晉國韓宣子會晤,單成公目光朝下,講話聲音不夠洪亮,叔向論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7]786-787這種在外交場所、社會活動中對于表情、目光、腳步、衣著等細節的注重,尤其表現了春秋貴族文化人的自重觀念。
傲是和惰相近的行為表現,都屬于對自我的放任與放棄,春秋嘉言亦不乏對于“傲”的批評,有時和“惰”連言論說。如公元前577年衛侯因郤犨送孫林父回衛國而設宴享之禮,寧殖觀察郤犨表現后發言說:“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斯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7]464-465又,公元前545年,鄭伯宴享蔡侯,子產評蔡侯不敬,曰:
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7]652
在這些言論所表達的思想中,“傲”同屬于一己威儀的表現,同是不自敬重,都受到嚴厲的批評。
春秋嘉言還有對“偷”的批評,偷為茍且之意,茍且也是對自我的放棄,即不自敬重。如公元前610年,魯襄仲到齊國拜盟歸來,向魯文公匯報說,齊國將不會攻打魯國,因為在此次外交事務中“齊侯之語偷”,然后引臧文仲之言“民主偷,必死”[7]350以論證,言論雖簡短,卻能集中表達魯國卿大夫對“偷”的批評。又如公元前542年,魯叔孫豹從諸侯澶淵之會回國,對孟孝伯論趙武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7]685在這兩則材料中,“偷”的主語皆為“語”,語言是思想的外在表現形式,“語偷”反映出一個人得過且過的狀態,是對自己的放棄,即不自重,同“怠”“傲”同屬于春秋嘉言所認為的“不敬”。
春秋嘉言通過對惰、怠、傲、偷的批評,實際上從反面來闡釋人對于一己的容止言行應有之敬,就是不怠惰、不傲慢、不茍且、不自棄。這種對自己的敬重更多地體現在禮儀與社會外交活動中,帶有儀節形式的意味,所以又常和“禮”相提并論,屬于禮的行為表現。綜觀春秋嘉言對敬慎自我的言論,其背景多為朝聘、晏享等禮儀場所,主體多為周王室、魯國、衛國、鄭國、晉國之卿大夫等貴族文化人,尤以周、魯為多,反映出這些中原國家對禮的形式之堅守。春秋后期,對禮儀形式的認識發生變化,代表為晉國的女叔齊。公元前537年,即魯昭公五年,魯侯前往晉國朝聘,對于魯侯的言行舉止,晉侯與女叔齊有禮儀之辯。女叔齊以為,魯侯不能守其國,行其政令,失去民心,即使熟悉瑣碎的外在禮儀形式,也是不知禮的。就整個春秋時代而論,一方面禮崩樂壞,禮的形式不斷被拋棄,所以“惰、怠、傲、偷”比比皆是;另一方面,貴族文化人努力維護禮的形式,闡發容止言行的“敬”乃是禮的外在表現,并對不能敬慎威儀、不自重的行為進行嚴肅的批評。
春秋嘉言對“怠、惰、傲、偷”的批評帶有因果的思考,即認為一個人如果不敬重自我的言行,則將會導致遭遇災難乃至滅亡的結果。如上文所論諸篇言辭,在單襄公的觀念中,敬慎威儀與否對成敗乃至命運具有決定意義。實際上這種觀念在春秋貴族文化人的思想世界里十分普遍,公元前552年,齊侯、衛侯在商任之會上不敬,叔向評論二人“怠禮,失政,失政,不立”[7]593,并因此預測二人將不免于難。客觀來說,這一因果判斷屬于道德倫理而不是科學判斷。早在唐代,柳宗元對此即指出“其說多誣淫”,因而“本諸理作《非國語》”,于此文有針對性地加以批駁,曰:“是五子者,雖曰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眾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9]754其因果關系雖未必恰當,而反映的思想觀念卻是真實的,這種主觀設想的因“不敬”而導致的巨大后果,從另一方面正反映出春秋嘉言對敬慎威儀的自重觀念的突出與強調。
四、敬業敬人的春秋嘉言之“敬”
春秋嘉言闡發的自律警戒與自重不怠的“敬”之觀念,主要指向自我。對于指向“我”之外的世界,春秋嘉言也從于人、于事的態度上對“敬”觀念有所闡發,共同構成春秋嘉言所論“敬”之內涵。如前所論,對事業、職責的敬重在西周金文中多有記載,是西周初年已有的“敬”之觀念,此義從敬畏天命引申拓展而來,主要反映人與事務的關系,指對王命、職事的應有態度。春秋嘉言沿襲此論,甚至其語言表述亦與金文相仿佛,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7]274;襄公十四年周靈王賜齊靈公命曰:“敬之哉!無廢朕命”[7]564;昭公二十八年晉國魏舒勉賈辛云:“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7]914此類“敬”為上對下的勉勵之辭,常用于執行事務之前,強調做事之前敬重認真的心態,所謂“敬其事則命以始”[7]193。不僅是初始時候的保持敬重認真的態度,春秋嘉言還強調對于職事自始至終的敬重,而且因為敬重,進一步強調謹慎,“敬”之此義又常與“慎”連言,所謂“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7]625。無論是對于事業開始時的勉勵,亦或對于整個職事始終的認真,這一層面的表述,多止于言辭概念,更多的屬于對西周以來的敬職、敬業思想的繼承。在繼承的基礎上,強調對于某一種具體職責的嚴格履行的觀念,屬于春秋嘉言在“敬”觀念認真負責義的拓展。如公元前655年,晉獻公聽聞夷吾的上訴而責備士在為二公子筑的城中置薪,士為晉國司空,回答自己所做都是堅守司空之職的使命,因為他認為“守官廢命,不敬”[7]206。又如公元前570年,諸侯在雞澤會盟,晉侯之弟揚干擾亂軍行,魏絳為晉國中軍司馬,不畏晉侯而殺戮處決揚干之仆,以生命來捍衛對職責的敬重,在寫給晉侯的《請罪書》中說“軍事有死無犯為敬”[7]502,表達的正是他敬重職守的觀念。春秋晉國是法家思想的一個重要起源地,晉國兩位卿大夫關于敬重職守的言論,本質上反映了法則至上的觀念。
“敬”于對他人而言,側重于恭敬、孝順、尊敬等義。這個意義在金文與《尚書》中不多見,《詩經》有之,如《小雅·小弁》說“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毛傳:“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4]421表達對父母恭敬的觀念。春秋嘉言對“敬”在這一層面的意義亦有闡發,本質上反映的是處理人際關系時的應有態度,這種關系首先是上下級關系,強調下對上的態度,包括子對父、弟對兄、臣對君、小國對霸主等,如作為在大國中艱難生存的鄭國,其卿大夫子駟曾論小國生存之道曰:“敬恭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7]521表達小國對大國的恭敬義;齊國晏平仲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7]599劉康公之論云:“敬恪恭儉,臣也。”[6]76指出作為臣子須當恭敬。魯國公不悅其父季武子任命自己為馬正,不愿就職,閔子馬見之,以子侍父之道勸勉曰:“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7]605“敬”在此一層面的意義反映出春秋時人的倫理觀念,屬于禮的范疇,如晏子所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7]906比較全面地羅列了人際倫理,“敬”的態度正是對臣、子、弟的要求,這是春秋嘉言于他人之“敬”的主要意義。當然,除了上下級關系,“敬”也含有指向平等的人際關系之義,強調對于他人的尊敬與尊重。如公元前627年,臼季向晉襄公舉薦冀缺,理由是他曾經看到冀缺于其妻,“敬,相待如賓”,并言“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7]291,此一“敬”義即是側重于平等關系中的尊敬。
綜上,春秋嘉言繼承和發揚著自西周以來“敬”的觀念,包含了敬畏、警戒、敬重、謹慎認真等豐富內涵。這些意義相近,難以絕對區分。一方面“敬”因具體對象不同而意義側重有別;另一方面雖然對象有別,重心卻不在對象,而在“我”。“敬”歸根結底是春秋嘉言對待“我”和自身、宇宙、他人、事務等的關系的具有豐富內涵的自我修養范疇,和信、禮、義、勇等共同構成春秋上層統治者所認同的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范疇中,“敬”又有其獨特性。其一,因“敬”更多層面地實踐于自我,故為諸多修身范疇的根本,嘉言所謂“敬,身之基也”[7]460;“敬,民之主也”[7]657。強調的正是“敬”為立身之本;其二,“敬”已屬于人物評價的范疇。“敬”作為對一個人一生的評價,是一個比較好的謚號,春秋人物中多有以“敬”為謚號的,如管敬仲、田敬仲等;而“和安而好敬”[6]439是祁奚從人物品質鑒定的角度對其子祁午的評價。因此“敬”的品質培養成為貴族教育的重要內容與目標,《國語》所載申叔時《施教論》闡述如何教導楚國太子時曰:“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而戒懼焉”;“明敬戒以導三事。”[6]529總之,作為修身范疇的“敬”在春秋嘉言中被大量言說闡述,豐富和拓展了西周以來的價值觀,成為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精神傳統的重要構成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