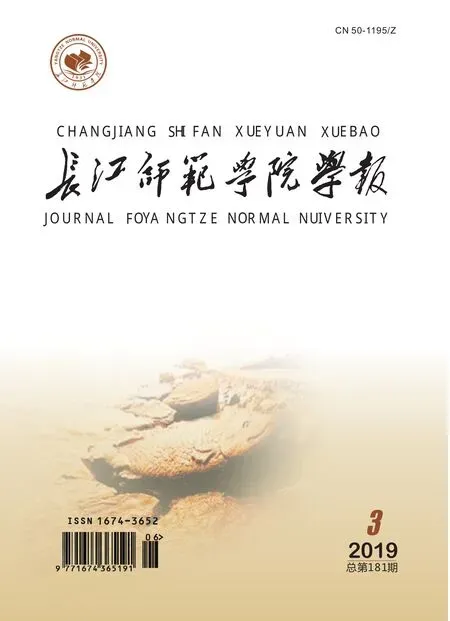中國俠文化研究2018年年度報告
王亞偉
(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2018年適逢改革開放40年,中國俠文化研究40年來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完整、系統的研究格局基本形成[1]。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中國從“新時期”進入“新時代”,中國俠文化研究也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2018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批準了北京大學高慧芳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比較視野下的唐宋女俠故事文化研究”(18BZW050),自2014年以來,國家社科基金中的俠文化項目已經達到8項,其中在研項目3項。相關研究專著陸續出版,特別是與金庸相關的專著,有上官圣泓的《金庸傳》[2]、胡文輝的《拜金集》[3]、孫宜學的《造俠者金庸》[4]。中國俠文化相關研究論文呈現出穩定態勢,以中國知網為主要檢索工具進行篩選與整理得到有效論文87篇。關于俠文化研究的學術史梳理,蘇靜針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史記》游俠研究情況做了總結與梳理,認為“研究的問題主要集中于游俠的身份辨析、游俠精神要義的闡發、文學之俠和社會之俠三個方面”[5];譚華專門對中國武俠文學外譯研究的情況做了專門的統計與分析,認為“應用研究占絕大多數,缺乏理論探索,而且多數研究都在微觀層面上對一些特定的問題進行分析描述,如具體的翻譯策略及武功招數、江湖人名等術語的翻譯,缺乏從宏觀層面對武俠文學翻譯進行系統的探討”[6]。本報告基于相關學術史研究及2017年年度報告[7],對2018年的中國俠文化研究情況,從武俠文學研究、武俠影視研究、俠的歷史文化研究三個方面予以梳理。
一、武俠文學研究
武俠文學研究是中國俠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本年度共發表論文52篇,其中武俠小說基礎理論研究論文2篇,中國古代武俠小說研究論文9篇,民國武俠小說研究論文11篇,金庸武俠小說研究論文21篇,臺灣武俠小說研究論文4篇,網絡武俠小說研究論文5篇。
(一)武俠小說理論研究
理論模型或研究方法的建構,目前是中國俠文化研究的弱項。近年來人們認識到“武俠小說研究的理論模型問題,已經成為武俠小說研究進一步深化發展的瓶頸”[8]。2018年度發表了兩篇值得關注的理論方法研究論文。韓云波從武俠小說類型學的研究困境出發,以還珠樓主武俠小說作為文本實證案例,提出由武俠意識形態、武俠形式建構、武俠專門知識三個子系統構成的“武俠小說類型知識體系”系統框架:“還珠樓主以‘第二世界’為核心從本體論、認識論、道德論、實踐論諸方面建立起了武俠意識形態子系統,以奇觀敘事為核心的成長體驗、正義迷局、奇觀異境形成了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場景中心的武俠形式建構子系統,以武功法寶和江湖世界建構了武俠專門知識子系統。”[9]這種研究模型的提出與運用,從結構要素的角度闡明了武俠小說的類型獨特性,對武俠小說研究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
武俠小說理論研究不僅體現在小說研究方法的建構上,也體現在武俠小說理論本體的闡釋上。徐淵對武俠小說的融合性理論進行了深入闡釋,表現在武俠小說類型特征與美學特征上。這種集俠武融合、俠情融合、“奇”之融合、“史”之融合、俠義公案和文化融合的武俠小說類型特征與“俠”之正義、“武”之神奇、“情”之美好、“奇”之超越、“史”之真實、情節之跌宕、文化之魅力交互的美學特征是歷時和共時、外部和內部綜合作用的結果[10]。這種融合性使得武俠小說突破了一般類型文學的界限,呈現出獨特的魅力。
(二)中國古代武俠小說研究
本年度中國古代武俠小說研究文章數量相對較多,研究的對象從唐至清末均有涉及,但其中研究對象基本確定,研究的傳統角度與方法被反復運用,觀點幾成定論,創新性的研究較少,故在此不過多贅述。
(三)民國武俠小說研究
第一,人物形象藝術研究。民國武俠小說的女性形象受到時代文化的熏染,已經與古代武俠小說中的女俠形象有所區別。陳樂從整體上闡釋了民國女俠透過服飾色彩來呈現其新變內涵,并在作家寫作態度與讀者期待視野的雙重作用下完成了這種變化[11]。在近現代保種圖存、追求進步的歷史背景下,女俠情感世界的復雜性得到展現,小說塑造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獨立與自強的時代楷模,此時的女俠具有了新的社會內涵[12]。
第二,敘事藝術研究。徐俊徇研究了朱貞木武俠小說的敘事策略,從奇詭敘事、人獸相安敘事、歸隱敘事三個維度做了梳理,較好地把握了敘事背后隱藏的深刻意義[13],使得朱貞木敘事策略的生成與形成背景得到了詳細的闡釋。孫文起認為,王度廬的武俠小說對倫理敘事的建構有著獨特的認識,作品從“平民”視角切入,展現出來的情感糾葛是作家對現實社會與自我族群體認的投射,其價值已不僅僅停留在武俠小說類型本身[14]。莊國瑞、盧敦基認為,需要對王度廬武俠小說進行再認識,并對其“悲劇俠情”的敘事書寫模式作了客觀的評價。以悲為美與以俠為累的模式,既是作家創作的創新之處,也是作家創作無法回避的缺憾。該文同時指出如何由武俠小說研究拓展到王度廬的整體創作的研究轉向,并在內容闡釋、文學思想、美學風格、歷史影響等方面形成系統性的認識的建議也值得參考[15]。
第三,副文本研究。蔡愛國對武俠小說評點進行了研究,由施濟群與陸澹庵對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的小說評點,均基于明清小說理論而展開。施濟群評點的價值在于為《江湖奇俠傳》的傳奇性提供辯護,立場較為傳統;陸澹庵一方面強化了對《近代俠義英雄傳》的文本細讀,另一方面則突顯了社會問題意識,就這一時代人們所關注的中西文化對比、武德修煉等話題展開討論[16]。
(四)金庸武俠小說研究
第一,文化內涵研究。于志晟認為,金庸小說具有豐富的傳統文化承載力與民族內涵,他對古典小說的形式進行了一系列的繼承與創新,具體表現為對古典小說古語詞、謙敬詞、文言語氣助詞、文言短語及句式的繼承和對章回體回目形式的接受,以及對古典詩詞的引用等多方面的承繼[17]。張寧通過透視拜師學藝與成長模式,闡釋了金庸小說對文化教育的價值與意義[18]。樊晶晶認為,《笑傲江湖》中的俠客隱士與笑傲江湖曲目共同呈現出作家對傳統文化中歸隱文化的體認,體現出作家對人生社會的看法與詩意的生存追求[19]。
第二,人物形象藝術研究。張永祎與張涵從作品形象與作家情感原型、鄉愁情結、江南女性以及婉約美學的多重互涉的關系中進行論述,使得金庸筆下江南女性形象的美學意蘊得到了具體呈現[20],但該文中的抒情性語言對學理性的闡釋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華珉朗同樣從江南文化視域進行考察,不僅聚焦于女性形象,而且從人物譜系與江南文化塑造的關系、人物思想傾向與文化烙印的關聯以及人物的淵源與價值的聯系中出發[21],將人物形象背后的江南文化內涵做了深入挖掘。
第三,敘事藝術研究。湯哲聲基于對《天龍八部》的文本把握,通過“前世輪回,命中注定”“因果報應,皆成冤孽”“去貪嗔癡,苦集滅道”三個佛學敘事結構的闡釋,突顯了金庸以佛學思想所建構的佛學武俠小說敘事模式,不僅能看到作家對佛家思想的透徹掌握,還看到金庸在武俠小說敘事模式上的貢獻[22]。馬琳、馬春燕從《射雕英雄傳》入手,通過“狗耕田”基本故事模式的設定和民間尋寶故事的重塑、奇幻瑰麗的天才想象與二元對立的美學原則的運用以及善惡有報、勤能補拙、忠義仁厚的觀念來進行闡釋,認為金庸武俠小說深受民間故事模式、民間審美趣味、民間價值取向的影響[23]。
第四,美學藝術研究。葉雋通過對《射雕英雄傳》中江南意象的分析,將僑易美學中的若干核心概念進行整體觀照,立足于金庸武俠小說中的煙雨江南意象,透過具體文本,僑易美學概念取得了較好的理解路徑。作者指出,以流動眼光和變化思維去審美,重視僑易之美的根源,同時要具有批判性的觀照思維[24]。該文拓展了金庸小說研究的美學理論方法,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第五,武功武學研究。俠文化的武功武學呈現出階段性與跨越性的顯著特點,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突出的重要因素,閃耀著作家的靈感之光。陳特從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修習類型入手,提煉出了小說中存在的三種“武學功夫論”類型,并與傳統文論中的文學功夫論相聯系,得出了以郭靖為代表的勤學苦練的“儒學功夫論”、以喬峰為代表的發揮天賦的“道家功夫論”、以令狐沖為代表的妙悟立成的“禪宗功夫論”。陳特還對這種隱藏在武學功夫論背后的江湖價值觀念加以闡釋,這種武學功夫論的書寫是匯通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果[25]。武功的修習除了自身內在的修行外,還需要外在隨身武器的輔助,黃祎通過對《天龍八部》中的武器進行探源與分類,并從更廣闊的視野解讀武器的符號內涵,能從其中深深地感受到金庸對武學的把握,集哲學意味、人生價值體認、詩意境界三位一體的文化哲理反思意味[26]。
(五)臺灣武俠小說研究
第一,“暴雨專案”研究。林保淳系統闡述了20世紀60年代臺灣當局針對武俠小說等展開一系列查禁措施的“暴雨專案”始末,結合當年臺灣7家報紙有關項目實施過程的報道及97種查禁書目等相關史料,對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27]。
第二,“鬼派”武俠小說研究。林保淳以積極中肯的態度對“鬼派”武俠小說給予了合理的評價與定位。他從創作時間與創作成就方面著眼,認為“鬼派”武俠小說的形成有其時代的土壤,武俠漫畫風潮的流行刺激了鬼派武俠小說的生成,出現了以陳青云為代表的“鬼派”作家。林保淳從具體的用字內容、藝術風格、情節結構、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進行分析,指出“非鬼即魔”的用字鋪陳、恨意充盈與陰森恐怖的場景氛圍,以及隱情偏激的人物性格等方面,都體現出“鬼派”武俠小說有其獨樹一幟的特點與寫作體式[28]。“鬼派”武俠小說在臺灣吸引了一批讀者,曾經風靡一時,其價值與意義不可忽視。
第三,“后金庸”臺灣武俠小說代表作《英雄志》研究。林保淳認為,《英雄志》目前雖未全部完成,但已體現出顛覆與創新的特色。作品顛覆了以往傳統武俠小說對“正義”“仁義”的堅守,引領讀者探尋更深層次的命題;在敘事策略的體現上,采取純文學技巧,為武俠小說探索了一種新的寫作手法的可能性[29]。該文促使人們對當下武俠小說創作加以反思,具有積極作用。
(六)網絡武俠小說研究
第一,小說敘事藝術研究。鄭保純將滄月《忘川》作為網絡武俠小說女性敘事的重要代表,進而對網絡女子武俠作家面臨的敘事修辭與意識形態挑戰做出闡釋,從而對女性敘事聲音的誕生正本清源[30]。在歷時與共時的梳理中,“女性向”的敘事從一開始就將文本作為自身的意識形態戰場,敘事策略本體就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發出聲音,凸顯出女性敘事區別于傳統男性敘事的顯性特征。
第二,網絡武俠小說譯介研究。網絡武俠小說翻譯平臺的建構與運營,以及翻譯所發揮的作用極其重要。劉毅與張佐堂以北美網絡翻譯平臺“武俠世界”為切入口,探討網絡武俠文學的譯介與傳播。承載武術文化的武俠小說是“武俠世界”平臺譯者們關注的重要對象,也是譯介傳播中的巨大挑戰,而“武俠世界”平臺受到西方讀者的熱衷追捧與接受正是在于譯者們的努力。因此,“武俠世界”平臺譯者們的跨文化認知、傳播策略和武術文化術語翻譯策略等,對譯介理論研究與實踐都具有啟示意義[31]。
第三,網絡仙俠小說研究。網絡仙俠小說可溯源至還珠樓主,但由于時代原因,還融入了西方宗教思想、網游文化、日本動漫文化等因素,因而有了與傳統仙俠小說不同的特征。段曉云借鑒愛德華·索亞的第三空間理論,從文學空間的研究角度切入網絡仙俠小說,認為通過文學想象空間、象征空間、生產與接受空間三個維度來解讀網絡仙俠小說,可使得中國網絡仙俠小說空間構建得到有效理解,由此傳統與現代、現實與想象、民間與精英的融合和碰撞,都可在網絡仙俠小說的空間中呈現出來[32],但其中對于仙俠空間書寫的價值仍待深入。張健、楊柳在對“仙俠小說”一詞在英譯世界里的解讀時,通過橫縱兩個維度梳理出“仙俠小說”這一概念在當下的發展與現狀,將該詞在網絡背景與英語世界中被賦予的內涵呈現了出來[33]。
二、武俠影視研究
武俠影視研究緊隨武俠文學研究的腳步,在研究深度與廣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2018年度共發表論文27篇,其中武俠電影史研究論文6篇,武俠電影作品研究論文20篇,武俠電影演員研究論文1篇。
(一)武俠電影史研究
本年度研究者從歷時性角度來梳理電影史某一時段的變化與內涵時,時段劃分具有多樣性,解讀角度呈現出多維特點。陳鴻秀從新世紀以來的武俠電影入手,通過俠之情懷的偏離、回歸與降調的變化、敘事風格從虛幻走向平實的趨勢、人物形象從另類英雄到有功夫的凡人的表現形式來進行歷時性的闡釋,指出武俠電影的“文學性”流變呈現出內涵、敘事、人物上的多角度變化過程,這種演變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34],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市場性。田玉愛立足于網絡媒體新技術發展,對仙俠劇的發展過程進行剖析,縱向以2005年《仙劍奇俠傳》的出現到2017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熱播作為研究的時段,橫向在仙俠劇的敘事體系、傳播特征兩個方面展現仙俠劇的發展過程[35]。該文對當下熱播劇的原因作出探究,對仙俠劇熱播現象與發展策略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二)武俠電影作品研究
第一,武俠電影作品內涵與主題研究。王凡與朱慧分別對《沖霄樓》與《天注定》中的主題與內蘊進行解析。前者強調小說《三俠五義》的先在性影響,但也受到了導演創作意識的時代性影響,電影中凸顯出了張徹武俠電影以男性英雄的深厚情誼為核心的“陽剛電影美學”特征,而且也潛在地折射出其本人創作主體意識對于文學改編中的主題詮釋、人物重塑、風格嬗變等方面所具有的主導性作用[36]。后者著重探討賈樟柯戲劇化手法塑造的俠客形象,指出俠客身份在游俠、流民以及暴徒中的游離,俠義在公義與私憤中的徘徊,武俠敘事在浪漫輕談與荒誕現實轉化下展現出底層群體的極端生活狀態,電影中的“俠客”彰顯的俠風是對荒誕生命的反抗,同時也給中國傳統俠文化在當代語境下的內涵做了新的注解[37]。曹怡平以《臥虎藏龍》主題衍生出的系列片作為反例進行研究。他指出,系列片作為一種商業策略,其反復制作的原因在于穩定的潛在觀眾和明確的觀影預期,但也存在一定的風險,并認為故事是否具有概念化、團隊實力是否旗鼓相當、能否有效復制創意流程是系列片制作可行與否的標準[38],巧實力的合理遵守是拍攝武俠系列片的重要準入原則。林保淳深入分析了從歷史事件“刺馬案”到武俠電影《投名狀》的生成過程,在展現由歷史生成文學具體邏輯理路的同時,凸顯出當代對歷史的重新把握,《投名狀》被賦予了新的主題與內涵。林保淳指出《投名狀》是“漁色負友”與“政治陰謀”兩相糅合的結果,影片給予了人物新的“定性”與“定位”,具有了人性的高度與史詩的格局,不僅凸顯出高超的藝術性,也展現了“后現代”“眾生喧嘩”的特點[39]。
第二,武俠電影作品藝術風格研究。楊梅就武俠電影的整體詩意風格進行了詳細的闡釋,通過電影《臥虎藏龍》《英雄》《新龍門客棧》在畫面營造、鏡頭類型修飾、音樂背景、俠義文化情懷、愛情表現以及民族氣韻等方面的具體分析,指出這既是對中國傳統繪畫詩歌的借鑒與繼承,也是對詩意精神的向往,而武俠電影正是當代人內心投射的具體載體[40]。楊帆論述了徐浩峰從文學作品到武俠電影生成的作者化路徑,建立起了第一手口述材料、文學與電影作品多文本互涉間的研究體系,對于徐浩峰的武俠電影作者化研究頗具總結性[41]。
第三,武俠電影作品敘事藝術研究。龐思雅專門就港臺武俠電影中的客棧、大漠、竹林為代表的敘事空間展開論述,指出這三個空間意象在形態與演變、形式與風格、文化表征等層面具有重要的敘事藝術價值,其以造型多樣化的視覺特征呈現出富有特色的東方意境、顛沛流離的現實寫照以及家國情懷的精神歸宿[42]。歐陽照、梁瀅以國產仙俠劇《青云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為素材,認為國產仙俠劇雖然在文化意蘊、立意以及格局上稍有欠缺,但在敘事創新上有了新的發展:在敘事特質上,故事視角與英雄人物的重心發生了位移,女性的主體意識得到了凸顯;在敘事觀念上,眾生平等、正邪無界的價值觀念得到了建構與廣泛認同[43]。仙俠劇的敘事創新不僅有利于促進武俠影視的發展,同時也反映了俠文化內部的變化。
第四,武俠電影作品人物藝術研究。倪子荃從《女俠白玫瑰》中的女俠形象塑造入手,深入挖掘20世紀20年代早期武俠電影中通過跨越性別的方式來建構女俠形象的時代性,以及由這種人物構形而形成的觀影機制。他指出,影視中在鏡像認同的時刻展示了女俠身體的性別與文化跨界的過程,女俠的鏡像自我與不穩定的身體意義邊界構成影片的觀影機制的重要特色。早期觀眾藉由女俠性別跨界的鏡像身體而進入主體認同位置,但是這個鏡像身體又并非抽象靜態的既有形象,而是一個邊界模糊與動態變化的構形過程[44]。這種深度闡釋對于理解早期武俠影視的視覺現代性,以及觀影機制中的通俗文化主體性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丁省偉與范銅鋼對武俠電影中的“武術人物”塑造的影響因素作了探研,他們通過《霍元甲》和《一代宗師》的解構與分析,從基本因素、外在因素以及關鍵因素來進行梳理與提煉[45]。但是限于篇幅,各個影響因素只是進行“蜻蜓點水式”的框架式總結,仍有待詳細論述。
第五,武俠電影元素研究。在多重互動的武俠電影元素合力促進下,武俠電影的藝術魅力才會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現。王博施指出,“楚留香”系列影視劇主題曲歌詞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具體包括:中國各種傳統文化交融中產生的俠文化、作為古龍原著的新派武俠小說、作為現代重要媒體形式的影視劇、作為流行音樂的主題曲、作為一種現代詩歌形式的歌詞等。這些復雜因素影響而成的音樂歌詞不僅僅是傳統文化、文學與現代通俗文化形式之間融匯的合理產物,生成的過程也體現出大眾對俠文化的接受與審美心理變化[46]。
第六,武俠電影與市場關系研究。石純從友聯公司拍攝的武俠神怪片與南洋市場的關系入手,指出友聯公司能突破此前市場武俠片類型的拍攝路徑,對武俠片類型進行新的定位,以打造武俠神怪類型片為公司特色來進行市場拓展。這種定位基于友聯公司對南洋市場需求的深刻洞察,其發行的基點在于迎合南洋觀眾的期待視野又不觸及南洋當地武俠電影的審查制度,從而不僅使得武俠神怪片開啟了20世紀30年代的新氣象,還成功開拓了南洋武俠影視市場,并將俠文化輻射到更加廣闊的地域,對早期中國武俠電影在海外傳播做出了積極的探索[47]。這種尋求電影與市場的發展路徑,對于當下武俠影視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武俠電影演員研究
黃望莉、曾敏運用“吸引力電影”理論與“白話現代主義”理論,對20世紀20年代早期武俠電影中的女明星進行探討,認為武俠女星在影像中存在“恣越”的身體呈現。這種呈現不僅是一種跨性別的混雜性與現代性的體驗,同時,更形成了一種影內影外的互動關聯對照關系。一方面打破了父系秩序、僭越男權規則的江湖神話,另一方面體現了參與現代社會文化、政治生活的女性訴求[48]。
三、俠的歷史文化研究
俠的歷史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專門領域,是武俠小說及武俠影視研究的基礎。2018年度共發表俠的歷史文化研究論文8篇,其中俠文化歷史內涵研究論文2篇,歷代文人俠客化研究論文3篇,新文學作家與俠文化的關系研究論文3篇。
(一)俠文化歷史內涵研究
從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維度進行考察,進而闡釋俠文化的內涵具有一定新意。才圣通過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俠所受到的來自民間與官方雙重評價的角度加以梳理,考察兩種對立性評價的深層原因,對俠生存于傳統時代的政治制度進行挖掘[49]。在中國傳統君主專制制度下,俠生成的俠文化既有催生其成長的一面,也有壓制其發展的一面。這是由封建專制制度的內在特征決定的,在立法與執法層面的雙重維度下,俠文化內涵得到了深入闡釋。該文從法理制度角度的解讀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對文學文獻的運用與把握仍稍有欠缺。
(二)歷代文人俠客化研究
嚴正道對巴蜀地域的俠文化生成過程進行梳理,從先秦時期先民生活的生存環境中提煉出俠文化的原始特征,進而分析秦漢時期秦燕趙等地豪俠入蜀所形成的豪俠文化。歷史上,文人有意識地對俠文化予以吸收,形成司馬相如、陳子昂、李白以及蘇軾為代表的巴蜀地區文人俠客化的獨特現象[50]。這種文化現象反映了俠文化在中華大地上遍地開花的景象,盡管與中原俠文化有所區別,但也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華夏俠文化的重要部分。
蔣勇將文人之俠的時間定位到中晚明時代,通過對中晚明階段文人的考察,指出文人尚俠在數量、規模以及文人交往中對俠精神的認同等方面呈現出集中化與典型化的態勢,證明了中國俠文化對文人階層的深刻影響,并推進了明代求“真”尚“情”文學思想的演進[51]。從這里能夠真切體會到俠文化對古代精英階層的巨大魅力,以及雅俗共賞的發展路徑,這為理解明代文學思想轉變的動因提供了重要佐證。
(三)新文學作家與俠文化研究
陳夫龍多年來致力于研究新文學作家與俠文化之間的關系,2018年度發表了3篇論文。關于魯迅與俠文化,陳夫龍認為魯迅鑄就了其自身獨立不羈、頑強堅韌、挺拔傲岸的精神界斗士的形象,魯迅的創作中擁有豐富的俠文化精神質素,其創作閃耀著俠文化的光輝[52]。關于郭沫若與俠文化,陳夫龍指出郭沫若能積極立足于時代的具體語境并對其做出及時的回應,并將抗戰的時代背景與俠文化緊密結合,以發掘歷史與現代的共通性,在給予筆下人物俠義情懷的同時,也賦予了俠文化新的時代內涵[53]。關于劉紹棠與俠文化,陳夫龍從快意恩仇與自由自在的民間江湖、勇武任俠與多情重意的俠者形象、存于大地的民間情懷三個維度來深入闡釋劉紹棠的鄉土文學的藝術建構[54]。關于魯迅、郭沫若等與中國俠文化的關系,學界已有了眾多研究成果,而關于劉紹棠與俠文化的關系則是首次專門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新時期作家對俠文化的創造性繼承轉化的結果,新文學作家本身之“雅”與非主流之“俠”得到了較為深度的融合,是作家受到時代精神的召喚使然。
四、結語
中國俠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支脈,順著歷史的文化長河流淌至今,仍舊蘊含了其獨有的文化養分,潛移默化地滋養著文化與文學的發展,并以豐富而絢爛多姿的形態呈現出來,歷久彌新,吸引著眾多研究者。通過以上梳理與回顧可見,2018年年度俠文化研究成果是比較豐富的,無論是韓云波對武俠小說研究理論方法的建構,還是蔡愛國與林保淳對武俠小說相關新材料的闡釋,抑或是蔣勇對俠文化的影響解讀等都頗具鮮明的代表性,使俠文化的豐富內涵得到了很好的挖掘,在某種程度上引領著俠文化研究的方向。本年度的研究也將作為俠文化研究領域的關鍵性節點,在下一年度里將掀起一股研究熱潮。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的逝世將意味著新一輪的“武俠熱”與“金庸熱”。以韓云波的《論金庸小說的“中國道路”》[55]與《主流化的創造性轉換——論金庸對中國武俠小說的貢獻》[56]等為代表的論文的發表已經拉開了2019年度“武俠熱”研究的序幕,并且相關“金庸熱”研究將成為2019年度俠文化研究領域內最大的一個亮點,中國俠文化研究格局的建構將會得到進一步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