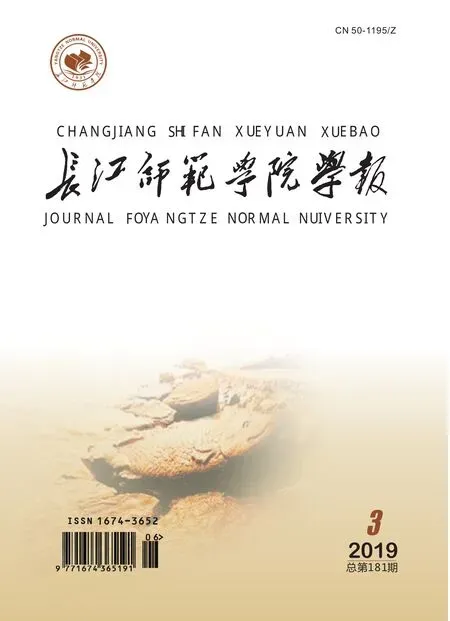漢代鏡銘體式演變與七言鏡銘的生成
時嘉藝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鏡銘出現于戰國,發展至漢代成為銅鏡的主體裝飾,其體式發展歷經三言、四言、六言再到七言的轉變,每一次變動都有其內在生成機制。鏡銘是七言體式文學誕生的早期形態之一,從內容、結構等角度將漢代七言鏡銘與七言詩歌比較,可以發現兩者有頗多近似之處。通過梳理鏡銘的體式演變和生成原理,可以從結構的視角構建較為完整的鏡銘發展史,亦可對漢代七言詩歌的起源予以補充。
一、漢代鏡銘體式的演變
從語體角度考察,詩歌的語體呈現從三言、四言、五言再到七言的發展趨勢。鏡銘與詩歌的發展線索基本一致,西漢時期的鏡銘中有三言體、四言體,其中以四言為主。西漢中晚期出現了六言體、七言體,新莽時期直至東漢中晚期,七言體得到大量運用,三言體亦有存續。
西漢早中期鏡銘體式與詩歌類似,均受《詩經》的影響,多以三言、四言為主。而與詩歌相異之處在于,鏡銘作為附屬于銅鏡上的實用性文字,其表現空間受到限制,故更加簡短。四言類鏡銘中多有類型化的固定書寫:“大樂富貴得所好,千秋萬歲,延年益壽”[1]34;“與天相壽,與地相長,富貴如言,長樂未央”[1]86;“服者君卿,萬歲未央”[1]94。還有一些較長的鏡銘,在簡單銘文的基礎上稍加變動,其實大同小異。比如:“見日之光,天下大陽,服者君卿,延年千歲,幸至未央,常以行。”[1]134內容多為求長壽、求富貴簡短韻語的組合。
又有三言類鏡銘,如祝壽類“壽如山,西王母,谷光憙,宜子孫”[1]84;求富類“長富貴,樂無事,日有憙,常得所喜,宜酒食”[2];相思類“悲思愁,愿君忠,君不說,相思愿毋絕”[3]。鏡銘中三言句子多是由四言省略而來(不說四言鏡銘由三言鏡銘增補,是因在目前所知出土西漢早期鏡銘中,四言出現更早,所占比重更大)。例如:“美宜之,上君卿,樂富昌,壽未央。”[1]110其中“上君卿,樂富昌”明顯是“上(服)君卿”“(大)樂富昌”的省略,“壽未央”也是“(長)壽未央”的省略,其他鏡銘中亦有“長樂未央”“萬歲未央”出現。由于鏡銘書寫空間多為固定的環形一周,所以對字數有嚴格要求。鏡銘中常出現省字現象,在一篇鏡銘末尾,如果書寫不完,就直接省去,如末尾本該出現“壽如金石為國保”,直接簡化為“為國保”三字,此類情況也較常見。
鏡銘中的三言韻文亦受同時期三言詩歌的影響,如漢武帝命人創作的《郊祀歌》十九首中,有七首全為三言,《赤蛟》一篇有“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4]154,從中可以看出帝王對永生的渴求。大約同時期的鏡銘也載有十分相似內容:“見日光,天下大陽,服者君卿,延年益壽,敬毋相忘,幸至未央。”[1]200又有樂府民歌《飲馬長城窟行》“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4]154,與鏡銘“道路遼遠,中有關梁。鑒不隱請(情),修毋相忘”[5]記載相似。
三言、四言體式延續直至新莽時期,鏡銘篇幅增長,內容更豐。求富類鏡銘會加入“賈市”“程萬物”等用語,顯示出當時商業的繁榮,如《洛陽燒溝漢墓》考古報告中有鏡銘:“日有憙,月由富,樂毋,常得意,美人會,竽瑟侍,賈市,程萬物。”[6](“樂毋”后缺一字,應補“事”,“賈市”前缺一字)簡單的求長壽類鏡銘演變為求仙類鏡銘,如新莽時期鏡銘:“上大山,見神人,食玉英,飲澧泉,駕交龍,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孫,貴富昌,樂未央。”[7]該類鏡銘又有賦體類七言形式“上大(太)山兮見仙人,食玉英兮飲澧(醴)泉,駕交(蛟)龍兮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孫”[8]。三言銘文與七言賦體的轉化在鏡銘中屢見不鮮,又如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藏有銅鏡,其銘為:“泿精華,精皎日,奄惠芳,承加澤,結微顏,安佼信,耀流光,似佳人。”[9]而在《漢銘齋藏鏡》中,同類銘文呈現出略有不同的賦體風貌,西漢中晚期清華銘圈帶鏡銘文如下:“泿精華兮精皎日(白),奄惠防(芳)兮宣加(嘉)澤,結微顏兮似佳人。”[1]250這種轉化不僅僅是句讀的區別,更與鏡銘體式演變密切相關,鏡工依據漢代不同時期流行的詩歌體式,在原有鏡銘上加以創造。
鏡銘發展至西漢末年,六言鏡銘出現,主要為昭明鏡和清白鏡兩種,因其與騷體詩聯系更加緊密,為行文省便,將在下一節探討,這里直接討論占據鏡銘主體形式的七言鏡銘。七言鏡銘以新莽時期的“尚方類”銘文鏡最盛,如:“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皂,非(徘)回(徊)名山采芝草,浮游天下敖(遨)四海,壽如今(金)石得天道。子孫長相保兮。”[1]312其中“尚方”表示官署,承擔為帝王制造用器的職能。王莽曾被賜予新都侯的稱號,篡位后定國號為“新”。故“尚方作鏡”“王氏作鏡”“新家作竟”,均表示王莽時期的官府制鏡,王莽為“安漢公”至新莽王朝建立,尚方機構已由王氏經營。至漢章帝時期,官府造鏡漸趨衰落,民間造鏡工坊興起,全國出現大量造鏡中心,鏡銘中的造鏡主體更加豐富,例如“朱氏”“杜氏”“龍氏”等等,“朱氏作竟快人意”此類銘文,亦多是七言為主。此外,又有雜以三言、四言和七言形式的鏡銘,參差錯落,別有韻致。例如西漢晚期鏡銘:“日有憙,月有富,樂毋有事宜酒食,居必安毋憂患,竽瑟侍,心志,樂已茂兮年固常然。”[10]更有“桼(七)言之紀從鏡始”[1]366之類語句明確標識鏡銘為七言詩之始的記錄。
通過對鏡銘體式的梳理會發現一個問題:鏡銘中為何從未出現過五言體?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說:“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后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世用之。”[11]說明語體的使用與詩體功用相關,五言、七言均可用于“俳諧倡樂”之屬,可是五言并不見于鏡銘,而摯虞也沒有說出某種形式不能用于某類文體的原因。陳直曾提及漢鏡銘缺失五言的原因:“或因當時五言歌謠流行,作者為了有別于這些通俗作品,所以就避免了五言。”[12]而鏡銘作為一種通俗韻文,恰應與當時流行的文體相合才是,故而鏡銘體中五言體的缺失應有其內在文體機制方面的原因。
筆者試圖對鏡銘中五言體的缺失作一推斷。根據葛曉音對五言體詩歌生成的論述,漢語詞匯的音節演變,是從單音節詞向雙音節詞過渡的過程,這種過渡在五言體中的運用相對困難[13]。以《詩經》為例,五言體在《詩經》中有以下幾種運用方式:一是“二+X+二”型,其中“X”多為虛詞,如《鄭風·女曰雞鳴》中“雜佩以增之”。二是“X+四”或“四+X”型,例如《小雅·斯干》“唯酒食是議”,《邶風·簡兮》“西方之人兮”。鏡銘原有的三言、四言很難轉化為這種形式。三是“二+三”型,如《齊風·盧令》“其人美且仁”“其人美且卷”“其人美且偲”,這種句式多為復沓節奏,相似或重復的內容也不適合在鏡銘中使用。故在鏡銘生成發展的過程中,五言體并不符合其以凝練為主的要求,鏡銘中缺少五言體也是事出有因。
二、七言鏡銘的生成
葛曉音曾探討過七言詩歌的生成原因,她認為:“在七言產生之前,四言和騷體這兩種詩體都是從散文句中提煉出主導的基本節奏音組。”[14]通過對楚辭、騷體詩和民間歌謠語句內部的拆分可以發現,四言和三言可以連綴成句形成七言,《成相篇》《為吏之道》就可視為連綴而成的雜言體七言。
鏡銘中的一類七言體即可視為三言體的連綴,“三+(兮)+三”型鏡銘是由三言句式組合而來。例如七言鏡銘:“上大(太)山兮見仙人,食玉英兮飲澧(醴)泉,駕交(蛟)龍兮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孫。”[1]352在另一則鏡銘中,同樣的內容則以三言形式呈現:“上華山,鳳皇(凰)集,見神鮮(仙),保長命,壽萬年,周復始,傳子孫,福祿進,日以前,食玉英,飲澧(醴)泉,駕青龍,乘浮云,白虎弓(引)。”[1]350每兩句三言,以虛詞相連,便形成七言句式。隨著制鏡技術不斷成熟,鏡銘可以容納更多文字,也就有一些虛詞出現,呈現出騷體詩的美感。
另有一類“四+三”型七言鏡銘則可視為騷體詩的簡省,對于該種鏡銘的溯源還需追至近期出土的海昏侯《衣鏡賦》一文。南昌海昏侯劉賀墓考古發掘出土的方形衣鏡,該鏡鏡掩(蓋)部分殘損嚴重,碎為數十塊,文字圖像辨識較為困難。鏡掩正反兩面都有彩繪和墨書文字。正面漆文為韻文,句式、意境與常見銅鏡鑄銘相同,且文字中直接寫出了“衣鏡”之名,故專家名之“衣鏡賦”。背面為孔子弟子圖像和傳記。劉賀生于公元前92年,卒于公元前59年,據此可推知《衣鏡賦》創作的大致年代為西漢中期。《衣鏡賦》釋文目前對外公布的有19行,包括缺失的一整行。內容如下:
新就衣鏡兮佳以明,質直見請兮政以方。
幸得降靈兮奉景光,脩容侍側兮辟非常。
猛獸鷙蟲兮守戶房,據雨蜚霧兮匢兇殃。傀偉造物兮除不詳。
右白虎兮左倉龍,下有玄鶴兮上鳳凰。
西王母兮東王公,福熹所歸兮淳恩臧,左右尚之兮日益昌。
□□□圣人兮孔子,□□之徒顏回卜商。
臨觀其意兮不亦康,[心]氣和平兮順陰陽。
[千秋萬]歲兮樂未央,[親安眾子兮]皆蒙慶,□□□□□□□□。[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的公眾號“器晤”上發布了關于《衣鏡賦》的一些簡單釋讀。筆者文末附有補充注釋,以期捋順行文。專家將海昏侯鏡掩上的篇章命名為“衣鏡賦”,顯然是因其具有明顯的“賦體”特征,句句又帶“兮”字,故可將其視為騷體賦的簡易形態。
賦是漢代文學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樣式。班固《漢書·藝文志》引《毛傳》“不歌而誦為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16]。漢代文人從功能、技巧等方面對賦體文學進行探索,產生了以《楚辭》為模仿對象的騷體賦,騷體賦的典型特征是以“兮”字句作為其基本句型[17]。騷體賦在漢初興起,以賈誼的《鵩鳥賦》《吊屈原賦》等為代表,至武宣時代顯盛。武帝命人為《楚辭》作傳,《楚辭章句》載:“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18]由此推動對《楚辭》的研究。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騷體賦在這一時期也乘勢而起。劉安或其門客創作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等為該體裁的代表作。這一風潮至宣帝時漸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再難達到前人的高度。
筆者認為,雖然《衣鏡賦》具有明顯的騷體賦特征,但其文辭簡樸、篇幅較短,亦無鋪陳揚抑,更加接近騷體詩。漢代的騷體七言多為“三+(兮)+三”“四+(兮)+三”的混雜,并漸趨成為一種固定的書寫形式。如劉邦《大風歌》是一句“三+(兮)+三”和“四+(兮)+三”。《秋風辭》也是以“三+(兮)+三”為主,雜兩句“四+(兮)+三”。東漢民謠中也有“四+(兮)+三”的節奏句,如《后漢書·皇甫嵩傳》引百姓歌:“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19]
《衣鏡賦》每句八言,呈現出與同時期鏡銘不同的語體特征。如果將其“兮”字去掉,每句呈現出“四+三”的句型,可將其視為早期七言鏡銘的起源。在東漢時期,句式為“四+三”型的七言鏡銘大量出現,例如西漢中晚期鏡銘:“湅治銅華清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長年益壽去不羊,與天長久而日月之光,千萬旦而未央。”[1]228新莽時期鏡銘:“尚方御竟大毋傷,左龍右虎辟不羊(祥),朱鳥玄武調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上有仙人高敖(遨)祥(翔),壽敝(比)金石如侯王兮.”[1]314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后世鏡銘都與該篇賦文有著緊密的承襲關系。倘若賦文中的“兮”字脫落,便形成“新就衣鏡佳以明,質直見請政以方”的七言詩體。可以推測,后世常見的七言鏡銘是從八言的賦體鏡銘中脫化而來,進而演變為相對獨立的韻文,可見騷體文學在當時影響之大。
關于騷體賦“兮”字脫落的原因,林曉光在《從“兮”字的脫落看漢晉騷體賦的文體變異》一文認為在傳抄過程中“兮”容易發生脫落:“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兮’字作為虛字,在賦已經轉化為書寫文本后,有無此字都不影響語意表達;另一方面恐怕是因為其極高的重復率,這一點可以從《九愍》這樣大篇幅的文辭中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對一個抄寫者而言,每隔若干字就要抄寫一個相同的字,無疑是十分厭煩的工作。”[20]鏡銘的書寫也是如此。一者因為鏡銘書寫空間有限,對字數有著嚴格的要求,省字現象在鏡銘中時有發生,“兮”字作為無意義的虛詞,只起舒緩語氣的作用,是很容易被省去的。而《衣鏡賦》書于鏡掩之上,書寫空間較大,自然可以呈現出內容、句式都更為豐富完整的面貌。又及刻工甚少重視文體的表現形式,省去多余的字體倒是為書寫提供了便利。而為貴族階層制作的器物在紋飾、賦文、書法等方面會更為考究,“兮”字可以造成句中延遲,使行文富有韻律之美,舒緩而有起伏,造鏡者便可選擇當時盛行的騷體賦(詩)來作為衣鏡文的載體。
第三類七言鏡銘體式由“六言句末+(兮)”型構成。上文曾提及鏡銘中有一些六言鏡銘,帶有明顯的騷體詩風格,有其獨特的韻律之美。例如“昭明鏡銘”:“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21]“清白鏡銘”:“潔清白以事君,怨陰歡之弇明。煥玄錫而流澤,恐志疏(或作疏遠)而日忘,懷靡美之窮禮,外承歡之可說。慕窈窕于靈景,愿永思而毋絕。”[22]稍晚也見到合昭明鏡和清白鏡銘于一鏡中,多見于銘重圈鏡,此類銅鏡完全以鏡銘作為鏡背的裝飾紋樣。如梁鑒藏“內清質”全銘鏡,其內圈銘作:“內(納)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外圈銘文則為:“潔清白以事君,怨陰歡之弇明。煥玄錫而流澤,恐志疏(或作疏遠)而日忘,懷靡美之窮禮,外承歡之可說。慕窈窕于靈景,愿永思而毋絕。”[23]357該類鏡銘文辭精美,又屢見于出土銅鏡之上,可自歸為一類。在出土銅鏡中,多見的是殘缺鏡銘,例如梁鑒藏有一面殘銘鏡:“潔(挈)精(清)[白]而事君,志(患)[污] 驩(穢)之合(弇)明。彼(被)玄錫之[流]澤,恐疏遠[而]日忘,懷[媚]美之窮(躬)禮(體),[外]承驩(歡)之可說(悅)。[慕窈窕于靈景,愿永思而毋]之紀(絕)。”[23]357因筆者未能見到實物,故摘錄李零補充的鏡銘,其中缺字用[ ]補出,錯字用( )補出。李零認為漢有完整鏡銘流行,人人皆熟讀于心,由于鏡銘設計不周,難以容納完整鏡銘,故有減省,造成殘銘鏡的現象[23]357。通過對鏡背裝飾的整體觀察可以看出,殘缺鏡銘的出現也并非完全由于工匠失誤,例如該條疏漏頗多的鏡銘出現在八角連弧紋鏡上,鏡銘亦多與繁復紋飾相搭配(參見《古鏡今照》圖44與高本漢《中國早期銅鏡》圖F8),說明在這些銅鏡中,鏡銘只是作為圖案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修飾意味高于文字本身內容。而在以銘文為主體內容的全銘鏡和《衣鏡賦》中,銘文是銅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未有隨意減省的現象,文辭的體式之美及教化意義才得以凸顯,使今人得以窺見鏡銘的完整面貌。在梳理鏡銘體式演變歷程時,應以其最完整的一則為主,才能反映文體的真實面貌。
全銘鏡的內外圈銘文亦可自由組合,例如山西朔縣漢墓出銘重圈鏡,其內圈銘與“昭明鏡銘”一致,外圈銘文替換為“姚皎光”鏡銘:“如(妙)皎光而耀美,挾佳都而無(承)間。懷驩(觀)察而性寧(紓),志(愛)存神而不遷。得并觀(見)而不棄(衰),精昭折而伴君。”[24](括號內文字為李零對釋文的修正)該類鏡銘在句末加“兮”字,便又構成了七言鏡銘,例如梁鑒有兩件“姚皎光”鏡,取鏡銘完整者如下:“姚(眺)皎光而曜美兮,挾佳都而承閑。懷驩(觀)察而恚予兮,愛存神而不遷。得竝埶(執)而不衰兮精(請)昭折(皙)而侍君。(外圈)”[23]357
故而,楚辭體對七言鏡銘的影響是靈活的,既可以通過刪去八言賦中的虛詞形成七言句式,又可通過在句中或句末增添“兮”字把韻文塑造成七言的形態。而增添“兮”字與刻工力求文字簡省也并不矛盾,在新莽時期,七言鏡銘已頗為普及,為適應當時的慣用句式,增添“兮”字湊為七言句亦在情理之中。不過,七言鏡銘也并非完全脫胎于楚辭體,廖群曾指出有些七言鏡銘更近似于民謠、順口溜:“揚州出土的規矩鏡有‘浮游天下及四海,堅如大石之國寶’句,就很難在四字后面加入‘兮’字,這種句式顯然并非是由楚騷‘兮’字句演化而來的。”[25]該鏡應為新莽時期規矩鏡,在鏡銘七言體的演變中已屬于后期成熟形態,完全脫離楚辭體形態,更接近于當時流行的民謠。
三、鏡銘的內在結構
鏡銘的主體內容為祝頌類文辭,與祝頌類詩歌不同,詩歌無論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呈現出一種定式。例如《郊祀歌》十九章是漢武帝時期的一組朝廷樂歌,其使用場合應為莊重的祭祀禮,文本結構安排必定具有嚴格的秩序性。例如《赤蛟》一篇,記錄了享用祭祀的全過程:“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暗濭。百君禮,六龍位,勺(酌)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輯(集)萬國。靈禗禗,象輿,票(飄)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讬玄德,長無衰。”[4]154神靈從享用祭品到降下福祉,這個順序是固定而不可隨意更改的。同理,《練時日》中的“靈之來”“靈之至”“靈已坐”[4]145記錄了神靈從遠方到來的過程。
早期鏡銘的結構安排并沒有顯明的秩序性。西漢早期三言、四言鏡銘中,只注重相鄰兩句是否貼切,句組之間關系任意性較大。例如“與天相壽,與地相長,富貴如言,長樂未央”[1]86前兩句中“天”“地”相對,“富貴”之后,祈求“長樂”,而前兩句和后兩句之間沒有太多的邏輯聯系。西漢早期鏡銘句序安排靈活,結構松散,可以調換。“與天相壽,與地相長,富貴如言,長樂未央”的各分句順序,在另一組鏡銘中會略有不同,在“清練銅華,雜錫銀黃,以成明鏡,令名文章,延年益壽,長樂未央,壽敝金石,與天為常,善哉毋傷”[1]226一則中,本位于句末的“長樂未央”被放置句中,而“與天為常”(近似“與天相壽”)被替換到句末。鏡銘的內容應是當時社會普遍盛行的祝頌語,制鏡者和用鏡者都熟記于心,個別句序的調整,并不影響對整篇鏡銘的理解。
而在海昏侯《衣鏡賦》中,賦文已具備內部結構的完整性,句子之間聯系緊密。賦文前四句首先陳說了衣鏡的品質及功能。中間部分描述鏡框上所繪的圖案,有白虎、蒼龍、玄鶴、鳳凰,以及西王母和東王公,它們保佑人們享有福澤。而后又描繪了圣人孔子及其弟子顏回、卜商等人,提示人在照鏡時,可以圣人和其弟子的言行檢視自己,如此便可保持康樂、調順陰陽。最后的“樂未央”“皆蒙慶”則為常見的祝頌套語。可以想見,鏡賦的作者應為級別較低的文人或較有文化的鏡師,他們根據上層的授意,結合當時流行的祝頌用語來創制鏡文。
銅鏡銘文中的七言體亦是如此。例如“尚方御竟大毋傷,左龍右虎辟不羊(祥),朱鳥玄武調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上有仙人高敖(遨)祥(翔),壽敝(比)金石如侯王兮”[1]314一詩,先說明銅鏡的來源為“尚方制鏡”,品質是“大毋傷”,再敘述圖案,位于鏡周四方的是“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處在中間的是受福對象子孫;繼而描寫高高在上的仙人,他們是長壽的象征;最后表達祝頌“壽比金石”。這種“鏡作者+鏡品質+鏡紋飾+祝頌語”的敘述方式與《衣鏡賦》如出一轍,多數鏡銘的結構均可以此為例。此時的三言鏡銘也漸趨成熟,例如:“上華山,鳳皇(凰)集,見神鮮(仙),保長命,壽萬年,周復始,傳子孫,福祿進,日以前,食玉英,飲澧(醴)泉,駕青龍,乘浮云,白虎弓(引)。”[1]350句序間邏輯性更強,完整呈現了上華山遇仙人,求得長生之法的過程。由于具有了完整的敘事結構,句間順序也不會任意變動。鏡銘形成了固定模版,比詩歌模式性更強,模板數量有限且不會輕易變更,各地域銅鏡亦會互相流動,融匯彼此風格,故出土銅鏡眾多,雷同卻也不少。但鏡銘畢竟是一種實用器具,鏡師在鑄造過程中,往往會因為文化水平限制,或鏡體空間促狹等,隨意增刪更改文字,這類現象在制造較為粗糙的銅鏡中時有發生。
鏡銘的書寫內容、順序與鏡背圖案息息相關,換言之,鏡銘是對圖案的釋讀,可視為圖案的腳注,銘文結構的安排依圖像而定,以四靈鏡和畫像鏡最為典型。新莽時期四靈鏡興盛,常有鏡銘:“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掌四彭(旁),朱爵(雀)玄武順陰陽,八子九孫治理、中央,刻婁(鏤)博局去不羊(祥),家常大富宜君王,千秋萬歲樂未央。”[1]328銅鏡主紋分布了四靈紋飾:北(下)玄武,南(上)朱雀,東(左)青龍,西(右)白虎。中心十二地支的“子”在下(北方玄武位),“午”在上(南方朱雀位),子午線穿鈕而過。紋飾與銘文相配,鏡背布局協調,渾然一體。北京瑞平2014年春季拍賣會拍賣一件龍虎銅鏡,鏡紐外龍虎對峙,銘文為“佳鏡兮樂未央,辟邪天祿居中央。杜氏所作成文章,服之吉利富貴昌。子孫備具金甫(鋪)堂,傳之后世以為常男封列侯皆九[卿]。”[26]諸多學者據此認為該類銅鏡命名為龍虎鏡實不確切,依鏡銘所言,鏡上圖案應為辟邪與天祿。畫像鏡多見于東漢,銅鏡內區的畫像旁往往標識榜題,如東漢永元三年,有銘神人白虎畫像鏡,鏡內按順時針方向分布有“永元三年作”“仙人”“西王母”“白虎”“仙人”“王公”“玉女”“云中玉昌(倡)”的榜題,鏡銘為:“石氏作竟世少有,東王公,西王母,人有三仙侍左右,后常侍,名玉女,云中玉昌□□鼓,白虎喜怒毋央咎,男為公侯女□□,千秋萬歲生長久。”[1]372銘文中出現的神仙恰與圖像對應。鏡銘與榜題相輔助,為四靈與畫像的辨識提供幫助。由此可知,鏡銘的書寫并非是獨立的系統,文辭之始與圖案息息相關,可以推測,上文所舉鏡銘是特為該類畫像鏡所作,據圖稿而成文。正如一面瑞獸博局鏡銘刻寫“上有禽守(獸)相因連,湅治銅錫自生文”[1]354,可以看出制鏡者在刻繪圖案和編輯銘文時的用心精巧。隨著造鏡的規模化生產,鏡銘與圖案的聯系才漸漸松散,有些繪有四靈圖案的銅鏡并沒有與之相配的“四靈類”鏡銘,推測此類銅鏡的制作不如“特供鏡”極費心思或可能較為晚出。
四、小結
漢代的七言詩并不多見,主要存于民間謠諺和樂府詩中。學者普遍認為七言詩主要是在《楚辭》和民間歌謠的雙重影響下產生的,同時銅鏡銘文、荀子《成相》的“三三七言”和《太平經》等也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27]。事實上,七言的銅鏡銘文的構成以四言和三言的組合為前提,生成方式與騷體詩(賦)息息相關,又和民間歌謠多有共通之處。某種新文體樣式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各種文體相互交流、相互滲透、承襲革新、孕育與演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