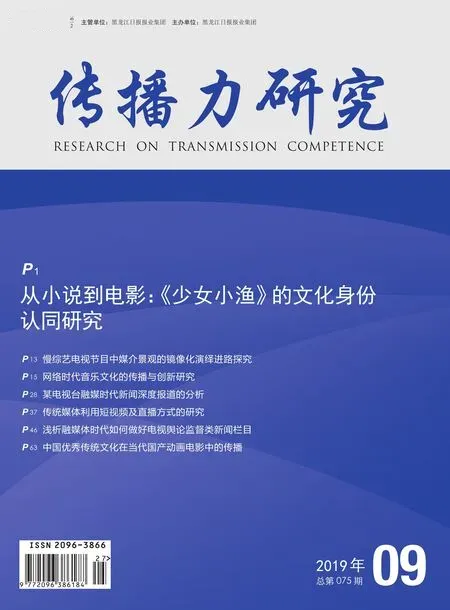愛國主義視域下的湖南精神探析
彭鍇 湖南廣播電視大學 彭忠信 邵陽學院
在湖湘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積淀而成的“忠誠、擔當、求是、圖強”的湖南精神,已成為了激勵三湘兒女不斷奮斗的重要精神力量,而“愛國主義”則是貫穿其中的核心內容。我們現在已邁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開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從愛國主義視域對“忠誠、擔當、求是、圖強”的湖南精神進行探析,對把握湖南精神的精神內核,進而確立湖南人民在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的忠誠精神
“心懷天下,憂國憂民”自古以來就是流傳在湖湘大地上的精神稟賦。戰國時期屈原被譽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雖遭流放,仍眷戀祖國、“哀民生之多艱”,求回朝興楚而不得,直至楚亡投身汨羅江,以身殉國。西漢時期賈誼貶至長沙,但仍然“國耳忘家,公耳忘私”(《治安策》)。北宋時期范仲淹推動“慶歷新政”,失敗后同樣遭讒被逐,仍“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岳陽樓記》中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絕唱。至南宋及明末時,面對金、元、清等異族的入侵,湖湘的儒家學者運用“華夷之辯”的理論,堅決抵抗,反對投降。在潭州(今長沙)創立碧泉書院的胡安國曾建議朝廷“當必志于收復中原,祗奉陵寢;必志于掃平仇敵,迎復兩宮”;其子胡宏寧可隱居衡山過清貧的生活,也不愿與主張妥協投降的秦檜往來,拒不接受秦檜的召用;胡宏的弟子,在城南、岳麓兩書院講學的張栻更以力主抗金聞名于世,并把抗金復仇作為治國大綱:“自古為國,必有大綱,復仇之義,今日之大綱也”(《南軒集·戊午讜議》)[1]。而明末的王夫之更是把民族利益視為至上,雖主張華夷平等,但認為漢族政權只能由漢人接任,不可由異族接任,“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黃書·原極》)。在舉兵抗清失敗之后,王夫之在民族淪亡的痛苦和強烈的民族意識的驅使下,返回家鄉衡陽,畢竟余生不遺余力地研究歷史上的興亡之道,尋求民族復興之路,終身不降清。他的愛國民族精神,在他的著作中隨處可見。這些儒家學者的愛國主義主要體現為“忠于民族”,已經掙開了忠于一家一姓的枷鎖,具有了更大的普適性。不過,這些古人的愛國主義精神主要體現為“忠君愛民”,雖有封建的某些局限和狹隘性,但仍不掩其愛國精神的光芒。近代以后,隨著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愛國主義精神在湖南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從“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左宗棠到“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的毛澤東,湖湘子弟們的愛國之心逐漸上升為對國家、民族、人民全面的忠誠。更重要的是,他們除借詩文表達之外,近代湖南人更是用實際行動努力改變中國的苦難命運。
二、“前赴后繼,不畏犧牲”的擔當精神
陳獨秀曾在《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中引用楊度的詩:“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他在文中感嘆:曾國藩、羅澤南等一介書生“扎硬寨”、“打死戰”,組建了赫赫有名的湘軍;黃興帶著一旅湖南兵就在漢陽抵擋了清廷的大批軍隊;蔡鍔帶病領兵,以彈藥不足的兩千殘旅死戰袁世凱十萬大軍,“他們是何等堅韌不拔的軍人”!在今日看,曾、羅、黃、蔡雖階級立場不一,但都以湖南人特有的“蠻勁”,表現了他們的為國擔當之心。湖南人的這種擔當精神有時顯得非常悲壯,甚至為了國家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新化人陳天華為例,陳天華在岳麓書院求學時就立志“國不安,吾不娶”,生前以強烈的愛國精神和革命勇氣撰寫了《猛回頭》《警世鐘》等一系列宣傳愛國反帝思想的文章,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他在投海前留下了三千余字的《絕命書》,寄望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去絕非行,共講愛國”“堅忍奉公,力學愛國”。他“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為加強警醒效果,不惜選擇以死明志,以身殉國。湖南人自近代之后為國做出的犧牲有目共睹。在湖南師范大學饒懷民教授主編的《三湘英烈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叢書里,所收錄的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湘籍英烈就有345名[2]。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人民更是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有姓名可考被政府追認為烈士的就有十五萬人之多。衡陽人夏明翰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面對國民黨的屠殺曾寫道:“越殺膽越大,殺絕也不怕。不斬蔣賊頭,何以謝天下”,隨后投筆從戎,參加第二次北伐。而在1928年因叛徒出賣被捕后,他更是寫道:“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之后,他大義凜然、英勇就義。夏明翰是共產黨員,他的“主義”一方面自然可以理解為“共產主義”,但中國共產黨人用“共產主義”救中國,其中也蘊含著“愛國主義”精神。而支持著一批又一批的湖湘兒女勇于擔當、前赴后繼、不畏犧牲的,也包含有愛國主義的“主義之真”。
三、“經世致用,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
湖南人的求是精神早在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詩句中即有體現,而自宋代開創的湖湘學派將這一精神予以繼承并發揚光大。湖湘學派提倡重踐履、輕空談的務實學風,體現得非常突出。如前文所述的湖湘儒者胡安國終身追求并倡導“強學習行,以圣人為標的,志于康濟時艱”(《安史》本傳)的經世致用的知行觀。[3]胡宏主張要將心性義理之學與經世致用相結合,反對坐而論道。張栻也以“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強調行動實踐對于獲知真理的重要性,主張要在力行實踐中實現儒家修齊治平的責任。明末王夫之進一步發展了湖湘學派的經世傳統,在知行觀方面批判了程朱理學的“先知后行說”,提出了“行先知后”的觀點。這些觀念和思想對后來的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黃興、毛澤東等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面對國家的內憂外患,他們在黑暗中苦苦探索,尋求救國救民的良方。[5]這和王夫之“視聽之明,可以攝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張之正蒙注·大心篇》)的觀點異曲同工。為了讓黨內外重視農民革命斗爭的重要性,為工人階級找到最可靠的同盟軍,毛澤東深入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村,考察當地的農民運動并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明確指出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這也幫助其養成了之后在工作中重視調查研究、掌握實際情況的習慣。在實踐觀上,毛澤東也充分吸收和發展了湖湘學派“力行第一”和“行先知后”的觀點。《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些著作的產生,就不是憑空想象得來,而是毛澤東經過秋收起義的失敗,在井岡山親自領導工農武裝,做了大量工作之后總結斗爭實踐經驗的結果,從而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最終實現了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而這些實踐和由之形成的理論,也凝練出了“實事求是”這一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它可以說是湖湘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在踐行救國圖存之路上的融合,至今仍指導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建設事業。
四、“敢為人先,開拓進取”的圖強精神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魏源等一批少數的先進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意識到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認為是否“師夷長技”是關系到能否戰勝外國侵略者,能否挽救國家于危難的大事。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指出:“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他這種“以師夷為手段,以制夷為目的”的反侵略主張,表現了一種光輝的愛國主義思想,是近代中國邁出通過向西方學習、改變國家命運的第一步。然而《海國圖志》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并沒有引起腐朽的清政府的重視,反而漂洋過海為日本的“明治維新”奠定了思想基礎。直到二十余年后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面對日益劇增的內憂外患,清朝的統治者才如夢方醒開始學習西方,而曾國藩、左宗棠等湖南人成為了最早一批領導洋務運動的地方官員。曾國藩等人本是傳統的封建士大夫,尊崇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儒家思想盡善盡美的意識可謂根深蒂固。但是,在國家民族危難現實和湖湘經世致用學風的雙重影響下,以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地方勢力以“富國強兵”為目的,成為了洋務運動最有力的推動者。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有了第一艘自制輪船,開辦了第一批新式學堂,建立了第一批翻譯館,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可以說,是曾國藩等人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建設。甲午戰爭失敗后,中國再次陷入彷徨,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以“變法開新”為己任,支持成立了長沙時務學堂。梁啟超、譚嗣同均為教習,使之成為維新運動的發源之地。梁啟超曾多次說:“新舊之哄,起于湘而波動于京師。”戊戌變法雖僅歷百日,但其開始了對中國長達兩千年封建制度的變革,啟蒙意義不言而喻。毛澤東青年時也以梁啟超為偶像,他和蔡和森等人在長沙創立新民學會,初時即為“培育新民”。而在之后為“改造中國與世界”尋求新思想的過程中,這批湖南青年或赴法求學,或留湘開展社會調查,卻殊途同歸,從眾多的救國思想中確立了新的共同的主張——“用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來改造中國。從此,新民學會從一個學術團體轉變成為一個革命團體。而由新民學會中的骨干分子成立的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作為全國六個發起小組之一,派出了毛澤東和何叔衡作為代表參加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應該說,魏、曾、譚、毛等湖南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所表現來的“敢為人先,開拓進取”的圖強精神影響了整個中國近現代發展的進程,也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推動國家建設的重要精神力量,并進一步發展為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
五、結語
湖南精神歷經千年傳承,有其悠久歷史的文化底蘊,亦有其與時俱進的現實作用,而愛國主義精神始終是其核心的靈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傳承和弘揚湖南精神,必須牢牢抓住愛國主義這一主線,才更加有利于激勵湖南人民對國家忠誠、為國家擔當、求發展真理、圖國家富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