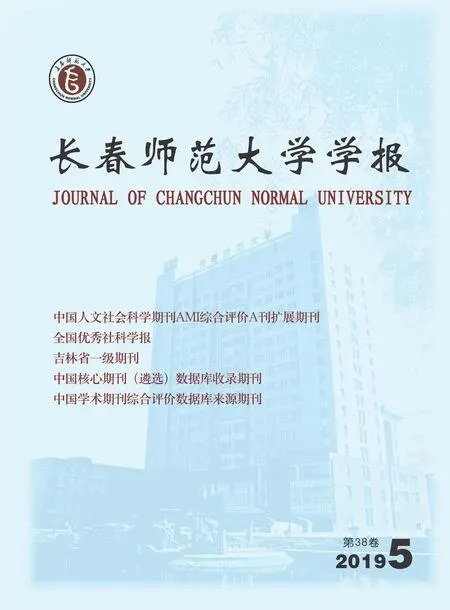試論金代的孝親教育
孫凌晨,羅丹丹
(1.長春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032;2.吉林省學校后勤管理指導中心,吉林 長春 130032)
中華文明底蘊深厚,孝道文化源遠流長,世世代代潤澤國人的心靈。金代統治者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摒棄原有習俗,接受儒家孝道思想,在社會上大力提倡孝親教育。
一、孝親教育的內容
孝道作為倫理綱常中最為重要的一種道德規范,對家庭的和睦乃至國家的穩定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孝道觀念源遠流長,早在《詩經》中便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1]之語。《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2]56;《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2]296;《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其致其嚴。五備也,然后能事親。”[3]53
中國古代社會以王權為核心,倫理政治化和政治倫理化是其鮮明特點,故“孝”必然會被導向政治倫理發展之路。孝的理論體系在先秦時期已出現政治化色彩的萌芽。孝在現實生活中被演化成一種社會規范,即孝道,從而使單純的孝與“忠”相聯系。《孝經》認為“孝”是道德的根本依據,是各個階層都應遵從的準則。統治者認為,孝能夠治理天下,“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3]36。孝道不僅是睦百姓、順天下的至德要道,也是子女的親情人倫關懷,“始于事親,忠于事君,終于立身”[4]3-4。故而,“孝道”為歷代中原王朝所傳承。
金代統治者注意到,孝道思想是中原地區一切人際關系得以展開的精神基礎和實踐起點,也是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的根本核心,對民眾的生活方式均有重大影響,在漢族民眾中廣泛流傳并深入人心。故女真統治者開始接受儒家思想,將推行孝親教育作為統治漢地的一種重要手段。
二、孝親教育的措施
為更好地在統治地區推行孝道思想,金代統治者借鑒前朝經驗,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舉措。
(一)對孝行給予物資嘉獎
金世宗認為,“凡士民之孝弟姻睦者舉而用之,其不顧廉恥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則加懲罰。”[5]卷8,187金章宗也認為,“孝義之人素行己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可檢勘前后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5]卷9,220明昌三年(1192),金章宗“詔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佑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5]卷9,220,后又“詔云內孝子孟興絹十六匹、粟二十石”[5]卷9,221,甚至“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舅姑割股者,并委所屬申覆朝廷,官支絹五匹、羊兩羫、酒兩瓶,以勸孝悌。”[6]502割股之事始見于《莊子·盜跖篇》:“介之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7]。介之推割股的行為發生在晉文公流亡落難時,目的是為人主盡忠。繼介之推之后的割股者是隋代晉陵人陳杲仁。《全唐文》載,“公(陳杲仁)事后親,親病須肉,時屬禁屠,肉不可致,公乃割股以充羹。”[8]卷915,9532與介之推不同,陳杲仁割股的目的是為孝親療疾。由于廣大民眾迷信割股可以為親人療疾,唐代割股之風益興盛,進而演變為一種民俗,并逐漸為封建統治者所褒獎。
在金代,因孝行而升遷者不乏其人。如明昌三年(1192),“以有司奏寧海州文登縣王震孝行,以嘗業進士,并試其文,特賜同進士出身,仍注教授一等職任”[5]卷9,222,“益都府舉王樞博學善書,事親至孝。敕(其)同進士出身,并附王澤榜”[5]卷9,224。
此外,金代統治者還從孝悌教育的角度出發,提倡幾世同居,并進行旌表嘉獎,給予免除賦役的賞賜。“三代同居孝義之家,委所屬申覆朝廷,旌表門閭,仍免戶下三年差發”。[6]502
(二)幫助官吏孝養親老
金代統治者采取多種方式為臣下孝養親老提供便利和幫助。如海陵王詔令“石抹榮外任時攜母同行,以便奉養,仍賜給錢萬貫”[5]卷91,2027;金世宗以韓鐸年高母老,“特與之便郡以奉養母親”[5]卷91,2027;金章宗以張萬公之母老邁,“特畀鄉郡,以遂孝養”[5]卷95,2103;李晏告老歸鄉后,金章宗特授其子李仲略為澤州刺史以便祿養[5]卷96,2128;金哀宗任命“石抹嵩為應奉翰林文字,以便奉養其父”[5]卷114,2519。在金代,因為養親而辭官者也大有人在。如金熙宗時期的蒲察通“因其父年老而辭官”[5]卷95,2105,金世宗時期的蕭貢也舍棄官職而回鄉奉老[5]卷105,2320。
(三)制定官員喪祭給假制度
父母去世,官員可以有喪葬、忌日和丁憂之假,以表達對親人的緬懷。金代政府對此形成制度化管理。海陵貞元元年(1153),“命內外官聞大功以上喪,止給當日假,若父母喪,聽給假三日,著為令。”[5]卷5,101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制子為改嫁母服喪三年”[5]卷6,141。明昌元年(1190),“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并給假一日。”[5]卷9,214泰和三年(1203),“定諸職官省親拜墓給假例。”[5]卷11,260“省親”是為健在的長輩盡孝,而“拜墓”是對已經過世的老人進行祭奠。金章宗為孝親教育的推行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社會風尚的良性發展。明昌元年(1190),“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并給假一日。”[5]卷9,214泰和三年(1203),“定諸職官省親拜墓給假例。”[5]卷11,260泰和五年(1205),“制司屬丞凡遭父母喪止給卒哭假,為永制。”[5]卷12,271金代政府雖然對行孝舉措沒有形成條例性管理,但對丁憂喪葬還是有明確規定的。
(四)以禮入法
金代政府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老人的利益,對不孝行為進行懲戒。如有針對養老的法律,“祖父母、父母無人侍養,而子孫遠游至經歲者,甚傷風化,雖舊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輕。其考前律,再議以聞。”[5]卷12,274“父母在,不遠游”[9]。政府還制定了“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5]卷11,254,并將對父母進行詛咒之人予以重罰[10]120。另外,“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各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三等。”這屬于“男入不孝”“婦入不義”之行為[10]89。金代政府針對該行為有“徒二年”之規定,使年邁者能夠被子孫孝養。
金代政府對僧道群體是否應盡孝道也有明文規定。尚書省于明昌三年(1192)上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壞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敕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于末。自今以后并聽拜父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故行之。”[5]卷9,221制令同意。可見金朝摒棄了遼朝過度崇佛的弊端,以傳統的孝道思想對僧道群體予以倫理約束。
三、孝親教育的成效
金代統治者通過大力提倡孝親教育,實現了移孝于忠的目的。孝親與忠君互為表里,孝的作用逐漸政治化和社會化。以孝事父的延伸等同以忠事君,利于維護統治,成為維護君主和宗法等級的有效工具。在金代,“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5]卷121,2633
《金史·孝友傳》中多有關于孝悌之行的記載。“孝友以至行傳于歷代之史,劭農、興孝之教不廢于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5]卷127,2745金世宗認為,“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后能。”[5]卷89,1984-1985在政府的大力倡導下,孝道得以在社會上盛行。如,“聶大中之先,廉孝傳家,士之稱家風者歸焉”[11];“奉直趙君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根本”[12]1431;“薛繼先事母孝,子純孝有父風”[13];“聶元吉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12]1424。
金代統治者對孝親教育的倡導,使社會上形成了“教育可行,孝弟可興矣”[5]卷10,227的良好風尚。到了金代中后期,更是出現“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管制,典章文物粲然成治規”[5]卷12,285的氣象,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北方廣大地區文明發展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