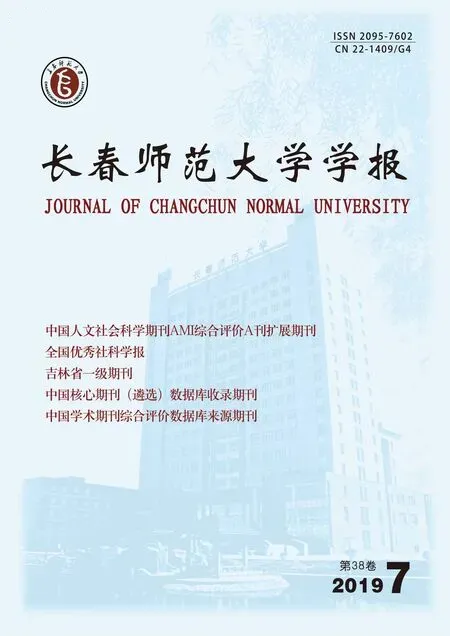北伐時期湖南地區的國民黨與基督教
李曄曄
(吉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1922年春,由上海爆發的“非基督運動”逐漸向北京、長沙、廣州等地蔓延,反教與否成為當時思想界、新聞界、教育界爭論的熱點話題,在中國的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一番極為熱烈的場面。具體到湖南地區而言,當地的反基督教運動在此風潮激蕩下有很大發展。1924年下半年,湖南地區學生即已組織“非基督教同盟”。1924年11月、12月,湖南益陽教會學校信義中學、長沙教會學校雅禮中學相繼發生大批學生退學事件。此后,醴陵、湘潭等地也相繼爆發類似事件,引發湖南地區劇烈的“反教運動”。中國共產黨湖南地方組織在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一是發動教育界組織‘最高主權維持會’,幫助安排退學學生轉學;二是原來學聯議決拒絕教會學校參加全省運動會,后來改為準許教會學校學生以個人名義參加,使教會學校學生不致產生誤會和對立。”[1]1926年6月北伐開始后,湖南地區的基督教會受到嚴重沖擊,“反教是國民黨全面推行反帝國主義運動所衍伸出來的支流。”[2]在洶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基督教會不斷改變自身的定位,努力褪去自身“侵略”的屬性,將基督教還原為宗教的本來面目,但長久以來的固定形象是難以短時期扭轉的。本文以北伐視閾中的基督教為研究對象,考察在革命風潮下國民黨黨政雙方對基督教的不同態度及基督教會的應對。
一、反文化侵略過程中國民黨黨政雙方的不同面目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之后國民黨日益表現出激進的反帝立場,國民政府之外交“主張在取消不平等條約,而從根本上恢復平等與互惠之原則,重訂新約,再對付外國之辦法。將與各國分別單獨交際,不承認所謂公使團與領事團等,外國貿易,仍當提倡,以舒稅收。”[3]1925年6月23日、28日,國民黨中央兩次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聲稱:“對于不平等條約,應宣布廢除,不應以請求修改為搪塞之具。”[4]同時,國民黨各省、市黨部為彰顯革命,也對廢除不平等條約極為熱心,呈現出一片熱鬧景象。北伐時期反帝浪潮得以大規模擴展,基督教也受到沖擊。“我們很知道反基督教運動是什么一回事,它不是由幾個煽動家手中創造出來,像帝國主義者所說的,而是中國勞苦群眾與國際帝國主義者沖突的表現。”[5]
北伐的討伐對象——北洋軍閥并不認可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邏輯關聯:“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近以反教運動甚囂塵上,昨特發出布告十張,寄與交涉公署。囑即轉知領團查照。”“查今日非教運動往往逾越軌范,肆意攻擊,甚或威逼群眾,傷人毀物,跡近暴動。顯有奸人暗中主使,藉此為名。意圖破壞國際信用,擾亂安寧秩序。本總司令惟有執法以繩,斷難寬容。為此布告軍民人等一體知悉。勿輕聽流言,任意盲從,自干刑法,中外傳教人等,并宜安居樂業,切勿張皇自擾。”[6]甚至對“非教運動”進行過干涉,“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會開會,并散布反對基督教之印刷品,查鼓吹仇教有背條約,自應設法防止,以免釀成事端。”[7]
在北伐開始前,國民黨對“非教運動”也采取不干涉的立場。“廣州學生界進舉反基督運動……反基督與基督徒遂成對峙之勢,政治委員會以此問題關系各校學生青年甚大,乃特于昨日會議提出討論,會以吾黨對于宗教問題,取信仰自由之義,對于此次反基督亦當本此態度處之。反對與贊成兩方,可自由討論,任其各個發表意見。但兩方皆不得為騷擾及壓迫之行為。”[8]
“非教運動”在北伐時期的革命語境中已經完全政治化,成為在反對帝國主義旗幟下進行的政治活動,屬于民眾運動的范疇,具有特定的政治意義。湖南地區的“非教運動”以反文化侵略最為突出。1926年12月14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青年部、國民黨長沙市黨部青年部、全國學聯會、長沙縣學聯會、雪恥會、青年婦女學藝社等共同發起成立了“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在成立大會上,國民黨湖南省黨部青年部部長周以栗提出:“文化侵略,是帝國主義一種殺人不見血,最陰狠的侵略政策。”“基督教現在毫無存在的價值,從事實方面證明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急先鋒……中國之淪為殖民地,全為基督教之恩賜。至于基督教會學校之專制守舊,禁止愛國運動,亦應急于反對。”[9]并表示要援助基督教會學校學生的自由斗爭。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直接支持下,湖南地區針對基督教的反文化侵略活動日趨激烈。
北伐時期湖南地區的反文化侵略活動在1926年12月25日前后達到一個高潮。“本月二十五日,為耶穌誕日,湖南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定于是日作大規模之反對宣傳,昨下午三時在第一中學大禮堂,召集各校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如下:“(一)定于二十五日上午在幻燈場舉行演講大會,痛述耶穌為帝國主義之工具,下午一時在教育會舉行游藝大會,表演耶穌與教會之黑幕;(二)推定游藝員、布置員、糾察員、募捐員。”[10]湖南“反文化侵略大同盟”的口號頗能反映人們對基督教與文化侵略關系的認識:“一、反對文化侵略;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的急先鋒基督教;三、援助教會群眾自由奮斗;四、贊助中國教徒收回教會;五、革新教會教育;六、政府從速頒布教會學校立案條例;七、嚴禁教會學校強迫學生讀圣經、做禮拜;八、教會群眾加入革命戰線;九、中國教室歸中國人自辦;十、反對麻醉中國人的基督教,中國不平等條約是基督教鬧起來的。”[11]在基督教重大節日圣誕節進行反教活動不是北伐時期的創舉,1924年湖南長沙地區就已經有過先例,當時提出的口號是:“(一)打倒基督教;(二)根本取消教會學校;(三)反對文化侵略;(四)謹防基督教之麻醉毒。”[12]只不過規模沒有此次大,影響也差之甚遠。
除了省會長沙外,湖南其他地區也大多發生涉及教會事件。“寶慶、瀏陽等縣,近因民眾運動,發生涉及教會事件。”[13]比較激烈的如新化地區對基督教福音堂的抵制:“反基督運動大同盟會,以耶穌誕期,福音堂例應舉行慶祝,特組織宣傳、糾察各隊,嚴厲制止平民參加,總務主任為吳興周,總指揮為曾宅三,自二十四日晚起督率各校糾察隊,在福音堂附近巡邏,宣傳隊則常駐福音堂門首輪流演講,以期喚醒民眾。”[14]湘潭地區舉行了大規模的反文化侵略示威大會:“本月二十五日,湘潭縣區黨部,工農商學軍警政報各界人士,舉行反文化侵略示威運動大游行,計劃團體一百余個,民眾七萬余人,民情激昂,秩序井然。”[15]其目的在于“促進民眾之同情,而使各教會與信徒之覺悟。”[16]顯然,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這一看法已經得到湖南地區很多民眾的認可。有鑒于此,湖南省基督教協進會向湖南省地方當局求援。湖南省政府認為此類事件“在民眾心理,無非欲急謀解放,然因充分表現之結果,或不免遇事熱烈,在此形勢之下,欲減少糾紛,端賴雙方之諒解。”[17]遂命令縣政府“嗣后對于此種事件,務須注意相機疏解。”[18]
從反對文化侵略來看,北伐時期的“反教運動”并非以“非科學性”這一角度來推進,更多的是關注基督教會“侵略”屬性。顯然,在革命視閾下仍與西方列強有著相當關聯的基督教往往成為革命過程中顯而易見的目標,而且反對基督教一般不會激起社會階層大的分裂。有論者在“反教運動”高漲之時就曾指出基督教會“無文化侵略之心,而實蒙文化侵略之害。”[19]國民黨黨政雙方的著力點是截然不同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極力推動反教的民眾運動,湖南省政府則力圖控制民眾運動的規模,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二、教育主權收回過程中國民黨黨政雙方的協作
從宏觀上說,教育主權的收回屬于反文化侵略的范疇。在教育主權收回過程中,國民黨黨政雙方配合相得益彰。
基督教教會學校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教學體系,打破了中國教育的固有傳統,提供了一套嶄新的教育制度,同時也為教育機構提供了師資力量及其他管理人才,中國自辦的一些高等院校往往以教會大學為樣板。但不容否認的是,教會學校還是培養大量福音傳播者的基地。這二重身份不斷撕扯教會學校在中國社會的定位及地位,使其在革命視野中成為一種反面的存在。“基督教在中國的勢力漸漸擴張,他的罪惡也隨之增大。他們辦學校的目的,是想麻醉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唯一依賴的青年,所以他們訓練的學生,只在做帝國主義的順民。”[20]“只有文化侵略可以有軟化馴服弱小民族的秒用,使弱小民族以受大國‘懷’、‘柔’之統治為莫大的光榮。”[21]
湖南長沙雅禮中學學生風潮是湖南地區收回教育主權過程中的一個典型事例。雅禮中學學生會以校方宣傳基督教為宗旨、實行文化侵略為由,提出關于改良校務的二十六條意見,而雅禮中學校方一直拖延推諉。從1926年12月4日開始,學生一致罷課,罷課風潮很快蔓延至湖南其他各教會學校。12月9日,雅禮中學學生會召集長沙其他教會學校學生開聯席會議,決定“教會學校學生此后,采取一致行動,以謀解放;擬組織教會學校學生聯合會,共同奮斗。”[22]很快,湖南長沙境內的“雅禮、成智、雅各等校相繼罷課”,湖南學生聯合會召開會議予以積極援助,“呈請政府頒行國民政府限制教會學校條例;必要時舉行教會學校示威大運動。”[23]雅禮校方一直寸步不讓,認為學生行為“軌外行動,絕對不能同情”,如果學生再堅持罷課,“本校惟有提前放假。”學生方面堅持己見,“再赴教育廳、省黨部、市黨部、總工會、市教聯會等處請求援助,并督解決。”而學生家長站在學生一邊,“各家長均以此次改良教務運動為正當,勉勵該生等堅持到底。”[24]
湖南省政府教育廳對此次風潮也極為重視,“除將國民政府取締私校規程,通知各教會學校一律遵辦外,并派省視學于愈眾、姚孟宗、王惕三君前往雅禮,及其他教會學校視察情形,持平處理。”[24]針對雅禮罷課風潮,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同樣持支持態度,“查基督教會在華設立學校,自應尊重我國教育主權,乃查其課程編制,及一切設施,全不合我國教育規程,純為藉名設校,實行文化侵略,在此革命區域之下,亟應從嚴取締,以免麻痹革命青年,消除民族革命意志。此次該校學生向校中當局所提出條件,俱系正當要求,且湘省各校多有實行者,唯獨該校當局,一味壓迫狡詐,不予答復。近復提倡提前放假,不惜犧牲數百青年光陰,殊屬藐玩。”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要求湖南省政府迅速飭令“該校容納學生要求,不得無故提前放假,荒廢青年學業,使該校風潮早日解決,并頒布教育會學校立案暫行條例,通令各教會學校,一律照章立案,以防文化侵略,而圖教育主權之收回。”[25]
但雅禮罷課風潮仍在發酵,校方立場并不因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政府對學生的支持而有所變化,仍然“停火食”、提前放假。雅禮中學學生會立即推舉代表“往教育廳陳明學校反抗命令,藐視政府,公然提前放假,請將學校關閉。”湖南省教育廳認為“該校既無故停辦,自應厚以處分。”[26]在政治壓力下,雅禮中學向國民政府立案,收回教育主權達到一定成效。
基督教會人士對此極力反對:“國家無直接教育權,教育兒童亦無專權設學校之名分,不有其權而收回,乃一滑稽之語言。”[27]但是學生的罷課風潮及隨之而來的收回教育權在社會上得到普遍支持。“近來反基督運動的潮流益漫溢全國,許多教會學校學生罷課的風潮連續不斷,我們視此種運動應為反帝國主義運動形式中之一種。”[28]在教育主權的收回方面,湖南地區的湖南省政府、國民黨黨部態度一致予以支持。反帝旗幟下收回教育主權既能顯示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又能進一步推動民眾運動。
在維持、發展國民革命這一過程中,國民黨黨政雙方的功能是不同的:國民黨黨部主要負責民眾運動的推廣和發動,政府主要負責社會秩序的維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在1926年8月一度向廣大民眾指出:“教會為帝國主義的先鋒”[29],強調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緊密關聯,明確表達了反教的立場。湖南省政府則不然,甚至致函湖南省國民黨黨部,要求允許基督徒加入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于昨函至省黨部,請準基督教徒加入黨部……查基督教徒,自愿接受本黨黨綱,請求加入本黨似無拒絕之必要。”[30]更呈現出國民黨黨部和政府二者之間態度的不同。
三、基督教會的應對之策
在“非教運動”開始之際,不少基督教信教人士就發出質疑:“所謂非宗教者,將一切宗教而非之乎?”[31]“自民國以來,約法上又有信教自由的規定,請問他們反對什么?是反對信教啊?是反對國法?”[32]北伐期間對基督教的沖擊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基督教會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與帝國主義徹底剝離:一方面是組織上擺脫外國控制、自立教會;一方面是在行動、宣傳上明確表態支持國民革命,反對帝國主義,聲稱“天主教與帝國主義立于反對之地位,天主教傳教士非帝國主義的先鋒隊。”[33]“愛國為圣經之明訓,圣教會亦命人愛慕國家。”[34]
面對復雜環境,湖南省基督教協進會一直在積極思索對策,在1926年9月29日、30日召開第二次年會,通過決議案,聲稱“本會根據基督真理,向各締約國要求從速廢除不平等條約;此后,凡關于中國教會一切交涉事件,請各教會直接與地方官廳辦理。”[35]試圖將基督教與原來的形象剝離,撇清與帝國主義的關系。同時致力于禁毒工作,“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拒毒委員會昨致各省區城市基督教協進會聯合會函:近年國內軍閥橫行無忌,以毒物為餉源,國外強徒,利己損人,使中華為欲壑,遂使煙氣彌漫。本會為中華國民拒毒會組織體之法定發起人,志在聯合全國同道,誓拒煙毒,再接再厲,不達不休。”[36]并將10月3日至9日設為拒毒周,要求各地教會注重文字宣傳和講道,并聯合社會各界推動拒毒運動的發展。
身處湘潭的美國傳教士甚至公開發表宣言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一、我們主張美國政府于最近的時間廢除在中國所享受的治外法權;二、我們主張美國政府于最近的期間同中國政府修改一切中美的條約,根據平等的原則,以中國主權為前提重新定約;三、我們主張在重訂條約時,凡屬于保護外國傳教士及基督教工作之傳教條約應一律廢除,因此項傳教條約實與基督教教義相違背,且阻礙教誨的進步;四、我們主張在中美邦交上應互相承認信教自由的原則,即美國政府對于在美國的中國人應保護其生命財產,并許其信仰自由,同時,中國政府對于在中國的美國人應保護其生命財產,并許其信仰自由;五、我們雖是美國的國民,但在中國為僑居者,故甚愿受中國政府的保護,但我們希望從中國政府所得的權利,與中國國民在美國所享受的權利一樣。”[37]湖南地區的基督教會通過這些舉動,積極去除“侵略”屬性,試圖重新在革命時代的中國社會中獲得新的位置。
但是,基督教會的這種做法沒有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可。“在最近兩三月內,基督教徒們有兩件差強人意的表示,其一是這般教徒們在十月初旬大做其拒毒運動……其二,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最近發表宣言,主張取消中國與列強所締結條約之關于教會及差會的特殊權利,而且主張把中國與列強所締結的一切條約根據平等的原則多少修改,這并不是表示基督教之本身的覺悟而是客觀革命空氣和反基督教空氣的壓迫著基督教徒,使他們不得不作如此最低限度的表示以見好與民眾而緩和反對的空氣。”[38]
在北伐軍進駐湖南之初,軍令明確規定不許擅自駐扎在學校:“總指揮部指令,準通令各軍隊不準擅駐學校……倘再有上項事情發生,準令遷移。”[39]對于教堂,受到革命思潮影響的北伐軍官兵認為基督教乃是帝國主義在華推行侵略的工具,“黨軍所到的地方,圣堂多被占據,圣堂里的祭臺圣像等多被搗毀。”[40]甚至很多教堂被作為駐軍之所,教士及教徒被趕出,教會事務停頓。駐湖南美國領事曾為此事聯絡唐生智,要求對教堂予以保護。唐生智也曾發布保護教堂的公告:“惟廣東軍隊,間有不服從該項布告者,似此情形,亟應請蔣總司令頒發布告,嚴禁軍隊駐扎教堂,防害教會工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在此情況下發出布告,要求各軍隊保護教堂:“我軍為救國救民而用兵,原非得已,打倒帝國主義,并不仇視外人,故凡外人僑居中國之教會及學校,茍非防害革命運動機關,我軍均應加以保護。”認為教會工作“純為眾生造福,核其性質,實為慈善。與現在政潮無關。”訓令各軍長官“迅飭所屬,毋得駐扎教會或學校,其有特別情形暫行駐扎者,亦應克日搬遷。”[41]
對基督教教會及牧師,國民黨湖南地方黨部并不是一律加以打擊,甚至在遇到困難時會予以協助。“美牧師寶翰臣等男女六人,于前月念間,行至沅陵縣屬茅灣地方,被匪攜去”。“昨交涉署電令桃源縣長,令其加緊營救:此事領團甚為注意,仰速商承駐軍長,會同臨地各縣縣長,加緊設法營救,務達安全出險目的,仍將辦理情形,隨時詳細呈報為要。”[42]神父王維舉被土匪捉去,也得到北伐軍的營救,順利脫險,認為“神父傳教,志在救人,人皆得以救之,匪盜行為害人,人皆得以誅之。”[43]
北伐過程中國民黨當局刻意避免與帝國主義列強發生直接摩擦,甚至向列強發出這樣的信號:打倒軍閥,并不是要徹底取消列強在華的利益。“無論何國人士,能不妨礙國民革命之行動及作戰者,一切生命財產,中正皆負完全保護之責,若有利用不平等條約,援助軍閥害我國民,斯為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縱欲保其友誼,亦恐礙于正義。”[44]1926年10月6日、12月23日,蔣介石先后兩次申明禁止槍擊外船:“為避免國際糾紛起見,令飭所部對于外艦行使漢口上下游時,如非違反戒嚴條例,不得自由放槍射擊,以免惹起外交上之糾紛。”[45]“沿江駐防部隊,嗣后外輪經過,毋許開槍射擊,以重邦交。”[46]其目的和保護教堂一樣,防止列強干涉北伐。1927年5月20日,國民黨中央再次頒發命令:“允許外商在合理條件之下,自由營業;對于外人生命財產自由一律保障;對于外國教堂,不得強占或搗毀,凡教堂、學校、醫院及私人住宅等一律維護其安全。”[47]
國民黨內部存在著“護教”與“反教”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之所以在北伐期間一度站在“反教”的陣營中,是為了表現堅定的反對帝國主義態度,最大可能地爭取民眾對國民黨的支持。
四、余論
一般而言,西方色彩濃厚的租界、基督教會大都具有二重屬性:一方面是西方列強殖民侵略的后果,是中國近代落后的象征;另一方面,從現代化角度考量,是中國社會接觸西方文明的媒介。在革命視閾下,人們對后一種屬性往往視而不見或有意忽視。在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劇烈變動中,基督教會若仍然與西方列強捆綁在一起,顯而易見會成為革命攻擊目標,必須作出改變。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欺凌使中國社會壓抑良久,這為反對帝國主義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北伐時期,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之間所謂的“不言自明”的關系首當其沖地遭到攻擊。在此期間,國民黨當局在沖擊基督教教會的同時保護教會人身財產安全,防范列強以種種借口來干涉中國革命;另一方面國民黨內對基督教的態度并不一致,秉持民眾運動理念的國民黨黨部往往更為激進,更徹底地反對一切與帝國主義相關的事物,而國民黨政府更在乎社會秩序的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