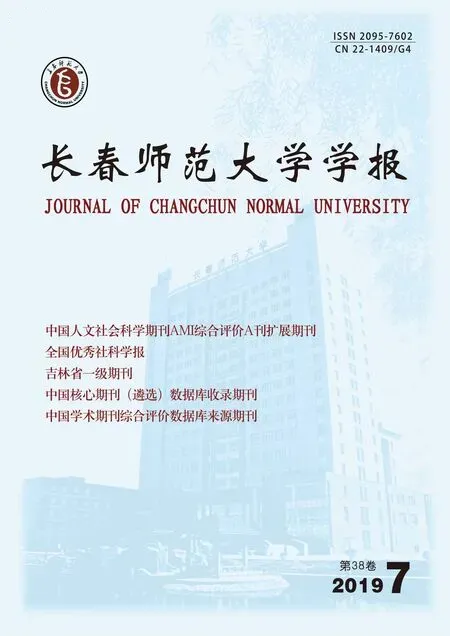一部杜詩研究的開疆拓土之作
——讀沈文凡先生《杜甫韻文韓國漢詩接受文獻緝考》有感
曹麗芳
(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
沈文凡先生洋洋八十五萬言的大著《杜甫韻文韓國漢詩接受文獻緝考》收錄詩人五百余位,涉獵詩篇近四千,囊括了韓國詩人用杜韻、次杜韻、依杜韻、效杜仿杜、賦得杜詩、以杜詩為韻、分韻等創作中幾乎全部的對杜詩接受范型,是對韓國杜詩接受文獻的首次全面細致梳理。作者在前言中標明是編宗旨在于:“皆以所搜討之原始文獻為依托,觀后人效杜之創作文本,體悟杜詩于東亞之接受盛況。”細閱全書,深感作者用心之高遠誠摯,用功之精勤不懈,收效之水到渠成。就筆者有限的識見來說,這部巨著確實為杜詩乃至唐代文學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方法和領域,古代文學研究者當會從中獲得不少啟迪。
所謂開辟新視角,不僅是說沈先生在杜甫詩歌文本、杜詩的當代接受、杜詩的歷時性接受等領域精耕細作后,又將研究視野拓展到域外,專注唐詩在東亞文化圈的接受考察數十載,撰有《日韓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在唐所作詩文研究》《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戶以來漢詩受容文獻初緝》等論文,更重要的是,沈先生一貫秉承重視第一手材料、一切觀點均以豐富翔實的原始文獻為依托的治學態度,獨具慧眼地將目光投向了浩如煙海的韓國漢詩創作領域,傾其心力,竭澤而漁,去做這項不少人望而卻步的工作。誰都知道這項工作的難度和所需毅力要遠在一般的材料搜集、整理之上。沈文凡先生歷時二十余載,零搜整緝,審慎校對,終成此煌煌巨著,其中艱辛可想而知。是書的首要意義不僅在于為其后的杜詩及古典文學研究導夫先路,開啟了無數法門,更在于提示人們:基礎文獻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能以任何理由而稍受忽視的,只有基礎文獻工作做扎實了,更高層面的理論研究才有展開的可能。筆者首次翻閱沈先生這部著作時,第一感覺就是可以以這部文獻緝考為中心,生發出許多課題。這種感覺無疑來自所面對文獻資料的豐富翔實、扎實可靠。
杜甫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詩人之一,他的巨大影響力不僅存在于國內的歷朝歷代,在日本、韓國詩人心目中也具有相當的典范意義。張伯偉先生曾說:“杜詩享有的獨尊的典范地位,在朝鮮半島文學史上歷時最久、影響最廣、印記最深。”[1]韓國詩人的杜詩接受,有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眾多方式,比如批解、注釋、評論、研究等。沈文凡先生著重從創作層面展示杜詩在韓國巨大而長久的影響,這是一個最為恰切,也最能使研究落到文本實處的途徑。陳文忠先生對文學接受層面和研究方向曾作過明確劃分:“一般說,人們對藝術作品的接受可區分為相互聯系的三個層面:作為普通讀者的純審美的閱讀欣賞;作為評論者的理性的闡釋研究;作為創作者的接受影響和模仿借用。與此相聯系,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也就可朝三個方面展開: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效果史研究;以詩評家為主體的闡釋史研究;以詩人創作者為主體的影響史研究。”[2]而沈文凡先生一貫重視其中的第三個方面,即以詩人創作者為主體的影響史研究。沈先生在其另一部著作《唐詩接受史論稿》中有言:“在接受史意義上,作為受詩歌文本影響而進行的詩歌創作,也即‘參與性的文學接受’,不僅包括后世文人在閱讀的基礎上吸收藝術和思想精髓,重新進行藝術創造而形成的詩作,而且還不能忽略對詩歌本文及作者進行評論性質的詩歌作品。……這兩種詩作,正是詩歌文本對后世詩歌創作產生影響的直觀表現,也正是由此不斷地創作——接受——再創作,才有了中國古代詩歌薪火相傳的發展和演變,這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文學現象和文學特點。”[3]這個重要的研究視點不僅適用于國內歷代文學的接受研究,同樣適用于域外詩人對中國文學的接受研究。從本書所收錄的近四千首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出近千年來韓國詩人對杜甫作品持續熱衷的洋洋大觀。誠如沈先生所說,韓國詩人在漢詩創作中,“微觀層面涉及到對杜詩名篇名句、用韻之接受,其中涉及杜公不同人生階段眾多名篇”,“宏觀層面則可呈現韓人對杜詩體裁、題材之整體接受面貌。韓人效杜,于諸詩體皆有嘗試。五言七言,古體律體,一并長篇排律、組詩、集句詩乃至非韻文”。題材方面也非常豐富,如節令述懷、登臨感慨、思家念友、集會遣興、感古傷今等等,無一不備。在所有引發韓國詩人詩興大發的時刻,幾乎都有杜詩的影子存在。甚至有些詩人作和杜詩、集杜詩數以百計,如金堉(1580—1658)除了有多首次杜詩外,還有長達四十韻的集杜五言古詩1首,題曰《北征詩呈石室金尚書》,且每句后都標明出處;又有集杜五言律3首、集杜五言絕句200首、集杜七言絕句12首。本書作者還搜緝到金堉在《潛谷筆譚》里對集句詩的一段議論,從中可見韓國詩人對中國集句詩的理解與接受軌跡。本書所收錄的大多數詩題中都有“次杜”“和杜”“用杜韻”“效杜”等字樣,韓人重視杜詩的面貌呈現得是如此直觀,使人一見便覺震撼。而對于沈文凡先生來說,搜羅如此豐富的材料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其中有不少詩篇需要仔細檢閱文本甚至是創作背景才能發掘其與杜詩之間的關系,如李民宬(1570—1629)《過平山憶申太師》只在自注中說到所用“塞翮”之典出自杜詩;沈師周(1691—1757)《五逸村拈唐人韻》只是在第四句寫到“草堂曾照少微星”。沈先生旨在搜羅全部與杜相關之作,在不計其數的詩歌海洋中能將此類詩篇盡數收錄,實屬難能可貴。
作為一部開疆拓土的奠基性著作,本書為今后的杜詩研究提供了無數新的領域與課題,誠如書序中所說:“就個案深入而言,從接受主體的角度,可以做某一位作家或某一個詩人群體的杜詩接受研究……從接受客體的角度,可以作某一首或某一組杜詩接受的專門研究……就宏觀拓展而言,本書所緝錄的文人的活動年代,自12世紀末直至20世紀初,時間跨度達八百年,從歷時性的角度,可以考察不同時代,不同政治、社會環境下對杜甫的接受情況……從共時性的角度,可以作對比研究”。除了這些創作方面的理論研究之外,還可以生發出其他很多思路,如在基本文獻的繼續搜求與完善方面,筆者以為本書也為學者們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和啟迪,使后來者有可能在考證緝遺方面繼續有所斬獲。本書所錄詩題中有不少是唱和詩,但其所收錄的有些只是其中的一人之作,我們可以詩題為線索搜求同題或同韻的他人作品,如奇大升(1527—1572)《次君沃用杜律韻〈贈別〉韻》所提到的君沃之作、柳根(1549—1627)《控江亭用李從事次杜律韻》所提到的李從事詩、趙絅(1586—1669)《次楊道一用老杜韻見寄之作》中所提到的楊道一詩等,起碼可以據這些詩題明確這些詩是曾經存在過的。本書所收錄的一些分韻詩在數量上偶有缺失,如金正國(1485—1541)《松石先生以少陵“老年花似霧中看”一句分韻作七絕以寄謹次以報》。按照詩題,二人之作均應為七首,本書收錄的金正國詩正為七首,而松石先生之作只有六首,缺少以“中”字為韻的一首。我們可以根據詩題或和詩的線索尋找這首佚失的作品。再如校勘。由于韓國詩人在接受杜詩的過程中會受到版本流傳、底本異同、理解傳抄等多種因素的復雜影響,本書作者在校對時用了極大功力,但限于本書的體例是文獻緝考,“貴遵原樣,貴秉全貌。是其詩題詩句有與古今之通行本有異或有簡省之處,悉遵原本”,這就為后來的研究者在校勘方面留下了一些工作空間。比如何受一(1553—1612)有詩題曰“次杜拾遺九”,我們知道杜甫行二,李白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杜甫的友人高適、嚴武作詩時也稱他為“杜二拾遺”或“杜二”,那么此處何來“杜拾遺九”呢?細檢何受一此詩所用韻腳字為臺、開、來、催,再檢杜詩可知其所次之詩當為《九日五首(其一)》,那么何受一詩題中的“九”極有可能是杜詩題中“九日”的“九”,如果理解為此處當有脫字,我們的疑問就可以迎刃而解。類似這樣的校勘工作是必須的,也是可以操作的。我們還可以將韓國詩人的詩歌創作當作文學批評的材料,從中了解他們對杜甫、杜詩的認識和評價。李穡(1328—1396)有《讀杜詩》二首,其中一首寫道:“錦里先生豈是貧,桑麻杜曲又回春。鉤簾丸藥身無病,畫紙敲針意更真。偶值亂離增節義,肯因衰老損精神。古今絕唱誰能繼,剩馥殘膏丐后人。”洪暹(1504—1585)的《杜甫》詩云:“先生天賦一何窮,獨向詩壇早策功。翰墨縱橫風雅后,形容漂泊峽山中。仲宣避亂辭多苦,庾信思鄉意自同。白首青山詩史在,草堂寧忍老孤忠。”類似這樣的讀杜詩、感杜詩中都有韓國詩人對杜甫、杜詩的獨到理解。我們還可以從一些詩序中發掘韓國詩人對杜詩和中國詩歌發展史的認識資料以及韓人對杜詩的接受心態,如李沃(1641—1698)在《和杜篇并序》中說:“粵自風雅之亡,后世為詩者,率繡繪肝腎,吟風弄月而止爾,何足與論性情之正哉?唯唐杜甫氏為詩家正宗,韻致沖淡,誠意惻怛,蓋不相背于賦興之遺旨。千載之下,想見其為人。況余近日所處,有同于子美夔蜀間身世,則其感發余懷者,又何如也?如《北征》諸篇,忠君愛國之意,溢于辭表。后世稱之,列之于左徒《離騷》、諸葛武侯《出師表》者,良有以也。”這段話以為自從風雅之聲衰亡以后,后世詩人只知雕章繪句、吟風弄月,其作品毫無性情可言,只有杜甫繼承了詩家遺旨,獨自承當起傳承風雅傳統的責任,并且極為成功。把杜甫放在漫長的詩史中來凸顯其地位,可見韓國詩人對杜甫的極力推崇。類似這樣的序文頗有幾篇,完全可以運用為文學批評史料。
《杜甫韻文韓國漢詩接受文獻緝考》作為一部搜羅宏富、功底扎實且富有開創性、奠基性的專著,在杜詩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和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用“功在先圣,惠及后學”來評價它極為恰當。正因為它如此重要且一定會成為無數研究杜詩者的案頭必備之書,所以對它的希望難免要更高一層。筆者對此書所寄望者尚有兩點:一是希望再版時最好能將韓國詩人所次杜詩的原題注出。在《杜甫五律、五排詩韻之明代接受文獻初緝》中,沈先生曾說:“明代詩人詩歌創作以杜甫詩為韻腳的詩例最為豐富。從用韻的角度來說,是屬于形式方面的問題。但以‘杜韻’為詩韻庫前提下使用杜甫詩韻也還是綜合考慮了具體某首詩詩韻與自己所創作詩歌在內容、聲韻、情蘊、體式等方面的相近性。”[4]韓國詩人也是一樣的,他們無論是集會上的群體創作,還是個人抒寫情懷的自由之作,在選擇所和韻、次韻的杜詩篇目時,除去題目中標為“抽韻”“拈韻”的情況外,其余往往都是因為與杜甫原作在本事、情感或者場合方面有近似性。即使是“抽韻”“拈韻”之作,既已選擇某首詩,便會在結構、意脈上接受該詩的影響。申叔舟(1417—1475)《次杜工部韻示謹甫》詩云:“鴨綠長江客里清,角聲悲壯撼邊城。醉中幽興三春暮,眼底孤云萬里生。今日一鞭直去往,明朝入站候陰晴。才疏自恨年空老,羞向遼陽說姓名。”所用為杜甫《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韻,杜詩云:“幕府秋風日夜清,澹云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里花饒笑,肯信吾今吏隱名。”[5]兩首詩從意脈結構上考察是極其相似的,所以如果將杜詩原作標出,會更方便讀者對照閱讀,了解韓國詩人是如何既接受杜詩規定性的影響,又能在有限范圍內變化翻新的。標出杜詩原作,還有利于全面考察某首詩的接受情況,比如杜甫的《秋興八首》《同谷七歌》《秦州雜詩》《詠懷古跡五首》等組詩都有大量韓國詩人的和韻、次韻之作,但如果考察這幾組詩全部的和作,只觀照到以組詩為單位且在標題中標明原題的作品是不夠的,還得去考察那些沒有標出原題的單篇和詩,如金克成(1474—1540)《宿高嶺用杜少陵韻》、周世鵬(1495—1554)《禹灣望李二相別墅次杜工部韻》所用均為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三)》韻,如果杜詩原詩被標示出來,我們考察《詠懷古跡五首》在韓國的學習、仿作情況時,其材料顯然會更為全面清晰。另外如前所說的校對工作也需要借助其所和原作才能對照校勘。在本書《凡例》中,作者曾說:“韓之詩人仿效杜詩,或以杜之詩題為韻,以杜之詩句分韻者,多因其所列題目詩句未盡合杜之原樣,勢不得不回環翻讀,依原題原韻詳加考證。”如果此“回環翻讀,依原題原韻詳加考證”的工作成果標注于本書中,則會大大省卻后來者的翻檢之勞,造福于學者多矣。二是希望對韓國漢詩作者的介紹能夠更加詳細一些,以便對韓國文學史了解尚淺的讀者獲得更多的認識,快捷地解決一些淺顯的問題。筆者在閱讀過程中看到金誠一(1538—1593)有《同五山次老杜〈秋興〉》,崔岦(1539—1612)亦有《和五山次杜韻賦天兵》,就猜想兩位詩人筆下的這位“五山”應該是同一個人,那么他是誰呢?從這兩處都看不出來。稍后看到書中收錄了車天輅(1556—1615)的三首《用老杜韻》詩,與崔岦所和詩的韻腳一致,且詩歌出處為《五山先生續集》,想必崔岦詩題中的五山就是車天輅了,又查其他文獻,知道車天輅號五山,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并且他們三人的生活年代相近,或可證明金誠一與崔岦所和之人都是車天輅,如此,則車天輅也當有次杜甫《秋興》之詩。作為一名對韓國文學史了解不多的讀者,筆者解決一個簡單的問題可算得是繞了一個大大的彎子。如果書中對作者的字號、生平經歷及交游等情況能有簡單的介紹,無疑可以省卻讀者花在簡單問題上的很多時間。
沈文凡先生多年來持續致力于唐詩的文本與接受史研究,從已經發表的論著來看,是同時向著范圍的闊大與課題的精深兩個領域雙向前行。如此一來,遇到的問題勢必越來越多,越來越有意味,也越來越有挑戰性。好在先生樂此不疲,在辛勞中時時能感受到人生的欣快,又好在先生在自己孜孜以求的同時又培育了很多精良的后學,從業于先生的博士、碩士研究生也加入了這項研究的隊伍,形成了一股生機勃勃的力量。我們祝愿隨著沈先生和他的學生們的工作順利進行,唐詩這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中最璀璨的明珠在域外所綻放的光芒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