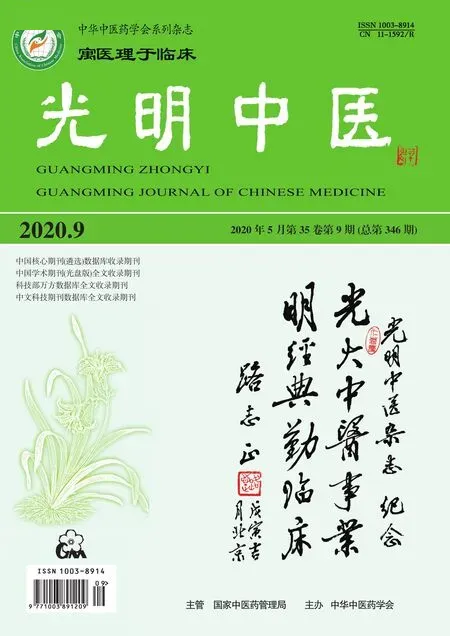《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雜志社鄭重聲明
2020-03-04 08:30:49
光明中醫 2020年9期
近期有作者來電反映,有人借我刊名義從事征稿與廣告活動,擾亂了正常的投稿秩序,影響了我們《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雜志社的聲譽。
《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雜志社鄭重聲明:本刊從未與任何公司或個人簽訂組稿與廣告合作協議,凡冒用我刊名義征稿和廣告的中介機構均未獲得我刊的任何許可,其工作人員均非我刊的工作人員,與之相關的經濟與法律關系與本刊無關。均屬違法行為,本刊將依法保留追訴權。
我社唯一投稿郵箱:zgzyyycjy@163.com,沒有其他征稿郵箱。《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雜志社官方網址:http://www.zgzyyycjy.com,收費只通過郵寄匯款,地址:北京市復興門南大街甲2號配樓知醫堂101室,郵編100031,收款單位: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雜志社。雜志社不通過任何賬戶和個人卡號收費。請廣大作者、讀者相互轉告,謹防上當。若有不明事宜,請來電垂詢。
特此聲明。
投稿郵箱:zgzyyycjy@163.com
電話查詢:010-57289309 010-57289308
財 務 部:010-87363190
官 網:http://www.zgzyyycjy.com
猜你喜歡
中國交通信息化(2022年5期)2022-07-23 08:22:42
現代臨床醫學(2021年3期)2021-07-16 07:36:44
中國民間療法(2021年5期)2021-06-09 09:21:42
法律方法(2021年4期)2021-03-16 05:35:10
公民與法治(2020年15期)2020-09-25 02:57:56
家庭醫學(下半月)(2020年6期)2020-08-24 07:46:14
考試與評價·八年級版(2018年7期)2018-12-31 00:00:00
知識經濟·中國直銷(2017年7期)2017-07-24 14:12:41
中國公路(2017年10期)2017-07-21 14:02:37
中國交通信息化(2017年3期)2017-06-08 06: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