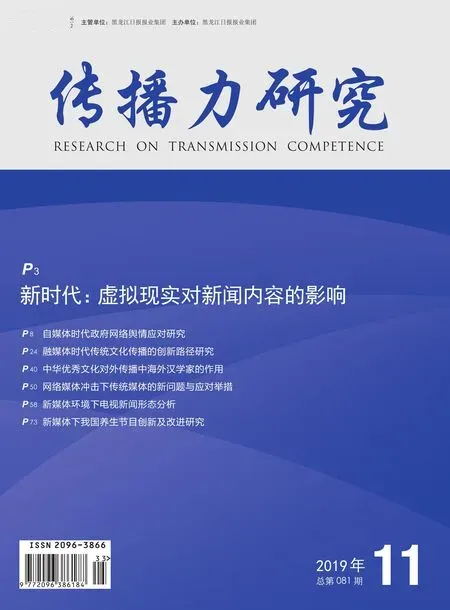論“明星真人秀”節目的火爆現象
朱媛晨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
在2013年之前,中國的真人秀節目大多以平民為主角,比如2005年的《超級女聲》,捧紅了一批平民偶像,比如2010年開始放送的《中國達人秀》,連續三季打破了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收視紀錄,再比如江蘇衛視的交友類真人秀節目《非誠勿擾》,通過參與節目的男女嘉賓們的直白言論,一直吸引著輿論關注并引發熱烈討論。而2013年,湖南衛視推出了一檔明星親子旅游生活體驗類的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這檔節目一時間火遍大江南北,自此以后,明星真人秀開始“異軍突起”,迅速占領了娛樂類電視節目的半壁江山。明星真人秀邀請為大眾所熟知的明星參與節目,制定游戲或比賽規則,記錄明星在游戲或比賽中的行為舉止,并通過塑造節目自身的真實性、競技性、沖突性來吸引受眾的目光。從表面上看,明星真人秀之所以能夠風靡的原因是由于明星本身具有“粉絲”基礎,能為真人秀帶來大量受眾。但是明星真人秀之所以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綜藝節目市場中占據半壁江山,并不僅僅是因為明星帶來的粉絲基礎,明星真人秀還滿足了受眾更深層次的精神需求,這才是它能夠持續“走紅”的原因。
一、從精神分析理論出發探究明星真人秀走紅的原因
勞拉·墨維在她的論文《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中從精神分析視角出發分析研究了大眾電影,她認為大眾電影滿足了群眾的窺視欲,也就是觀看的快感,而窺視欲則是在自戀的氛圍中滋養出來的,大眾電影也同樣滿足了觀看者自戀的快感。如今的明星真人秀也與當時墨維所論述的大眾電影有相似性,同樣滿足了觀眾兩方面的快感。
(一)滿足群眾“窺視”的快感
精神分析學說認為每個人的潛意識中都有偷窺他人的欲望,而明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往往被大眾所追捧,因此人們更加渴望了解明星的一切,希望窺視他們的身體、性格和生活,而明星真人秀就很好地滿足了受眾對明星的窺視欲。
真人秀節目最常使用的噱頭,就是把明星的身體作為看點來吸引受眾的關注,比如熱播的明星真人秀《奔跑吧,兄弟》就將“林志玲熱巴濕身肉搏”、“長腿女神組團來戰”等涉及或者描寫明星身體的信息作為看點來宣傳節目,再比如江蘇衛視的《星跳水立方》也一直使用“腹肌”、“肌肉”、“翹臀”、“素顏”等關鍵詞來迎合觀眾對明星身體的窺視欲。這在明星真人秀的宣傳與賣點中是屢見不鮮的手段。在此,節目制作方利用明星的身體打造節目看點,并進行有意識的夸張和渲染,以達到吸引受眾的目的。
除了通過將明星身體作為賣點以滿足受眾對明星身體的窺視欲望之外,通過消費明星的情感生活或熒幕外的私生活以滿足受眾在其他方面的窺視欲,也是明星真人秀吸引眼球的重要手段。
明星真人秀常常利用明星的情感生活作為賣點來進行炒作,其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在節目中通過放大參與節目的一對男女嘉賓之間的交流互動,并對其進行后期宣傳,營造曖昧氣氛,也就是俗稱的“炒CP”。明星真人秀也會選擇直接邀請明星夫妻或者情侶一起參與節目,而此時節目的宣傳重點就一定會落在這對明星夫妻或情侶之間的互動上,因為這對明星不管是秀恩愛還是有爭執,都極大地滿足了觀眾對明星情感生活的窺視欲望。
還有一些明星真人秀則將直接鏡頭延伸到明星的家中,通過放送明星房屋的裝潢擺設、明星的家居生活、明星的起居洗漱、明星的日常三餐等等屬于個人隱私的內容,來吸引觀眾。相比較于明星穿著光鮮地參與頒獎典禮、接受采訪或者演出作品,明星的私生活更能夠引起觀眾的興趣,而明星真人秀正是利用了觀眾的窺視欲來達到其宣傳目的。
(二)滿足群眾“自戀”的快感
之前已經論述過,由于窺視欲的作用,觀眾希望能夠通過節目設定的場景、情節,看到明星們在現實生活中不為人知的一面,還希望能夠看到明星作為普通人的生活常態以及他們面對突發狀況時的行為舉止。近年來,明星真人秀也常常以完成任務、分工協作、競技比賽等形式作為節目的基本框架,將明星還原到觀眾所希望看到或者說所認為的“最真實的狀態”,以喚醒受眾的認同感。在此過程中,明星面對節目組的設置必須要完成許多任務,這讓觀眾發現,原來明星也像普通人一樣,會遇到各種困難,要進行一系列挑戰。事實上,觀眾在觀看明星真人秀時也是一個身份認同的形成過程。如果明星完美地完成了任務,那么觀眾就會將這個明星形象認同為另一個理想化的自我,明星此時就成了觀眾所認為的自我形象在銀幕上的投射。相反,如果明星在任務進行中大出洋相,不僅僅為節目制作了“笑料”,同時也滿足了觀眾的“自戀”心理,觀眾會認為自己能夠比明星做得更出色,逐漸認為自己和明星之間的差距并非不可逾越甚至自己高于明星,從而獲得越來越強的自我存在感和認同感。
二、從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出發評價明星真人秀
(一)同一性與可預見性
1944年,西奧多·阿多諾和馬克斯·霍克海默用“文化工業”這個概念來描述群氓文化的產品及其生產過程。他們聲稱,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具有兩個特征:第一,同質性,“電影、廣播和雜志構成了一個體系,生產出來的東西從整體到局部都是千篇一律的……所有的群氓文化都差不多”;第二,可預見性:“只看一部電影的開頭,就可以猜到其結局……一點兒懸念也沒有……其結果就是同樣的東西被翻來覆去地再生產”。
而明星真人秀也具有同質性,諸如《奔跑吧兄弟》、《極限挑戰》、《極速前進》之類的明星真人秀在形式上都有相似性,所有的明星真人秀都要求明星完成任務,而明星在完成任務中或依靠行為舉止的搞笑、或揭露自己的私生活、或賣弄自己的肉體,其目的就是為搏觀眾一笑,甚至沒有任何道德、精神、政治的內涵,因為明星真人秀就是依靠滿足群眾窺視欲與自戀欲來吸引受眾的。可以說如今不同類型的明星真人秀實質是都是“換湯不換藥”,可能邀請的明星不同,拍攝地點不同,游戲形式不同,但其本質都是一樣的。
雖然明星真人秀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并不符合文化工業產品的第二個特征——可預見性,由于其游戲競技主題帶有不確定性,因此最終是誰取得了勝利似乎是不可預見的,但是從節目過程以及節目性質上來講,它依舊具有可預見性。因為我們都不用去點開觀看,就能知道明星真人秀的主題,它只是為了吸引觀眾,我們不需要去預測明星真人秀,因為它本身根本就沒有劇情可言,甚至可以說預測真人秀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明星真人秀的結果對于其節目本身來說并不重要,明星真人秀更看重的是節目過程中產生的能夠吸引觀眾的“爆點”,因此在這個層面上看,它比其他文化工業產品,比如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等,更具有可預見性。
于是,我們可以認為明星真人秀依舊符合文化工業產品的特征,首先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其次是無懸念可言的可預見性。
(二)虛假性與欺騙性
馬爾庫塞于1937年在《文化的肯定性質》這篇文章中對“肯定的文化”做了詳盡的闡釋,他認為肯定的文化就是被資本主義異化了的文化。首先,文化的藝術性和審美性屈從于利潤的動機和交換價值,異化成為文化商品,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生活。文化的否定性也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對現實的完全認同和支持。肯定文化的生產者所關心的只有經濟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就必然趨同、附和于現實,才能給生產者帶來經濟利益。并且,肯定性質的文化具有虛假性,而這種虛假性使得大眾失去判斷能力,將人們對現實世界的反抗消解于其虛假性中。
并且如今觀眾喜歡看真人秀,因為它滿足了觀眾自身的窺視欲與自戀心理,因為觀眾以為他們看到了明星的真實私生活,看到了明星工作之余真實的一面,殊不知明星真人秀由于受到了市場形態和權力意志的操縱,努力構建以向觀眾展示的是一個“真實”的“虛假世界”:節目流程有臺本安排,限定了每一個環節的拍攝地點拍攝時間,節目展示的只是它希望可以、也能夠給觀眾展示的東西;活動進行有劇本編排,甚至明星在節目上展現的笑料也可能是節目制作人想出來讓明星展現的,并不是明星的真實表現;明星形象有規定人設,他在節目上的種種表現只是為了符合他的節目“人設”,而并不是他的真實性格。前述文章中提到的女明星素顏,實際上女明星可能也化了妝,只不過用“素顏”這個噱頭更容易引起受眾關注,而炒CP 也極有可能只是男女明星配合節目組吸引熱點而上演的一出“好戲”。
明星真人秀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再是明星真實的展現,而是演技的考驗,體現著大眾文化的虛假性和欺騙性。由于市場操控和權力意志,明星也被異化為文化工業中的消費品,成為文化工業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鏈條。他們出演真人秀的出場費明碼標價,他們消費自己的形象、消費自己的身體、消費自己的情感生活、消費自己的隱私,其個性也受經濟利益的驅動與制約,在節目中戴上了虛假的面具,配合權利集團賣力演出“愚樂”大眾,而大眾則沉浸在他們表演出的虛假世界中,追尋著虛假的快樂。
大眾認為觀看明星真人秀是他們自發選擇的結果,殊不知他們觀看節目也是受了節目宣傳的效果,而觀眾更是在觀看節目的過程中,跟隨著節目演進和明星表現,也慢慢失去了主動思考的能力,然后被節目的剪輯效果所牽引。此時大眾由于失去了在大眾文化中自我思考的主體地位,就成為了資本家創造經濟利益的工具。
運用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來分析明星真人秀節目,是為了能夠向大眾揭示明星真人秀的同質性與欺騙性。大眾在觀看明星真人秀時確實可以緩解現實世界所帶來的焦慮,但在娛樂自身的同時也要能夠冷靜看待,不要為人所“愚樂”,更不要沉浸于虛假世界。如果沉浸在明星真人秀的虛假“陷阱”之中,就會導致消費異化,最終導致精神危機。馬爾庫塞在《愛欲與文明》中提出,人的本質是愛欲,而類似于像按照廣告來放送、娛樂、行動和消費都是虛假的需求,因為這是由特殊的社會利益強加到個人身上的,明星真人秀也是一種“虛假消費”,節目組通過廣告等多種方式的宣傳,來吸引觀眾消費節目。觀眾觀看明星真人秀也并非出于本質需求,只是出于欲望。在扭曲的消費觀念的引導之下,觀眾沉浸于明星真人秀帶來的窺視欲與自戀感的滿足之中,卻忽視了自己精神方面的真正需求:藝術的審美、文化的批判、人文的關懷。這樣下去必將導致人性的異化,使人與自我分離,最終陷入萎靡不振的精神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