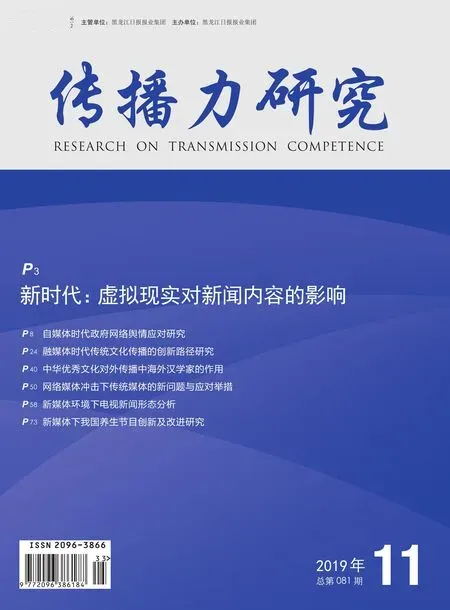“散淡秀逸”
——評江西音樂廣播何莉玲廣播文藝作品的創作特點
許寧 萬爽 江西廣播電視臺
創作代際間的差異與創作特點,可窺見不同時代的受眾在審美趣味上的變化,把握廣播文藝創作審美的變遷。何莉玲是江西音樂廣播資深女主持人,播音名牧風,2001年考入江西音樂廣播從事編輯、播音工作。她屢獲大獎,累計獲國家級一等獎1 次、二等獎2 次、三等獎2 次,江西廣播電視獎一等獎8 次、二等獎16 次,被評為江西電臺首屆十佳播音員主持人,列入“省直文藝新聞優秀年輕人才”名單。業績上看,她是江西廣播文藝創作領域“70 后”一代中的佼佼者。筆者認為她在廣播文藝創作中所體現出的創作特點為“散淡秀逸”——語言的“散文化”偏好、播講的“恬淡”語態、構思的“雅秀”視角、創作的“飄逸”靈韻。
一、語言的“散文化”偏好
這里指的是文稿創作的文本語言,廣播文藝作品的語言要具有文學的美感。何莉玲在長期的創作過程中形成了語言“散文化”的創作偏好。
2015年創作的《半闕歌》是紀念好萊塢配樂大師詹姆斯·霍納的音樂專題,作品運用隨曲解說的手法解說霍納作品中的隱喻性和指向性。對電影《勇敢的心》影片開頭音樂的解讀是這樣寫道“當愛爾蘭肘風笛的聲音奏響,電影《勇敢的心》的開場鏡頭象鳥的翅膀一樣,掠過藏青色的山巒,白霧從蘇格蘭高地的小河上慢慢升起再緩緩散去,我們聽到的這一段憂傷細碎的小提琴沒有低音襯托,隱隱透出無奈和心酸。四支圓號有一個不祥的和聲,這是音樂中非常典型的黑暗邪惡的象征。這是一段弦樂的過渡,也似乎是一種無力的掙扎,然后,管弦組慢慢的匯入音流,似乎在積聚力量。忽然獨奏圓號吹出帶有升騰力量的旋律,在音樂語匯中往往代表著一種期盼,或者一種光輝的誕生;然而我們聽到大提琴冷漠的對答,似乎也預示了前路的坎坷與荊棘。”解說詞是說明文體,旨在闡述清晰,音樂語匯是聯想開放的“虛”,輔以主持人語言才能明晰的指向“實”,這是對音樂解說的難度所在,虛實之間的把握考驗著創作者的編輯功力。經過多年的摸索,這段解說詞中明顯的感受到何莉玲以“散文化”語言具化了“虛”、柔化了“實”,與音樂相得益彰。
二、播講的“恬淡”語態
語態就是說話的態度、敘述的方式,此處分析的是有聲語言播講。廣播文藝創作通常是突出藝術素材的,主持人語言是為素材服務的。何莉玲的播講語態“恬淡自然”、“不喧賓奪主”,用她的話說是“用力地小聲唱”,用近乎于溫柔的旁白語調進行創作。
在音樂專題《絲路》中,開頭的播講是“門外是睜不開眼的沙漠艷陽,窟門無聲地打開,眼睛一時間還不能適應石窟里的黑暗,氣質如蘭的講解員把小手電的光打在墻上:當那些穿越千年的色彩和線條跳入眼眶,中學歷史課本上的插圖,余秋雨《文化苦旅》里的文字,大唐王國曾經的優雅從容,黃沙下一場延續千年的繁盛與沒落,全都呼得一下塞到我的喉頭,幾乎要逼下我的眼淚。”以自我的感受開場,容易給人深刻的個人化印記,文稿中又充滿了傳統文化的描寫,因此在播講中她克制自我表現的成分,由感性進而理性。
三、構思的“雅秀”視角
好的文藝作品離不開構思,構思離不開創作者的精神世界、人生經歷、文化知識等。何莉玲追求“雅”的視角,在作品中善于“雅”中寓“秀”進行創作。
個人代表作《從瞬間到永恒——聆聽德彪西》,主題來自德彪西的音樂特點:不重視旋律,音樂線條讓人難以記住。對音樂家作品的闡釋本身就難度極高,需要心中有“雅”的智慧才能欣賞。節目的構思設計上有兩條線條始終貫穿:一是對德彪西各時期代表作品的賞析,二是對德彪西的再認識。節目欲揚先抑,引導聽眾的期待,然后結合德彪西的個人經歷來介紹的“印象派音樂”,從德彪西的反叛傳統,到知音甚少卻堅持自己的創作和美學觀點,然后再到師法自然、向東方音樂學習,終于自成一派,樹立了獨特的音樂風格和音樂流派。何莉玲用了不同于以往簡單介紹人物作品的創作手法,時刻在聽眾的立場上制造和滿足聽眾的期待,在德彪西的個人經歷中聽眾可以感受到堅持的力量,最后又將主題上升到:抓住每一個瞬間,就是抓住永恒。這些積極又正面的導向讓這期節目既有欣賞價值又有社會意義。
四、創作的“飄逸”靈韻
靈韻是建立在與審美接受者交往過程中,建立在經驗交流的基礎上。作為廣播文藝節目的生產者,對美的理解不能超前或落后于受眾。在多年的創作中,何莉玲習慣用“飄逸”的傳播技巧來建構傳與受之間的經驗交流。
其獲中國廣播影視大獎提名的作品《尋找牡丹亭》,在文中寫道“等我到達古代南安府后花園的時候,正趕上牡丹亭公園改建工程,想象中‘朝飛暮卷,裊晴絲懸’的閑庭院一派繁忙。沒有了地理空間的意象,杜麗娘初見園林時‘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的感嘆便有些空中樓閣,那個古典少女的掙扎與釋放也無處著力,不免讓人嗒然若失。而與‘后花園’相對的西方愛情意象應該是‘陽臺’吧,一個遮蔽、隱秘,一個則敞開、外露,雖然各有不同的文化積淀,但卻有著相似的文化隱喻。”其實“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很難用語言描述,與西方戲劇的具象不同,原著與戲曲都使用“虛擬性”的特點。她巧妙的將湯顯祖的“后花園”與莎士比亞的“陽臺”類比,寓虛于實,拓寬想象的空間,點明兩位大師創作的共同點,可謂“一箭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