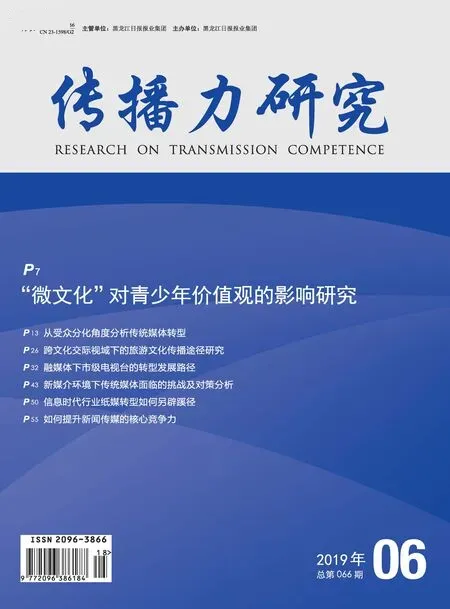“樹典型”之研究綜述
田豐 重慶大學新聞學院
一、相關概念
典型原意是鑄造用的模具,后來衍生出“模范”的含義。中國在歷史上通過表彰“忠”“孝”“節”“義”的典型人物來進行教化,以達到自身執政目的。毛澤東于1943年發表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將樹典型作為一種工作方法來闡述。
二、社會學取向下的“樹典型”研究
目前的研究多從社會學角度,被引用最多的是學者劉林平、萬向東所著的《論“樹典型”——對一種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行為模式的社會學研究》。他們認為,樹典型和民族心理中的群體主義取向有關,和計劃體制下的政治本位、領導本位的價值取向等因素有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治者通過教化和獎懲把施政理念內化為被統治者的行為動機。采用樹典型能節約經濟激勵費用、節省管理成本和起到“帶頭作用、骨干作用和橋梁作用”。[1]
學者黃鵬進則從鄉村治理角度,對樹典型策略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樹典型”自古以來都是一種“德治社會中一項十分重要的權利技術”[2],都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集體化動員的一種嫻熟的技巧性藝術”[3]。這背后的邏輯是“國家——社會”二元分析范式。研究者同時也指出了“典型”在新農村建設中也存在“異化”,失去了樹立典型的政治初衷。
學者苗春鳳從社會評價論的視角,認為典型是權威評價活動的產物,有助于權威機構加強對社會的動員、控制和整合。在當代社會中,權威機構仍然需要樹立典型提倡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進行社會整合,但必須堅持權威評價與民眾評價相結合。[4]
學者郭曉寧則以來自軍隊的兩個案例為例,對轉型期的所面臨的國情和多元文化涌現后,帶來的政治權威與民間大眾的結合,促進典型影響力增強進行了闡述。[5]
學者韓志明、顧盼以“典型政治”及其運作為例,研究了價值分配的國家邏輯,認為樹典型是一項國家治理技術,其實質是圍繞倫理價值而建構起來的權威性分配行動,主要體現著國家的意志和需要。相對于由法律法規所建立起來“硬”性懲戒體系,典型政治具有調控社會行為的“軟”功能,并主要通過優劣對比機制、簡單重復機制、雙向選擇機制和宣傳學習機制等來運作。[6]
三、傳播學取向下的“樹典型”研究
“樹典型”行為其實質就是一個傳播行為,是主流價值符號塑造和傳播的過程。
學者苗春鳳結合當下日益多元的傳播環境,提出要引入互動儀式鏈,通過建構典型的符號,來構建和引領社會公認的價值觀。[7]他呼吁要注重傳與受的“互動”,將樹典型帶入到具體的情景中去,重塑社會認同、符號認同和價值認同。
學者張楊波分析了廣東省婦聯開展的“好丈夫、好妻子”評選活動的傳播效果,研究結論不僅扭轉了人們以往認為典型在樹立之后肯定會產生預期效果的傳統觀念,而且部分證實了默頓和拉扎斯菲爾德的回飛鏢效應的存在。[8]
四、總結與討論
社會學取向下的“樹典型”研究對于社會治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具有指導意義。政治權威越來越注重大眾評價,這將帶來政治行為模式的改變。傳播學取向下“樹典型”研究則從傳播五要素著手進行了梳理,開始有學者注重效果評估,開始研究受眾,這是傳播學科引入的一大優勢,對于更好的進行“樹典型”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已有的文獻多采用質化分析,對“樹典型”的研究還停留在理論的引入、現狀的概述上,鮮見采用量化分析,研究還未深入,對當下信息時代,面對海量的信息和價值觀多元的研究還很欠缺。
當今社會,樹典型依然是社會治理、企業(組織)凝聚發展的一個有效的技術路徑,隨著消費社會的浪潮繼續深入發展,異化后人們會產生“返祖”現象,他們呼吁人性的回歸,他們需要符號的價值和價值觀的引領,將多元價值觀、碎片化的個體重新聚合在一起,尋得“心靈的安寧”,這將成為社會治理和組織發展的穩定基石。
未來,“樹典型”要更加注重受眾研究,傳播效果研究,借助社會學量化研究方法,借助大數據的優勢,從典型的選取、誕生、塑造、宣傳和維護整個流程進行修正,以適應信息時代的要求和受眾的需要,使得“樹典型”這一古老的治理模式“老樹發新芽”,煥發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