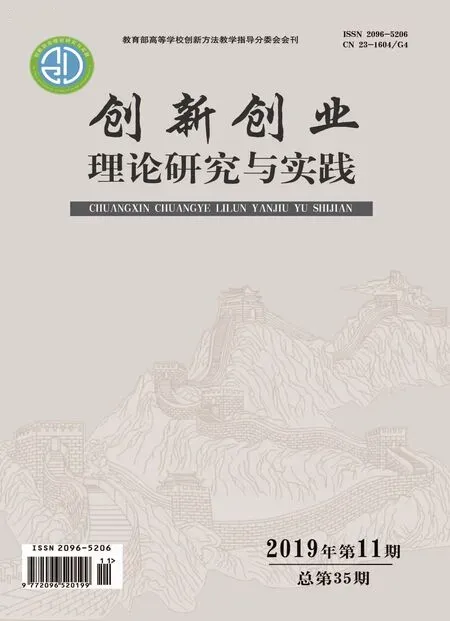地方高師院校教育質量評估的現狀及對策探究
江立員,李紅
(宜春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江西宜春 330800)
辦學質量是教育的生命線。高校教育質量自試行評估以來,促進了我國高校的發展。進入新時代后,我國高等教育由快速擴張走向質量提升,在此背景下,依據 《普通高等學校本科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案(試行)》和《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案(試行)》開展的本科高校和高職高專院校的教育質量評估,經實踐證明,在教育質量評估的主體、指標、機制和結果運用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地方師范院校更是如此。
1 地方高師院校教育質量評估現狀
1.1 評估主體單一化
教育質量評估結論要具有客觀性、公正性和權威性,首要條件是評估主體的構成要科學、合理。《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指出:“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由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組織實施。”“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是教育評估的主體,學術機構、社會團體參加教育評估只是一種補充。”理論上,學術機構、社會團體只是教育評估的一種補充——實際多數情況下并未參與,即使參與也受制于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缺乏真正獨立的評估權。
教育行政部門主導高校教育質量評估,有利于政府及時掌握高校教育信息,進而從宏觀層面來調控高等教育,促進高校的建設與發展。教育行政部門選聘的入校評估人員,雖然不乏高校教育管理專家,但他們實際上受雇于教育行政部門,這種評估主體就會集管理者、舉辦者和評估者于一身,權責利糾纏于一體[1],容易導致教育質量評估過程中產生不合理的現象,影響評估結論的合理性和權威性。
地方高師院校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門,因其辦學目標的特殊性,又因其經濟訴求和人事訴求對政府的依賴性更強于非師范類高校,目前這類高校的教育質量評估更帶有明顯的行政強制性,即使是它們的內部管理型評估,也往往要考慮到行政影響因素。目前,這種單一化的評估主體主導的教育質量評估,難以對高師院校教育的內適質量和外適質量做出理性、客觀和科學的評價。
1.2 評估指標大眾化
評估主體的單一性自然會導致評估指標體系存在“一言堂”的缺陷。隨著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標準卻沒及時跟進完善,仍存在重共性、輕個性的缺陷,沒有充分考慮到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的院校之間的差異性。現行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案(試行)》和《高職高專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式(試行)》就以同一套指標體系去評估所有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院校的教育質量。
在以上兩個評估方案中,有些評估指標不是地方高師院校能決定的,而是由政府確定。例如,“辦學定位”豈能由師范院校自身決定?畢竟地方高師院校都是公辦高校,他們的辦學定位明確為培養小學、幼兒師資;再者“辦學定位”并沒有好壞之分,只是為了適應社會的需求而確定的,對這一指標進行評分是否合理?有些評估指標明顯不適用于師范院校。例如,《高職高專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式(試行)》中的二級指標有“產學研結合”,此項指標對高職院校來說是必要且適宜的,產學研相結合是時代賦予高職院校的職責;但“產學研結合”并不適合專科層次的高師院校,因為高師院校的職責是培養小學、幼兒園師資。此指標的確定,不得不逼迫高師院校去為這些統一標準而盲目投入人力物力,分散高師院校的辦學資源。又如,現行的評估指標側重以教學條件和過程為基本參數,涉及外部評價的指標太少,高職高專評估指標有“就業與社會聲譽”一條,而實際上這條外部評估的可操作性不大。大眾化的評估指標導致的后果是評估專業性缺欠,高師院校的辦學特色無法體現。
1.3 評估機制風險化
教育評估機制是評估主體在評估過程中的相互作用機理。它一般由評估資源配置機制、過程監管機制、法律保障機制、結果反饋機制等組成[2]。目前,高校教育質量評估主要程序包括高校自評、專家進校評估、結論審議與發布等環節。學校自評環節主要是對照評估方案開展,有些自評要素多會“自圓其說”,補充性措施較多;專家進校評估主要在高校校園內開展,借助于訪談、現場聽課、查閱材料、考察座談等形式,而此時高校展示的受評材料是經過精心準備的,接受訪談、座談和聽課的對象多數接受過“迎評培訓”;至于結論的審議與發布,則主要是教育部評估中心根據專家委員會審議的最終結果,正式在官方媒體發布評估結論,因“暫緩通過”的高校會減少招生數量、暫停備案新設專業,實際上接受評估的高校絕大多數都會獲得“通過”結論。
高校教育質量評估之所以會出現以上一些問題,其根源在于評估機制不健全,缺乏法律保障機制,這就必然導致不少教育質量評估流于形式,過程監管不到位,結果效能運用不合理,必然誘發一些風險。例如,道德風險、尋租風險、技術風險等。這些風險的存在不僅影響到了教育質量評估質量,也影響到了評估的信譽,造成了不良社會影響,“陽光評估”政策的公信力不高。
1.4 評估結果功利化
現行的高校教育質量評估主要是應教育部的要求而開展的,其目的在于回應政府和社會的問責[3]。評估結論為“暫緩通過”的高校,政府將減少其招生數量,暫停備案其新設專業。例如,2017年4月27日,《廣州日報》數據和數字化研究院(GDI)發布“2017廣州日報高職高專排行榜”,是權威媒體作為第三方評估、發布的專業性公益榜單,也直接影響到各高校的招生及民間投資。因此,目前高校所進行的教育質量評估結果功利化現象非常明顯。
功利化的教育評估,必然導致只關注評估結果和管理要求、促進功能和事實判斷,容易忽視高校教育的基礎性保障、發展過程、知識增進和價值提升[4]。難以著眼于國家高等教育的改革發展、用人學校的期盼和學生本人的全面發展。而這與高校教育質量評估“以評促建,以評促改,以評促管,評建結合,重在建設”的原則背道而馳。
2 改善地方高師院校教育質量評估現狀的主要對策
2.1 推行多元評估,淡化政府管控高教職能
高校教育質量評估應借鑒美國、英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對當前以教育行政部門單一主導的評估體系進行改革,建立多元主體參與評估的評估體制。教育部明確提出高校教育要推進“管、辦、評”分離,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互相關系[5],因為多元評估主體可根據自身差異化特征和不同需求,對評估指標有選擇性地開展評估,能實現評估效果和評估功能上的互補[6]。多元主體參與的教育評估能提高評估的專業化和獨立性,符合我國教育治理體系走向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當然,多元主體參與教育評估,仍需教育行政部門引導,但引導評估不等同于“主導”評估。教育行政部門除評估基礎設施、教學硬件和師資隊伍外,重在對教育質量評估的宏觀政策和制度方面的組織、引導和決策,監督和規范各評估主體的評估行為,其目的是在推進教育評估走向透明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學化。在高等教育質量評估工作中,政府職能特征由“控制”轉向“引導”已經成為評估改革的新態勢[7]。
2.2 實行分類評估,強化師范教育評估要素
我國高校從辦學層次上分,分為本科院校和專科層次院校,其教育質量評估有兩個指標體系;從辦學類型上分,本科院校分為研究型大學、研究教學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等,專科層次高校分為高等職業院校、高等師范院校。目前,同層次高校使用的評估方案是統一的,不同類型高校使用的評估指標體系也是統一的。根據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高校的功能、定位,確定不同的教育質量評估指標體系,實行分類評估,這樣的評估才能更好地反映高校的教育質量,這也是高校教育質量評估發展的趨勢。
以培養小學、幼兒園師資為主的大專層次的地方高師院校,其教育質量評估應單獨設置評估指標體系,評估指標要強化師范性。例如,評估高校教師教學應重視其引領示范作用,不忽略高校教師的親和力。評估師范生的學習應重點考察其基礎學歷,關注其自我發展的能力;要重視評估師范生的教學基本技能、教育專業知識和教育教學實踐環節等。在設計評估指標體系時,要堅持學術性服務于師范性的立場。
2.3 健全評估機制,合理規避各類評估風險
高等教育質量評估立法,厘清各評估主體的權益,是保障教育質量評估科學性和專業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例如,美國國會先后出臺了《保障受益者權益的聯邦政策》《美國聯邦管理條例》等法規,對教育認證機構的運行做出了明確的行政規制[8]。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評估缺乏相應的法律和政策制度的支持,政府應盡快為高校教育質量評估立法,擬制必要的法律保障制度,推行“依法評估”的理念,設計完整的高校教育質量評估法制框架。
高等教育質量評估只有立法了,才能規范其評估的過程與監管細則,提升各評估主體的責任意識,建立健全的教育評估的風險防控機制,對評估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尋租風險、技術風險進行有效預判、預警和識別,將各類風險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內,進而獲取公信力強的評估績效。
2.4 堅持診斷功能,強制問責轉為自愿問責
地方高師院校都是公辦高校,其管理體制以行政本位為主,缺乏自主尋求外部教育評估的內驅力。此外,地方高師院校在外部教育評估的作用和功能的認識上也存在較大偏差,他們習慣性地接受政府對其進行監管與問責。教育評估作為保障教育質量和推動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要淡化評估結果的功利性,要強調評估的診斷、導向、監控和激勵等方面的功能。
師范教育更多的要強調個人價值提升、教育綜合素質的培養,并非類似于企業的效率產生。其教育質量的評估要從以往的結果評估和管理評估向素質提升、教育治理轉變。評估應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質量觀,超越問責邏輯,由外部強制問責制轉向高校“自愿問責機制”建設[9]。如此,地方高師院校的教育質量評估才有生命力。
3 結語
在新時代,隨著農村小學、幼兒園的快速發展,地方師范院校迎來了重大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改革挑戰。坦然面對目前地方高師院校教育質量評估存在的問題現狀,推行教育行政部門、第三方評估機構、學生與家長共同參與評估的機制,擬制符合地方師范院校辦學特點的評估指標,健全評估機制,推行教育質量評估中政府職能重“導向”與高校“自愿問責”的評估理念,才能進一步推進和保障地方高師院校教育評估走向科學化、綜合化、社會化、透明化及制度化,達到深化地方高師院校教育改革的目的,進而促使地方師范院校培養更多合格的小學、幼兒師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