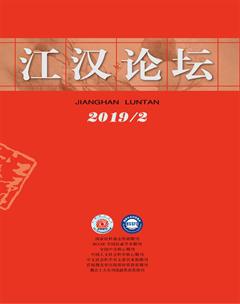良序如何可能
摘要:治理是變無序為有序的行為,有序包括劣序和良序,治理包括惡治和善治。從縱向(垂直維度)來考察,善治就是以平等為前提,在治道(治理的技術和藝術)上構建權力和利益的均衡(均壓),進而在政道(治理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上構建權威和權利的均衡(均壓),從而構建良序。霸權所構建的秩序是劣序。私利所充斥的狀態是無序。從橫向(水平維度)來考察,治理的目的就是實現沖突的最小化和合作的最大化,進而實現社會隔閡的最小化、社會信任的最大化。良序是某種趨于沖突最小化(從零沖突到軟控制)社會狀態,這種沖突最小化推動社會持續發展。劣序是某種趨于合作最小化(從零合作到硬控制)社會狀態,這種合作最小化阻礙社會發展。
關鍵詞:良序(善治);權力(權威);利益(權利);沖突(隔閡);合作(信任)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治理循環研究”(18BZX017)
中圖分類號:B82-051?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19)02-0048-05
治理的中心問題是構建秩序。秩序是行為的有序結構亦即行為依照某種模式相互關聯,這種相互關聯并非純粹特殊的和偶然的,而是具有某種可以辨識的規范。規范是因應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而形成的社會行為的慣例。具體規范集合的方式是制度,是為人們所廣泛理解和接受的在特定領域里的社會行為的組織方法。換句話說,這種有序結構是反復出現的行為模式和可以預期的重復態勢。秩序包括良序和劣序兩種狀態,由此決定治理包括善治和惡治兩種方式。善治是構建良序的治理,惡治是構建劣序的治理。
模型是討論問題的一種適宜方法,就是將問題明晰化,將概念(范疇)、判斷(命題)、推理(推論)直觀化,類似某種思想實驗。我們試圖通過構建幾種善治模型,探討良序如何可能問題。
一、良序的垂直維度:權力(權威)和利益(權利)的均衡(均壓)
有序是治理的目標,而良序則是善治的目標。這里首先需要區分兩點:(1)有序和無序;(2)良序和劣序。我以日常生活中的排隊為例說明:第一種狀態是沒有形成任何隊列,所有人都爭先恐后,強者憑借實力優先得利、多得利甚至全得利。“實力”是指:體力(體能)、腦力(智能)、社會結合能力(同盟、共謀)諸項。弱者缺乏相應實力滯后得利、少得利甚至不得利。第二種狀態是強制維持隊列,例如專人維持隊列,保證特定個人或者群體優先,其他人被迫被動服從。第三種狀態是自發形成隊列,例如人們按照先來后到原則,保證每一個人機會均等,所有人自覺自愿遵守。在政治哲學上,上述三種狀態,第一種近似由叢林法則所支配的自然社會,亦即無序社會。霍布斯將“自然狀態”等同于“戰爭狀態”:“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① 第二、三種近似由人間法則所支配的政治社會,均屬由治理所構建的有序社會:第二種近似由惡治所構建的劣序社會;第三種近似由善治所構建的良序社會。
有序和無序的區分在于秩序有無,而良序和劣序的區分又在于什么?由上可知:首先,成本大小:成本小的是良序,成本大的是劣序。相比強制維持秩序,自發形成秩序所需要的成本較小。這里“成本”是指一切生活資源的支出和扣除,包括人力、物力、財力諸項。其次,代價多少:代價多的是劣序,代價少的是良序。相比強制維持秩序,自發形成秩序所付出的代價較少。這里“代價”包括一切生活善(好)的減損和喪失,包括尊嚴、自由、快樂諸項。由此可知:(1)良序和劣序的劃分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它們之間不是間斷的,而是連續的;(2)良序和劣序的劃分不在于構建秩序的內在動機和目的,而在于構建秩序的外在手段和效果。亞里士多德在關于政體的劃分中,明確“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的利益的政體就都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②。變態政體就是專制政體,在這種政體中,人與人的關系就是主奴關系,或者君臣關系;正宗政體就是城邦公民政治,在這種政體中,人與人的關系就是自由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如果我們將變態政體理解為劣序,將正宗政體理解為良序,那么,兼顧公共利益還是只顧統治者們利益就是區分良序和劣序的關鍵。而關鍵的關鍵則是整個秩序是否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礎上。但是,構建良序并非一定是在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構建劣序亦非一定是在為極少數極個別人謀利益。主觀上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客觀上違背絕大多數人意愿,仍然增加維持秩序的成本和代價。反之,為極少數極個別人謀利益亦有可能構成絕大多數人意愿。例如人們愿意給老弱病殘孕讓位,亦不嫉妒讓特殊貢獻者優先,但不愿意權貴、富豪享有特權。
關于無序、劣序和良序三者之間的關系,我這里借用吳稼祥三個權力落差公式說明。在吳稼祥那里,“權力落差”或稱“權威落差”,是指“在當權者和服從者之間存在著社會和政治地位上的落差”③。設K為權力落差(即不平等程度),A為權力,F為自由,則
K=A/F
變式一:F=A/K
變式二:A=KF
“權力落差與權力成正比,與自由成反比”,這意謂著權力行使是以自由、平等為代價的。它包含了三種情況:第一,假定自由最大化(K→∝),平等最大化亦即權力落差最小化(K→0),權力最小化(A→0),這種模式即變式二,吳稼祥稱為“自由模式”或“無政府模式”(當然,“自由”≠“無政府”);第二,假定權力最大化(A→∝),權力落差最大化亦即平等最小化(K→∝),權力最大化(A→∝),這種模式即變式一,吳稼祥稱為“奴役模式”或“極權模式”④;第三,假定權力和自由均等(A=F),權力落差取常數1(K=1),這種模式即從上述初始公式中推出。整個來說,我們可以將上述三式理解為治理模式,于是,第一種情況(變式二)即無序狀態(非治理),第二種情況(變式一)即劣序狀態(惡治),第三種情況(初始公式)即良序狀態(善治)。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推論:善治就是以平等為前提,通過權力和自由的均衡,構建良序(K=A/F=1,其中A=F)。
上圖構建了K(權力落差即不平等程度)與A(權力)、F(自由)的關系。在這一直角三角形中,呈45°角對角線就是權利和自由的均衡(A=F),權力落差最小化亦即平等最大化(K=1)。權利落差沿這一對角線兩邊區間就是良序狀態(善治),沿右下區間遞減為無序狀態(非治理),沿左上區間遞增為劣序狀態(惡治)。
吳稼祥在討論權力效用時,將物理學上的“壓力”(“壓強”)引申為政治學上的“壓力”:“是指不平等關系中上面的支配者施加在下面被支配者身上的力度。這種力度,可以用大小、時效、范圍和層級來衡量。”⑤ 他將政治壓力區分為“高壓”、“負壓”等等,以此分析中國歷朝歷代政體。我這里借用吳稼祥政治壓力概念,經過修正,給出各種可能:
在正壓、負壓中,都有高壓、低壓兩種情況。調壓是指權力調整,包括給低壓加壓,給高壓減壓。穩態包括內部性穩定與外部性穩定,非穩態或是內憂導致,或是外患引發。均壓是指權力均衡。吳稼祥說:“所謂均壓,是指政治體系中支配者在權力上自上而下逐層施加壓力,而被支配者在權利上自下而上間接或直接施加壓力,當兩種力量達到平衡時,就是均壓政治。”⑥ 如果我們僅僅從權力運作技藝層面來考慮問題,那么,不是高壓,不是負壓,正是均壓接近我們所謂良序狀態。吳稼祥曾分析過各種政治所面臨的風險:“高壓穩態”政治的風險是癌變,“高壓非穩態”政治的風險是土崩,“負壓政治”的風險是瓦解⑦。在他的排序中,單就壓力而言,負壓優于無壓,無壓優于混壓(內高壓—外低壓),混壓優于高壓⑧。但是,如果不就中國傳統政治現實性,而就政治可能性而言,均壓政治風險最小。它也就是前述權力和自由的均衡亦即權威和權利的均衡。
上述我們只是從權力運作技藝層面來考慮問題,這是治道,還有政道,亦即權力運作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問題。蔣慶指出:“所謂‘政道,就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而‘治道則是合法的政治權力具體落實與運作的制度性安排,以及運用合法權力的方法與藝術。”⑨ 韋伯曾經提出“支配的正當性根據”有三:“傳統型的、卡里斯瑪(個人魅力)型的和法制型的。”⑩ 此為“政道”。福柯曾經提出“治理術”的“權力形式”:“這種權力形式的目標是人口,其主要知識形式是政治經濟學,其根本的技術工具是安全配置。”{11} “牧領、新的外交—軍事技術,以及公共管理。”{12} 此為“治道”。
權力并不等于權力意志,權力是主體具有的體力、智力和社會結合能量的總和。政治權力主要就是一種社會結合能量,不像經濟利益那樣是物態的,可以量化,但有物質外觀,也有強弱之別,主要是一個政治學的范疇。資源配置是通過權力實現的。權力并不等于資源,而是一種資源動員、配置和運用的能力。被賦予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權力就是權威,換句話說,權威是披上了合法性和正當性外衣的權力,基于相關主體(權力被支配者和其他權力支配者)承認,不可能具有物態量化形式,主要是一個法哲學的范疇。反之,未被賦予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權力就是霸權,換句話說,霸權是未披上合法性和正當性外衣的權力,不基于相關主體承認,是權力主體的自我授權,是權力的裸體。權力也不等于秩序,而是一種秩序建構、換構和解構的能力。顯然,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權威所構建的秩序無疑優于不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權力所構建的秩序。由此,我們將權威所構建的秩序稱為“良序”,將霸權所構建的秩序稱為“劣序”。正如權威是權力的合法化一樣,權利是利益的合法化。利益是滿足主體需求的善(好)。經濟利益通常具有物態,甚至可以量化,確有公私之分,主要是一個經濟學的范疇。被賦予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利益就是權利,權利是披上了合法性和正當性外衣的利益,基于相關主體(利益相關各方)承認,不可能具有物態量化形式,主要是一個法哲學的范疇。反之,未被賦予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利益就是私利,換句話說,私利是未披上合法性和正當性外衣的利益,不基于相關主體承認,是利益主體的自我授權,是赤裸的利益。每種權利都會因其他權利而限制自身,法律就是所有權利的協調和集合,超越法律的權利就是權利的濫用、自我否定,不再成為權利。因此,法權比權利更深入。權力運作以及秩序構建必須保障公民權利。由此,我們將權利所構建的秩序稱為“良序”,將私利所充斥的狀態稱為“無序”。
上圖從垂直角度來劃分良序、劣序、無序。只有當權力和利益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亦即權力轉換為權威,利益轉換為權利,才能構建良序。反之,霸權所構建的秩序就是劣序,私利所充斥的狀態就是無序。這是一個定性分析方法,堪與圖1定量分析方法參照。其中,自由可以作為一種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利益,與利益處于同一層面上。總之,權威、權利是道的問題,主要是法哲學的問題;權力是術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學的問題;利益是利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學的問題。善治的關鍵是:在治道(治理的技術和藝術)上構建權力和利益的均衡,進而在政道(治理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上構建權威和權利的均衡,從而構建良序。
二、良序的水平維度:沖突(隔閡)最小化和合作(信任)最大化
我們所探討的良序不是自然世界的,而是政治社會的。我們必須將政治社會的秩序與自然世界的秩序區別開來,譬如用熵增(正熵流)原理來解釋無序,用熵減(負熵流)原理來解釋有序,均與社會秩序無甚關聯。社會的“良序”意義只有從提出它的意圖,亦即它的負面狀態中才能得到理解、解釋。權力與利益、權威與權利之間關系表現于上下縱向垂直維度上,而沖突與合作、隔閡與信任關系則表現于前后左右橫向水平維度上。由此,我們試圖從“沖突—合作”模型中定義“良序”。
治理的目的就是實現沖突的最小化和合作的最大化。在下圖中,x(0
中國傳統劃分治世與亂世的根據亦即在此。上圖左上區間是亂世,右下區間是治世。亂世是治理失敗的社會無序狀態,表現為沖突的力量超過合作的力量;反之,治世是治理成功的社會有序狀態,表現為合作的力量超過沖突的力量。當然,中國傳統所謂治亂循環是和分合循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聯系在一起的。兩對概念所描述的事實適用不同標準:治亂是說社會的有序和無序,分合是說國家的分裂和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治世通常是在國家統一局面下實現的,如文景之治、貞開之治、康乾之治等(治世亦稱盛世:如漢唐盛世、康乾盛世等)。治是因,盛是果,治與興、盛的關系是因果關系,由治而盛。反之,亂與衰、亡的關系同樣是因果關系,亂是因,衰是果。
但是,這種分析所采用的視角只是實證的視角,并非價值的視角。從價值角度看,治理不僅要實現社會沖突的最小化、社會合作的最大化,而且要實現社會隔閡的最小化、社會信任的最大化。沖突的最小化、合作的最大化有可能是人們從現實功利的角度出發選擇的結果,避免沖突、維持合作并不能說明治理的成效。當統治只是取決于力,而非取決于理時,往往造成人們對治理的離心力——社會隔閡。相反,社會信任說明人們對治理的向心力。有的社會規范、社會制度在沖突最小化、合作最大化方面成效顯著,但在社會隔閡最小化、社會信任最大化方面卻功效不足,于是造成分裂、混亂、新的隔閡和新的沖突,處于一種治亂循環的狀態。
為了描述良序狀態,我們將沖突最小化等同于合作最大化,反之亦然,以便簡化所分析的問題。
我們將良序描述為某種趨于沖突最小化社會狀態;同時把這種沖突最小化描述為一個區間:它的上限是零沖突社會狀態,而下限則是可控制社會狀態。這是它的正值區間。而從可控制社會狀態到零合作社會狀態則是它的負值區間。
當然,在這一描述中,社會控制方式同樣應當得到我們關注。社會控制方式通常包括硬控制和軟控制。在政治運作中,兩者是經常交叉(重疊)在一起的。在不同社會—文化約束條件下,它們之間結合比例不同。一般地說,沖突越小,軟控制越起主導作用;沖突越大,硬控制越占支配地位。顯然,善治不是指硬控制主導型,而是指軟控制主導型。軟控制比硬控制更具有某種彈性或者兼容性能。以第二種解釋來修正第一種解釋,我們得出這樣一個定義:良序是指某種趨于沖突最小化社會狀態,這種沖突最小化處于一個區間:從零沖突社會狀態到沖突較小的軟控制社會狀態。這是它的正值區間。而從沖突較大的硬控制社會狀態到零合作社會狀態則是它的負值區間。
當然,良序狀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因而,最大限度減少社會沖突,在社會控制中,最大限度減少硬控制,實現軟控制,始終必須以社會發展為前提,努力實現社會持續發展。由此我們得出這樣一個補充定義:良序是指某種趨于沖突最小化社會狀態,這種沖突最小化并不阻礙社會發展,而是推動社會持續發展。前者是底線要求,后者是高線要求。零發展不是善治,可發展且可持續才是善治。統籌兼顧,在平衡中發展,在經濟、環境、人口、資源和社會各個方面的平衡中發展,這樣才是全面、協調、持續發展。反之,不僅不可持續發展,而且不能發展,就是劣序。
以上三圖都是從水平角度來劃分良序、劣序。硬控制是指政治強力以至政治暴力控制形式,而軟控制則是指文化意識以至文化心理控制形式。因此,在我們關于“良序”這一定義中,內在地包含了善治文化元素。換句話說,一方面,建設善治文化是建設良序社會、良序世界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善治文化建設又是良序社會、良序世界建設的必要條件。
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不是良序的必要性問題,而是良序的可能性問題。良序社會何以可能?良序世界何以可能?我們的回答是:所謂良序社會、良序世界,即是沖突最小化,亦是合作最大化世界,內在地包含了良序文化元素。通過這樣一種概念界定,我們將良序社會、良序世界的問題與良序文化的問題融為一體。如果良序社會、良序世界是人們構造的可能世界,那么良序文化正是構造這一可能世界的全部意義、價值、信念、理想等等的總和,就是減少社會隔閡和增加社會信任的文化。
良序既排除了一元狀態也排除了二元狀態。一元的社會和文化是極權的狀態,在這種極權中,自由被最小化;二元的社會和文化是斗爭的狀態,兩極之間的沖突和對抗造成斗爭。良序所承諾的既不是一元也不是二元,它只能是多元。這里“多元”不是就政治而言,而是就社會、文化而言,是公共政治領域賴以確立的多元社會文化背景。雖然,良序以多元狀態為前提,但我們卻不能反過來說,任何多元狀態都是良序狀態。多種元素相互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往往造成某種無序狀態(自由、平等最大化,權力最小化),這種無序狀態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良序狀態。因而,為了實現良序,我們必須將無序的自然社會狀態轉變為有序的政治社會狀態,這種轉變就是治理。有序狀態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權力最大化、自由、平等最小化,增加治理成本、代價實現的,這種有序就是劣序,這種治理就是惡治(壞的治理);另一種則是權力和自由的均衡,減少治理成本、代價實現的,這種有序才是良序,這種治理才是善治(好的治理)。為了實現權力和利益的均衡(均壓),進而實現權威和權利的均衡(均壓),必須劃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保護個人利益,防止國家權力的侵犯;同時維護國家權威,限制個人權利的濫用。只有以多元社會文化為背景,確立公共政治領域,才能真正實現良序。實現有序并且良序的狀態才是真正的善治。
所謂“善治(良序)”,概括地說,就是確立多元一體格局。“一體”,就是拒斥無序狀態,確立有序狀態,以便控制沖突,將沖突最小化在可控制并且軟控制區間內,以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在激烈沖突、尖銳對抗中受到破壞,遭到毀滅。“多元”,就是拒斥劣序狀態,確立良序狀態,推動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在自由競爭中持續發展,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狀態中將合作最大化。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狀態,除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確立公共政治領域之外,迄今為止,幾乎沒有別的道路,引導我們通往這一美好前景。
注釋:
① [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94頁。
②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35頁。
③④⑤⑥⑦⑧ 引用或參見吳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與雙主體法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7、188、320、330、15、320—322頁。
⑨ 蔣慶:《再論政治儒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⑩ 參見[德]韋伯:《韋伯作品集Ⅰ:學術與政治》,錢永祥、林振賢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200頁。
{11}{12} [法]米歇爾·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錢翰、陳曉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3頁。
作者簡介:程廣云,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5。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