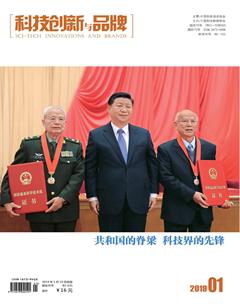董合忠:與棉花為伍的農業專家
龐貝 毛艷玲
山東省農業科學院有一位長期與棉花為伍的科學家,他就是山東棉花研究中心研究員董合忠,一位獲得4項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6項省部科技成果一等獎的棉花專家。
他個子不高很壯實,言談親切接地氣,皮膚稍黑,穿著樸素,整天樂呵呵的,像極了種棉花的農民。
這個像極了農民的農業科學家專“種”棉花,而且種了幾十年,還種出了很多門道,幾乎把棉花種成了“花”。苦中作樂,解決抗蟲棉早衰難題
我國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產圍和消費國之一,總產量和單產均居世界前列。這里面少不了廣大棉農的精耕細作,更少不了像董合忠這樣的棉花專家的功勞。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他就和棉花打起了交道。這個有著博士學歷的“農民”,像種花一樣種棉花,還功夫不負苦心人地真把棉花種出了“花”。
那時候,我國棉花單產不高,棉鈴蟲發生和為害嚴重,轉Bt基因抗蟲棉開始在我國內地棉區大面積推廣。這對控制棉鈴蟲危害、增收增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傳統植棉技術栽培管理的轉基因抗蟲棉,出現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早衰。早衰減產降質,成為阻礙抗蟲棉推廣普及和棉花豐產的技術瓶頸。
要解決早衰問題,必須知道原因出在哪。那時候,我國農業領域對轉基因抗蟲棉的認識不足,對其早衰的原因和控制技術缺乏研究。基于現實需要,董合忠帶領“棉花耕作栽培與生理生態創新團隊,開始了他們的新征程。
首先,他們對不同來源的抗蟲棉品種進行了多年多地的對比,發現容易早衰的抗蟲棉花品種都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結鈴性強,庫源比例大(鈴庫大、葉源小)。他們當時推測抗蟲棉早衰與庫源關系有關。
然后,他們將抗蟲棉品種與遺傳背景相同或相近的非抗蟲棉品種進行對比,發現非抗蟲棉在嚴格控制棉鈴蟲發生、不產生任何為害的前提下,也像抗蟲棉一樣容易早衰,而讓棉鈴蟲輕度危害、失掉少量蒂鈴的非抗蟲棉,早衰得到顯著緩解或延緩,初步證實早衰與庫源關系有關。
隨后,為進一步驗證上述推測,董合忠帶領團隊通過嫁接、環割、去早果枝等措施,并結合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證實,改變庫源比例通過內源激素的變化影響庫源關系,庫源關系失調導致衰老相關基因差異表達引起早衰。從而認識到,協調庫源關系是控制棉花早衰的根本途徑。這些研究發現,為解決抗蟲棉早衰找到了金鑰匙。
之后十多年問,董合忠不是出現在田問地頭,就是埋首實驗室里。好在,這些辛苦沒有白費。在他和團隊的努力下,他們率先將“熟相”概念引入棉花,明確了庫源比例與熟相的關系,揭示了Bt抗蟲棉早衰的機制,建立以協調庫源關系為主線的抗蟲棉防早衰栽培技術。2006年,這項成果獲得山東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007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就是這項技術,入選全國和山東省主推技術,累計推廣5000多萬畝,有效緩解了抗蟲棉早衰的難題,推動了Bt棉在黃河流域棉區的推廣普及,極大地推動了棉花種植效益的提高。
除此之外,董合忠還主持育成抗蟲棉花新品種K638、K836、魯棉522和魯棉532,均成為山東省主導品種,極大地促進了抗蟲棉的增產、增效、增收。
洞察深遠,促成植棉區向鹽堿地轉移
我國棉花種植范圍東起遼河流域和長汀三角洲,西至新疆塔里木盆地,南自海南島崖城,北抵新疆瑪納斯河流域。按積溫多少、維度高低和降水量等自然條件,可分為黃河流域棉區、長汀流域棉區、西北內陸棉區、北部特早熟棉區和華南棉區。
但進入21世紀以來,受天氣環境變化和種植經濟作物的影響,北部特早熟棉區和華南棉區棉花種植面積已逐漸減少,棉花生產主要向西北內陸棉區、黃河流域棉區和長江流域棉區集中,而且這些棉區的棉花在不斷向鹽堿地轉移。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經濟作物要優化品種品質和區域布局,鞏同主產區棉花生產,科學合理劃定棉花生產保護區。
或許是對產業發展的長期關注和深徹洞察,早在20多年前,董合忠就出于棉花種植的產地轉移需求展開了研究。他和團隊研究的鹽堿地植棉技術成果,也直接促成了棉花種植向鹽堿地轉移。
在鹽堿地里種棉花可不容易,成苗難、熟相差、肥效低、用工多都是棘手問題,特別是成苗難是世界性難題。
針對這些困難,董合忠帶領科研團隊潛心研究,提出了根區鹽分差異分布促進棉花成苗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創立了溝畦覆膜種植、部分根區滴灌、預覆膜栽培、短季棉晚春播等誘導根區鹽分差異分布、實現保苗增產的鹽堿地植棉新技術。
采用該技術植棉可以在含鹽量0.7%以下的鹽堿地實現一播全苗,被農業部確定為全國主推技術。截至2013年,該技術已累計推廣6000多萬畝,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棉花種植向濱海鹽堿地的成功轉移。該成果先后獲得2012年山東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013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面對榮譽,董合忠坦言,“鹽堿地種棉花的訣竅,是把棉花種在含鹽量低的溝里,或者通過部分根區滴灌讓一部分根系處在低鹽堿的環境里。實際上是老百姓給我們的啟發才產生了這個技術,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老百姓發明的。”
那是十幾年前,董合忠到東營的鹽堿地考察棉花試驗示范田,發現鹽堿地上的棉花出苗不齊,缺苗斷壟情況十分嚴重。但是他偶然問發現,老百姓隨意將種子撒在了田地旁邊的澆水溝里,結果溝里的棉花卻苗齊苗全苗壯。董合忠立刻從澆水溝和田壟中取了土樣,分析發現溝中央區域含鹽量最低,壟上最高的地方含鹽量最高,鹽分濃度從壟到溝、自上到下依次降低。
有時科學的進步就來自于對偶然發現的深入思考,基于對這一發現的深入研究,才有了后來鹽堿地植棉技術的重大突破,而這一突破,解決了鹽堿地植棉成苗難的問題,直接推動了棉花種植向鹽堿地的成功轉移。
心系棉農,推行輕簡化植棉
棉花產量上去了,適合種植的地域擴大了,然而,對于棉農來說,種植棉花最大的攔路虎莫過于辛苦。我國傳統植棉主要依賴精耕細作生產技術,程序繁瑣、用工多、勞動強度大、效率低,成為新時期棉花生產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
董合忠對植棉農民的辛苦有深刻的體察,讓棉農少一分辛勞,多一分收獲,成為他新時期科研的導向。
他認為長期以來我國棉花種植以戶為單位分散經營,西方的大規模全程機械化、智能化作業并不適合中國國情,只能走中國特色的農業技術路線。
什么才是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技術路線?
董合忠在自身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外現有輕簡化、機械化植棉的理論與技術成果,形成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棉花輕簡化栽培理論與技術體系。
何謂棉花輕簡栽培技術,即簡化管理工序、減少作業次數,農機農藝融合、良種良法配套,實現棉花“種、管、收”全程輕便簡捷、節本增效的栽培技術和方法。
為了這套技術的建立,他和研究團隊聯合湖北、安徽、河北、新疆等省區科學家聯合攻關,突破了精量播種、簡化整枝、輕簡施肥、水肥協同管理、集中吐絮等關鍵技術并闡明了相關理論機制,建立了分別適宜于黃河流域、長汀流域和西北內陸棉區的棉花輕簡化栽培技術。
按照他們的技術走下來,平均省工30%~50%、減少物化投入10%~20%、增產5%~10%。
以播種為例,過去,棉花都是大量播種或足量播種,一畝地需要8~10斤種子。1斤種子約有5000粒,5萬粒種子的出苗按70%來算的話就有3萬多棵苗,但黃河流域棉區地里只需要5000多棵苗,多余的棉苗要通過不斷疏苗、問苗和定苗解決掉,費工費時,還浪費種子。而采取精量播種后,通過單粒精播、適當淺播,不僅能夠實現全苗壯苗,而且只需2~3斤種子,放苗時略微調劑,就可以減免疏苗、問苗和定苗等環節,大大減少了工作量,也節約了種子。
技術的真正價值在于應用,“為了便于農民接受,我們進行了科學‘包裝和通俗化處理,使之成為一種通俗易懂、便于操作的‘傻瓜技術。我們在傳授技術時,告訴老百姓一個大概的道理和一個大致的范圍就可以了,他們在這個范圍里面進行種植操作即可。就是讓老百姓能明白、易掌握。”董合忠介紹說。
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植棉國家采用全程機械化操作,由于生產與生態條件、種植方式存在差異,包括山東在內的內地棉區不能完全照搬國外現有棉花機械化生產技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雖然通過學習國外先進的機械化植棉技術,基本實現了全程機械化植棉,但沒有實現輕簡化,投入大、成本高,纖維質量不高等問題近些年凸顯出來。因此,全國各棉區實現輕簡化植棉的意義都很大。
董合忠認為,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輕簡植棉、快樂植棉,需要依靠配套農業機械和配套棉花品種。機械化是輕簡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輕簡化的全部。輕簡化植棉還包括簡化管理工序、減少作業次數,強調量力而行、因地制宜、與時俱進,更符合中國國情,為此,董合忠團隊開展了棉花全程輕簡化植棉技術研究,突破了種管收各環節的關鍵技術,而且實現了農機農藝融合、良種良法配套。
“我們建立了基于精量播種與集中收獲為核心內容的全程輕簡化植棉技術,將植棉用工由過去的15~25個左右降為5~10個。”
鑒于其省工省時節本增效的顯著作用,該技術被農業部確定為全國主推技術,已在主要產棉區大面積推廣應用,取得十分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開創出適合中國國情的輕簡化植棉新路子,促進了棉花生產從傳統勞動密集型向輕簡節本型的重大轉變,獲得2016—2017年度中華農業科技獎一等獎、2017年山東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國際棉花咨詢委員會(ICAC)給予高度評價,并向全球主要產棉國家進行了推介。
技術方向緊貼產業發展趨勢,研究成果切合國家戰略需求,技術路線服務農民切實需要,扎根農業發展現實一一從棉田里走來的董合忠,以一言一行為我們詮釋什么是農民自己的科學家一一像農民,愛農民,更一心為農民;守望棉田幾十年,董合忠用根植大地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注解了怎樣才是“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