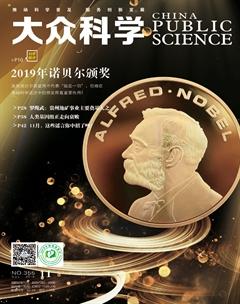人類基因組正走向衰敗
文澤波
人類對于自身的基因探究從未停止。1990年,人類基因組計劃啟動,十三年后(2003年),研究人員宣布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了基本上整個人類基因組的高質量序列。2007年,“炎黃計劃”完成了100%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在了解了基因和蛋白質的功能之后,這些知識將在醫學,生物技術和生命科學領域產生重大影響。不過,隨著人們對基因的了解越來越深入,科學家們也越來越確認,人類的基因正在發生著大量的、危險的突變。
高于閾值200倍的突變速率
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赫爾曼·約瑟夫·穆勒(HermannJosephMuller)在大約70年前就吹響了哨聲——平均每個新生兒帶著50-100個新的突變出生,人類基因組里有很多基因連鎖群(linkagegroup),相當于捆綁遺傳有害基因會影響這些基因連鎖群,產生連鎖反應。穆勒指出,每代每個人的突變應當不超過0.5個,如果突變率太高,人類基因組會不可避免的惡化,最終導致人類滅亡。
2018年,在一次美國衛生研究院(NIH)的演講中,研究了突變載量18年的康奈爾大學的遺傳學教授JohnC.Sanford指出,“學遺傳學的人都知道,人類基因組累積了越來越多的有害突變,突變載量太大。現在科學家們的共識是,人類突變的速率是,每代人的每個人平均貢獻了100個突變。”這個數字,超過了穆勒給出的閾值0.5整整200倍。
在這段時間里,不斷有科學家提出類似的佐證。1997年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遺傳學家詹姆斯克勞(JamesF.Crow)表示,過去的幾百年里,有害突變一直在不斷累積,而有害突變導致的繁殖能力下降率大概是每代人下降1~2%。1996年,德克薩斯大學醫學分校的研究者也表示:在研究中發現人類線粒體基因組累積的突變太多。1999年,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生物學家AdamEyre-Walker和愛丁堡大學的生物學家PeterD. Keightley發表論文:人類的基因突變率非常高,而且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有益突變,大部分是有害的。
征兆其實已經出現在我們周圍

既然基因已經朝著有害的方向突變了幾百年,對我們有什么影響呢?答案是:那些病已經出現在眼前了——糖尿病、過敏、肥胖癥、甚至近視眼都是人類基因有害突變積累引發的征兆。這其中的原由,與自然選擇作用的降低不無關系。以I型糖尿病(高度可遺傳糖尿病)舉個例子,在過去還沒有藥物能夠治療糖尿病時,這種疾病會導致患者死亡,使得該類基因的遺傳率降低,自然選擇作用明顯。而現代社會,人們可以通過胰島素使得這類患者正常生活,繁衍后代,于是糖尿病基因就會在這樣的繁衍中遺傳下去。I型糖尿病基因就很難在人類的基因庫中剔除。這一基因遺傳時間越長,由其引發的有害基因突變的幾率也就越大。
而在科學家們對小鼠、蠕蟲和其他許多動物的實驗中發現,在沒有自然選擇的情況下,實驗室動物的突變發生率會不斷增長,整個種群會變弱,適合度(生物個體或群體適應環境的程度)降低。從這一角度出發,科學技術進步的同時,降低了自然選擇的作用,為有人類害基因的突變提供了一個“避難所”。
事實上,早在2010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生物學家邁克爾·林奇(MichaelLynch)就在論文上表示:在美國,自閉癥、男性不孕不育、哮喘、免疫系統紊亂、糖尿病等疾病的增長率遠遠超過了預期;美國和英國的國民智商在過去的100年里呈緩慢下降趨勢。有害突變在人類基因池中不斷累積,每代人的生理和心智機能會衰退1%。此外還有研究發現,人們身體里“愛學習”的基因也在逐漸衰落。
風口上的“人工基因合成”
如果說人類為什么能夠抗住這么猛烈的傷害,那么一定是因為我們原本強大的基因——它本是在自然選擇中不斷錘煉出來的。但是它還能抗多久,我們不得而知。按照邁克爾·林奇的說法,如果沒有自然選擇,人類生理、形態、神經活動水平每200- 300年就會大變樣。
當然,人類并不會坐以待斃。2016年,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醫學院舉行了一場特殊的會議,大約150名科學家、律師和企業家秘密會面討論創造一個完全人工合成的人類基因組的可能性——科學家們探討是否能化學重組那些從父母親遺傳給子女的基因材料。會議上為什么要邀請律師呢?原因是,人工改變人類的基因不光是技術的問題,還是人類道德倫理與法律的問題。2018年,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一事便被判為違法行為。解決人類基因組走向衰敗一事,任重而道遠。(編輯/侯幫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