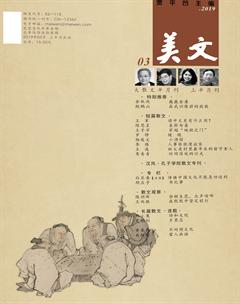文學之路

張華
英國牛津大學資深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在其受到舉世矚目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書中,多次提到今天中東地區在過去時代的一些文學著作。這些文學著作記錄的“歷史”,成為他梳理和撰寫這部全新的世界史的重要史料來源和依據。
比如,在該書前言中,彼得·弗蘭科潘說:非常幸運的是,我在學校學了俄語。我的老師是迪克·哈登(Dick Haddon),一個曾在海軍情報部工作過的非常聰明的人,他堅信掌握俄語及其語言靈魂的最佳方式是了解其燦爛的文學和農村音樂。更幸運的是,他還給有興趣的人教授阿拉伯語,讓我們接觸到了伊斯蘭的文化和歷史,受到了阿拉伯古典文化精髓的洗禮。語言的學習打開了發現新世界的大門,或用我后來想出的一句話說,打開了我們這些西方人重新發現新世界的大門。再比如,他在這部歷史著作的每一章幾乎都要提到不同時期的一些詩人、作家,并從這些詩人、作家的描述中尋找其得出新的歷史結論的文字支撐……總而言之,這部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影響的新“歷史”,有意或無意之間給了文學以足夠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或者說,這部新“歷史”正是新歷史主義的又一部偉大代表作品!
顯然,將這部偉大作品視為具有鮮明新歷史主義特征的歷史著作并不為過,畢竟,彼得· 弗蘭科潘是一位歷史學家;當然,我們也可以把它作為文學作品來看待,因為,這部著作本身也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或曰具有很強的文學性。新歷史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歐美學術領域,它與當時的解構主義思潮有著必然聯系,在歷史與文學的關系方面產生了許多頗有新意的觀點,我本人一直比較感興趣的就是它所強調的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關系,直白一點來講,即二者之間可以互相支撐,互為文本。
彼得· 弗蘭科潘圍繞絲綢之路將其作品分出章節,主要有:信仰之路、基督之路、變革之路、和睦之路、皮毛之路、奴隸之路、天堂之路、鐵蹄之路、重生之路、黃金之路、白銀之路、西歐之路、帝國之路、危機之路、戰爭之路、黑金之路、妥協之路、小麥之路、納粹之路、冷戰之路、美國之路、霸權之路、中東之路、伊戰之路、新絲綢之路。在我看來,這部著作中的所有這些“道路”既是語言鋪就的,又是文學先行的,作者向我們展示的就是絲綢之路上的“文學之路”。這也就是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語言的學習打開了發現新世界的大門”,并“堅信掌握俄語及其語言靈魂的最佳方式是了解其燦爛的文學和農村音樂”,而從這個意義上看,“一帶一路”也應是“語言鋪路,文學先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