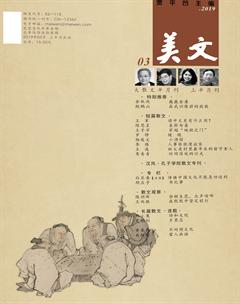假面“快樂”:青山七惠筆下的欲望
周閱 鄭高詠


持續閱讀2015年創刊以來的《美文》“漢風專刊”,無論是主持人的導讀評論,還是其每篇蘊含人文交流內容的文章,均能給我們這樣一個深刻印象,即:文學是了解異域文化的一個特殊并且有效的工具,對于歷史文化如此,對于當代文化亦是如此。比如,如今去日本旅游的中國民眾越來越多,觀光日本文化古跡也好,接觸日本現實生活也好,了解到的只是些表面的文化現象,而若想更深入地去了解當代日本人的現實生活,特別是他們的感情生活,文學作品顯然是一種頗為獨特的工具。大家知道,日本男女之間的感情生活在世界上本就特殊,日本著名的文學藝術作品有所記載和描述,但是今天日本男女的情感世界怎樣特殊,特殊到什么程度,多數中國人并不了解。作為長期關注日本文學和中日人文交流的學者,為了讓中國讀者更多了解當代日本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我們特別申請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批準號16PT08)追蹤當代日本文學作品中反映的現實文化生活。此篇文章即是其一。
一
“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真正的真品。即便原本存在真品,那個真品也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在不知不覺間變成贗品……”這是小說《快樂》中“鼻梁太低,嘴也太尖,與其說長得可愛,不如說有些呆傻”的女主人公芙祐子的一段心理活動。在這個無論怎樣打扮“都無法完全消除她身上的土氣”的女性身邊,總圍繞著一些時尚漂亮的女孩,這些女孩總對芙祐子說些諸如“只有在芙祐子面前,我才能展示真實的自己”一類的話,但是,“芙祐子其實根本沒有看出那些女性朋友在自己面前展示的‘真實的自己和她們在其他朋友面前開懷大笑的樣子之間有任何區別”。關于何為“真實的自己”的思考,不僅充滿了芙祐子的內心,也貫穿于《快樂》的全篇。
《快樂》是日本八零后新銳女作家青山七惠完成于2013年的長篇小說,最初刊載于《群像》雜志,緊接著由講談社出版了單行本(2013年)和文庫本(2015年)。2005年9月,年僅二十二歲的青山七惠以處女作《窗燈》(《窓の燈》)獲得素有“芥川獎搖籃”之稱的第42屆日本“文藝獎”。此后又先后獲得日本文壇最具分量的兩個文學獎項——第136回“芥川龍之介獎”(2007年,《一個人的好天氣》《ひとり日和》)和第35回“川端康成文學獎”(2009年,《碎片》《かけら》)。
《快樂》描寫了榊慎司、耀子和小谷德史、芙祐子兩對夫婦在威尼斯度過的短短五天假期,以四人在水城的碼頭碰面開始,以亞德里亞海面上搖曳的歸程結束,序幕和尾聲都充滿波浪起伏的畫面感,喻示著人物暗自激蕩的心緒。尤其結尾的一句意味深長:“沉默的小船被亞得里亞海中不斷涌起的海浪沖洗著,在翡翠色的海面上平靜地搖曳。”該句獨立成段,可見作者的強調之意。句中存在著兩組矛盾:首先,“沉默”這一修飾語同海浪的“不斷涌起”和“沖洗”構成了矛盾的意象;同時,“平靜”與“搖曳”亦形成了內在的張力。實際上,小說中兩對夫婦、四個男女之間的關系,正是以表面的“沉默”和“平靜”掩蓋著內心的涌動和“搖曳”,甚至是驚濤駭浪。
榊慎司、耀子夫婦結婚八年,丈夫慎司以其他男人垂涎自己的妻子為榮,小說多次描寫他借助想象來撫慰干涸的內心:“他想象著妻子赤身裸體被那些肌肉發達的外國男人侵犯時的情景。”“慎司面帶微笑,聽著兩人說話,腦海中卻想象著妻子發出興奮的尖叫……”他之所以精心安排此次意大利之行,就是為了促成耀子與徳史的越軌行為。在慎司那難以理喻的欲望背后,是婚姻中的“不均衡”——慎司矮小丑陋,耀子高雅靚麗,耀子比慎司高出一頭,“他們就像從馬戲團逃出來的美女馴獸師和小丑”。這種組合使慎司產生了強烈的自卑,于是他以事業的成功、賺取的財富,以及同女神妻子的出雙入對來遮蔽內心強烈的自卑。
小谷德史、芙祐子夫婦相識才三年,與榊夫婦相同的是夫妻間的貌合神離,芙祐子將性生活看作自己“應盡的義務”,并以“堅定的使命感”去踐行。兩對夫妻外表上嚴重的“不均衡”也如出一轍,所不同的只是角色分配——丈夫德史有“運動員的體格,而且眉眼清秀,魅力非凡”,而妻子芙祐子卻身材肥短,“上下一般粗,屁股呈四方形,雙腿又粗又難看,腹部的皮膚已經松弛”。芙祐子經過不懈的追逐才終于得到了因長期受到追捧而業已對女性失望厭煩的德史,因此,芙祐子時時刻刻都在提防其他女性對丈夫的覬覦,也單純地為自己對丈夫所擁有的“特權”而得意。
《快樂》通篇都充滿了或明或暗的欲望。日文版的腰封上寫著:“瘋狂的愛、中毒的欲望、燃燒不盡的孤獨”,稱其是一篇“以鮮烈筆致描寫的官能心理小說”。欲望,在慎司身上表現為設法讓妻子出軌的畸形性欲;在德史那里是無底洞般的貪婪食欲;在耀子心中是重返十九歲狂亂之夜的渴求;在芙祐子眼里則是緊緊抓住丈夫的強烈期盼;此外還有四位主人公周遭的不同人物的各類欲望……
小說中,德史食量巨大并且不斷地感到饑餓,他總是剛剛飽餐完畢就開始考慮幾小時之后的下一頓飯,甚至在大家都暈船作嘔時也仍然惦記著吃飯。“這種饑餓感有鮮明的形狀,仿佛將手伸進喉嚨就能掏出來。感覺很強烈,讓人覺得它似乎馬上就要沖破喉嚨對人大聲訴說那種迫切的感覺。”但是,對美食的貪戀只是表面現象,“他吃飯不是因為喜歡那些食物,而是為了滿足真正的欲望,而這種欲望只有用吃飯這種方式才能得到滿足。”青山七惠筆下濃墨重彩加以渲染的德史的食欲,實則是其性欲的轉換形式。對芙祐子來說,“丈夫旺盛的食欲讓她感到自豪。她覺得這或許暗示著他們夫妻的臥房中沒有完全發泄出來的同等旺盛的性欲”。這一點,早在十五年前德史與耀子在花店偶遇,繼而在小巷子里瘋狂做愛時就已經確定了,作者對此給予了充分的鋪墊——當時年僅十九歲的“耀子感覺自己變成了他的食物。同時,她也感覺他變成了自己的食物。”如此刻意地把德史的性欲轉換為食欲來描寫,意在表明,日常生活中的德史實際上處處都在回避和掩蓋著內心真實的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所有的人都在掩飾真實的自己,回避真實的欲望。而這,正是日本社會的現狀,也恰是青山七惠描寫欲望的目的所在。小說并不是為了展示欲望本身,正如青山七惠在2013年接受南都網采訪時所言:“我倒不是特別在乎‘情色的場景”,這類場景在“《快樂》里有很多,根據情節和人物需要來設計的”。而青山七惠創作《快樂》時的“需要”,就是要喚起人們內心真正的自我,提醒人們卸下假面,正視自己真心的追求。
二
《快樂》中的兩對夫婦在生活中都帶著假面,“丈夫表現出丈夫應有的樣子,妻子表現出妻子應有的樣子,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規則”。不僅是在外人面前,甚至夫妻之間也是如此。耀子總是“拿出一種完美的程式化態度”,她習慣于附和,“因為,這是她在這種場合下應該做的”。就連她到達酒店時收拾行李,也“整個動作完全是機械性的”,甚至度假期間的夫妻生活也“像往常一樣按照固定的程序草草地做了愛”。對此,耀子其實有著清醒的認識,當她看著鏡子中自己的身影,就感到“那個自己是一個幻影,生活在丈夫理想中的幻影”。盡管如此,她依然在維護這個優雅、美麗的幻影,不惜為此失去自我。
榊夫婦的衣著永遠“高雅大方,沒有絲毫瑕疵”,這實際上是一種象喻,他們對真我的拋棄正是為了維護這光鮮的表象。小說中的一個細節值得注意,“耀子總是那樣光彩奪目,穿著衣服的時候,她的身體總能勾起他的欲望,但是一旦當她脫光衣服的時候,她的身體卻不像穿著衣服的時候那樣能夠激發他的興趣”。可見慎司需要的只是耀子的假面而非真實的耀子,也正因如此他才“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妻子”,“專注于婚外情”。作為美麗幻影的耀子只不過是丈夫在人前炫耀的資本。日語中有“建前”(たてまえ)和“本音”(ほんね)兩個含義相對的詞匯,前者指在人前說的場面話,后者是內心真實的聲音,這兩個常用詞語通常被看作日本人“表里不一”的性格特征的表現,由此可以窺見日本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兩面性。
許多夫妻都只是形式上維持著婚姻關系,這是日本社會的現實。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出現了“卒婚”(そつこん)現象,日語中的“卒”是畢業之意,“卒婚”即從婚姻中畢業,也就是說夫婦雙方雖然表面上仍然是婚姻關系,但實際上卻各自獨立生活,偶有來往而互不干擾。這個誕生于日本現代社會的新造詞語最初源自杉山由美子的著作《推薦卒婚》(《卒婚のススメ》,2004年),以后逐漸得到人們的認可并迅速流行起來。Interstation網站在2014年9月以日本各地兩百名30—60歲的女性為對象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有56.8%的女性想要“卒婚”。另據關西電力企業2017年對四十歲以上已婚女性的調查,每三人中即有一人對“卒婚”感興趣。
與“卒婚”狀態不同的是,《快樂》中的四位主人公都沒有選擇各自放飛,他們因不愿摘掉假面而摒棄了真正的自我。“慎司和耀子做愛的時候,始終打不起精神”;德史面對芙祐子時“從未對這個天真的妻子產生過充滿激情的欲望”;而芙祐子在望著丈夫的背影時,即使閃現出一絲欲望也是“瞬間又消退了”。欲望的喪失源自偽裝的疲憊,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習慣性麻木。小說通過主人公們的對話大篇幅地討論著真品與贗品的話題:“看到真品卻感覺它像贗品,您不覺得奇怪嗎?”“真正的真品到底在哪兒呢?”“……有些人看到真品之后就會對仿制品感到失望或因為自己得不到真品而痛苦不堪,而另外一些人卻根本不想這些,他們會努力去尋找那個適合自己且對自己有用的仿制品并樂在其中。二者比起來,我覺得后者更幸運。”說這話的慎司正是把妻子當作了“適合自己且對自己有用的仿制品”,并且“樂在其中”地維持著與耀子的夫妻關系。
耀子是最典型的從小被打造出來的“作品”,直到十九歲的那個冬夜,當她“無垢的身體與心靈最大限度地享受到那個震撼全身的強烈瞬間,她才感覺自己以前披著一身人為制造出來的鎧甲”。而且,耀子發現,“自己作為被別人打造出來的那個耀子活著,比作為真正的自己活得更容易。因此,她殺掉了自己心中的那個小小的耀子,那個因害怕進入澆鑄模型而發出柔弱呼救的耀子,變成大家眼中的‘耀子……”但是,那個被殺掉的真實的耀子并沒有死去,她一直在發出微弱的呼喊:“快放我出去!”
實際上,《快樂》中耀子之外的其他三人也都在內心深處各有呼號。因此,小說的最后,以芙祐子“失蹤”為契機,在分頭尋找芙祐子的過程中,包括芙祐子在內的所有人,都有了異乎尋常的經歷——芙祐子跟隨一個意大利男人去了他的房間;德史被一個半老鞋匠帶回了家,在遭到侵犯后突然記起了十五年前小巷中的少女就是現在的耀子;慎司被一個酷似往日情人的女子偷走了錢包……最終,慎司終于看到了他想象中的一幕。也就是說,這些在日本社會被打造出來并得到精心維護的形象在異國他鄉全部坍塌了。這里,青山七惠對故事場所的選擇富有深意。在意大利,除了相約而來的四位主人公,周圍都是初次見面的陌生人,沒有員工,沒有上司,也沒有親朋好友,只有在這樣的情境中,假面才易于卸下,內心才得以暴露。青山七惠在《快樂》之前的作品中多描寫日本年輕人的“淡淡的日常”,而《快樂》則被讀者冠以“重口味”的標簽,這種改變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了異域空間而達成。正是地中海島國黏濁的熱風,使得日本社會長期偽裝著的四個中年人終于壓抑不住郁積已久的內心風暴。
三
中國出版界和學界較為普遍地認為《快樂》是青山七惠的“轉型”之作,其作品由此一改以往的小清新風格,筆鋒轉為犀利,情節也變得黏稠濃重。但實際上,青山七惠的“轉型”并非始于《快樂》,而是在2010年創作首部長篇《我的男友》(《わたしの彼氏》)時就已經開始了。日本文學界也認為青山七惠是一個善于描寫日常生活細節的作家,并把她的小說比作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有著緩慢細膩的長鏡頭。但青山七惠并不滿足于這樣的評價,她一直試圖開拓新的空間。《我的男友》就是她嘗試的富于情節起伏性和速度感的作品。到了《快樂》,這種沖擊性更上層樓。在講談社《群像》雜志“創作合評”欄目關于《快樂》的對談中,作家町田康評價說:“人物帶有很強的疲軟感,在這種倦怠之中,重大的事件轟隆隆地發生,此類寫法在近來的小說中頗為少見。”
另一方面,《快樂》之“轉型”,也并不僅僅是筆法和情節上的,轉型的表現更多地在于作品主題從描摹個人成長轉向了透視社會現象。青山七惠看到行走于日本大街小巷的蕓蕓眾生往往都是帶著假面的“贗品”,因此才要在作品中借助人物的對話和心里活動揭示出來。她在回答中國《羊城晚報》的采訪提問時曾表示,自己以往的作品較多關注日常生活,而對政治、經濟少有興趣,但她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作為小說家不能一直這樣,因此要有意識地嘗試社會性的話題,她明確表示這是自己“作為小說家的抱負”。剝去假面而表現欲望,這其實是青山七惠創作中一直存在的潛流,早在處女作《窗燈》中,她就借主人公之口表達過,最想看到的并不是平淡的日常,而是平淡表情下潛藏的矛盾和欲望。隨著年齡的增長,青山七惠筆下的欲望已經不再囿于個人內心,而是發散到人與人的關系,即擴展到了社會層面。雖然“欲望”屬于人的內心世界,但《快樂》中欲望的實質是指向對真實自我的承認,指向假面之下的真實內心,指向對真正的“快樂”的追求,盡管最終結果未必快樂。
自從青山七惠辭去旅游公司的工作專事寫作,她便一心想要“尋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答案,想寫一輩子這個主題”,她對媒體表示,“《我的男友》是我第一次嘗試復雜的人物關系”,今后也將一如既往地關注這一主題。而當今日本社會泛濫的“食草族”“御宅族”等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人們普遍地回避與他者的關系。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每五年一次的國勢調查,2015年的“終生未婚率”(即在五十歲時尚未結婚的人口比例)男性為23.37%,女性為14.06%,比2010年調查時分別上升了3.23%和3.45%。這意味著男性每四人中有一人,女性每七人中有一人終生未婚。而且年輕一代終生不想結婚的人還在逐年增加。日本放送協會(NHK)2010年制作的紀錄片《無緣社會——無緣死的沖擊》展現了日本進入“無緣社會”的嚴峻現狀:“無血緣”,即終身未婚的單身人士越來越多,還有許多獨居老人沒有親人陪伴,死在家中很久才被發現,以致出現了一個新詞——“無緣死”;“無地緣”,即鄉村的年輕人漂流于城市中極少回鄉,故鄉觀念日趨淡薄;“無社緣”,即缺少真實的社交,沒有真實的朋友,越來越多的人依靠手機和網絡與不見面的人交流,即使上班族當中也有許多“便當男”,他們在午餐時間寧愿默默在自己的座位上吃自己帶的盒飯,也不愿和同事交流。人們日益沉溺于一己之內心,他人、社會乃至世界都與我無關。這一點在日本的作家群體中也不例外。青山七惠在2010年同中村文則等日本作家參加“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會”,與麥家等中國作家進行了座談,她回憶道:“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作家在發言的時候,大都以自己為中心來講,比如我是一個怎樣的作家,我是怎樣寫作的,而中國作家更關心自己受到哪個作家精神上的啟發這樣的問題。”這實際上也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了日本社會的上述現象。
日本在經歷了高速經濟增長期之后,從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以來,進入了持續低迷的階段,被稱為“失落的二十年”。在這個過程中,“宅”文化盛行、低出生率、超高齡化、消費萎縮、失去欲望等現象席卷日本。近年來,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經常掛在嘴邊的是“不想做”“沒霸氣”“無消費愿望”(やる気がない、覇気がない、消費意欲がない),以至于有人說這是“沒沒的一代”(ないない世代)。據日本電通集團下屬的“電通年輕人研究部”(ワカモン電通若者研究部)就二十九歲以下群體的月平均消費所進行的調查,僅2000年到2014年的四年間,月平均支出就從20.5萬日元下降到了17.4萬日元,每月減少了三萬多日元。這一調查從消費的側面揭示出日本人欲望的下降。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撰寫的《低欲望社會》(《低欲望社會 〈大志なき時代〉の新·國富論》,小學館,2015年)在日本的熱銷也很能說明問題。
全面進入“低欲望社會”的日本,人們即使不得不與他人產生某種關系,也往往帶著假面交往,正如《快樂》中的兩對夫婦那樣。因此,在《快樂》中,青山七惠讓耀子意識到了“封存在靈柩中的那個自己的孤獨”,并讓耀子渴望“他再瘋狂地抱她一次,讓他抵達自己身心的深處——利用這個機會,殺掉那個偽裝的自己,用他的熱情溫暖那個真正的自己,讓她永遠蘇醒。”(180)也就是說,她試圖讓耀子撕掉假面,在與他人的真正交流中回歸真我,試圖讓更多被“殺掉”的“小小的耀子”復活。
中國媒體把《快樂》宣傳為青山七惠真正意義上的“成人之作”,這里“成人”的內涵不應是賺取讀者注目的噱頭,而應指作者的走向成熟,以及作品對社會的反映。這,也應該是理解小說在“快樂”的表象之下書寫“欲望”的關鍵。

周閱

鄭高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