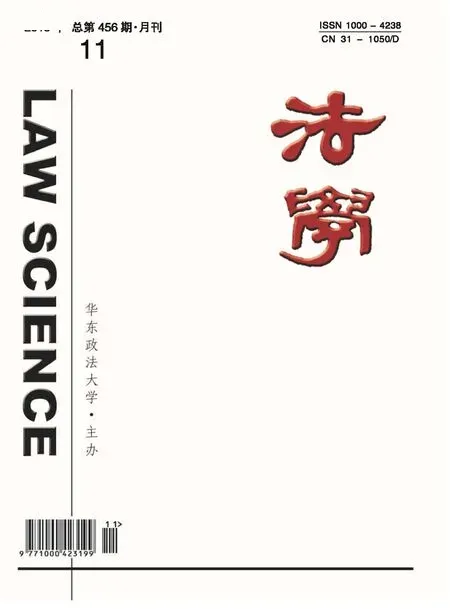習慣法的嚴格概念與類型
——兼與陳景輝教授商榷
●張瓊文
我國當前習慣法研究多為實證研究和對策研究,包括對習慣法歷史演變的探尋、對各地方習慣法的記錄與整理、對習慣法與國家法各自社會作用的定位。但是,“何為習慣法”這一前提性概念問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目前的習慣法研究大多基于不嚴格的習慣法概念。陳景輝教授在《法學》2018年第1期發表了《“習慣法”是法律嗎?》一文(以下簡稱陳文),尖銳地批評了學界通行的習慣法概念,該概念錯把本屬于其他范疇的規范視為習慣法;而按照嚴格的習慣法概念標準,習慣法不可能存在,因此“習慣法”不是一個有效概念。〔1〕參見陳景輝:《“習慣法”是法律嗎?》,《法學》2018年第1期。該文是國內對習慣法嚴格概念的一次重要探索,其方法和命題都具有示范意義。本文認可陳文對通行習慣法概念的批評,但指出按照嚴格習慣法概念,仍至少可能存在著兩種習慣法,即作為其他法律類型效力來源的習慣法和作為獨立法律類型的習慣法,分別稱之為習慣法I和習慣法II。這一結論雖然將習慣法限縮到相對狹窄的范圍內,但證立了習慣法是存在的,再次恢復了“習慣法”這一經典概念的有效性。
一、陳文對通行習慣法概念的批評
陳文的習慣法不存在論建立在對通行習慣法概念的批評之上。下面在簡要介紹通行習慣法概念基本學說的基礎上,概括陳文提出的四個批評及其由此得出的“習慣法不存在”之結論。
(一)通行習慣法概念及其基本學說類型
通行的習慣法概念分為兩種具體學說:“國家認可說”和“非國家認可說”。國家認可說認為,習慣以法律的方式發揮指引行為作用即成為習慣法。有人定義如下,習慣法是由國家認可而具有法律效力的習慣或慣例,即習慣或通過立法機關的立法程序認可而成為法,或通過法官在判決中認可而成為法。〔2〕參見孫國華主編:《中華法學大辭典?法理學卷》,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頁。“寫入立法”和(在實行判例法制度的國家中)“寫入判例”是“認可”的兩種途徑,習慣通過這兩種途徑擁有法律地位,按照法律方式發揮其指引行為的作用。
非國家認可說認為,習慣不必以法律的方式發揮規范性指引作用,其只要與法律分享指引行為這一作用就可以成為習慣法。其下大致包括兩類觀點:(1)依賴權威社會組織的習慣法。即習慣法是獨立于國家法律之外,由某種權威社會組織頒布的行為規范總和。〔3〕參見高其才:《中國的習慣法初探》,《政治與法律》1993年第2期。例如,足球協會作為一種權威社會組織制定的規章條例。(2)不依賴權威社會組織的習慣法,即習慣法等于民間規范,是在公民長期生活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套地方性規范。〔4〕參見喻中:《論習慣法的誕生》,《政法論叢》2008年第5期。這兩種觀點的不同在于,前者依賴于足協這樣的社會權威,而后者不依賴于社會權威;其共同點在于,在該習慣法的定義中都找不到國家的影子,習慣法得以成立無需借助立法、司法、行政等方式的“認可”。
兩種學說分享著一個共同的前提:習慣法的產生有賴于習慣和法律發生某種聯系。這種聯系要么體現為法律對習慣的“認可”,要么體現為法律與習慣分享共同屬性(均具有指引行為的作用)。陳文認為,這兩種聯系只會將其他范疇的規范誤認為習慣法,這種通行概念是極其不嚴格的,由此出發反而可能推出習慣法不存在的結論。
(二)陳文對通行習慣法概念的批評
陳文的批評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習慣并非習慣法。雖然習慣法本質上帶有習慣的要素,但是并非所有的習慣都是習慣法,習慣必須經過實在法體系的檢驗才能夠成為法律。〔5〕同前注〔1〕,陳景輝文。陳文列舉了結婚送紅包的民間習慣,其顯然不是法律。這也說明非國家認可說的失敗,習慣與法律分享指引行為這一共同屬性,并不能得出習慣是法律的結論,這是基本的邏輯要求。
第二,某些民間習慣雖然與法律產生了“關聯”,但也不會成為法律,仍然是習慣。〔6〕同前注〔1〕,陳景輝文。陳文以《民法總則》第10條“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來說明這一點。這一“授權性條款”允許法官適用習慣,但是習慣并不因此成為法律的一部分。這就像法律也會要求法官在數罪并罰時運用算數規則去計算刑期,卻并不會使算數規則變成法律一樣。〔7〕See Matthew Kramer,Why the Axioms and Theorems of Arithmetic are not Legal Norm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27,No.3 (2007),pp.550-560.參見[英]約瑟夫?拉茲:《權威、法律和道德》,劉葉深譯,《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2002年第2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0頁。這對非國家認可說而言,無疑是第二次打擊。
第三,被“認可”成為法律的習慣也不是習慣法,而是屬于其他法律類型。陳文探討了習慣成為法律的兩種方式:立法和判決。〔8〕同前注〔1〕,陳景輝文。法律類型是依靠其淵源來判定的,無論其內容為何,只要其來自立法和判決這兩種淵源,只會成為立法〔9〕“立法”在本文中有時用作動詞,有時用作名詞,根據語境不難判斷。我們放棄了“制定法”這一用法,因為習慣法也可以成文化,也可以是“制定法”。詳見二(一)中的論述。和判例法,不可能產生習慣法這一獨立的法律類型。這從根本上否定了國家認可說,即經過國家“認可”的習慣只能成為其他法律類型,根本沒有習慣法的立錐之地。
第四,習慣法不但在法律類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習慣本身的屬性(陳文稱其具有“事實性”)也與法律的規范性屬性相沖突,這就使得習慣和法律不能相容,從而在根本層次上消滅了習慣法存在的可能性。〔10〕同前注〔1〕,陳景輝文。此觀點總結自陳文,其中有很多地方需要進一步澄清,才能表示贊成與反對。具體澄清參見下文三(五)、四(三)。
可以把陳文對通行習慣法概念的批評為兩個:“分類學批評”(批評一至三)和“性質沖突批評”(批評四)。前者從法的分類的角度出發論證習慣法是一個無效的“偽概念”,因為習慣要么被法律拒之門外從而不成其為法律,要么在進入法律之門的瞬間就被其他法律類型所吸收。“性質沖突批評”意在切斷習慣與法律發生聯系的可能,讓“習慣”與“法”不可能構成一個有效的組合詞。綜上所述,通行的不嚴格習慣法概念所認為的“習慣法”根本就不是習慣法,似乎已經很難找到習慣法存在的空間,陳文由此得出了習慣法不存在的結論。
二、嚴格習慣法概念的三個標準
陳文指出了通行習慣法概念的不嚴格性,這一批評也隱含了一種嚴格的習慣法概念。陳文雖然多次運用其嚴格習慣法概念,并得出習慣法不存在的結論,但該文并未系統闡釋嚴格習慣法概念應該包含的內容。欲證明習慣法是存在的,有必要系統提出嚴格習慣法概念應該包含的標準。以陳文的觀點為基礎,本文認為嚴格習慣法概念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標準:法律權威性標準、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和習慣特有規范性標準。其中標準一確保習慣法具有法律的屬性,實現了習慣法與法律外要素的界分,標準二用于實現習慣法與其他法律類型的界分,標準三確保習慣法具有習慣的屬性。最后是對設置標準的理由的闡釋。
(一)法律權威性標準:法律屬性
法律與非法律規范最關鍵區別就在于法律是具有獨特權威性的指令體系。〔11〕參見陳景輝:《法律的界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頁。倘若缺少法律權威性這一重要特征,法律將不可能存在,更何況習慣法。什么是法律所具有的獨特權威性呢?下面先闡明何為實踐權威,再說明法律作為實踐權威的一種,所具有的特殊性。
(1)實踐權威的特性。一個規范具有實踐權威性則必須滿足兩個條件:a,該規范必須能夠在人們和適用于他們的理由之間起中介作用。b,人們能夠不求助于規范所依賴的理由而確定該規范的身份。〔12〕同前注〔7〕,拉茲文。條件a說明了實踐權威是為其服從者服務的,條件b則說明了發揮這種服務作用的獨特之處,即人們會用實踐權威性規范來“替代”對相關理由的思考,權威性規范相對于那些理由具有優先性。僅僅具備條件a,無法將權威與建議、請求區分開來,后者也是行動者和正確行動理由之間的中介。因此,條件b包含的優先性命題對于界定實踐權威來說是最關鍵的。例如,正確對待軍官命令的方式是直接遵循命令,而不是把軍官作出該命令的理由再權衡一遍。
(2)法律權威的獨特性。作為一種特殊的實踐權威,法律具備一定的獨特性,主要包含三個。〔13〕See Joseph Raz,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150-154.第一,法律是全面的,即只要愿意它可以調整任何領域,而其他的實踐權威則無法做出如此全面的主張,它們都有著各自適當的領域。第二,法律還主張在其疆域內具有至上性,即它可以調整、取消、建立其他的規范體系。第三,法律具有開放性,其規范內容可以進行不同程度地變動,吸納其他規范體系的內容。
習慣法如若存在,則必須具有法律權威性(實踐權威屬性+法律的獨特性),在這一標準下,非國家認可說是完全失敗的。不依賴于社會權威的習慣根本無法發揮實踐權威的作用,例如,是否遵循道德規范要進行實質合理性的考量,這缺少了實踐權威所具有的“優先性”和“替代”作用。足協這樣社會權威頒布的規范雖然有替代作用,但其僅僅具有某一領域的實踐權威性,無法具有全面性和主張至上性,因此都不可能是法律,更不用說是習慣法。
最后澄清一個相關的誤解。習慣法通常被認為是不成文法,且法律成文化往往被認為與法律權威性相等同,這就很容易使人們產生一種誤解,即:“習慣法”并不具備法律權威性,因此不是法律。但這個推論的兩個前提都是不成立的,法律權威性與成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首先,成文化不見得一定具有權威。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成文化:立法式成文化(legislative codification)和百科全書式成文化(encyclopedic codification)。〔14〕See Andrei Marmor,Social Conventions: From Language to Law,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50-52.毫無疑問,前者具備法律權威性,而后者只是完成了一項匯總、記錄工作,其下規范并不具有法律權威性。民間習慣也可以編纂成文,習慣完全可以以百科全書式成文化的方式呈現出來,但不具有法律權威性。其次,具有權威性的法律也不見得一定是成文化的,很多國家是不成文憲法國家,其憲法規范中包含了很多憲法慣例,它們都具有法律權威性,但并沒有采取立法式成文化的方式。因此,成文化與權威性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獨立的概念。對于習慣法而言,非成文化并非其必須要具備的特征,但法律權威性卻是其成立的必要條件。
(二)獨立性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
這一標準是為了使得習慣法區別于立法、判例法等其他法律類型,習慣法如若存在,其不能與立法、判例法等法律類型包容、交叉,否則習慣法概念就是冗余的、無效的。如何才是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呢?這并不要求內容上的獨立性,而是要求效力來源上的獨立性。不同法律類型完全可以記錄同樣的內容,而不會發生法律類型上的混淆,例如,某立法機關制定的立法和法官發展出的判例法均可以包含關于公平交易的相同內容的規則,我們得到的仍是分屬兩個獨立法律類型的規則,不會發生混淆。法律類型的獨立在于其各自的效力來源不同。〔15〕同前注〔1〕,陳景輝文。對于法律類型的界分來說,形式效力來源雖然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卻是必然要素。〔16〕法律實證主義者和非法律實證主義者都接受形式淵源在法律概念中的重要地位,雖然他們對法律內容道德性的地位有分歧。See 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45-52.See 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76-186.See 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33-237.See Robert Alexy,The Argument from Injustice,Clarendon Press,2002,pp.87-88.立法之所以是立法,就是因為擁有立法權的機關按照法律程序制定了它,而不是源自其擁有什么樣的內容。判例法則因為有裁判權的法官按照程序行使了權力。
因此習慣法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實質上就是習慣法效力不能來自立法、判例法的效力來源,即習慣法不是因享有規范創制權的立法機關的立法和法官的判決而擁有法律效力的。至于習慣法的內容,完全可以和立法、判例法有交叉、重疊,這并不會造成習慣法與其他兩種法律類型的混淆。該標準是一個否定性標準,它并沒有肯定地說明習慣法是否應該具有以及具有什么樣的效力來源,而只是指出它的效力不能來自立法、判例法的效力來源。國家認可說無法滿足該標準,該學說之下的“習慣法”只是被其他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認可的習慣,應屬于其他法律類型。
(三)習慣特有規范性標準:習慣屬性
此標準為肯定性標準,其要求習慣法必須體現習慣特有的屬性。同樣,這種習慣屬性并非體現在規范內容上,一條立法的內容完全可以是習慣,例如:立法機關規定“我國道路通行方向為社會大多數人實際上的通行方向”,欲探知該社會的道路通行方向,需要觀察該社會的通行習慣。雖然以習慣為內容,但該規范仍然是立法,而非習慣法,因為其效力來源是立法機關行使了立法權。所以,習慣法與立法、判例法的區別并不在于內容上具有習慣屬性,而是某規范通過習慣特有的方式成為法律,擁有法律屬性。
什么是習慣特有的方式呢?由于“習慣”一詞在漢語中所指并不完全清晰,先要辨析兩種不同的“習慣”:作為行為規律的習慣和作為規范的習慣。前者包括“張三說話時習慣性地擠眼睛”“山西人習慣吃面條”等,它們所體現的是一種外在行為規律性,并不具有規范性意義,即使該行為規律被違背也不招致任何批評。后者包括“排隊的習慣”“結婚送紅包的習慣”等,它們在具有外在行為規律性的同時,也具有規范性意義,如插隊行為是應當被批評的。只有作為規范的習慣才與習慣法相關,習慣法作為一種規范,其強調的不僅是行為的規律性,也包括給出遵循該行為模式的理由。〔17〕陳文在習慣具有規范性這一點稍顯模糊,該文既作出了上述區分;同時又強調習慣是事實性的,同前注〔1〕,陳景輝文。但從整體來看,在此問題上陳文應該與本文的觀點是一致的。
那么什么是習慣特有的規范性呢?或者說,習慣給出的行動理由有什么獨特性呢?習慣的一個必然特征在于其給出的理由中一部分是依賴于服從的理由。〔18〕參見劉葉深:《論習慣在實踐推理中的角色》,《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對此說明如下:第一,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是習慣概念的必然要素。所謂依賴于服從的理由(compliance dependent reasons)是指其他人實際遵循規范是我遵循該規范的部分理由。〔19〕同前注〔14〕,Marmor書,第8頁。許多遵循某一規范的理由都不屬于此類型。例如:某一群體內人們大體一致地不盜竊,但其理由來自于躲避刑罰,而不是他人也如此行動。在這種情形下,人們獨立地依據相同的理由而大體一致地行動,他人如何行動在我的行動理由結構中不起任何作用。再如:遵循立法的理由并不必然是“依賴于服從的”,人們大體一致地遵循立法者頒布的“不得闖紅燈”的規則,是源于立法的權威屬性,而不是其他人的實際服從。“依賴于服從的理由”確立了習慣的獨特性質,可以作為習慣與其他規范的分界點。
第二,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只是習慣給出的部分理由,而非全部。習慣給出的是一個理由結構,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并非全部,該結構中必然還包含其他理由。例如:右側通行的習慣中確實包含了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只有大多數人都右側通行,我右側通行才是有理由的。但是,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并不能窮盡該規則包含的理由結構,該規則之所以能指引人的行為還因為其服務于“交通便利”這一價值,沒有這一價值很難說明為什么人們會遵循右側通行的規則。因此依賴于服從的理由雖然是習慣的必然要素,但并非其全部要素。〔20〕同前注〔18〕,劉葉深文。
根據習慣特有規范性標準,習慣法必須是被人們部分地基于依賴于服從的理由而被接受為法律的規范。其習慣屬性體現在其成為法律的方式上,而非其內容上。
(四)標準設立的依據
上述習慣法嚴格概念設置的標準合理性何在呢?設置的基本思路在于,先通過標準一劃清法律與非法律的界限,使法律外的習慣不會被誤認為習慣法;然后再通過標準二、標準三劃清習慣法與立法、判例法這些毫無爭議法律類型的界限,并完成自身性質的界定,使得立法、判例法不會被誤認為習慣法。在這里可能有一個疑問:即標準二、標準三中任何一個不都可以完成第二個劃清嗎?這兩個標準會不會是重疊的?確實,作為否定性標準的標準二和作為肯定性標準的標準三確實有交叉之處,兩者有時是在從不同角度檢驗同一個屬性。但交叉并不意味著完全相同,兩個標準都是必要的。下面分別看看在標準一排除了非法律規范之后,只使用后兩個標準中的一個會帶來什么問題。
第一,只使用否定性的標準二只能找到不是立法、判例法的法律規范,但這些規范是不是以習慣的方式被接受為法律尚不得而知,因此不能斷定其都是習慣法。事實上,正如本文三(五)、四(三)所論述的,確實有些規范不是基于依賴于服從理由而被接受為法律的,它們可能是基于(例如)民主、正義等價值為理由而被接受的。所以要想準確劃定習慣法還需要以標準三為補充,檢驗其習慣屬性。
第二,只使用肯定性的標準三確實可以包括被以習慣方式被接受的習慣法,但是也會把部分立法和判例法包括進來。正如本文三(五)所論述的,立法和判例法的效力來源也可能是習慣,即這兩種法律類型最終是官員們基于依賴于服從的理由而接受的。在這個意義上,只依賴標準三會包含過寬,需要否定性的標準二將這些立法和判例法排除在外。
綜上所述,標準二和標準三都是不可或缺的,雖然兩者在檢驗習慣法時會有交叉,會從不同角度檢驗同一性質,但這并不能否定任何一個標準的必要性。
三、習慣法I:作為其他法律類型效力來源的習慣法
本文認為至少存在著兩種同時滿足上述三個標準的習慣法。其中習慣法I是立法、判例法這些毫無爭議的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論證分為以下幾個層次:首先,說明各法律類型必然奠基于效力來源之上,且效力來源獨立于法律類型而存在,這就滿足了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其次,批評兩種關于效力來源的理論;第三,證明將效力來源視為官員間實踐構成的承認規則是合理的;第四,論證此種合理的效力來源具有法律屬性,滿足了法律權威性標準;第五,證明此種效力來源可能具有習慣屬性,因而滿足了習慣特有規范性標準,最終證立習慣法I是存在的。
(一)法律類型效力來源的必然存在及其獨立性
法律并不是規范的松散集合,而是一個規范體系,各規范間存在著邏輯聯系,某些法律規范的“法律身份”要依賴于其他規范,即其他規范更具有根本性。拉茲稱這種法律體系構成原理為“起源原則”〔21〕[英]約瑟夫?拉茲:《法律體系的概念》,吳玉章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根據起源原則,法律體系將以效力鏈條的方式形成內部結構。〔22〕參見[奧]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129頁。當我們追問某一條法律為什么有效時,必然會沿著效力鏈條追溯到效力來源之處。例如,我們追問為什么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是有效的,得到的答案必然是,因為行政機關創制行政法規的權力來自于法律的授權;那為什么該部授權法律有效呢?因為憲法授權國會制定該法律;我們可以繼續追問為什么憲法有效。只要這一有效性追問是正當的,我們必然要借助效力來源給予最終回答。這就是效力來源存在的必然性。根據這種效力鏈條理論,我們可以合理地追問立法機關制定的立法和司法機關創制的判例法這兩種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是什么。
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不會等同于該法律類型本身,即效力來源具有獨立性。當然,一部立法的效力是完全可以沿著效力鏈條追溯到另一部立法的,例如,刑法的效力來自于該國的成文憲法。但是當我們對憲法的效力進行追問時,不可能存在另一部立法作為其效力來源。而憲法又不能自稱其是天然有效的。這就意味著該國立法這一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必然要追溯得更遠,其必然不是立法本身。判例法這一法律類型也是如此,此處不再贅述。綜上所述,立法、判例法這兩種毫無爭議的法律類型必然要奠基于其各自的效力來源,而該效力來源具有獨立性。因此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滿足了習慣法存在的第二個檢驗標準——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
(二)兩種效力來源理論的缺陷
有三種不同的理論可用于具體說明各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一是將某個人或者機構作為各個法律類型乃至整個法律體系的效力來源,其代表觀點是約翰?奧斯丁提出的最高主權者;〔23〕參見[英]約翰?奧斯丁:《法理學的范圍》,劉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25頁。二是將與人類實踐完全劃清界限的規范作為法律體系最終的效力來源,其代表性觀點是漢斯?凱爾森提出的基本規范;〔24〕同前注〔22〕,凱爾森書,第132頁。第三種也將規范作為各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但強調該規范是由人類實踐構成的,其代表性觀點是哈特提出的承認規則。〔25〕參見[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許家馨、李冠宜譯,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0~100頁。本節先分別檢討前兩種效力來源理論,指出其缺陷所在,下一節再闡述為什么以實踐為基礎的承認規則理論才更為合理。對第一種和第二種理論的探討很有必要,因為假如它們是成立的,那么其所確立的效力來源基本不會成為習慣法:奧斯丁主張的最高主權者是一個人或者機構,根本不是法律規范;而凱爾森提出的基本規范是被“預設”的,〔26〕同前注〔22〕,凱爾森書,第130~132頁。與人類實踐割裂開來,而習慣恰恰需要人類重復性實踐才能形成。
奧斯丁和凱爾森的效力來源理論的缺陷如下:第一,兩種理論都錯誤地認為所有效力鏈條最終都會匯聚到一個“點”上,沒有認識到法律體系內各效力鏈條的盡頭可能呈現出多元狀態。例如,在美國這一成文憲法國家,憲法中沒有明確授權法官有創制判例法的權力(判例法的合法性更多來自于傳統),而國會創制立法的權力是憲法明確授權的。這就意味著立法所在的效力鏈條終結于憲法,而判例法則無法追溯到憲法。兩個效力鏈條并未匯聚到一個“點”上。在奧斯丁理論中,作為效力來源的主權者就面臨著這種困境,他可以合理地作為立法的終極來源,但他如何成為判例法的終極來源呢?在美國哪個機構是這個主權者呢?哪個機構曾經明確肯認過判例法的合法性呢?凱爾森的基本規范也有同樣的遭遇,基本規范授權第一屆制憲會議制定憲法,但是并沒有授權法官創制判例法,兩條效力鏈條無法聚合于基本規范這個“點”。所以就像拉茲所說的,法律體系被奧斯丁和凱爾森錯誤地想象成了有共同根部的樹形結構。〔27〕同前注〔21〕,拉茲書,第117~121頁。
第二,奧斯丁的理論無法有效說明主權者為什么有權創制法律。主權者之所以能夠正當地創制立法,有賴于授予其立法權的規則,具體包括立法者如何選任、繼替的規則,規定立法程序的規則,以及劃定立法權限的規則。〔28〕同前注〔25〕,哈特書,第47~56,60~65頁。這些規則是先于立法者的。奧斯丁的主權者行使權力假如依賴于授予其權力的規則,那么他就不是這些規則的效力來源;假如他先于所有規則,那么無法說明他為什么會擁有立法權。換句話說,奧斯丁無法說明在不違背休謨定律的前提下,如何從主權者這一事實性存在推導出作為規范性存在的法律體系來。他需要一個規范性前提。
第三,凱爾森的基本規范無法有效說明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凱爾森拒絕從事實中推論出應當,基本規范本身是規范性存在,它作為法律體系的效力來源能夠賦予其他法律以規范性效力。但基本規范的缺陷在于它僅僅通過規范內容來判斷效力鏈條的連續與中斷,并未考慮規范背后人們的實踐。A國第一部憲法為什么是有效的,因為基本規范規定第一屆制憲會議有權制定憲法。設想假如與A國毫無關系的B國的某一立法授權A國第一屆制憲會議制定憲法,這一立法肯定會被A國人民嗤之以鼻,當作毫無約束力的無稽之談。〔29〕See H.L.A.Hart,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Clarendon Press,1983,pp.319-321.但凱爾森的效力鏈條理論只考慮規范內容中授權性規定,不考慮作為事實存在的人類實踐,他會認定A國法律體系是B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基本規范在此作出了錯誤的鑒別,它無法起到劃定法律體系界限的作用。
(三)承認規則:以官員實踐作為效力來源
對照之下,哈特的承認規則理論就具有了獨特的優勢,作為效力來源,承認規則也為習慣法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下面先簡述其內容,再展現其相對于前兩種理論的優勢。
首先,哈特將承認規則視為法律體系的效力來源。其他法律擁有效力是因其滿足了承認規則設定的條件,〔30〕See Jules Coleman,The Practice of Princip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83.且不存在更高位階的標準來鑒別承認規則的效力。承認規則成為法體系中的一員恰恰是因為它提供了用于鑒別其他規則的標準。〔31〕See Grant Lamond,Legal sources,the Rule of Recognition,and Customary Law,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Vol.59,No.1(2014),pp.25-48.
第二,官員間大體一致的實踐構成了承認規則。根據哈特的社會規則理論,規則是奠基于社會實踐的,這種實踐具有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外在方面表現為規則之下的行為大體一致,呈現出一種規律性;內在方面則表現為對外在行為模式持一種一致的批判反思態度,即把該行為模式當作按照其行動的正當理由。〔32〕同前注〔25〕,哈特書,第51~53頁。承認規則也是社會規則的一種,哈特認為對該規則持有批判反思態度的人僅限于官員,普通公民無需對承認規則持有內在觀點。〔33〕同上注,第103~106頁。雖然《法律的概念》文本中也有其他稍有差異的表述,但“承認規則僅需官員群體接受”的觀點表述得更為正式。官員們對于哪些規則可以算作法律有著一種大體一致的內在觀點和外在行為的一致性,這就是該國法律效力的鑒別標準。
第三,承認規則理論的相對優勢。承認規則理論彌補了奧斯丁和凱爾森理論的上述缺陷。(1)承認規則作為官員間的復雜實踐,其允許各個效力鏈條的終端多元化。官員們在實踐中可以接受多種法律效力形式并存,而不用假定一種效力來源是最高的。〔34〕同上注,第64頁。(2)最高主權者的立法權是由承認規則賦予的,哈特不會像奧斯丁一樣,設立一個超越于所有規則之上的主權者,以至于難以解釋主權者的權力來源。(3)根據承認規則理論,一條規范是否有效要取決于規范下官員們對其持有的批判反思態度,缺乏這種實踐態度的紙面規則根本不具有效力。因此由于缺乏A國官員內在觀點的支持,B國授權A國制憲會議立憲的立法根本不會在A國有效力。這就解決了凱爾森法律體系統一性的困境。
作為最具合理性的效力來源,承認規則這一已滿足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的規范是否可能是習慣法呢?下面兩節將分別探討承認規則的法律屬性與習慣屬性,以最終完成對習慣法I存在的證明。
(四)承認規則的法律屬性
承認規則是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嗎?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對此有許多模棱兩可的表述:a,承認規則無法被追問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因為法律效力有無,需要借助承認規則來判斷,承認規則無法判斷其自身的法律效力,因此承認規則既非有效也非無效;〔35〕同前注〔25〕,哈特書,第97、98頁。b,承認規則只是一種從外在觀察者角度看到的事實,它表現在官員實踐當中;〔36〕同上注,第97、98、99、100頁。c,當我們說該法律體系的承認規則十分優越的時候,承認規則也可以從價值的角度來看待。〔37〕同上注,第97頁。
這些表述似乎意味著“承認規則并不是法律體系一部分”。因為根據a,承認規則既非有效也非無效,如何能夠成為法律?根據b,承認規則是一種從外在視角觀察到的事實,迥異于哈特所謂的從內在視角觀察到的規則,連規則都不是,如何成為法律?根據c,承認規則是一種價值判斷,按照哈特法律實證主義的立場,法律是價值無涉的,因此其絕不是一種法律判斷。但是上述推斷并不合理,理由如下:
第一,我們也可以在《法律的概念》中找到很多明確肯定承認規則是法律的論述。例如,哈特認為,法律體系出現的標志就是二級規則的出現,還說“法律是初級規則與次級規則的結合”,〔38〕同上注,第72頁。而所謂的次級規則(即本文所稱的二級規則)就包括承認規則。這是對承認規則法律身份的明確認可。
第二,上述模棱兩可的論斷也存在從其他角度解讀的可能性。例如,a可以被理解為承認規則不具有普通法律的法律效力,但其法律身份通過另外的東西來賦予。b和c可以理解為作為法律的一部分,承認規則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待,從法律體系外觀察者角度看,可以不接受該法律對自己的約束力(即所謂的將其看作事實);從價值評價的角度,可以對其作出價值判斷。但這些其他角度并不影響官員們從內在角度來看待承認規則,將其作為有效的法律規范接受下來。為什么不可以從多角度來看待同一事物呢?
第三,哈特上述模棱兩可的表述也許是其堅持錯誤的前提預設所導致的不幸結果,而修正這些錯誤前提并不會推翻承認規則作為效力來源的有效性。作為法律實證主義的代表,哈特堅持法律與道德相分離,法律體系自成系統。與此同時,哈特還力圖將法律體系看作是具有規范性的規則體系,這種規范性是通過形式淵源來賦予和傳遞的。〔39〕德沃金稱這些形式性因素為“譜系”,see 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7.這些形式淵源分別依循一定鏈條最終追溯到承認規則處時,承認規則自身的規范性來自于何處就成為無解的難題,只能歸之于“既非有效也非無效”“轉化成一種事實”這些奇怪的陳述。假如哈特放棄法律是獨立于道德的封閉系統,愿意訴諸某些實質價值(特別是法治價值)來論證承認規則為什么是有約束力的,那么上述模棱兩可的論述就可以避免了。〔40〕See Ronald Dworkin,Justice in Rob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4-35.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承認規則符合法律權威性標準。承認規則顯現在官員們的實踐中,這意味著,在這個社會中哪些是鑒別法律的效力標準,我們不需要完全訴諸政治價值的辯論,我們只要觀察官員們的實踐即可。這就意味著官員們的實踐“替代了”實質性價值爭論。而且官員們的決定也會主張具有全面性、至上性和開放性。這就滿足了法律權威性標準的所有要求。〔41〕關于習慣法是否可以具有法律權威性的類似論證,see David Lefkowitz,Customary Law and the Case for Incorporationism,Legal Theory,vol.11 (2005),pp.409-412.他所批評的觀點,see Matthew Kramer,Where Law and Morality Mee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92-97.
(五)承認規則的習慣屬性
承認規則是習慣嗎?其被接受為法律是部分出于“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嗎?下面分為三個層次論述:首先闡述哈特關于承認規則性質論述的前后變化;其次,闡述一種對哈特觀點的合理批評;最后,本文提出這一批評并不會排除承認規則是習慣的可能性。
1.哈特的“慣習主義轉向”。《法律的概念》第一版認定承認規則是社會規則的一種,但這并不意味著承認規則就是習慣。〔42〕同前注〔18〕,劉葉深文。習慣的獨特性在于其給出的部分理由是“依賴于服從的”,即人們遵循習慣的理由部分地來自于其他人也如此行動。但社會規則并不必然如此。例如:人們一致接受“不殺人”這一社會規則,但理由是“殺人是殘忍的”,而不是其他人對這一規則的接受與遵循。換句話說,雖然接受規則的理由是一致的,但這種一致性并不是接受規則的理由。所以,朱莉?迪克森在細致分析《法律的概念》第一版文本的基礎上認為,早期哈特并不是一個規則的慣習主義者。〔43〕See Julie Dickson,Is the Rule of Recognition Really Conventional?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27(2007),issue 3,pp.374-382.這個結論相當合理。
但是,哈特后期似乎經歷了一個關于承認規則的慣習主義轉向。〔44〕See Leslie Green,Positivism and Conventionalism,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vol.XII,No.1 (1999),pp.37-41.他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后記中這樣寫道:“的確,我在本書中是把承認規則視為建立在司法部門內慣習性的共識上。這一點至少在英國及美國的法律實務中確實如此。英國法官之所以會把國會立法(或者美國法官之看待憲法)視為優于其他法律淵源者,其所持理由之一,的確包含他的司法同僚以及他們的前輩們都這么做的這件事實。”〔45〕同前注〔25〕,哈特書,第234頁。譯文有所修正。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哈特一方面認可了承認規則是習慣,遵循承認規則的理由正是習慣所要求的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即“司法同僚和他們的前輩都這么做”;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哈特有所保留,只說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只是“其所持理由之一”,但他沒有說是不是“主要理由”或者“必然理由”,所以他對于把承認規則完全看作習慣還有點猶豫。盡管有這些猶豫,哈特后期較為偏向于認為承認規則是一種習慣。
2.對慣習主義轉向的批評:兼及“性質沖突批評”。對承認規則習慣屬性最經典的批評來自于德沃金。〔46〕其他類似的批評者包括 Julie Dickson,同前注〔43〕,Dickson文;Leslie Green,同前注〔44〕,Green文。他區分了慣習性規則(conventional rules)和偶合性規則(concurrent rules)。〔47〕同前注〔39〕,Dworkin書,第53~54頁。慣習性規則就是習慣,其作用主要在于協調人們的行為,使各種行為不相互沖突。因此他人如何行為就為我相應地行為給出了理由,即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兩種完全相反的行為模式可以達到同樣的協調效果,到底應該選擇哪種,慣習性規則在所不問,這就是慣習性規則的任意性。〔48〕See Andrei Marmor,Legal Conventionalism,in Jules Coleman (ed.),Hart’s Postscript: Essays on the Postscript to The Concept of La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03-204.偶合性規則作為人們的行動理由是源于該規則所服務的價值,而不是人們的一致性實踐。例如,“不得殺人”這條規則之所以成為行動理由,不是因為很多人都認可這條規則,而是由于人的生命作為重要的價值不容無正當理由的剝奪。那么法律僅僅是慣習性規則嗎?法律僅僅是協調人們的行為,使彼此不相沖突嗎?答案是否定的。〔49〕哈特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同前注〔25〕,哈特書,第234頁。我們不會說,法律“禁止盜竊”與法律“允許盜竊”是完全一樣的,盡管它們都實現了行為的協調。我們知道兩者存在很大的差別:前者體現了個人財產自主的價值,后者違背了該價值。法律恰恰是追求并實現各種價值的,而非僅僅是協調行為。承認規則是法律體系的根基,它起到識別其他法律規范之作用,法官之所以承認國會立法為有效的法律規范,很大程度上是訴諸民主這一政治價值,而不僅僅是與其他法官的行為相協調。在這個意義上,承認規則更接近于偶合性規則,而非習慣。
陳文的“性質沖突批評”實際上也與此類似。雖然他在文章中的表述是,習慣不適合用來說明法律的性質,〔50〕同前注〔1〕,陳景輝文。但被理解為其不適合作為其他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更為妥當。假如在這一“轉譯”的過程中沒有丟失什么特別重要的東西,那么“性質沖突批評”就成為:習慣不適合作為其他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因為法律效力不可能僅僅建立在具有“任意性”的習慣之上,或者法律不可能只是建立在依賴于服從的理由之上,在此意義上,習慣法Ⅰ似乎垮掉了。
3.習慣法I存在的“可能”空間。本文承認德沃金對哈特慣習主義轉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習慣法I并沒有因此垮掉。理由在于:德沃金摧毀的和本文試圖證立的不是同一個命題。德沃金的論證(包括“性質沖突批評”)試圖摧毀的是,“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是承認規則給出的主要理由或必然理由。就像德沃金所合理展示的,官員遵守承認規則很大程度上是訴諸于政治價值的,這否定了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成為“主要理由”的可能性;而且(例如)在某一情形下,法官可以只訴諸民主價值而接受某一國會立法為有效法律,這就否定了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是“必然理由”的可能性。
但德沃金的摧毀效果僅此而已,他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在某些情形下,“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是承認規則給出的“可能理由”。〔51〕其實陳文也認識到了習慣作為其他法律類型效力來源的可能性,例如該文指出:“習慣在來源命題之下的確具備生存的空間,只要特定社群中的人們,依照習慣這種獨特的事實來創造他們用以約束自身的法律,那么毫無疑問,法律在這個社群中就會被化約為習慣。……(法律)化約為習慣這種特殊的社會事實,卻只是偶然的結果,而不是這個命題所得出的必然結果。”同上注。只是陳文沒有意識到,他指出的“生存空間”和“偶然的結果”就證立了習慣法存在的可能性。法律作為眾人合作的事業,官員也需要協調彼此運用法律的行為,所以“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在其中發揮作用是很正常的。例如,一名法官在考慮是否接受某一法律原則在本案中可否適用時,他一方面要考慮民主價值(該法律原則是否為民選機關所頒布),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其他法官是否已普遍接受該原則,以確保法官群體做出全體一致的判決。后一個方面就是“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在發揮指引作用。而一旦承認規則給出了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哪怕這些理由僅僅是其給出的部分理由,承認規則也具有了習慣屬性。因為根據習慣的定義,依賴于服從的理由也僅僅是習慣給出的“部分理由”,而非全部理由。陳文想否認習慣法存在的可能性,他要證明的是一個全稱否定命題(習慣法不可能存在),而本文試圖證明的是一個特稱肯定命題(習慣法在某些條件下可能存在)。既然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是承認規則給出的“可能理由”,特稱肯定命題就是正確的,習慣法I就有了存在的“可能”空間。
綜上所述,法律類型必然要奠基于獨立的效力來源,這滿足了習慣法存在的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而承認規則是對效力來源最為合理的一種理論解釋,它滿足法律權威性標準的要求,也可能具有習慣屬性,這就證立了習慣法I是可能存在的。
四、習慣法II:作為獨立法律類型的習慣法
即使上文所述的習慣法I是可能存在的,這一觀點也許并不具有顛覆性,因為有人可能把習慣法存在與否的爭論理解成與立法、判例法并行的法律類型是否存在的爭論,而習慣法I只是指出其他兩種法律類型的效力來源是習慣法,盡管效力來源也是一種獨立的法律要素,但不是新的法律類型。對于這些人,本部分闡述的習慣法II就變得更為重要了。下面將先反思陳文“分類學批評”所采用的“四分法”預設,然后指出該預設忽視了“授權外造法”這一可能產生獨立法律類型的造法方式,繼而本文將分別說明該種類型規范可能具有的習慣屬性及法律屬性,以證立其滿足了習慣法存在的三個標準。
(一)“四分法”:分類學批評的預設前提
如本文一(二)所述,陳文細致地分析了習慣可能與法律相關的四種方式,〔52〕同前注〔1〕,陳景輝文。即以習慣為內容的立法、以習慣為內容的判例法、通過法律授權可以適用的習慣、純粹的民間習慣。其中第一種、第二種方式產生的分別是立法和判例法,第三、第四種方式產生的不是法律,是法律外的習慣。因此,作為法律類型的習慣法毫無立錐之地。本文稱這一分析框架為“四分法”。
按照是否得到法律授權來看,“四分法”中,前兩種方式至少得到了“創制法律”的授權,〔53〕這里之所以強調“至少”是因為在判例法中,作出判決的行為既是法律的創制又是法律的適用,是一體的。See John Gardner,Law as a Leap of Fa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75.第三種方式得到的是“適用法律”的授權,第四種方式沒有得到任何法律授權。而通過授權與否、授予什么權力,四分法涵蓋了授予創制法律的權力(第一和第二種方式)和沒有授予創制法律的權力(第三和第四種方式)兩種情形,但是它并沒有考慮到在兩者之外可能存在的“授權外造法”情形。本文認為,這種造法形式產生了習慣法II。
(二)產生獨立法律類型的“授權外造法”
所謂“授權外造法”指的是擁有法律創制權的主體在授權范圍之外創制規范,在得到其他機構的認可與接受的前提下,該規范擁有了法律的身份。這一定義也意味著“造法”并不等于“行使立法權造法”,前者范圍更大。〔54〕約翰?加德納區分了造法(law-making)與立法(legislation),也體現了相似的觀點,同上注,第54頁。為了形象起見,用一個思想實驗來說明。某一立法官員一直履職良好,深得公民信任。該國憲法明確規定立法官員創制法律要遵循兩個限制:一是程序性限制,規范頒布前必須付諸公共輿論討論;二是實質性限制,立法官員不得對工資問題立法。公民A由于身體有缺陷,用人單位不給予其同等的工資。A向立法官員反映,希望可以獲得同等的工資。立法官員設身處地考慮之后,頒布了一條法律,對身體有缺陷者不得在工資上予以差別對待,該條法律并未付諸公共輿論討論。由于多種原因(包括忙于其他事務、該法調整事務不是足夠引人矚目,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該立法官員過去的立法足夠合理和值得信任),這條法律并未引起反對,其他官員也開始適用該法,公民們普遍遵循。這條規范得以保留在了法律體系當中。
這條法律是什么類型的法律呢?本文認為,這條法律應該被理解為習慣法。有人可能認為,該條規范明顯是立法。但是,這一回答是禁不住推敲的。理由如下:
第一,立法需要符合承認規則設定的條件,“授權外造法”則不符合這些條件。有人認為,這條規范是由立法官員頒布的,當然屬于立法。但是,我們并不會因為一個人擔任立法者這一公共職務,就把他說的所有話都當作法律。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書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使獨享立法權力的國王也需要通過相關規則來區分國王頒布的法律和其對妻子、侍女下達的私人指令。〔55〕同前注〔25〕,哈特書,第62頁。因此,只看到某人是立法官員并不能徑直斷定其“頒布”的東西就是法律,我們還要借助立法官員產生的規則(如選舉規則)、立法的程序性規則和實體性規則來綜合判斷。在思想實驗中,立法的程序限制規則和實體性限制規則都被違背了,所以其立法身份十分可疑。當然,本文也承認,使立法生效的某些標準被輕微違背,可以無爭議地產生出一部立法來。但像本思想實驗所展示的情形,相關立法規則被極大地、明顯地違背時,無法產生出一部有效的立法。
第二,該條規則效力產生的時間不符合立法的特征。立法從其頒布之時產生效力,但習慣法的效力要想產生往往需要經歷一個漸進的過程,很難說出它是在什么時間點開始生效的。〔56〕同前注〔53〕,John Gardner書,第70~72頁。本思想實驗中這條工資法產生之初是否具有效力是存疑的,其效力產生于其他社會主體,特別是其他官員逐漸認可、接受的過程。試想該規范被其他官員集體批評并抵制,我們只會把這條工資法理解為自始無效,而不會將其理解為效力被取消。其他官員參與的過程是一個漸進過程: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遵守并適用該規范,這典型是習慣法生效的特征。
第三,該條規范只具有立法的外觀,而不具有立法的實質。有人可能認為,該條法律是立法,因為其采取了立法的典型記錄形式,即成文法的形式。但是,外在的記錄形式并不是鑒別法律類別的關鍵因素。就像本文在二(一)中所論述的那樣,成文化分為兩種:立法式成文化和百科全書式成文化。兩種成文化的區別不在于記錄方式的不同,而在于有無相關的授權。習慣完全可以采取百科全書式成文化方式,這并不會使其具有法律權威性。而立法式成文化的關鍵在于該文本被作為權威來對待,這只有在擁有立法權的情況下才可能。所以,沒有授權而僅僅從記錄形式來判定這條規范的立法屬性是錯誤的。
第四,即使該條法律成為立法,也需要依賴于其他條件,即需要承認規則發生一次變更。這條法律是否可能具有立法身份呢?我們可以想象隨著人們對這條法律的接受,也開始接受立法官員可以在工資領域、不經輿論討論行使立法權的正當性,即公民和其他官員從接受一條法律發展為接受一種新的立法授權。此時,那條法律最好被看作是立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溯及既往的嫌疑。但這一轉變的關鍵在于承認規則(習慣法I)發生了一次變動。而在這一變動之前,該條法律仍然是授權之外的,因此不是立法,只能等著其他官員共同參與使其變成一條習慣法。習慣法Ⅱ的產生方式是“授權外造法”,承認規則(習慣法Ⅰ)一旦將某一造法方式記錄下來,該種造法方式就不是“授權外”了。但是在有限授權之外仍然還會存在新的造法方式,因此習慣法II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會因為承認規則的一次變動而被消滅。這也意味著“授權外造法”產生的習慣法Ⅱ在習慣法Ⅰ中找不到效力來源。
獨立法律類型的習慣法將不限于立法者的“授權外造法”,也可能是由其他官員(如法官、行政官員)推動;也可能沒有一個官員是率先的,而是官員們集體一致行動的產物,例如:英國的憲法慣例“國王不得為非”就是被英國官員們集體接受的,而非由某個官員率先提出的。但無論采取哪種形式,其原理與思想實驗中的情形是相同的,這些官員都沒有被明確授權依照此種方式集體造法。綜上所述,“授權外造法”與立法、判例法有著根本的不同,這滿足了習慣法嚴格概念中的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
(三)習慣法II的習慣屬性
成功經受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的檢驗之后,習慣法II還需要通過習慣特有規范性標準和法律權威性標準的檢驗。前一標準事關習慣法II的習慣屬性之有無,即習慣法II被官員們合作接受是基于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嗎?本文要再次依賴于三(五)中所使用的區分對此予以說明,即在官員群體接受授權外造法規范時,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是“主要理由”“必然理由”,還是“可能理由”?習慣法II可以被看作官員群體的“合作造法”,某一立法官員在授權之外創制了一個規范,相當于發出的一個信號,有待于其他官員合作參與進來以賦予其法律效力。關鍵在于其他官員的接受和認可是不是“主要地”“必然地”基于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呢?答案是否定的。以思想實驗為例,其他官員之所以接受立法官員“授權外”創制的規范,完全可以以分配正義(A得到了不正義的對待)、政治正當性(立法官員是處理該問題最為合適的主體)為理由,其他官員遵循、接受該授權外創制的規范可以不在其理由結構中扮演任何角色。這就意味著依賴于服從的理由不會是“必然理由”。法律體系是不是應該接納某一規范為法律,也并不僅僅是官員們彼此協調行為的問題,而是涉及到實質價值考量,因此主要用于協調行為的“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在這里也不會是“主要理由”。
但是這并沒有消滅習慣法II存在的空間。因為我們只要證明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可以合理地作為官員們接受授權外造法的“可能理由”即可,即其他官員接受授權外造法規范在某些條件下可以是我合理地接受其為法律的部分理由。法律作為一項合作性事業,除了考慮實質正義等價值之外,官員們行動協調一致也有其價值,例如能夠保證對法律內容的基本共識,進而保證公民行動的可預期性,當其他官員都接受某一規范時,這就會成為我也接受該規范的理由。因此,把依賴于服從的理由看作是“可能理由”是非常合理的。哪怕依賴于服從的理由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而是與其他實質性價值組成一個理由結構,這也不能否認其接受的規范具有習慣屬性。因為習慣也只是把依賴于服從的理由作為“部分”理由,而非全部理由。總之只要作為“可能理由”是成立的,習慣法II就有存在的空間,習慣法就是一個有效概念。
(四)習慣法II的法律屬性
習慣法II是否符合法律權威性標準不難判斷。無論對于普通民眾還是對于官員來說,“授權外造法”產生的這條規范都可以替代我們對個案中具體價值的考量與權衡,在思想實驗中就是替代了我們對A在工資上予以同等對待是否公平的考量。這典型是法律權威發揮作用的方式。更具有挑戰性的質疑是,“授權外造法”難道不就是違法嗎?違法創制的規范還能叫作法律嗎?為了回應這一質疑,必須區分授權外造法和違法行為。在厘清法律這一概念時,必然借助于法律的理想形態,這一理想形態雖然不會直接作為法律效力的鑒別標準,但在法律效力鑒別標準中會有所體現。“授權外造法”可以被看作法律理想形態于特定情境下在法律鑒別標準中的合理體現,而普通的違法行為則與法律理想形態毫無關系,兩者在概念上有著本質的區別。下面先概要性地闡述法律理想形態及其與法律效力標準的關系,再回到主題,說明“授權外造法”體現了什么樣的法律理想形態,以及其與違法的區別。
第一,法律的理想形態及其在法律效力標準中的體現。法律是人造物的一種。一類事物之所以被歸入“法律”這一概念之下是因為它們具有共同的特征,以區別于其他人造物。人造物分類則要依賴該類事物的理想形態,而不僅僅依賴其事實狀態。法律的事實狀態是由法律實際擁有的特征構成的,包括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由規則組成、存在管理規則體系的官員、法律規范內容不必然符合道德等。但這些特征無法指明法律的獨特性。一個大型強盜集團完全可以擁有上述所有的特征。難道我們要不合理地承認強盜集團發展出來的規則體系也是法律?一旦考慮法律與強盜集團各自的理想形態,我們就會避開上述尷尬的結論。理想形態即該類事物所應該具有的形態。理想形態的強盜仍是追求其不當私利的;而理想形態的法律則服務于其治下民眾的利益。理想形態的差異是法律與強盜集團的指令區分開的關鍵點。
法律的理想形態應該是什么樣的?〔57〕關于如何構造一個理想理論的方法,See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350-354; see A.John Simmons,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38,pp.18-22; see Laura Valentini,On the Apparent Paradox of Ideal Theor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17,No.3,p.346.至少可以形成如下共識:(1)法律的理想形態必然是由一些政治價值所界定的;〔58〕法律實證主義者也承認這一點,see Joseph Raz,On Morality and the Nature of Law,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vol.48,2003,pp.1-3.(2)這些政治價值中既包括程序性價值(如規范間的一致性、規范的穩定性)等,〔59〕朗?富勒只強調了程序性價值在法律理想形態中的地位,但忽視了實質性價值,see Lon 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p.46-91.也包括實質性的價值(如民主、平等、人權等);(3)法律的理想形態將這些價值以獨特的方式統合起來,使其不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種價值,而構成了法律獨有的內在價值,即法治價值。〔60〕這一觀點在德沃金那里有最明確的表述,同前注〔12〕,Dworkin書,第202~206頁。
理想形態并不會成為判定某一個體是否屬于該類事物的標準。該類事物中,不同個體一般會不同程度地符合理想形態,偏離理想形態的個體有時也會被歸入該類事物。〔61〕馬克?墨菲將這一原理在法律概念中的應用概括為弱自然法命題,see Mark Murphy,Nature Law in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9-56.正如壞椅子也是椅子家族的一員。雖然理想形態不會成為判定事物種類身份的充分必要條件,但它會對事物的事實狀態有所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1)人們可以正當地訴諸理想形態來評價、批評人造物的事實狀態;(2)創制、管理人造物的相關人員有理由或者有義務以理想形態為目標提升人造物的事實狀態,其中就包括創制、解釋、接受更加符合理想形態的事物識別標準。以法律為例,無論是法律實證主義者還是自然法學者都承認很多法律都一定程度地偏離了法律的理想形態,但它們仍然是法律;同時也都會訴諸法律的理想形態來批評現實當中的法律,管理法律的官員也背負著壓力去優化法律,包括創制修改法律、更佳地解釋適用法律等。雖然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不可能消失,但理想對現實的壓力不可否認。
掌控法律識別標準的官員也背負著這種理想的壓力,一方面是程序性價值的壓力,如要保證法律更加穩定、一致,具有可預期性;另一方面是實質性價值的壓力,如要竭力使法律符合平等、民主。這兩種理想的壓力也會產生沖突,而且也沒有哪一種可以絕對優于另外一種。“授權外造法”就可以看作是在法律理想形態壓力下所作出的變動,雖然并非所有的變動都是合理的,〔62〕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并不支持所有的“授權外造法”,“授權外造法”的危害也絕對不可低估。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我們結論的否定,因為我們只需要證明授權外行為在某些情形下確實能夠合理地帶來法律就足夠了。但至少其源于對法律理想形態的追求。這也是某些“授權外造法”的正當性依據所在。
第二,“授權外造法” 所體現的法律理想形態及其與違法的區別。以前面的思想實驗為例,該“授權外造法”至少是如下法律理想形態壓力下的產物:(1)法律理想形態中的實質性政治價值:平等與專業性。立法者頒布這一工資法的初衷主要是通過調整工資標準以實現對A的平等保護。而且立法者在過去的立法工作中展現了優良的工作記錄,這是其專業能力的極好證明,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問題上這種專業能力也能得到很好的運用。(2)法律理想形態中的程序性政治價值:保護可預期性。“授權外造法”必須得到其他官員的逐步接受才能夠確立起來,這種造法方式要求官員們大體一致的集體行動。雖然這種造法方式是全新的,但是與秘密法、朝令夕改的法律相比,大體一致地公開行動仍然是明確的、可預期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很多法律理想形態中的政治價值在“授權外造法”中沒有得到充分實現,甚至遭到了損害。例如:這種“突然”造法的模式傷害了可預期性的另外一個方面,即對造法方式可預期性的破壞,沒有訴諸公共輿論討論一定程度上傷及了民主價值,該工資立法是否真的能促進平等也沒有通過輿論辯論來證立。但立法者以及其他接受該規范的官員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考慮了這些對立價值之后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盡管該選擇不必然正確,但這足以說明“授權外立法”是法律理想形態壓力的結果。普通的違法行為根本不是盡力實現法律理想形態的產物,恰恰是對理想的違背與嘲弄。試想某立法官員劣跡斑斑,近日又通過一部圈地“法”,將公共土地據為己有。該“法”雖然得以印制并發行,但其他官員拒不遵循,并公開譴責該法違背公平公正,違背基本的立法程序,堅決否定其法律資格。“授權外造法”與普通違法行為的不同之處也正是其對法律理想形態的真誠尊重。
綜上所述,“授權外造法”是一種獨立的產生法律的方式,符合習慣法存在的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該國官員們可以基于依賴于服從的理由接受該規范的有效性,具有習慣屬性,符合習慣特有規范性標準;該規范是法律理想形態壓力下的產物,具有一定的正當性,這不同于違法行為,其具有法律的屬性。因此習慣法II是可能存在的。
五、結語
基本概念清晰嚴格是一門學科研究規范性的重要標志,習慣法研究也不例外。通行習慣法概念卻缺乏這種嚴格性,它所認定的“習慣法”要么并不是法律,要么是屬于立法、判例法這些其他法律類型,這使得大多數習慣法研究實質上是習慣研究或者對其他法律類型的研究,無法清晰明確地樹立起自己的研究對象。因此習慣法研究應該奠基于習慣法的嚴格概念之上,本文提出的法律權威性標準、獨立于其他法律類型標準和習慣特有規范性標準就是這樣的一種努力。依照此種習慣法的嚴格概念并不會得出“習慣法不存在”的結論,作為立法、判例法等法律類型效力來源的承認規則(習慣法Ⅰ)和通過“授權外造法”方式產生的規范(習慣法Ⅱ)能夠同時滿足上述三個檢驗標準,盡管這些“真正的”習慣法比通行習慣法概念所識別的“習慣法”范圍狹小了很多,但“習慣法是存在的”這一命題得以證立,“習慣法”仍然是個有效的法學概念。這一研究也意味著法理學教材中作為通說的“法的分類”相關內容需要作出相應的增加與調整,以展現更為復雜的理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