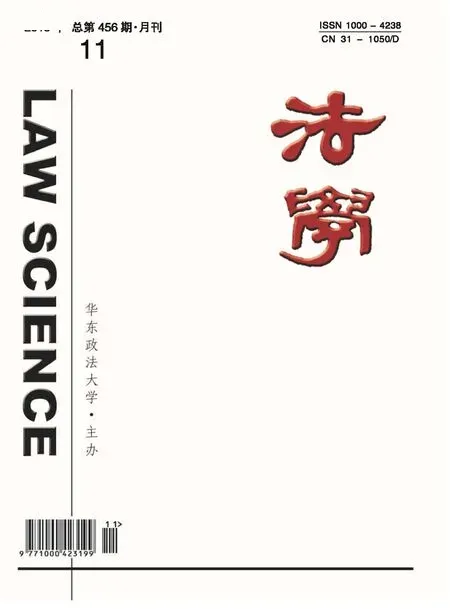論威懾型環境規制中的執法可實現性
●胡 苑
一、問題的引出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伴隨著生態環境的迅速惡化。環境問題一般被認為是企業生產造成的外部不經濟性的外溢。既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企業經營性行為造成的,那么通過立法對企業不利環境的行為進行規訓和懲罰,理應可促使企業改變行為,積極遵守環境法律。我國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素來被認為懲罰力度不足,企業守法成本高而違法成本低。為應對環境危機,改進立法強化環境懲罰力度成為法律共同體的共識。2015年新修訂實施的《環境保護法》通過采納按日計罰等制度具有了嚴刑峻法的特征,被認為能“為深受環境問題困擾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提供最有力環保法律后盾,有助于扭轉伴隨其經濟快速發展而生的生態環境惡化趨勢”。〔1〕《我國通過史上最嚴新環保法 新法于明年1月1日施行》,http://www.npc.gov.cn/huiyi/lfzt/hjbhfxzaca/2014-04/25/content_1861232.htm,2019年1月15日訪問。
按照以上理論預想,新《環境保護法》的實施應能極大改善我國的環境質量狀況。但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17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強懲罰型環境立法的實施效果似乎差強人意。〔2〕2017 年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地級市及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在內的74個城市空氣優良天數比例為72.7%,比2016年還下降了1.5 個百分點;水體質量則有升有降,長江水體質量總體上升而黃河水體質量總體下降;作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723個縣域中,2017年生態環境“變好”的縣域有57個,占7.9%,而“變差”的縣域卻有81個,占11.2%。參見《2017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第9頁、第17~19頁、第38頁。有學者也明確指出,新《環境保護法》規定的按日計罰制度實際執行效果不佳,環境執法與環境立法出現背離。〔3〕參見鄭少華、王慧:《中國環境法治四十年:法律文本、法律實施與未來走向》,《法學》2018年第11期。盡管各界對按日計罰制度的功效寄予厚望,然而其在執法實踐中的使用率卻很低,在環保部門2016年辦理的 22 730 起案件中,按日計罰的適用率不到5%。〔4〕參見胡紅玲:《環境保護按日計罰制度適用反思與完善——以美國環境保護按日連續處罰制度為借鑒》,《政治與法律》2018年第8期。
肩負重大期望的立法變革實效未及預期,引致了后面的一個推斷,即環境執法環節出了問題。無獨有偶,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環境法治——全球首份報告》(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First Global Report)對全球環境法治狀況進行了系統評估,指出自1972 年以來,盡管全球環境法和相關機構蓬勃發展,但執法不力的全球趨勢加劇了環境威脅,全球范圍內的環境法數量增長了38倍,但很多法律并未能真正得到落實。〔5〕參見《全球首部環境法治狀況評估報告發布》,《中國環境報》2019年2月1日第4版。可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環境執法的有效實現都是一個難題。
環境執法緣何難以實現?是法律“傳送帶”模式流程出錯,還是環境執法機構自身的問題,抑或是執法過程的問題?盡管一般觀點認為良好的環境法律實施依賴于立法、執法以及司法各環節的密切配合與互動,但這多個環節之間的環境法律制度是如何互動的我們知之甚少。環境執法被視為自然的政治運作過程中的一種機構履責型自發性行為,所有關于環境執法的問題幾乎都被遮蔽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簡單描述之下,造成的后果便是針對執法不力開藥方時,“除了反復強調‘從嚴’,動員‘真抓實干’,很難找到具體的抓手。”〔6〕戴昕、申欣旺:《規范如何“落地”——法律實施的未來與互聯網平臺治理的現實》,《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4期。為了改進這一境況,本文嘗試梳理出環境執法的基本脈絡,分析其在我國具體條件約束下的可實現性。
二、執法在威懾型環境規制中的核心作用
對環境執法不能的解讀,需要理解環境執法在現代國家規制演變中的形成歷史,以及如何呈現出今日所見之“命令—控制型”威懾形態。在還原執法作為威懾型環境規制中心環節的真實場域下,環境執法幾已成為環境法治實現之主要抓手,反映于現實便是應對環境危機的策略建構于層層推進環境執法的阻嚇懲罰機制之上。而從其效果上看,這種威懾型環境執法模式似乎出現了難以避免的實施困境和執行偏離。
(一)威懾型環境規制的形成
規制(Regulation)一詞作為法學、經濟學及政治學等多學科共同關注的對象,其含義層次豐富且尚無明確界定,本文取其較為常見的一類含義,即規制意味著作為規制主體的政府部門“在建立系統性的監管體制時,所進行的一種資源調控和制度安排。這一調控和安排包含兩個特征: 第一,總是建立在援引和適用一系列社會所肯認的重要規則之上;第二,經常存在一個同時具備監督和執行功能的專門的公共機構。”〔7〕Colin Scott:《作為規制與治理工具的行政許可》,石肖雪譯,《法學研究》2014年第2期;Julia Black,Critical Reflections on Regulation,Australian Jounal of Legal Philosophy,27(1),2002,pp.1-35.
規制的興起伴隨著國家能力的提升并以“行政國家”的面目出現。以美國為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美國歷史上的進步運動時期,也是美國構建行政國家的時期。美國內戰以及戰后重建使聯邦政府的地位和權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業化社會的到來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則帶來了諸多跨越各州邊界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8〕宋雅琴:《美國行政法的歷史演進及其借鑒意義——行政與法互動的視角》,《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年第1期。隨后的經濟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更使得國家深度介入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管控。這個階段規制的興起主要是對市場失靈進行管控,被稱為經濟性規制。
威懾型環境規制的形成內嵌于規制演化的過程中,工業化的深入和全球化使得環境問題成為困擾人類社會發展和存續的重要問題。以美國1970年清潔空氣法立法為發軔,人類社會開啟了所謂的第一代現代環境法的立法和實施過程。在此背景下,中國也逐步形成了相對完備、數量龐大的環境法律體系。諸多文獻都認為中國的環境立法具有舶來性,〔9〕參見李啟家:《“環境法學的發展與改革”研討會紀要》,《清華法治論衡》2015年第1期;柯堅、劉志堅:《我國環境法學研究十年(2008—2017年):熱議題與冷思考》,《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1期。與更早面臨環境危機的發達國家立法路徑一脈相承,以“命令—控制型”的威懾為主要特征。其主要通過執法機關的權力運作,輔之以環境政策的補充,對企業的環境表現予以監管,并對違規企業予以懲罰,借由威懾使得企業在違法和守法中進行權衡,并進而服從環境法律規定。這些以環境保護(此外還有健康和安全)等社會問題為核心的規制被稱為社會性規制。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后經濟性規制出現了放松管制的浪潮,而社會性規制則一直持續強化,并興盛至今。〔10〕參見張紅鳳、楊慧:《規制經濟學沿革的內在邏輯及發展方向》,《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雖然社會性規制領域也出現了探索市場激勵型規制措施的理論和實踐,但從總體上看,要求政府控制污染、防治生態惡化的民意一直在持續形成共識并被強化。
(二)環境法律“傳送帶”中的執法中心化
如果把法治過程主要分為立法和法律的實現這兩個要素的話,那么法律的實現其實是包含行政執法和司法這兩類主要環節。法律“傳送帶”的概念本來是表述在行政國家時期對行政權的控制,要求行政機關不折不扣地實施代議機關制定的法律,〔11〕參見毛瑋:《行政法紅燈和綠燈模式之比較》,《法治論叢》2009年第4期;同前注〔8〕,宋雅琴文;顏昌武、林木子:《行政國家的興起及其合法性危機》,《理論與改革》2018年第2期。但因環境法涉及科學技術等復雜性問題,需要借助“專家知識”,所以在“依‘法’行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依‘裁量’行政”。〔12〕參見王明遠、金峰:《科學不確定性背景下的環境正義——基于轉基因生物安全問題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王明遠教授實際上在文中探討的不僅是“依‘法’行政”發展到“依‘裁量’行政”,更是環境風險行政下應發展到“依‘裁量+參與’行政”,但這主要是從應然角度的探討,目前國內環境法的主流狀態還是依法行政基礎上的依裁量行政。也就是說,國家對環境保護義務之具體化表現為立法權負有義務制定具體且符合環境保護本質的執法規范,而行政權應基于憲法并依據法規執行環境生態保護義務,同時制定環境規劃,司法權則應依法進行司法審查。〔13〕參見陳慈陽:《環境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頁。這是典型環境法“傳送帶”的界定,同時也體現出環境執法權是環境保護規范實現的核心,司法僅是提供補充性的審查功能。環境法誕生的背景和時代,加上環境法自身的特性,使得行政執法而不是司法成為環境法治實現的核心,環境法其實主要就是環境規制(監管)法。
當然,從基本原理上看,行政執法成為環境法治的核心也是有跡可循的。此處筆者想援引Pistor和許成鋼教授提出的“不完備法律理論”(Incomplete Law Theory)來解釋這個問題。所謂“不完備法律”,是指“如果法律中對其規范內容的所有相關適用都有明確的規定,并且在證據成立的情況下能夠得到執行,那么法律就是完備的法律。這就要求法律文本的內容是不言自明的,即每位當事人在無須法律解釋的隱含前提下均同意該項法律的含義。否則,法律就是不完備的。”〔14〕Pistor,K.& Xu,C.,Incomplete Law,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tics,(35),2003,pp.931-1014.法律作為具有穩定性和普適性的規范一定是不完備的,也即法律條文的內容一般不能完全涵蓋每一具體個案的全部情況,也很難準確無差別地傳達給所有當事人,而立法機關立法程序煩瑣而漫長,這樣就存在立法機關的原始立法權之外的剩余立法權的分配問題。
法經濟學中的Becker-Stigler模型認為,這種剩余立法權以及關于法律實施的執法權只需要法庭就夠了,不需要另外的“監管者”,但這是默認法律是完備情形下的推導。〔15〕See K.& Xu,C.,& Pistor,Law Enforcement Under Incomplete Law: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Working Paper No.Te/02/332,http://Sticerd.Lse.Ac.Uk/Dps/Te/Te442.Pdf,2002.而恰是因為法律不完備,才需要監管者等主動執法人員。因為當法律不完備時,其無法有效地阻止違法,且法庭是被動的法律實施方,只能等待當事人提起訴訟,案件進入法庭后才能行使剩余立法權和法律實施權。現實情況是很多受害方出于各種原因不愿提起訴訟,最終導致法律實施不足。在法律不完備的情況下,執法機構的設計和立法及執法權的最優分配就變得至關重要,引入司法之外的法律實施機制,即由監管者主動執法,可以緩解威懾失效的問題。〔16〕同前注〔14〕,Pistor、K.& Xu,C.文;許成鋼:《法律、執法與金融監管——介紹“法律的不完備性”理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1年第5期。一般而言,越是技術變革較快和受社會經濟變化影響的領域,立法權越難以迅速適應社會變動之需,相應地,司法系統的回應也不足,環境規制法正是這樣的一個領域。在整個環境治理中,環境規制及環境執法的優先配置恐怕是環境法首要考慮的內容,這一點不光在我國如此,在主要的工業國家基本上也是如此。環境問題所引發的危害首先是環境容量的減損和環境生態質量的下降,而環境又是靜默的,只有等到足夠多且能負擔司法費用的受害人出現時才會有司法案件出現,進而對立法不足進行彌補。因此,預防性的環境行政執法在很多國家都實際上成了環境法的主要內容,以期通過前端執法的管控,預防嚴重環境損害的出現。
(三)威懾的“去污名化”與執行困境
盡管《環境保護法》的修訂選擇了強化威懾的模式,但從學術討論的角度看,對第一代“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模式的反思與聲討一直不絕于耳。有學者總結了這些批判,即“第一代環境規制過于嚴格、負擔過重和成本高昂;無法激勵污染預防手段的創新,無法明智地進行風險管理;其本質是個大雜燴,以分散的方式關注不同媒介上的不同環境問題,同時忽視了環境和生態系統功能上的相互依賴性;依賴缺乏民主責任的聯邦官僚管理體制。”〔17〕[美]理查德?斯圖爾特:《環境規制的新時代》,載王慧編譯:《美國環境法的改革:規制效率與有效執行》,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也有學者認為,“當前的環境執法以威懾(嚇阻)理論為基礎,主張通過提高違法成本來改變企業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方式,進而對企業的違法行為產生威懾”,環境執法應“對威懾型執法的內在邏輯進行規范性和實踐性反思,將考察的視角由外而內從執法主體轉向執法對象,從而帶來執法模式的轉型和變革。”〔18〕何香柏:《我國威懾型環境執法困境的破解——基于觀念和機制的分析》,《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還有更多的學者撰寫了關于第二代環境法、第三代環境規制以及環境規制的反身法趨向的論述,都對“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進行了深刻檢討并就規制改革進行了歸納和設想。〔19〕這些文獻包括但不限于郭武:《論中國第二代環境法的形成和發展趨勢》,《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譚冰霖:《論第三代環境規制》,《現代法學》2018年第1期;譚冰霖:《環境規制的反身法路向》,《中外法學》2016年第6期。
無論我們意識到與否,盡管威懾是一個讓人感覺不那么愉悅的詞,但行為規則的存在,包括作為正式規則的法律和作為非正式規則的風俗和信仰等,其背后必然包含“一個恒常固定的懲罰結構”,沒有懲罰存在便沒有規則存在。〔20〕參見桑本謙:《法律解釋的困境》,《法學研究》2004年第5期。只不過這種懲罰有的時候過于輕微,比如不過是周圍人的小聲非議,以至于經常被人所忽略。現代國家的刑法用刑事法庭和監禁乃至死刑取代了初民社會的血親復仇。即便是在威懾力最不顯見的民法領域,阿克塞爾羅德發現的“互惠利他”模型也讓我們領略到“以牙還牙”的合作型競爭策略能夠最后勝出的核心還是在于保有了對合作方潛在行使懲罰的能力。〔21〕參見[美] 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合作的進化》修訂版,吳堅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從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到福柯的《規訓與懲罰》,雖然懲罰的形式越來越人道和文明,但人類社會越來越高規格秩序的背后無不隱現著更大規模的威懾逐步取代小群體威懾的過程。
是故,環境規制改善的核心,未必是威懾型環境執法有多么面目可憎從而應該拋棄懲罰。正如人們對警察抓獲罪犯從來都是歡欣鼓舞,威懾的存在本身并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保持秩序以促成更多的合作。整個法律大廈最初都是慢慢演化于威懾與懲罰機制之上,包括環境法在內的法律部門在可見的未來還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這套機制。〔22〕國外學者近期的一項研究認為,“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至少解釋了1990年至2008年間美國企業污染中可觀察污染排放下降的75%。See Shapiro,J.S.,& Walker,R.,Why Is Pollution from U.S.Manufacturing Declining? The Rol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Productivity,and Trade,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 (2017).那么問題究竟出在何處?有學者指出,環境監管中的規范執行始終會出現偏離效應,“在功能主義的立場下”,偏離“是行政機關為了解決諸多矛盾而對規范執行進行系統性調整的結果”,此類偏離既可能改善環境監管,也可能使得環境監管失靈,需要進行“環境監管改革將規范執行的調整機制納入到法律調整的范圍內”。〔23〕曹煒:《環境監管中的“規范執行偏離效應”研究》,《中國法學》2018年第6期。該研究對環境執法不力的情況作出了頗有意義的解讀,并提出了進行監管改革、強化問責機制等來對環境規制進行控制和糾偏。不過,若執法偏離是不能避免的,僅靠執法環節的改進能否真正糾正呢?基于此,本文擬進一步分析環境規制執法偏離背后的具體原因,并就可能的改進方向提出淺見。
三、威懾型環境規制執法實現維度的考察
需要考慮的是,環境規制執法偏離所指向的具體對象是環境規制體系中的規制內容和目標,也即被認為能夠實現環境保護的立法以及基于立法演繹的規制政策。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才是整個環境規制體系真正要實現的目標,立法內容以及規制政策本身并不是目標而是實現目標的具體方案。立基于此,雖然在客觀執法實力約束下的傳統環境執法短期內難有顯效,但并不意味環境執法必然無法改善。要探求改進路徑,首先還需要找到執法不能的根本原因。
(一)環境執法實現維度之形態分析
關于環境執法的困境,執法經濟學的研究或許能為推進分析提供些許思路。Becker在其《犯罪與刑罰:一個經濟學的進路》一文中根據威懾假說指出,法律的威懾力并不是單一維度的考量,而是懲罰嚴厲程度和懲罰概率等多個因素的乘積,懲罰概率的增加通常能夠減少罪行,富有司法經驗的人通常會認為,懲罰概率遠比懲罰的嚴厲程度更能影響到違法行為的數量。〔24〕See Becker & Gary,S.,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6(2) ,1968,pp.169-217.Becker模型中還設定了一個參數“其他影響因素”,但因這個參數在每個具體個案中都具有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兜底但不關鍵的參數,故不納入討論。提高制裁的嚴厲程度往往被視為規制環境違法行為的貌似有吸引力的解決方案,然而更嚴厲的懲罰并非靈丹妙藥。無論制裁多么嚴厲,如果抓獲的可能性為零,則環境違法的成本也為零。〔25〕See Bishop,p.,Criminal Law as a Preventative Too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mpliance Versus Deterrence,Northern Ireland Legal Quarterly,60(3),2009,pp.279-304.執法環節擁有的自由裁量權的上限和下限由成文法限定,懲罰的嚴厲程度主要由立法環節決定,環境保護法雖提高了懲罰力度但未能實現較好效果,問題是出在了懲罰概率上。
歸根結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表述背后的隱含意味是環境執法部門能執法而不執法。若把關注的重心放到執法概率上,則更可能看到現實中環境執法部門面臨的條件約束。作為環境規制者的生態環保部門,只要在科層體系中相對靠近基層,其履責一般依賴于兩個基本的條件,一個是執法動因,另一個是執法實力。考慮到主觀執法動因與客觀執法實力的不同配合,環境執法實現維度形態的現實形態可分為四種基本情況:一是主觀上有執法動因,客觀上有執法實力,這是環境執法最為理想的一種狀態,一般立法中所默認的也是這樣一種狀態;二是主觀上沒有執法動因,但客觀上有執法實力,這一類也是通常國內所詬病的執法不嚴的主要類型;三是主觀上有執法動因,但客觀上無執法實力,如重視環境保護但地方經濟比較差,環保機構沒有相應預算即屬于此種情況;四是主觀上無執法動因,客觀上無執法實力,這是環境執法最難實現的一種狀態。
只有執法動因和執法實力兼備時,才可能實現較理想的執法結果。立法環節處于前端,因遠離執法階段產生了抽象性的抽離,很難考慮到執法動因和執法實力的現實欠缺均會造成執法困境,正如上述四類形態中三類情況都會出現執法困難。且從目前對環境執法難問題的理解上看,主流的思路會歸咎于地方保護主義、地方懶政、官員腐化及規制俘獲等原因,〔26〕參見余光輝、陳亮:《論我國環境執法機制的完善——從規制俘獲的視角》,《法律科學》2010年第5期;侯佳儒、王倩:《突破環境執法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環境經濟》2013年第Z1期;敖平富、秦昌波、巨文慧:《環境執法在環保垂改中的基本路徑與主要任務》,《中國環境管理》2016年第6期。也即囿于地方環境執法部門主觀上不愿意執法之角度去理解,而對執法所需要保障的執法實力未作深入的理解。若將主客觀因素混同在一起的話,就可能會對環境執法困境之根源產生誤解,從而做出一系列有偏差的應對。
(二)環境執法動因困境之分析
在分析威懾型環境規制中的執法機構為何會缺乏執法動因時,筆者并不準備把腐敗及規制俘獲這些非法的情況作為主要原因來進行分析,這些非法的狀態肯定會存在,但其在當前中國環境執法動因困境中并非主流(后文關于地方缺乏環境執法意愿的特殊性結構會對此問題加以解釋)。
1.多重委托代理機制的損耗
如前所述,環境規制是在行政國家興起的背景下演繹而生的,從侵害產生后司法階段的侵權責任為主提前到企業生產階段預防性的行政責任為主,有其形成的特定歷史條件。無論是從環境信托理論,還是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公眾作為納稅人普遍對國家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這一公共產品上提出了諸多期待。但在政府履責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多重“委托—代理”機制下的損耗。〔27〕參見劉有貴、蔣年云:《委托代理理論述評》,《學術界》2006年第1期。就我國具體情況而言,第一重委托代理是需求良好生存環境的公眾對政府的初級委托授權,由政府來代為提供環境治理;第二重委托代理出現在作為整體上接受公眾委托的中央政府將職責分發到各個地方政府的過程;第三重委托代理是各地方的省級人民政府及其環保部門又將環境治理任務向市級派發,由市級以及市派駐縣級的基層執法單位作為代理人來履責的過程。而環境執法的具體落實還需要基層執法人員針對行政相對人執法,從基層環境機構將其職責分由具體工作人員執行的過程看,至少已經構成了第四重委托代理關系。
在委托代理理論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存在著利益上的不一致,同時代理人因直接處理受托事務相比委托人有更多的信息優勢,委托人雖名義上可管控代理人的行為,但因難以觀察到代理人執行事務的努力程度而在事實上缺乏控制權。“體系中的組成機構具有顯著的自主性,它們各自擁有組織目標,容易在執法過程中產生摩擦和分歧。”〔28〕劉楊:《執法能力的損耗與重建——以基層食藥監執法為經驗樣本》,《法學研究》2019年第1期。在多層的委托代理的情況下,良好環境治理的意愿在一層一層的委托代理體制中不斷出現科層損耗。此外,米塞斯在《人的行為》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只存在獨立個體的個人行為,并不存在所謂的集體組織行為。〔29〕參見[奧]路德維希?米塞斯:《人的行為》,夏道平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5頁。環境保護部門作為一個執行組織體,其職責任務的完成實際上需借助每一個執法人員,而具體執法者的行為不僅受其自身動機偏好的指引,還因直接與執法對象反復博弈而產生了社會性損耗。“由于違法過剩的存在,當國家法律在街頭官僚的制度現實中演化成案件指標的行政管理時,基層執法者不僅會出現‘目標替換’,即以案件指標作為工作重心,而且還會出現‘路徑依賴’,即選擇最簡便、最順手的違法形態進行查處。這樣兩種手法無疑大大抵消了國家法律賦予執法者最正式的工作任務。”〔30〕王波:《執法過程的性質:法律在一個城市工商所的現實運作》,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頁。在科層損耗和社會損耗的雙重影響下,實際上的環境執法者并沒有非常強的動因履責,尤其是在環境立法本身也存在不足從而未必能真實反映委托人意志的情況下,這在現實中就呈現為環境執法機構在實際執法中經常會缺乏執法意愿。
2.中國“政府幫助型市場”結構的制約
目前普遍的觀點認為,環境執法不力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保護主義,如我國不少地方曾出現過以“紅頭文件”的方式免除一切環境審查手續吸引企業進駐各種“開發區”,甚至“環評”和“三同時”驗收也成為企業污染的“保護傘”的情況。〔31〕參見李愛年、劉翱:《環境執法生態化:生態文明建設的執法機制創新》,《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3期。出現這么強的地方保護主義,除了腐敗、規制俘獲等非常規性的原因外,還在于我國有著非常特殊的地方治理結構安排。借鑒經濟學中企業組織最優邊界理論,有學者提出了介乎于韋伯官僚科層制和純粹市場外包制之間的行政發包制理論。〔32〕參見周黎安:《行政發包制》,《社會》2014年第6期。我國作為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區域差異明顯的大國,管理鏈條長而復雜,要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組織架構確實較難,正是依靠非常特殊的行政發包制體制完成了“行政權分配、經濟激勵和內部控制”機制的有效整合。〔33〕參見周黎安:《行政發包制:一種混合治理形態》,《文化縱橫》2015年第1期。
行政發包制對中國經濟的奇跡提供了較為有效的解釋。〔34〕參見周黎安:《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頁。在此基礎上,學者還進一步提煉出了我國“官場+市場”〔35〕為避免表述可能招致的歧義,本文將其替換為“政府幫助型市場”的表述。相關內容可參見周黎安:《“官場+市場”與中國增長故事》,《社會》2018年第2期。的結構,在縱向行政發包和橫向政治晉升錦標賽的基礎上,這一結構保證了地方官員有很強的動力幫助地方企業的發展,“在最積極的意義上實現了轄區內政治企業家與民間企業家精神的結合”。作為一種增長機制,“官場+市場”它不一定保證創造最好的結果,但在總體上可以避免最壞的結果,中國正是借助該模式地方政府實現了從潛在的“掠奪之手”到“幫助之手”的驚險跳躍。〔36〕同上注。正因為這種特殊的激勵結構,筆者認為影響環境執法的因素中腐敗及規制俘獲等不是主要原因。形成地方保護的主要原因還是處于競爭中的官員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追求,而短期內企業的經濟表現和環境治理具有一定的負向相關性。從此角度言,地方保護對環境治理的影響很難被完全界定為非法的因素,但目前主流觀點關于執法不力的落腳點還是一邊倒地批判地方保護主義。如果地方保護主義的形成根植于中國特殊的經濟增長結構,那么就需要意識到環境規制在我國的天命很可能就是要“戴著鐐銬跳舞”。
(三)環境執法實力困境之分析
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像中國這樣體量龐大而必須有多重委托代理架構,因此環境執法的意愿可能在某些國家并不構成核心障礙。而從全球首份環境法治報告亦可知,環境執法難在全球是普遍存在的,這很可能預示著客觀方面的環境執法實力缺乏是一個更根本性的原因。
1.公共執法專業化的高資源需求
現代意義上的行政執法是有了國家后才出現的,其背后的支撐條件是工業革命多次深化以及城市化下的分工細化所帶來的經濟空前發展。生產力的大幅提高和生存資源的極大豐富使得行政國家下的專業化公共執法發展起來,從警察系統到現代社會工商、稅務、交通、環境、安全等公共性事務都歸于政府規制,使得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已經對公共執法習以為常。然而“回顧歷史,在初民社會和古代社會,法律幾乎全由私人執行。復仇是一種典型的私人執法。在古希臘的雅典,不僅侵權和違約,而且犯罪皆由私人提起訴訟。數個世紀以來,歐洲許多國家存在私人執法模式。”〔37〕徐昕:《法律的私人執行》,《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威懾型環境規制下的環境執法本質是由國家財政收入供養的專業環境執法團隊取代了環境領域的私人執法,因已形成路徑依賴而鮮被質疑和反思,在既有習慣上衍生出來的環境公共執法可能會忽略這個領域的一些特殊性特征。
專業化的公共執法雖具有規模優勢、技術優勢,同時也能避免科斯所揭示的受污染人群之間合作交易成本過高從而阻卻私人執法行動的問題,〔38〕試想若環保部門不介入管控企業污染,則受污染的周圍居民要自行聯合起來去找工廠協商,大量群體之間協商合作有高昂的交易成本,加上“搭便車”效應,則此類行動很可能無法發起。See 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1960,pp.1-44.但整個公共執法系統與私人執法系統相比有其自身的劣勢,即成本高昂。相對而言,私人執法中的私人同時也是執法實力所需資源的自我供給者,其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生產性活動,執法成本是內部化的。若執法的收益不足以彌補執法的損失,則私方個體在衡量后便不會采取執法行動。環境公共執法體系既因成本無法內部化,也因環境的靜默性而使得反饋基本上不存在,這會導致環境公共執法體系在不需要大力監管的問題上投入極大的資源,而在往往需要高強度監管的領域能夠投入的資源又過少,〔39〕See Wendy P.Feiner,Just When You Thought It Was Safe to Go Back in the Water: A Guide to Complying with the 1996 Amendments to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Environmental Lawyer,Vol.4,Issue 1,1997,pp.193-224.從而導致環境規制經常是要么無效要么過度的狀態,〔40〕See Davies,J.Clarence and Jan Mazurek,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Evaluating the System,Washington,D.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998),p.269.加之執法資源在各層級之間的損耗,所以分外昂貴。此外,環境執法的技術性需求會讓本已高昂的成本雪上加霜。環境執法要借助多樣的儀器設備和充分的檢測過程,技術問題的復雜性會使得環境執法較之其他公共執法領域更缺乏執法實力。
2.中國財政分權下的硬預算約束
我國現實中出現的環境執法實力困境,還有本土性的特殊原因。前述“行政發包制”即體現著中國財政分權的本質是經濟分權和政治集權的有機結合。分稅制改革后,我國整體上出現了地方財政收入緊張、地方財權無法匹配地方事權的情況。有學者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我國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問題具有關聯性,具體表現為:“其一,財政分權改變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和模式,降低了環境治理的投入,并最終影響環境污染水平;其二,財政分權對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在環境方面的投入強度和方向也形成較大的制約;其三,財政分權明顯改變了區域產業發展結構,帶動了高污染產業的發展,加劇了污染物的排放。”〔41〕張欣怡:《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行為與環境污染問題研究——基于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15年第3期。由于各地環境類公共產品皆由地方財政負擔,環境執法人員裝備配備以及執法活動的經費面臨與其他領域的開支進行競爭的情況,所以筆者將其稱為中國財政分權下的硬預算約束問題。
硬預算約束一詞本來是相對于軟預算約束〔42〕軟預算約束是指“如果預算制度無法對政府行為形成強有力的約束力,地方政府能夠通過多種方式輕易地突破預算來設置自身的發展目標或實施政策性工程。”余錦亮、盧洪友:《分類預算、軟約束與財政努力程度——對地方政府收支行為激勵效應的一個檢驗》,《經濟科學》2018年第4期。提出的。軟預算約束會引發資金浪費、資源無效率配置和地方債務問題,〔43〕參見冉富強:《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困境解決的法治機制》,《當代法學》2014年第3期。所以一直被認為需要變成硬預算約束。我國《預算法》出臺后,地方政府的各項預算支出也正在變得越來越“硬”。硬預算約束本來是好事,但對于地方環境執法資源事實上則意味著短期內更緊缺經費總量下的更激烈的競爭。由于環境危害具有隱蔽性和累積性,短期不易顯現,環境執法在有限財政資源的分配中作為非緊急性的任務可能會被劣后排序,從而事實上面臨著硬預算約束下更大的影響。
四、“不完備法律”理論下的環境執法實現增進
回到“不完備法律”理論,如果說傳統領域的法律具有不完備特征,那么環境規制所涉及的法律則尤其不完備。有學者對我國多個地方環境立法及政府規章進行實證研究的結果是“沒有證據支持地方環保立法能夠有效地改善當地環境質量”,〔44〕包群、邵敏、楊大利:《環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嗎?》,《經濟研究》2013年第12期。這也支持了筆者的觀點。“不完備法律”理論對于立法的謹慎立場和動態一體化看待立法、執法與司法環節之間關聯性的思路,頗值借鑒。威懾型環境規制在污染控制的初始階段較為有效,在此階段“命令—控制型”體系的低效會被初步減排的低成本所掩蓋。〔45〕同前注〔17〕,理查德?斯圖爾特文,第129~133頁。由于法律不完備,傳統的立法結構并不適合在環境規制領域進一步擴張,更應該在確定一個基準執法線的情況下賦予執法部門更多的剩余立法權,同時寬泛性理解“執法”,將通過訴訟實現的法律實施也納入“執法”的考量中,重視司法階段的剩余立法權。
(一)現有改進措施的效果分析
緊隨《環境保護法》的修訂,中國為應對環境危機推行了一系列的組合拳措施。黨政同責、環境約談、環境督察與中央以及地方層級環保機構改革等一系列不同尋常的強力型機制在相近的時間點出臺,密集應對威懾型環境規制中的執法難題。那么,這些措施能否及時促進環境法律的徹底實施,并一改環境執法軟弱的頑疾?回歸到上述環境執法需要主觀執法動因和客觀執法實力兼備的判斷,比照之后可大致對應分析出現有對策的實施效果。
在現有的改進措施中,黨政同責、環境約談、環境督察基本上還是通過問責懲處機制以增強環保部門的執法意愿,僅有中央及地方層級環保機構改革稍微涉及執法實力的提升。中央層級的環保機構改革主要是將涉及同類環境要素或者生態系統的不同部門監管事項合并,〔46〕參見《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http://www.gov.cn/xinwen/2018-03/17/content_5275116.htm,2019年1月6日訪問。地方層級的環保機構改革主要是將基層環境質量監測及執法部門上提一個行政級別。〔47〕參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16-09/22/content_5110853.htm,2019年1月6日訪問。無論中央還是地方的環保機構改革都并不直接增加環境執法預算,而是通過部門職能整合及降低科層損耗的方式間接提高環境執法預算的使用效率。但從總體上看,環保機構改革的本身著力點還是強化環保部門的執法動因。
一般而言,執法實力所依賴的資金資源短期內很難發生大幅的增長,如果強化的因素都是主觀上的環保機構執法意愿,而客觀的執法資源配套未能跟上,那么將會發生怎樣的結果?首先有可能發生的是重點時段內的壓力型執法,因屬于嚴打期所以短暫調用其他領域的資源在環保領域運動式執行,等關注期過后隨著調配來的執法資源歸位,執法實力也回歸正常狀態,隨后環境違法“死灰復燃”;〔48〕大量新聞報道中此類現象比比皆是。參見《嚴防“散亂污”企業死灰復燃》,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7-08/17/c_129683119.htm,2019 年 1月 10 日訪問;《污染企業死灰復燃?當地:已責令不得擅自恢復生產》,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7/0721/c178291-29419439.html,2019 年 1 月 10 日訪問。或者,如果資源競爭較大很難調用,執法實力完全匹配不了執法要求,那么或會出現虛假執法,或會出現過度執法。虛假執法是指執法者沒有相應實力執法時只能靠編造執法內容或虛填表格執法等方式滿足上級的嚴抓要求,“規范化要求與執法現實之間的差異并非較高與較低現實的程度差別,而近乎目標與實際之間的根本背離。”〔49〕同前注〔30〕,王波書,第48頁。過度執法是指因執法實力不足,難以鑒別環境違法者和守法者,于是在上級壓力下“一禁了之”的執法方式。如果說我國前段時間因為環保約談和環保督察各地出現的環境執法“一刀切”現象不正常,則隨后糾偏出現的被關停企業全部恢復生產也同樣是一種不正常現象,〔50〕參見《關停企業復產 中小企業終于看到了希望!1500多家躺槍企業恢復生產!》,http://www.sohu.com/a/190702589_99898799,2019 年 1 月 10 日訪問。這正好說明了環境執法部門不具備精細執法的足夠實力。
現有的措施延續了威懾理論,但其強化對規制者問責懲罰力度的同時對環境規制執法不能的本質欠缺考量。環境規制執法領域下猛藥造成的執法動因極強而缺乏配套執法實力,雖多少會有一定的執法改進,但同時也會批量制造短期執法、虛假執法和過度執法,這不僅浪費了緊缺的執法資源,還使得“威懾失靈”與“威懾過度”同時出現,而這絕非強化規制的初衷。所以我們面臨的問題其實是,如果環境執法實力無法很快提升,并與環境執法動因同步配套的情況下,如何改進環境執法效果?
(二)執法階段的“剩余立法權”重塑:威懾型執法轉向柔性執法
如前所述,在當前的條件約束下,威懾型環境規制下準確懲罰的幾率難以迅速提升,加上環境規制之特性,“命令—控制型”環境執法的成本太高而在事實上無法實現。威懾機制的本質是為了建立秩序,改進的方案并不是不要威懾,而是應看到公共執法有其最優威懾邊際,〔51〕關于最優執法理論,同前注〔24〕,Becker、Gary,S.文;George J.Stigler,The Optimum Enforcement of Law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78),1970,pp.526-536.超過邊際投入激增而結果要么是威懾失靈、要么是威懾過度。“當法律本身非優化時,嚴格執法產生的成本甚至可能超過違法給社會帶來的損失,使執法得不償失,降低社會福利。”〔52〕楊曉維、張云輝:《從威懾到最優執法理論:經濟學的視角》,《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12期。執法不嚴,有時候不過是客觀制約下的“無法嚴”和“不能嚴”。應在保留現有立法提供的威懾的基礎上,剩余的執法力量轉向柔性執法。目前展開的地方環保機構垂改,將市一級的監測站收歸省級并專門負責環境質量監測,這為執法階段設置環保底線提供了基礎。國家層級立法可在嚴管并向社會公眾公開監測數據的基礎上,規定各地方環境質量不下降或每年逐級改善前提下的概括性授權,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考慮各地的環境規制政策和進行試驗試點,以期在實踐中演化出能調和多方正當性利益沖突的“最大福利下的最小成本”之規則。
柔性執法“亦稱非強制行政,是指行政主體在行政活動中針對相對人所實施的不帶命令性或強制性的行為”,“主要包括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獎勵、行政調解、行政給付和行政信息服務等非強制權力手段。”〔53〕劉福元:《城管柔性執法:非強制框架下的效益考慮與路徑選擇》,《中國法學》2018年第3期。環境柔性執法的目的是為了實際執法中留出供環保部門、企業、行業組織、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公眾等互動博弈的空間,公私合作有時“可跳出行政機關的日常工作,促成既有利于環境,又容易理解,被監管者也容易接受的結果。”〔54〕Isaac Cheng:《美國環境執法:一個實踐者的角度》,《法律適用》2014年第4期。激勵性監管、協商性監管、行政指導和自我監管等柔性執法方式都是“更多地尊重被監管主體的意愿,采用柔性手段引導被監管主體自愿做出某種行為。”〔55〕蔣建湘、李沫:《治理理念下的柔性監管論》,《法學》2013年第10期。這類以合作為特征的執法方法,較多地運用了信息機制和正向激勵機制來引導企業環境守法,其實質是埃里克森所言的“自我實施的個人倫理、雙方合約、非正式實施的規范、組織機構的控制和法律”等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社會控制系統的綜合作用。〔56〕參見[美]羅伯特?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頁。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產生了不同于公共執法的間接威懾力,是一種低成本的秩序生成力量。
美國早已出現了對威懾型環境規制的反思和修正,作為最早大規模適用市場激勵性機制如“泡泡計劃”進行排污權交易的國家,其對生態標簽、信息披露以及環境審計管理等自律性制度也多有應用,〔57〕同前注〔17〕,理查德?斯圖爾特文,第14~107頁。聯邦環保署還開展過“環境領導者計劃”(Environmental Leader Program)和“明星軌跡計劃”(Star Track)等監管合作項目,所有參加項目的企業都需要進行環境合規審計并適用環境管理體系,進行信息公開,作為回報,參加企業在相應審計中發現的違法行為只要及時改正便可不受罰款處罰。試點表明,規制機構與受規制企業之間的密切合作可以提高環境執法效果,合作監管通過促進雙方找到環境規制中的共同點,增強了規制系統的合法性。〔58〕See David B.Spence,Can the Second Generation Learn from the First-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Regulatory Reform,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29,Issue 1,2001,pp.205-222.
我國地方執法中也早有柔性執法之實踐。廣東省貴嶼鎮作為廢舊電子廢物非法拆解小作坊的集聚地,曾被譽為世界“最毒之地”。〔59〕See Manwen Zhang,Guixian Feng,Wenhua Yin,Bing Xie,Mingzhong Ren,Zhengcheng Xu,Sukun Zhang,Zongwei Cai,Airborne PCDD/Fs in Two E-Waste Recycling Regions After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Vol.62,2017,pp.3-10.當地政府采取了幫助式執法的模式,通過設立循環經濟產業園,協調原上千家零散拆解戶組成企業全部遷入園區,既兼顧了當地群眾生計也實現了環境要求。〔60〕參見《“電子垃圾之都”的綠色蛻變》,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7-08/15/content_7660317.htm,2019年1月15日訪問。而按照法律嚴格實施這些小作坊本來應該被全部取締,這種“有法必依”未必合理,也不具有地方合法性。此外,正如環境規制的重點不在于懲罰企業,而在于強化企業的環境管理,〔61〕See Coglianese,C.,The Manageri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17),2008,pp.54-74.我國試點的企業環境監督員制度巧妙地實現了環境規制與企業管理的結合。〔62〕參見鄭少華:《論企業環境監督員的法律地位》,《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10期。各地推行的環境信用等制度也體現了環境規制改進的努力。我國“政府幫助型市場”結構和財政分權等影響從嚴執法的特殊約束,以及黨政體制下強調“執法為民”的群眾工作屬性,〔63〕參見陳柏峰:《黨政體制如何塑造基層執法》,《法學研究》2017年第4期。可能并不適合在沒有執法資源增長下的進一步“從嚴執法”,反而有利于柔性執法下剩余立法權的映現和重構。
(三)司法階段的“剩余立法權”重塑:環境執法的謙抑與環境司法的補足
一般而言,廣義的執法也包括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定職權范圍和程序將法律規范適用于現實的社會關系之活動”,“私人訴訟作為執法手段在大陸法看來也許有些奇怪”,但私人提起訴訟,從實現的效果上看,確實起到了“臨時替代行政機關履行責任的作用”。〔64〕同前注〔37〕,徐昕文。法律經濟學一直將司法過程作為執法的主要環節,不完備法律理論也是在有機一體的邏輯中考慮行政執法和司法環節之間剩余立法權的分配。〔65〕同前注〔14〕,Pistor、K.& Xu,C.文。“表面化的形式主義分析難以描述立法運作及其與法庭之間關系的復雜性,當代議機關在制定涉及社會和經濟的基本法律時不愿或者不能詳盡立法以明確政策方向時,不管這是否屬于立法缺位,其結果都是給案件中的法官留下了廣泛的自由裁量權。”〔66〕Chayes,A.,The Role of the Judge in Public Law Litigation,Harvard Law Review,89(7),1976,pp.1281-1316.即便在我國這種偏大陸法系的國家,法官在法庭審判中通過對法律的闡釋實際上行使了“剩余立法權”,“兩高”的司法解釋更是集中體現了對法條遺漏進行補充和修正的 “剩余立法權”。當我們把司法階段也納入提高法律執行度的考量范圍時,環境規制下的行政執法困難自然可以期待更多地發揮司法的能動性。
環境法律法規的執行,尤其是作為規制法的執行,其實施主要依賴環保部門的主動作為,而環保部門的行動又受到執法動因和執法實力的雙重約束。“民事責任則不同,民事責任賦予了個體主動的權利,基于個人愛惜自身及自己財產的本能,民事責任有很強的發動機制。私人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較之于行政機關,往往會更加主動地通過各種途徑尋求救濟,能夠使民事責任落到實處。”〔67〕胡苑、鄭少華:《從威權管制到社會治理——關于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的幾點思考》,《現代法學》2010年第6期。較為有趣的是,盡管我們把司法看作被動的過程,但發起訴訟進入司法程序的私主體是有行為動因的;盡管作為環境規制主體的環保部門是主動執法者,但具體執法的個體則實際上不一定有行為動因。之前由于法律不完備使得執法占優的原因,在威懾達到一個臨界點后,尤其是在輔之以社會條件和技術條件發展的情況下,可能重新指向司法偏好。
司法過程中法官能夠作為第三方仔細衡量各方當事人所面臨糾紛背后的真實利益沖突,社會發展脈絡中的那些不能簡單用對錯判定的矛盾也會不可避免地進入法院的視野中來。環境法所涉問題復雜,司法的優勢能夠使得環境法律的實現更具有正當性和符合歷史進程。以“謝某某訴江蘇天楹賽特環保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大氣污染侵權案”〔68〕參見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通中民終字第0700號民事判決書。為例,“我國《侵權責任法》及先前的相關司法解釋對于環境侵權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均持完全倒置的立場,但這種舉證責任分配方式遭到了司法實務的普遍抵制。”〔69〕王倩:《環境侵權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闡釋》,《法學》2017年第4期。社會發展導致了法律在提供確定性的同時,也需要保護不斷增長和差異化的群體及個體利益,從而引發了越來越具體和嚴格的監管,而吊詭的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具體立法之所以會缺乏合法性并且更難以實施,正是因為它無法捍衛所有不同的利益,所以這似乎是一個基本的悖論。”〔70〕Rooij B.V.,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Regular Enforcement and Political Campaigns,Development &Change,37(1),2010,pp.57-74.通過剩余立法權的行使,司法相對來講更有能力彌合和調停不同利益,即便裁判模式下的個案會出現偏差,但無數個案件延續起來的結果應能夠求得多方利益沖突下的最優解。
社會有機體似乎也在自我演化以調和現實中難以解決的諸多涉環境沖突,典型體現便是近年來我國環境司法的迅猛發展,顯示出司法補足之能動性。自2007年貴陽市首設環保法庭以來,我國開展了環境司法專門化的探索之路,出臺了一系列關于公益訴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政策法規。至2018年全國法院共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合議庭或巡回法庭1 000個,2013年至2017年各級法院依法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1.1萬件、檢察機關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1 383件、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252件。〔71〕參見《環境資源審判: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84832.html,2019年1月18日訪問。傳統上在環境規制階段由政府行政執法處理的案件正越來越多地從執法環節走入法庭審理,這一方面反映了環境執法力所不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較之于硬性適用剛性立法下的環境規制執法,由司法來解決利益沖突下的復雜環境案件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也更能促進法律所追求秩序的真正實現。
五、結語
環境執法困難是個時時在談而刻刻存在的問題,這提醒關注者應尋求真實癥結之所在。隨著經濟發展、公眾環境意識的提升、產業變遷、執法技術手段還有信息監管手段的進步,基于威懾機制的環境規制執法效果也會隨之漸進性改進。但環境的迅速惡化激發了社會各界對盡快解決問題的期待,面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我國已經作出了從嚴治理的立法回應,然而立法并未如想象中是問題的答案,反而似乎只是問題的起點。“人們通常認為法律的執行是理所當然的,并將任何違反正式法律的行為視為該法律的部分失敗”,〔72〕Becker,Gary S.,Stigler,George J.,Law 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3,Issue 1,1974,pp.1-18.這種直覺化的思路掩蓋了環境執法現實中面臨困難的客觀狀況。
基于環境執法在“行政國家”時代環境規制中的中心地位,應予以重視并探索改進環境執法效果。但環境執法在我國“一管就死,一放就亂”,說明環境問題具有復雜性,不能簡單依靠傳統的強化威懾規制的“單行道加速”模式。對執行法律所需條件進行系統分析時,可以看到環境執法受到執法機構的執法動因和執法實力的雙重約束,這是各國環境執法普遍困難的原因,除此之外,我國的體制還產生了不利于威懾型環境執法推進的特殊約束。盡管威懾型環境規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支撐規制運轉的資源有限,應區分良好的意愿與事實的法律效果,承認客觀約束的存在并將其作為制度改進的前提,而不是視若無睹地蠻干。在一個需求無限而資源有限的世界,少一些理想和法條至上主義,多一些法理至上主義,在立法和規制克制中容許在現實中演化出低成本的環境法治實現規則,或許是環境執法困境下的一個可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