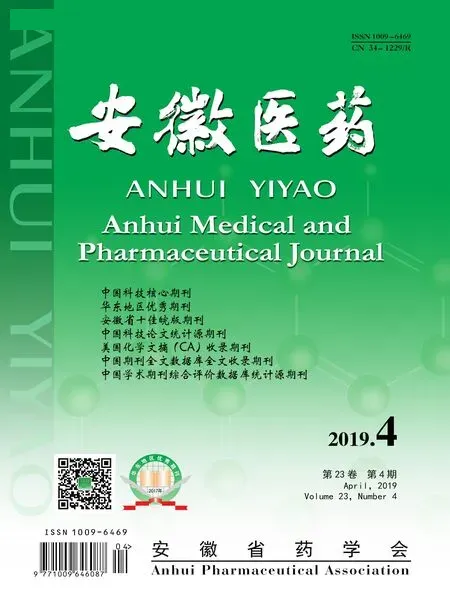兒童發育性髖關節脫位的治療進展
盧紅信,陳笑天,肖玉周
發育性髖關節脫位(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又稱作發育性髖關節發育不良,是一種較為常見的小兒矯形外科疾病。DDH系指生長過程中,因先天或后天因素[1]而導致的股骨頭與髖臼喪失正常的解剖關系,進而形成髖關節一系列包括骨性、軟骨性以及軟組織等病理改變的疾病[2]。該病在兒童中發病率較高,常見于女性兒童,男女比例約為1∶4[3]。伴隨著病兒年齡的增長,DDH的癥狀也呈現出動態性和進展性變化[4]。現在公認為,早診斷、早治療意義重大,可以有效提高兒童DDH的治愈率。DDH治療的主要目的是盡快實現髖關節頭臼同心圓解剖關系,確保其正常的生長發育潛能,避免生長紊亂[5]。基于兒童DDH的治療方式較多,對兒童DDH治療方式的選擇與其年齡、病理解剖狀態等相關[6]。現就國內外近幾年對其治療進展作一綜述。
1 出生至6個月
目前國內外公認出生至6個月為治療DDH的黃金階段。經過保守治療即可獲得較好的效果。首選的治療方式為Pavlik吊帶。Pavlik吊帶是一種動態性固定的尼龍材質支具,在一定的活動范圍內允許髖關節進行內收、外展活動,進而早期實現股骨頭復位和促進髖臼正常發育的治療效果。Pavlik吊帶治療要求每周復查超聲調整松緊,3周后觀察髖關節是否取得穩定的同心圓復位,如已取得理想復位,則應佩戴8~12周,逐漸停止。如若未能取得理想復位,應當停止吊帶治療改用其他治療方案。Gulati等[7]學者發現Pavlik吊帶治療對DDH的治愈率在90%以上,認為其是嬰兒期DDH的有效治療方法。Graf分型是Pavlik吊帶治療DDH是否復位成功的重要的相關因素之一。但是由于病兒存在髖臼指數(AI)過高、雙髖關節脫位等危險因素,可能出現股骨頭缺血性壞死(Avascular necrosis,AVN)、股神經麻痹等并發癥[8]。最近有研究表明6個月內的DDH病兒采用支具治療,其效果與Pavlik吊帶相當,而且其使用更方便,但是由于研究的病例太少,結論尚不能明確[9]。
2 7~18個月
對于7~18個月年齡段的病兒,其體質量以及活動量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使用Pavlik吊帶治療效果明顯下降,因此選用閉合復位石膏固定,若閉合復位失敗可選用關節鏡下清除術。
2.1閉合復位石膏固定雖然國內外曾經提倡對患肢牽引,但現在由于對其爭議較大,故使用患肢牽引也越來越少[10]。關節造影常被用來評估股骨頭覆蓋和復位的情況以及最佳的固定位置。關于石膏固定所采用的方法,常用的有改良蛙式石膏固定以及人類石膏固定。改良蛙式石膏固定具體方法為病兒在全麻下進行復位,必要的時候,可離斷部分內收肌和髂腰肌。置病兒雙髖關節于屈曲110°,外展外旋90°位,在此狀態下,將髖關節之下和踝關節之上的部分肢體石膏固定,雙膝之前放置一根方形木棒,以增加復位后髖關節的強度和穩定性。相比人類石膏,在改良蛙式石膏的保護下,病兒進行坐臥等身體活動時,股骨頭能夠在髖臼中做屈伸與旋轉活動,從而產生一種自我塑形改造的應力。石膏固定復位全程分為三期,每期約3個月,總共9個月。對于治療滿9個月的病兒,其AI仍大于35°,應適當延遲石膏固定時間[11]。程增輝和馬瑞雪[12]認為改良蛙式石膏固定治療DDH的優良率達97.8%。宋猛[13]通過系統分析發現在一定范圍內,減少髖關節外展角度,可以有效減少AVN的發生。
2.2關節鏡下清除術隨著髖關節鏡技術的不斷發展,近幾年應用關節鏡治療DDH逐漸引起關注。關節鏡主要適用于7~18個月的DDH病兒,全麻下閉合復位失敗的病兒,閉合復位后安全角的范圍低于20°的病兒,在髖關節鏡輔助下觀察關節內的病變狀況,發現并給予清除妨礙股骨頭復位的主要因素,從而能夠增加復位后的安全角范圍。關節鏡手術可以采取前側入路,選取髂前上棘與恥骨聯合水平線的交點,由于關節鏡入路距旋股內、外側動脈較遠,所以不易造成血管損傷,術后發展股骨頭壞死的風險也較小。丁仰坤等[14]通過對15例(16髖)DDH病兒行關節鏡下清除術,均取得成功復位,安全區范圍由術前13.6°增加到術后的41.1°,無一例發生再脫位。他們認為關節鏡下清除術是一種安全且創傷小的術式,可以有效處理關節內的病變。由于國內外應用髖關節鏡治療DDH仍處于探索階段,因此其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地觀察。?ztürk H等[15]對9例DDH病兒行關節鏡下清除術,平均隨訪47.7個月(范圍22~79個月)。AI由術前平均角度39.9°(范圍34°~52°)減少為術后平均角度26°(范圍22°~34°)。其中2例出現髖臼發育不良。
3 18個月以上至8歲
對于病兒年齡在18個月以上至8歲,下肢基本承重,軟組織的改變也變得更加牢固。閉合復位往往效果較差且其失敗率較高,常需進行切開復位或截骨術。切開復位可以單獨應用,也可以聯合其他手術,如骨盆、股骨截骨。
3.1單純切開復位目前,國內外普遍認同對于年齡大于18個月以及保守治療失敗是切開復位的指征。單純切開復位通常采用的手術方式有Ferguson術式,手術采取內側入路,其優點在于:不受視線干擾的情況下,清除影響髖關節復位的囊內以及囊外組織,其中包含攣縮緊張的髂腰肌和內收肌,增粗肥大的圓韌帶以及妨礙復位的髖臼內軟組織。Hoellwarth等[16]通過對18例DDH病兒進行研究,運用Ferguson術式復位成功,認為此術式是一種理想的復位方式。但有不少學者報道以此術式進行復位,AVN發生率較高。因此Ferguson術式仍需要長期的臨床隨訪和觀察。
3.2截骨術
3.2.1Salter骨盆截骨術 Salter骨盆截骨術適用于年齡在18個月到6歲、頭臼對稱以及AI<45°的病兒。自1961年加拿大Salter醫生報道Salter骨盆截骨術后,現已在臨床上廣泛使用。Salter截骨術通過截斷髂骨,截骨遠端以恥骨聯合為支點,使髖臼向前下外方旋轉,以增加對股骨頭的包容度,進而達到理想的治療效果。該術式為完全性截骨,需要內固定。6歲以上的兒童由于恥骨聯合旋轉作用有限,髖臼旋轉也受到一定影響,并且大齡兒童截骨后對股骨頭的包容也很有限。而重度髖臼發育不良比如AI>45°和髖關節未取得中心性復位是此術式的禁忌證。Salter骨盆截骨術對于髖臼生長發育異常的矯形能力和治療效果是有限的,且只能使髖日指數減少約15°[17]。劉振[18]進行改良Salter截骨術研究,術前將內收肌切斷,牽開關節囊和股骨頭,并擴大加深髖臼,行股骨近端旋轉截骨術,改變股骨頸的前傾角,從而達到了復位目的,消除再脫位因素,使股骨頭得以良好復位。通過研究分析48例(53髖)病兒,發現改良Salter截骨術優良率可以提高到91.67%。由于疾病復雜多變、手術技巧以及Salter截骨術局限性等因素,術后可能出現再脫位等并發癥[19]。因此嚴格地掌握手術適應證以及手術技巧,對于臨床醫生來說,至關重要。
3.2.2三聯截骨術 三聯截骨術通過截斷髖臼上緣以及恥骨上下支,將髖臼旋轉,以達到髖臼完全包容股骨頭,提高了髖關節的匹配比率,讓頭臼得以同心圓重塑復位。目前,三聯截骨術主要有Le Coeur、Steel、Tonnis 截骨。Le Coeur截骨是通過截斷鄰近恥骨聯合處的恥骨上、下支以及髂骨截骨。由于截斷的恥骨和坐骨位置距離髖臼較遠,再加上附著的骶棘、骶結節韌帶,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髖臼的轉動。Steel截骨通過后方入路在坐骨結節位置截斷坐骨,前方切口對恥骨和髂骨進行截斷,此術式的截骨位置距離髖臼相對較近,髖臼的調整范圍要更加優于Le Coeur術式。Tonnis截骨位置比Steel截骨更加靠近髖臼,經后方入路,將坐骨截斷,再從前路截斷坐骨髂骨,骶結節韌帶、骶棘韌帶在坐骨截骨下方,雖然此術式旋轉髖臼方便,但因與坐骨神經距離較近,坐骨截骨具有一定的風險。柴家超等[20]通過對53例(67髖)DDH病兒行Steel截骨術,術后臼頭指數 (Acetabular-Head-Index,AHI)88.92%,比術前提高40.7%,術后進行隨訪無一例發生再脫位。Vukasinovic等[21]系統分析了75例運用Tonnis截骨術的病兒,術后鴨步形態由17例(23.9%)減少為4例(5.6%),CE角增大了17.85°(114%)。三聯截骨術能夠明顯改善分布于髖臼軟骨的應力,從而達到延緩髖關節退行性損傷的目的[22]。van Stralen等[23]卻認為三聯截骨術存在著一定缺陷。對于早中期病兒可能有較好的效果,但當病兒發育成熟以后,仍可殘留髖臼發育不良。
3.2.3Bernese髖臼周圍截骨術 Ganz和Mast醫生于1988年首先報道此術式(因此也稱作Ganz截骨術)。Ganz截骨術治療DDH,該術式通常采用改良Smith-Petersen入路(即單側偏內切口)或髂腹股溝入路,恥骨截骨在靠近髖臼內側緣進行,在髖臼下溝行不完全性坐骨截骨,進而使髖關節游離,旋轉髖臼,頭臼得以合適的覆蓋。這種術式的優點有:在旋轉骨盆的同時,髖臼三維再定位,以及適度的內側位移髖關節旋轉中心和保護后柱的完整性[24]。涂俊和盧曉林[25]通過研究11例DDH病兒,平均隨訪16.4個月,術后CE角平均改善25.3°,截骨處均骨性愈合,大大改善了其髖關節的功能。但Leunig等[26]認為該術式的并發癥如坐骨神經麻痹可達15%以上。最新一項研究發現,Ganz截骨術危險因素包括:年齡大于25歲、術前髖臼包容良或差、術前關節間隙小于2 mm或大于5 mm[27]。由于該術式并發癥相對較高以及操作復雜困難,因此需要臨床醫生更長的學習曲線以及更加豐富的臨床經驗。

3.2.5Dega髖臼成形術 此術式與Pemberton截骨術相類似,同屬骨盆不完全性截骨。不同點在于Dega截骨術只截斷了“Y”型軟骨上方的髂骨部分作為鉸鏈,來矯正髖臼的形狀和方向,進而改善股骨頭的覆蓋。由于該術式不受“Y”型軟骨閉合及不受年齡段影響,可提供不同程度的外側覆蓋,并且沒有對“Y”型軟骨構成損傷和影響髖臼發育的風險,因此使用范圍比Pemberton截骨術更寬。Aksoy等[30]通過對35例(43髖)DDH病兒行Dega截骨術進行回顧分析,平均隨訪5年,AI從術前的平均35°下降到最后隨訪的13°,他們認為該術式在改善股骨頭包容和AI等方面是治療DDH病兒行之有效的術式之一。Akgül等[31]研究發現該術式可以增加T?nnis Ⅲ度和Ⅳ度脫位的髖臼包容,進而改善其穩定性和防止以后出現殘留的髖臼發育不良,他們認為該術式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方式,中遠期的療效令人期待。
3.2.6股骨截骨術 包括股骨短縮截骨、內翻截骨以及去旋轉截骨,以矯正股骨的近端畸形。股骨近端畸形是DDH病兒最常見的繼發性病變之一,主要類型有股骨頭前傾和髖外翻,進而導致在髖臼上的重力和肌力方向的異常,可能會造成持久的殘存畸形。在此情況下,治療可以選擇股骨近端截骨術,此術式目的在于將股骨頭牢固地回納到髖臼中,其原理在于改變了髖關節的應力,將股骨頭與髖臼的關系重建,改變了股骨頸軸的方向及長度,并且改變了髖關節的外展肌力臂和大轉子的位置,以股骨頭外側緣至股骨頭凹的關節軟骨來負重。目前普遍認為前傾角增大可影響髖脫位復位和復位后髖臼的發育以及髖關節功能,甚至可能再脫位。通常認為前傾角大于40°,需要行旋轉截骨。T?zün等[32]認為股骨近端短縮截骨能夠有效減少手術并發癥。股骨近端內翻截骨增加了關節軟骨負重面積以及去旋轉截骨改變了股骨頭在髖臼中的方向,共同矯正股骨頭與髖臼異常的位置關系。Ning B等[33]研究發現股骨去旋轉內翻截骨有益于關節復位的穩定性和中心復位,有效提高手術效果。但有學者提出股骨去旋轉內翻截骨并不是關節復位穩定的必要步驟,是否需行股骨去旋轉截骨應根據手術前MRI評價結果來決定。許多學者嘗試骨盆截骨術聯合股骨截骨術治療兒童DDH,能夠使股骨頭獲得良好的覆蓋,術后臨床癥狀和影像學異常均得到良好改善,認為此聯合方式是治療兒童DDH的有效方法[34-35]。
4 8歲以上(大齡DDH)
大齡DDH病兒的軟組織及骨性改變情況更為嚴重,骨骼塑形能力降低,頭臼形態可能難以復位,甚至關節軟骨已有損傷。治療上不能以達到復位為目的,而應注重功能的恢復,行姑息性手術,包括Chiari骨盆內移截骨術和Staheli髖臼延伸術,甚至有些研究建議放棄治療,直至成年以后再接受髖關節置換手術。
4.1Chiari截骨術Chiari截骨術適用于頭臼形容性較差、未能取得同心圓復位、髖臼缺乏塑形潛力以及髖關節半脫位伴疼痛的病兒。Chiari醫生1955年首次報道該術式,這是一種姑息性的骨盆內移截骨術,通過骨盆的內移增加髖臼的包容范圍,提高髖部的穩定性以及負重面積,進而改善病兒的關節疼痛癥狀,提高其生活質量。邱國良等[36]通過對60例髖臼發育不良的病兒行Chiari截骨術,得出所有的參數指標均有一定的改善,能較為有效地治療大齡DDH病兒。但此術式局限性在于外緣缺少透明軟骨面,日后由于股骨頭撞擊塑形雖可化生纖維軟骨,但是這種軟骨相對較薄,光滑程度及耐磨性能遠不如透明軟骨。因而,該術式只能起到延緩骨性關節炎發生的作用,卻無法從根本改變疾病的進展過程。Chiari截骨術也是在對髖關節無法行其他重建性手術的一種理想選擇。
4.2Staheli髖臼延伸術Staheli髖臼延伸術同樣也是一種姑息性的手術方式。由于此術式在增加了髖臼容積的同時,髖臼對股骨頭的壓力作用并沒有增加,因而療效令人滿意。不少學者嘗試使用Chiari聯合Staheli手術最大程度地增加骨盆對股骨頭的包容,增加股骨頭的負重面積,減少單位負重,也取得較好的療效。Staheli術在治療兒童DDH上能較大程度地矯正髖臼發育不良,術后的植骨塊吸收率也很低,但其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觀察。
此外,在大齡髖關節脫位病兒中,軟骨損傷應值得重視,其發病率較高。若不妥善處理,軟骨損傷進一步發展可以引起并加重髖關節的疼痛、僵硬、活動度下降及功能喪失[37]。修復髖關節的軟骨損傷對減緩疼痛、恢復功能并取得滿意的臨床效果有重要作用。現在已有多種新的治療手段如軟骨移植、骨膜移植、自體軟骨細胞移植等用于軟骨損傷的修復[38]。在髖關節軟骨損傷的修復中,這些治療方法可經由髖關節切開復位與骨盆截骨手術實施,也可在髖關節鏡下微創手術實現,值得在大齡的髖關節脫位兒童中進一步探索并推廣應用。
5 前景與展望
綜上所述,早診斷、早治療是提高DDH治愈率的關鍵。DDH的治療分為保守治療和手術治療,每種治療方法都有各自的優缺點,因此對DDH治療方式的選擇應根據病兒的年齡、頭臼發育狀況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從而制定個體化的方案。通過實現頭臼同心圓復位,改善股骨頭與髖臼的關系,進而獲得較為穩定的髖關節,最大限度地恢復關節功能。隨著材料學和手術技術的不斷發展及改進,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兒童DDH的認識及理解愈發深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探索出更多合適的治療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