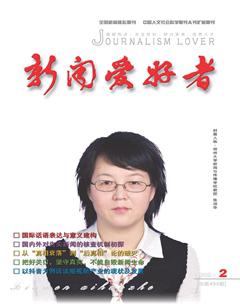國際話語表達與意義建構
趙永華 孟林山
【摘要】以習近平2013—2018年關涉“一帶一路”的國際話語為研究對象,運用積極話語分析方法,以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展現中國國家領導人對“一帶一路”的話語表達和意義建構。研究發現,在各種國際場合,習近平闡釋“一帶一路”的國際話語議題廣泛而主旨明確,在話語表達中運用多種語義資源對“一帶一路”的定位、實質、內涵和效果做了清晰說明。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話語反映出“主體間性”認識論,蘊含著中國的外交思想。
【關鍵詞】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國際話語;積極話語分析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一股逆全球化的風潮在全球蔓延: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并實行“美國優先”政策,極右勢力在歐洲泛濫,這些情況“從不同角度都折射出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國家已呈泛濫之勢”[1]。曾經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歐美各主要國家,如今卻在沖擊和遲滯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依據自身的國家發展戰略,結合全球發展趨勢與要求,提出了“一帶一路”這一旨在促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中國方案”。
在對“一帶一路”定位的認知上,不同國家基于本國的需要有著不同的認識。從溫和的社會建構主義視角來看,中國和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建構,其實質是個體(中國)、社會共同體(國際社會)以及認知對象(“一帶一路”倡議)這三個要素相互作用的過程。國家之間的交流猶如一場對話,一場好的對話是對話者之間能夠清楚了解雙方的意圖和想法,并基于各自的利益進行協商,最終達成共識。“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當前外交的重要內容,在對外傳播上似乎并未能夠很好地將自己的意圖和想法告知世界。
那么,如何向國際社會更好地解釋和說明“一帶一路”?我國國家領導人對“一帶一路”的直接表述是對“一帶一路”所做的最好說明。習近平主席在國際上的公開話語,既是向世界傳達中國對外政策和外交立場態度的重要傳播方式,也是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政策的重要途徑與窗口。習近平主席在國際會議上的演講、在海外媒體上發表的署名文章,都是可供研究的優質樣本。本文選取習近平2013—2018年有關“一帶一路”的國際話語進行分析,嘗試對其話語的呈現方式和意義的建構過程予以解讀,并挖掘話語背后的外交思想和文化內涵。
二、研究設計
(一)積極話語分析:作為批判話語分析的補充與互補
在研究方法上,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discourse
analysis,簡稱CDA)是最常使用的話語分析方法。但批判話語分析對社會現實一般是采取較為尖銳的批評態度,分析話語背后的權力因素,解構當前的話語,具有一定的后現代色彩。然而,只有批評是不夠的,是無助于社會問題解決的。為了使話語分析更具建設性,馬丁于1999年提出了“積極話語分析”(positivediscourseanalysis,簡稱PDA)這一命題,主張話語分析應該采取積極友好的態度。其實,積極話語分析不僅同批判話語分析一樣重視社會沖突、社會歧視與社會不平等,而且還關心外交、斡旋、談判、會議以及咨詢等語篇。[2]在馬丁看來,積極話語分析并不是對批判話語分析的顛覆與替代,而是補充與互補。[3]批判話語分析傾向于解構,關注那些對權力機構抱有負面情緒的話語;而積極話語分析傾向于建構,既關注批判話語分析所關注的語篇,也重視具有建設性的積極語篇。
由于傳統國際關系與冷戰對抗意識的歷史慣性,世界各國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多傾向于單純的批判,往往與“中國威脅論”等政治意識形態相掛鉤,以試圖消解“一帶一路”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合理性與建設作用。就當前國際形勢而言,世界各國也并未提出更具實踐操作性和國際視野的全球經濟振興方案。純粹的批判解構不但無益于現實問題的解決,更會造成全球分裂狀況的加劇,使政治和經濟問題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根據本文研究對象及所要解決的問題,本文采取積極話語分析的研究方法。
(二)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得益于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當前的話語分析已經逐步走向了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相結合的道路。本文嘗試建立“習近平‘一帶一路國際話語”小型專題庫構成本文的研究基礎,進而采取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展開研究,首先是對關涉“一帶一路”的所有語篇的數據分析;其次是從語料庫中選取最有價值的語篇進行評價分析。
1.量化分析
積極話語分析作為一種質化研究方法,同批判話語分析一樣,有著“過于注重主觀價值判斷的缺陷”[4]。因此,本文以語料庫為基礎進行積極話語分析,對習近平有關“一帶一路”國際話語的所有語篇進行量化,通過關鍵詞分析、詞頻分析等數據分析,以此來展現習近平“一帶一路”話語的主題呈現。
2.質化分析
由于傳統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無法對評價意義進行闡釋,“評價模式”便由此誕生。[5]“評價模式”是基于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三個純理論假說而來,目的在于描述話語互動中的價值判斷和評價的語言資源。它的核心概念為“系統”,“評價系統是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新發展,屬闡釋性研究”[6]。評價系統又包括三個次系統:態度系統、介入系統和級差系統。雖然該模式自身存在一定的模糊性[7],但是通過與語料庫分析相結合,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其不足。
(三)樣本的收集與整理
本文的研究樣本是習近平2013—2018年關涉“一帶一路”的所有國際演講、海外采訪及署名文章。2013年5月31日,習近平在對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哥斯達黎加、墨西哥進行國事訪問前夕,接受了三國媒體的聯合書面采訪,并在此次聯合采訪中首次面對國際受眾提到“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詞匯。2013年9月7日與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分別在哈薩克斯坦與印度尼西亞發表演講,先后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這是習近平有關“一帶一路”國際話語的闡述開端。此后,隨著習近平外交活動的增多與深入,關涉“一帶一路”的國際話語逐年增多,成為中國對外交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話題,并在2017年達到了最高點。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在此期間,習近平先后進行了四場演講活動,分別是:祝酒辭、高峰論壇開幕式演講、圓桌峰會開幕辭以及圓桌峰會閉幕辭。
在樣本的原始數據收集方面,筆者借助于人民網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數據庫”,先后以“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絲路”等關鍵詞進行搜索,實現了對樣本的初步收集,數據采集截止日期為2018年1月25日。隨后,通過人工閱讀,以定性的方式進行篩選,剔除了以下類型的文本:《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媒體對習近平國際話語的解讀;非國際語境的有關“一帶一路”的語篇(如國內政務會議、黨內會議);對習近平“一帶一路”國際話語的新聞報道(非全文刊登);習近平在各個會議中講話內容的摘要匯編。最終,得到80份有待分析的國際話語語篇,共約25萬字。其中,國際媒體采訪3篇,親筆賀信4篇,海外媒體上發表署名文章24篇,國際演講與發言49篇。這80份語篇的年度分布,如圖1所示(其中,2018年有一篇未列入)。
在樣本的自然語言處理方面,筆者通過NLPIR分詞系統進行中文詞匯劃分,將劃分好的樣本輸入至語料庫軟件AntConc,從而建立“習近平‘一帶一路國際話語”小型專題庫。
三、基于語料庫的關鍵詞詞頻分析與索引分析
(一)關鍵詞詞頻分析
通過圖悅、NLPIR以及AntConc對習近平關涉“一帶一路”的語篇進行詞頻分析,并將數據進行整理,總結出以下47個關鍵詞及其詞頻與權重。
由表1可知,在習近平關涉“一帶一路”的國際話語中,“合作”“經濟”“世界”“共同”“和平”“國際”“建設”“一帶一路”“共贏”“亞洲”是詞頻最高、權重較大的十個關鍵詞。根據詞語情感分析,這47個主要關鍵詞皆呈現出正向情緒。其中,核心關鍵詞“一帶一路”的詞頻為294,權重是0.8974;“倡議”的詞頻為123,權重是0.8427;“戰略”的詞頻為329,權重是0.8829。
通過對“一帶一路”“倡議”“戰略”這三個關鍵詞進行索引分析,可從數據上得出中國國家領導人對“一帶一路”定位的表述是清晰的,向國際社會傳遞了有關“一帶一路”是“經濟合作倡議”而非“地緣政治戰略”的信號。
(二)對三個關鍵詞的索引分析
1.關于關鍵詞“一帶一路”的索引分析
對關鍵詞“一帶一路”的索引分析,包括“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三個關鍵詞,其索引行的主要搭配情況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習近平“一帶一路”國際話語的表述方式中,與關鍵詞“一帶一路”搭配最為緊密的詞語是“倡議”“合作”“建設”“平臺”,僅有一篇署名文章《讓中阿友誼如尼羅河水奔涌向前》使用了“中阿共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這一搭配方式。在以“一帶一路”為核心詞的詞語搭配上,更傾向于使用“倡議”“合作”“建設”“平臺”這些搭配方式。“‘一帶一路戰略”這一搭配所使用的語境是在地區性國際會議中,意在強調地區發展。
2.關于關鍵詞“倡議”的索引分析
通過對“一帶一路”的索引分析可知,“一帶一路倡議”是習近平國際話語中最常使用的組合方式。進一步而言,還須對“倡議”這一關鍵詞進行索引分析,其索引的主要搭配情況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倡議”這一關鍵詞最主要的搭配對象是“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此外,表中第3—6項是特殊語境下對“倡議”一詞的使用,如“核安全國際倡議”的搭配出自2016年4月1日習近平在華盛頓核安全峰會上的講話《加強國際核安全體系推進全球核安全治理》中;“安全與合作倡議”的搭配出自2014年5月21日習近平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的講話《積極樹立亞洲安全觀共創安全合作新局面》中;“建立亞非中心倡議”的搭配出自2015年4月22日習近平在亞非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弘揚萬隆精神推進合作共贏》中;“區域合作倡議”出自2017年6月9日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七次會議上的講話;“草原之路倡議”出自2014年8月22日,習近平在蒙古國國家大呼拉爾的演講《守望相助,共創中蒙關系發展新時代》中。
3.關于關鍵詞“戰略”的索引分析
在習近平關涉“一帶一路”的國際話語中,“戰略”一詞的使用方式與主要搭配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關于關鍵詞“戰略”的使用與搭配,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具體戰略名稱和相關具體戰略行為的定位。在戰略名稱方面,語料庫中并無“一帶一路戰略”這一直接搭配。包含“一帶一路”和“戰略”這兩個關鍵詞的語句共有三句,且是和“戰略對接”這一詞組進行搭配的。其中“共建‘一帶一路,加緊國家戰略對接”出自2016年6月21日習近平在烏茲別克斯坦媒體發表的署名文章《譜寫中烏友好新華章》;“加快‘一帶一路倡議和‘四角戰略對接”出自2016年10月12日習近平在柬埔寨媒體發表的署名文章《做肝膽相照的好鄰居、真朋友》;“‘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出自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雖然“一帶一路”和“戰略”這兩個關鍵詞出現在同一個句子當中,但是“戰略”一詞并非與“一帶一路”直接搭配。
目前,國際上對于“一帶一路”的認知還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識主要有四種:“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論、中國版“再平衡”戰略論、“中國經濟自我救贖”論,以及中國“新懷柔政策”論。[8]作為與中國為鄰的地緣大國印度,其對“一帶一路”的定位認知亦存在著不同看法,“重大機遇”論和“戰略憂患”論并存。[9]日本對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是“中國基于經濟與政治雙重考量而提出的戰略構想”。經濟上解決國內產能過剩,提升全球經濟影響力;政治上將“一帶一路”定位成為“地緣戰略工具”,重構東亞國際秩序。[10]緬甸作為中國西南方向的重要鄰國,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對其自身而言,是發展的一大機遇,可以借此搭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便車”[11]。越南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定位,根據實證調研結果,不同階層有不同的認知和態度,即官方和智庫是懷疑和謹慎歡迎,商界和民間是不關心和不了解。[12]印尼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則呈現“兩極分化”現象,即政府支持和歡迎;軍方與反對聯盟因“中國威脅論”而抱有疑慮;華人群體支持;學界態度謹慎并懷有批評態度。[13]
根據以上各國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態度可知,多數國家將“一帶一路”倡議定位為中國的一種“地緣政治戰略”,而非一種“經濟合作倡議”,政治意圖大于經濟目的。為此,中國的媒體、智庫做了大量的解釋工作,但很難把握這些解釋工作實際產生的效果有多大。多項調查結果表明,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力、國際影響力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當前,在新時代對外話語體系創新的背景下,國家領導人面向國際的話語輸出成為我國對外傳播的創新話語方式。作為傳播者,國家領導人比媒體擁有更廣泛和更有力的影響。習近平有關“一帶一路”的國際話語向世界清晰地闡明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本質和內涵,有助于國際社會正確認識和對待“一帶一路”倡議。
四、對重要語篇的評價系統分析
2013年至2018年,“一帶一路”在習近平的國際演講中逐漸從非主體、非核心內容轉變為核心主旨議題,“一帶一路”的重要性日漸凸顯。尤其是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辦之后,“一帶一路”作為關鍵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際會議之中,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關注熱點。通過對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的四篇演講進行評價分析,能夠更加準確地解讀習近平和中國政府對于“一帶一路”的意義建構。為了研究方便,筆者將“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辭”“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圓桌峰會的開幕辭《開辟合作新起點 謀求發展新動力》”“圓桌峰會的閉幕辭”分別命名為“語篇一”“語篇二”“語篇三”“語篇四”。
(一)態度系統分析
態度系統的子系統有三個:情感系統、判斷系統、鑒賞系統。通過對上述四篇語篇的態度系統分析,可以得出說話者對于“一帶一路”所作出的判斷和態度。
1.情感系統分析:肯定“一帶一路”的光明前景
習近平在對“一帶一路”的情感定位上,是對其持樂觀積極的態度,這在語篇一和語篇二中有明顯體現。說話者認為“一帶一路”是“充滿希望的道路”,是“偉大的事業”,是能夠為人類帶來光明未來的,即“我們的事業會像古絲綢之路一樣流傳久遠、澤被后代”“造福世界,造福人民”。說話者通過“充滿希望的”“偉大的”這樣包含積極情感的詞組形容“一帶一路”,以此來展示其樂觀肯定的態度。
2.判斷系統分析:“一帶一路”的本質
習近平在對“一帶一路”本質的闡釋上,曾多次使用“‘一帶一路是……”“‘一帶一路不是……而是……”這樣的表述方式,以此來對“一帶一路”的本質進行判斷,這在四篇語篇之中均有體現。說話者通過對“一帶一路”歷史傳承的肯定,表明了“一帶一路”源自歷史,面向未來,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是符合世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通過否定“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肯定“戰略對接、優勢互補”,通過對“一帶一路”核心內容的直接闡述,表明了“一帶一路”并非傳統國際政治中的“地緣政治戰略”和排他性的經濟合作組織,而是為解決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問題所提出的倡議和方案,是各國平等參與的發展平臺。
3.鑒賞系統分析:“一帶一路”的價值和意義
習近平通過對“文明與溝通”“過去、當下與未來”“人民與國家”“國家與國際”“理想與現實”等幾組重要概念關系的闡述,表達了“一帶一路”自身所蘊含的價值與意義,這在四篇語篇之中均有體現。說話者表明了“一帶一路”的重要價值和意義:第一,“一帶一路”促進了世界文明的交流與發展;第二,“一帶一路”有助于維護世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第三,“一帶一路”有助于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第四,“一帶一路”是提高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
(二)介入系統分析:“一帶一路”的歷史繼承與合理性
介入系統的子系統有兩個:自言系統、借言系統。通過對這四篇語篇的介入系統分析,可以分析出說話者如何通過介入系統語義資源的運用來說明“一帶一路”的歷史繼承與合理性。自言的使用,表明說話者能夠為自己的話語內容承擔責任;借言的使用,目的在于讓說話者的內容闡述更具客觀性和說服力。
為了論證“一帶一路”的歷史繼承與合理性,說話者在四篇語篇之中都運用了借言系統,尤其在語篇一和語篇二中有明顯體現。例如,語篇一中說話者將一些代表古今的符號進行對比,如古代建筑(故宮、長城、天壇)和現代建筑(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中國傳統藝術(京劇、相聲)和西方藝術(芭蕾舞、交響樂),世界潮流中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里的外國人。通過對客觀存在現象的借言,使得說話者所說的“北京更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東西方不同文明時時刻刻在這里相遇和交融”這句話更具客觀性和說服力。
語篇二中,說話者通過借言的方式,列舉了有關“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物(“鎏金銅蠶”“千年沉船‘黑石號”)、歷史記錄者(杜環、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古城古港(酒泉、敦煌、吐魯番、喀什、撒馬爾罕、巴格達、君士坦丁堡等)、文化經貿交流活動(絲綢、瓷器、漆器、鐵器、胡椒、亞麻等)、相關歷史文字記載(“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舶交海中,不知其數”),通過這些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客觀實際與文字記錄,來說明“一帶一路”的歷史悠久和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進而建構起“一帶一路”的歷史繼承性。
(三)級差系統分析:“一帶一路”倡議成果顯著
級差系統的子系統有兩個:語勢和聚焦。其中,語勢又分強勢和弱勢,聚焦又分明顯與模糊。通過對這四篇語篇的級差系統分析可以發現,說話者在表達“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果時,調用的是“強勢語勢”和“明顯聚焦”的語義資源,這在語篇二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說話者用“4年”來指代“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并付諸實踐的四年,通過調用“明顯聚焦”的語義資源,即“這是政策溝通不斷深化的4年”“這是設施聯通不斷加強的4年”“這是貿易暢通不斷提升的4年”“這是資金融通不斷擴大的4年”“這是民心相通不斷促進的4年”,來表明“一帶一路”倡議的顯著成果。此外,說話者還分別運用強勢語勢來詳細印證這五個方面“4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說話者通過大量的詳實數據(合作的國家數量、貿易額度、投資額度、貸款額度、獎學金名額)和例證(與各國的發展政策協調對接、合作項目的建設與推進、金融服務支持、人文合作項目),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果進行了描述和論證,體現了說話者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充分肯定。
五、習近平“一帶一路”國際話語中的認識論
(一)“主體間性”詞匯的使用
“一帶一路”倡議所蘊藏的價值觀是“主體間性”認識論。近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得益于“主體—客體”認識論,它對于人類肯定自我價值、研究客觀世界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單純的“主體—客體”模式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物的關系時是行之有效的,但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就遇到了“他人不是客體”的困窘。[14]傳統的國際關系即是建立在“主體—客體”認識論的基礎之上的。當前,建立以“主體間性”為認識論前提的新型國際關系勢在必行。
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關涉“一帶一路”的國際話語中充分體現出“主體間性”的認識論。對習近平有關“一帶一路”國際話語的數據分析,其語篇的關鍵詞詞頻與權重最高的47個詞匯中,有28個關鍵詞(如表5所示)體現了“主體間性”的認識論,占比59.6%。從微觀角度分析,詞匯的頻繁使用表示說話者重視該觀念,是說話者自身所持有的價值觀和認識論的具體體現。“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以“零和博弈”“贏家通吃”的“主體—客體”認識論為價值預設的,也不是西方國家眼里的排他性“地緣政治戰略”“政治—經濟的意識形態聯盟”,而是由中國首倡,旨在通過多邊平等協商合作實現國家間的戰略對接、優勢互補,最終實現共同發展。
(二)“主體間性”的話語表達
1.出發點和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共商、共建、共享”
2017年5月15日,習近平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并致開幕辭《開辟合作新起點 謀求發展新動力》。在演講中,習近平表明了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
在“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框架內,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這是我提出這一倡議的初衷,也是希望通過這一倡議實現的最高目標。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正是“主體間性”認識論的體現。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靠一國之力、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它的實現必然要依靠世界各國堅持不懈的努力。“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這正是“主體間性”認識論的體現。
正如“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一樣,“一帶一路”建設不是一兩個大國主動參與、其他國家被迫參加就能夠成功實現的,需要調動各國的主動性,使各國以平等的姿態加入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之中,共同商議發展政策、共同進行項目建設、共同分享勞動果實。
2.實質:“戰略對接、優勢互補”
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并發表開幕式演講《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演講中,習近平明確說明了“一帶一路”的實質:
我多次說過,“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各方通過政策對接,實現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戰略對接”“優勢互補”體現了互為主體、承認雙方主體性的新型國際關系。在中文語境下,這種“主體間性”思維即是“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所求之“同”與“和”是國家之間的最高共同利益,所存之“異”與“不同”則是國家之間尊重、承認對方的主體地位和差異性。“一帶一路”通過與不同國家的國家戰略進行對接,通過平等協商合作,共同促進雙方甚至多方的政策對接,使“主體間性”認識論貫穿于新型國際關系的建構之中。
3.踐行中國外交政策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自提出之日起,就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基本原則。“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對外交往的一項重要內容,體現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在開幕式演講中,習近平表達了關于“一帶一路”建設的五點意見:
第一,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各國應該尊重彼此主權、尊嚴、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第二,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繁榮之路。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
第三,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開放之路。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一帶一路”建設要以開放為導向,解決經濟增長和平衡問題……
第四,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創新之路。創新是推動發展的重要力量。“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創舉,搞好“一帶一路”建設也要向創新要動力……
第五,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帶一路”建設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以上這五點意見,分別從國際關系、經濟發展、對外開放、技術與制度創新、文明交流這五個角度闡述了“一帶一路”的價值與意義,而這五個方面,正是中國外交政策宗旨的體現,即“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15]。
通過上述一系列對習近平有關“一帶一路”國際話語的分析可知,中國國家領導人對“一帶一路”的定位是一種經濟合作倡議,并非是具有排他性的經濟合作組織以及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地緣政治戰略。通過對語篇評價系統的分析可知,“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質是國家間的發展戰略對接、以“共商、共享、共建”為原則的全球公共產品,其最終目的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一種全新的全球化方式共促世界和平發展。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對外傳播戰略研究”(15ZDA07)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俄媒體交流、戰略傳播與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的構建研究”(16ZDA217)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徐堅.逆全球化風潮與全球化的轉型發展[J].國際問題研究,2017(3).
[2]朱永生.積極話語分析:對批評話語分析的反撥與補充[J].英語研究,2006(4).
[3]朱永生.積極話語分析:對批評話語分析的反撥與補充[J].英語研究,2006(4).
[4]錢毓芳.語料庫與批判話語分析[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0(3).
[5]劉世生,劉立華.評價研究視角下的話語分析[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
[6]王振華.評價系統及其運作: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新發展[J].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01(6).
[7]劉世生,劉立華.評價研究視角下的話語分析[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
[8]馬建英.美國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與反應[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10).
[9]林民旺.印度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及中國的政策選擇[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5).
[10]黃鳳志,劉瑞.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與應對[J].現代國際關系,2015(11).
[11]李晨陽,宋少軍.緬甸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和反應[J].南洋問題研究,2016(4).
[12]顧強.越南各階層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與態度及其應對策略研究:對越南進行的實證調研分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6(5).
[13]潘玥,常小竹.印尼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反應及中國的應對建議[J].現代國際關系,2017(5).
[14]郭湛.論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性[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3).
[15]習近平.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
(趙永華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孟林山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編校:張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