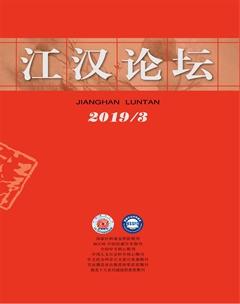20世紀上半葉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地主制經(jīng)濟的變化
摘要: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抑制了地主制經(jīng)濟規(guī)模的擴張,但并未能促使其向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方向轉(zhuǎn)化。地主階級通過租佃制和高利貸剝奪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剩余,轉(zhuǎn)而投向城市部門。農(nóng)業(yè)部門缺乏積累與投入,技術(shù)進步停滯,生產(chǎn)方式落后,生產(chǎn)效率低下。這不僅削弱了農(nóng)業(yè)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也使廣大地主頑固地堅持租佃制經(jīng)營,反映出中國地主制經(jīng)濟與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發(fā)展之間的尖銳矛盾。實踐表明,只有徹底摧毀地主制經(jīng)濟,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才有發(fā)展的可能。
關(guān)鍵詞:20世紀上半葉;城市化;地主制經(jīng)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鄉(xiāng)村地籍整理研究”(12BZS059)
中圖分類號:F129?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19)03-0113-06
一、引言
關(guān)于舊中國地主制經(jīng)濟的特點,已有廣泛討論。第一種觀點強調(diào)中國地主制經(jīng)濟的封建性。① 第二種觀點認為地主租佃制經(jīng)濟在唐宋以后逐步得到確立,地主和農(nóng)民近似市場經(jīng)濟中的平等主體,租佃關(guān)系是一種契約關(guān)系。② 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的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實際上是政治權(quán)力、土地權(quán)力、商業(yè)資本、高利貸資本的綜合體,因此具有很大的融通性,顯示出“彈性”的特征。③ 近代以來的經(jīng)濟社會變遷,使地主制經(jīng)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一種看法是封建地主制經(jīng)濟在近代趨向衰落。④ 相反的觀點是封建地主制經(jīng)濟仍在農(nóng)村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⑤
本文的重點是考察城市化進程對地主制經(jīng)濟的影響。關(guān)于這一問題,學術(shù)界也有初步探討。⑥ 近代中國工業(yè)與城市部門的發(fā)展,對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因此,關(guān)于舊中國地主制經(jīng)濟的特點及其變化,需要結(jié)合工業(yè)及城市部門的影響加以分析。以往研究雖有涉及,但是關(guān)于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特征缺乏辨析,因此,城市化進程對地主制經(jīng)濟的影響,也沒有得到十分清晰的說明,以致人們對地主制經(jīng)濟的發(fā)展狀況莫衷一是。本文擬以20世紀上半葉為中心,進一步考察近代工業(yè)與城市化對地主經(jīng)濟的影響,并希望能對舊中國地主經(jīng)濟的特點有所辨明。
二、工業(yè)化與社會動蕩所推動的城市化進程
據(jù)美國學者斯金納爾估計,1843—1894年,中國城鎮(zhèn)人口從2072萬增至2351萬,城鎮(zhèn)人口在總?cè)丝谥械谋戎赜?.1%增至6%。從1894—1949年,城鎮(zhèn)人口從2351萬增至5765萬,城鎮(zhèn)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在長達近110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城市化率大約為5.5個百分點的增長。⑦
德懷特·珀金斯認為,1900—1910年,中國城市人口數(shù)(不含香港)1464萬人,1938年為2456萬人,1953年為4753萬人。⑧據(jù)卜凱調(diào)查,1929—1933年間,中國城市人口約占10%;市鎮(zhèn)人口約占11%,村莊人口約占79%。⑨ 劉大中和葉孔嘉對1933年人口的職業(yè)分布作過詳細估計。1933年,全國就業(yè)人口為2.5921億,其中2.0491億人即79%從事農(nóng)業(yè);5430萬人(包括一定比例從事雙重職業(yè)人口)即21%在非農(nóng)部門就業(yè)。總?cè)丝谥校?3%生活在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家庭里,27%為非農(nóng)家庭成員。⑩
從1912年至1949年,中國人口幾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長,城市人口的增長率可能達到2%。{11} 20世紀中葉中國各省區(qū)城市化水平,以東北最高,在20%左右;廣東、江蘇等10余省在10%以上;其余在10%以下。{12}
近代中國城市化有兩個動力源泉:一是工業(yè)化所推動的城市化,一是社會動蕩所導致的城市化。
19世紀80年代,農(nóng)業(yè)約占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66.79%,非農(nóng)業(yè)占33.21%。非農(nóng)業(yè)部門包括采礦業(yè)、制造業(yè)、建筑業(yè)、運輸業(yè)、貿(mào)易、金融等。不過這時的制造業(yè),幾乎全是手工業(yè)。{13}
19世紀末期,小型的近代工業(yè)部門出現(xiàn)。1894年前,商辦和官辦工廠合計108家,資本1.8億元,雇傭工人約8萬人。{14} 1913年中國工廠數(shù)698家,資本3.3億元,雇傭工人27萬人。{15} 1920年,中國工廠數(shù)1759家,資本約5億元,工人約56萬人。{16} 1933年,中資工廠數(shù)3167家,雇傭職工55萬人,總產(chǎn)值約14億元。{17} 到1943年,在大后方有工廠3758家,工人24萬余人。{18}
在中國近代工業(yè)經(jīng)濟中,還有一個規(guī)模龐大的外資部門。{19} 巫寶三推算,1933年工廠總數(shù)為3841家(中資3167家,外資674家),雇傭工人73萬余名,總產(chǎn)值約22億。在計入滿洲工業(yè)發(fā)展數(shù)據(jù)后,劉大中和葉孔嘉推算出1933年工業(yè)產(chǎn)值超過26億,雇傭工人超過107萬。{20} 1937年中國工業(yè)資本38億,其中中國資本約10億,占26%,外資資本約28億,占74%。{21}
在中國工業(yè)制造中,手工業(yè)制造要超過工廠工業(yè)制造。1933年,工業(yè)制造凈值約為19億元,其中手工業(yè)凈值約為14億元,約占工業(yè)制造凈值的72%。{22}
從工業(yè)的年均增長率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和戰(zhàn)后工業(yè)明顯擴大(1912—1920年,13.4%),隨后是1921—1922年的戰(zhàn)后衰退;從1923—1936年,平均增長率為8.7%;1912—1942年為8.4%; 1912—1949年平均年增長率為5.6%。{23}
根據(jù)劉一葉的估計,1933年國內(nèi)生產(chǎn)凈值為288.6億元,其中農(nóng)業(yè)凈值187.6億元,約占65%;非農(nóng)部門凈值101億,約占35%。{24}
在工業(yè)與城市部門就業(yè)的工人,其工資水平遠高于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部門的工資。{25} 近代工業(yè)與城市化進程使農(nóng)業(yè)部門的勞動力流動有了新的變化。
1922年江蘇等5省9縣,南方省份農(nóng)村離村率約為3.85%,北方省份農(nóng)民離村率為5.49%。{26} 離村農(nóng)民流動的方向,一是往西北、東北新墾區(qū)流動{27};一是流徙海外{28};一是流入城市。
江蘇宜興“附城鄉(xiāng)村,頗有入城進工廠工作者,甚有往蘇、滬、錫等埠在紗廠紡織者”。1927年,進城務(wù)工的農(nóng)村婦女達6000人。{29} 隨著無錫工廠的增加,周圍農(nóng)村過去的雇農(nóng),都進廠當工人去了。{30} 鎮(zhèn)江每年從蘇北和山東涌入的季節(jié)工4000—5000人。{31} 禮社為無錫一個鎮(zhèn),在1932年前后,流動出去的人口有755人,占該鎮(zhèn)總?cè)丝诘?1%。約四分之三的人流動到外縣,其中上海最多,400余人,其次是蘇州。流往本縣城區(qū)的100余人。{32} 山西農(nóng)民發(fā)現(xiàn)種田不能維持生計的時候,都跑到太原尋求仆役之類的工作。{33} 由于“武漢工廠林立,商業(yè)繁盛”,“附近居民貧窮者多入工廠”。{34} 據(jù)1934年調(diào)查,山東泗水縣農(nóng)民外出謀生,遠者至東三省,近者至南京。{35}
據(jù)有關(guān)學者研究統(tǒng)計,在1935年21個省1001個縣中,有1.7%的農(nóng)戶和4.2%的鄉(xiāng)村青年棄農(nóng)進城。{36}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商業(yè)產(chǎn)權(quán)的價值相對于農(nóng)村產(chǎn)權(quán)迅速上升。圖1 顯示,1934年,各省城市地價都要遠高于農(nóng)村地價。整體而言,工商業(yè)發(fā)達的南方各省要高于北方各省。根據(jù)重慶等13市縣1931—1943城鄉(xiāng)地價資料計算,商業(yè)地產(chǎn)價格指數(shù)每上升1個百分點,農(nóng)村地價指數(shù)僅上升0.669個百分點。{37}
說明:根據(jù)《全國土地調(diào)查報告綱要》(中央土地專門委員會1937年刊行)第60頁“第四十二表·各省歷年平均城廂地價”繪制。
抗戰(zhàn)前的蘇南農(nóng)村,土地投資年純利潤只有8.7%左右,而工業(yè)投資的平均利潤為30.2%,商業(yè)投資的平均利潤為31.4%。{38} 以前地主的錢用于在農(nóng)村放高利貸。隨著城市投資機會的增加,地主開始投資城市的商業(yè)活動,或?qū)㈠X存入城市銀行中。{39} 凡稍有資產(chǎn)的人家都由鄉(xiāng)而鎮(zhèn),由鎮(zhèn)而城,由城而市,這可以說是資金的逃亡。{40}
持續(xù)的社會動蕩從另一個方面加速了城市化進程,導致城市的畸形發(fā)展。
20世紀20、30年代,天災(zāi)人禍頻仍。{41}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1912—1930年間,軍閥之間共發(fā)生戰(zhàn)爭152次。{42}
如表1所示,1934—1935年間,江蘇等16省176個縣中,只有4縣沒有發(fā)生災(zāi)患,約為總數(shù)的2.3%;超過70%的縣災(zāi)情都比較嚴重;更糟糕的是,政府基本上沒有采取十分有效的救災(zāi)措施。卜凱認為,匪患、兵災(zāi)以及自然災(zāi)害是影響農(nóng)村發(fā)展最主要的原因。{43}
各省盜匪橫行,稍微富裕的家庭,就有被搶劫的危險。{44} 河南輝縣,因為遭遇“匪患”,地主富農(nóng)出賣田地較多,中農(nóng)、貧農(nóng)由于沒有被綁架的危險,田地數(shù)下降反而較慢。鄉(xiāng)村土地的購買者多為城市地主及商業(yè)高利貸者。{45} 1928—1933年間,江蘇邳縣,由于匪患甚烈,收獲不佳,很少有地主商人愿意買進田畝,導致地價降落。{46}
一些小有資本的人還留在農(nóng)村,靠出租土地、經(jīng)營高利貸等生活,農(nóng)村最為富有的階層則逃往城市。{47} 在匪患的影響下,使南陽城居民由2萬人驟增至4萬人。{48} 四川華陽縣地主住在鄉(xiāng)村者,占57.6%,住在場鎮(zhèn)者,占12.2%,住在城市者,占30.2%。{49} 江蘇宜興和橋鎮(zhèn)是宜興最大的一個市鎮(zhèn)。在30年代,城鎮(zhèn)人口逐漸增加。鎮(zhèn)里的地主,有地1000—1500畝的,有十五、六戶;有地100—1000畝的,有五、六十戶;總計土地在30000畝以上。{50}
1924年,各地居外地主的比重,江蘇昆山為65.9%,江蘇南通為15.8%,安徽宿縣為27.4%,湖北武昌為50%。{51} 據(jù)實業(yè)部1934年調(diào)查,上海、江蘇(16個縣區(qū))、浙江(9縣區(qū))、安徽(4縣)、江西(43縣區(qū))地主城居比例分別為20%、27.7%、37.2%、18.7%、22.6%,平均為25.1%。{52}
如圖2所示。efg是總?cè)丝谇€,lmc是必要的工業(yè)化曲線,在這個水平上,所有剩余勞動力都轉(zhuǎn)移到城市中來了。ijc是現(xiàn)實工業(yè)化水平上,可能達到的城市化進程。但是,由于社會動蕩,一部分農(nóng)村居民被迫遷往城市,導致現(xiàn)實的城市化程度abc曲線所在的位置要高于可能的城市化程度ijc曲線。
三、地主制經(jīng)濟的變化
在《華北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黃宗智描述了兩個“力農(nóng)致富”的地主代表,河北豐潤縣米廠村的董天望和平谷縣大北關(guān)村的張彩樓,經(jīng)過幾代人的努力,他們上升到一個小地主的規(guī)模。{53} 這兩個農(nóng)戶主要是靠力農(nóng)致富。其現(xiàn)金收入來源于經(jīng)濟作物的生產(chǎn)和銷售,正是現(xiàn)金的積聚讓他們有能力不斷擴大土地規(guī)模。一個頗具規(guī)模的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幫了忙。
但是,對于大多數(shù)小農(nóng)來講,正是市場制度惡化了其生存處境。{54} 很多農(nóng)戶耕作一年,收支不能平衡,必須借債以敷生計。根據(jù)土地委員會1934年調(diào)查,全國農(nóng)戶負債百分比為43.87%。{55} 各省農(nóng)戶借貸年利率集中在2分至4分之間。{56} 中國農(nóng)村借款來源,主要是典當行、錢莊、商店、地主、富農(nóng)、商人等。{57} 由于利率奇高,使本利的累積格外迅速。{58} 據(jù)土地委員會調(diào)查,農(nóng)村借貸,信用借貸占33.6%,田地抵押占46.61%,房屋及其他不動產(chǎn)抵押11.65%,物品抵押8.38%。{59} 一些農(nóng)戶在債務(wù)的重壓之下被迫出售土地。{60} 大多數(shù)情況下,農(nóng)戶出賣土地并非通過一次交易來完成,常常要經(jīng)過抵押、典當、絕賣三個步驟。{61} 一些土地所有者在土地賣出去之際,還堅持保留耕作的權(quán)利,即所謂“田面權(quán)”。{62}
表2顯示,1931年與1912年比較,自耕農(nóng)略有減少,佃農(nóng)略有增加,半自耕農(nóng)沒有變化。在20年間,約有3%的農(nóng)戶從自耕農(nóng)下降為佃農(nóng)。1931—1936年間,自耕農(nóng)沒有變化,半自耕農(nóng)增加1%,佃農(nóng)減少1%。
珀金斯估計,佃農(nóng)占農(nóng)戶的百分比,1912年為28%,1917—1918年為27%,1930年代初為33%,1931—1936年為30%。{63} 可見,盡管入不敷出,債務(wù)繁重,但并沒有出現(xiàn)想象中的大批農(nóng)民破產(chǎn)。《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寫道:“在相對和平時期,中國經(jīng)濟表現(xiàn)出驚人的恢復力,顯示出傳統(tǒng)技術(shù)和地方化了組織擁有壓倒一切的頑強性的確切標志。”{64}
一部分農(nóng)民在債務(wù)壓力下失去了土地,一些農(nóng)民上升為富農(nóng)或地主。但是,對于力農(nóng)致富的小地主而言,其家庭的財富優(yōu)勢很難保持。一個重要的威脅來自分家制度,地主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維持一兩代人以上,然后就被別的家庭所替代。{65}
黃宗智指出,傳統(tǒng)中國農(nóng)村社會貧富差別的周期性變化與勞動人口/家庭人口比率的變化有莫大關(guān)系。盡管由于缺乏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資料,不能確切地知道最佳比率是多少,但最佳比肯定是存在的。超過這一比率,一個富裕家庭就開始了一個向下衰落的過程。在抗戰(zhàn)前的大部分時間里,并沒有出現(xiàn)大比例的農(nóng)民破產(chǎn)的問題,土地供給由農(nóng)戶平均人口壓力周期決定。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認為,在近代中國農(nóng)村,由于小農(nóng)生產(chǎn)的韌性,土地的供給會保持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規(guī)模上。土地價格的變化主要由需求來決定。
圖3顯示,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nóng)村地價整體來說是上漲的。但是,結(jié)合物價變化曲線,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抗戰(zhàn)前的大部分時間里,地價與物價基本重疊。說明地價的變化主要是物價變化所致。剔除物價的影響,農(nóng)村地價變化較小。1906—1928年期間,地價有較小幅度的漲幅。在1930年以后,農(nóng)村地價出現(xiàn)小幅下跌。由于這時物價有比較明顯的上漲,漲跌之間,彰顯出在30年代世界經(jīng)濟危機影響下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蕭條,契合了以往研究的看法。1935年前后地價漲幅又在物價之上,表明真實地價又在上漲。直到1937年后,地價才大幅上漲。1937年后地價上漲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通貨膨脹的影響。但是,剔除物價上漲部分,1937年后大部分時間里,地價也還是保持了上升的趨勢。這可能與數(shù)據(jù)來源有關(guān)。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數(shù)據(jù)主要來自于國統(tǒng)區(qū)。有資料表明,隨著大量游資涌入大后方,促使后方農(nóng)村地價上漲。{66} 根據(jù)重慶等13縣市1931—1943年數(shù)據(jù)計算,1937年之后的農(nóng)村地價比1937年之前的地價高出1.716倍。{67}
說明:地價指數(shù)變化趨勢根據(jù)《中國土地利用》表4、《中國各重要市縣地價調(diào)查報告》(1944年)合并計算并進行對數(shù)化處理后得出;物價指數(shù)變化趨勢根據(jù)《中國土地利用》表4、《中華民國統(tǒng)計年鑒(1948年)》表65合并計算并進行對數(shù)化處理后得出。
由于農(nóng)村土地供給保持在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規(guī)模上,地價主要由需求決定。抗戰(zhàn)前地價變化不大,說明這一時期的需求也基本保持穩(wěn)定。{68} 關(guān)于浙江、云南、河南、湖南等地的調(diào)查都表明,1928—1948年間土地向地主群體集中的趨勢并不顯著。{69} 珀金斯指出,這主要是因為20世紀出現(xiàn)了許多新興的有利的投資場所。但是,也許更重要的是,在20世紀土地并不是一個安全的投資方式。{70}
盡管民國時期土地集中趨勢沒有進一步加強,土地占有不平等問題依然是突出的。耕地在農(nóng)戶中分配的基尼系數(shù)是0.588;按人口分組后的計算結(jié)果是0.492。{71}
在城市化進程中,傳統(tǒng)士紳地主走向衰落。{72}地主階級分化為“鄉(xiāng)居地主”與“城居地主”兩大群體。“鄉(xiāng)居地主”由于小農(nóng)內(nèi)部經(jīng)過分化而形成,其購買土地的資金主要來自農(nóng)業(yè),大多是小地主,而且容易在人口壓力下走向衰落。“城居地主”往往都是中等及以上的地主。{73}
關(guān)于城居地主的報告大量見于當時的文獻中。{74}珀金斯寫道,被調(diào)查的8省37個村莊中,四分之一的耕地為本村人所有,四分之三的耕地為外村人所有。{75} 據(jù)金陵大學農(nóng)經(jīng)系30年代對鄂、皖、贛三省調(diào)查,居鄉(xiāng)大、中、小地主平均田產(chǎn)分別為892、200、57畝;居外大、中、小地主平均田產(chǎn)分別為1364、713、375畝。{76}
根據(jù)江蘇省民政廳1930年對514戶大地主調(diào)查的結(jié)果,軍政人員占27.23%,高利貸者占42.86%,商人占22.36%,資本家占7.45%。{77} 另外,在一些地方,土匪等惡勢力也趁勢崛起。豫西土匪猖獗,導致一些土地荒蕪,并逐漸為豪紳所控制。{78}
據(jù)珀金斯估計,地租約占到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量的30—35%。{79} 曹幸穗估計,舊中國蘇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佃農(nóng)消費21%,自耕農(nóng)消費42%,地租20%,賦稅7%,貸款利息4%,商業(yè)利潤6%。{80} 地主通常都是地主、高利貸與商人的“三位一體”。他們不僅壟斷了城鄉(xiāng)之間的貿(mào)易,又是高利貸的主要金主。{81}1930年對江蘇南部161戶大地主(1000畝以上)進行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117戶涉及到商業(yè)、金融或?qū)崢I(yè),其余44戶則擁有軍職或官職。{82}
調(diào)查表明,與鄉(xiāng)居地主比較,城居地主與農(nóng)民之間的關(guān)系更加疏遠。{83} 在華北,城居地主依靠所謂“中人”與農(nóng)民打交道。{84}在江南,城居地主通過“租棧”來管理佃戶。{85} 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關(guān)系越來越失去人情味,在此背景下,佃戶對地主的反抗大大升級。{86}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農(nóng)民抗租事件頻繁發(fā)生。在1922—1931年這10年間,從上海的兩家報紙《申報》和《新聞報》上,總共記錄下197起與地租有關(guān)的事件。{87} 1922年至1931年,江蘇共發(fā)生佃農(nóng)風潮125起。{88} 這反過來又會加劇地主群體對鄉(xiāng)村的疏離。
隨著地主精英從鄉(xiāng)下徙居城鎮(zhèn),諸如興修水利、農(nóng)村饑荒救濟等重要工作就無人顧及了,而在以往,這些事務(wù)均由作為社區(qū)領(lǐng)袖的大土地所有者承擔。{89} 在一些地方,這一現(xiàn)象直接導致了村政的惡化。{90} 杜贊奇指出,在華北農(nóng)村,由于不堪國家的賦稅勒索,“保護型經(jīng)紀”紛紛隱退,村莊領(lǐng)袖的位置被“贏利型經(jīng)紀”所取代。{91} 這是國家索取無度的結(jié)果,又反過來加劇了農(nóng)村的負擔。{92} 及至20世紀30年代初,江南地主不得不將地租收入的1/5-2/3向政府納稅。到國民黨統(tǒng)治的最后四年,地主更是每況愈下,稅收扶搖直上。{93}
在農(nóng)民反抗與政府賦稅榨取的雙重壓力下,土地所有權(quán)變得無利可圖。{94} 在這樣的壓力下,地主經(jīng)濟的擴張得到一定程度的阻遏。白凱將發(fā)生在江南農(nóng)村的這一過程視為地主階級“統(tǒng)治的動搖。”曹幸穗則將其視為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必然結(jié)果。在商品經(jīng)濟的初興階段,地區(qū)趨于集中,這時握有貨幣的富有者競相購買土地,而當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土地以外的工商業(yè)投資獲利更豐時,最富有的人非但不會添置田產(chǎn),還會變賣土地轉(zhuǎn)而投資于工商業(yè)。{95} 農(nóng)業(yè)成為一個單向性開放系統(tǒng)。不僅大部分農(nóng)業(yè)剩余,乃至農(nóng)村人才等都流向了城市。{96}
四、結(jié)論
在春秋時期,中國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就初步確立。在中國歷史上,關(guān)于土地產(chǎn)權(quán)的爭奪是激烈的。土地經(jīng)營方面,除了農(nóng)民的自耕外,地主土地主要是租佃經(jīng)營。莊園制經(jīng)濟,以及地主的自營土地在某些時候或地區(qū)出現(xiàn)過,但并不占據(jù)主導地位。究其原因,一是在經(jīng)濟上,土地相對于勞動力更加稀缺,農(nóng)佃競爭使地租一直高居不下,對地主而言,租佃經(jīng)營與自主經(jīng)營的收益差別不大。一是在政治上,由儒家思想所主導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制度設(shè)置,并不鼓勵地主階級致力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進步,而是汲汲于科舉仕途。
近代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發(fā)展。到20世紀上半葉,已出現(xiàn)了一個頗具規(guī)模的城市部門。這一城市化進程由兩個方面的力量所推動。積極方面的力量來自近代以來的工商業(yè)發(fā)展;消極的方面則是民國鼎革以后持續(xù)的社會動蕩。這樣一個獨特的城市化進程對地主制經(jīng)濟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商業(yè)產(chǎn)權(quán)價值相對于農(nóng)村產(chǎn)權(quán)價值大幅上漲,投資于城市工商業(yè)部門較之投資于農(nóng)業(yè)部門,獲利差別懸殊。在持續(xù)的社會動蕩中,城市不僅能為生命財產(chǎn)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還能為富裕人群提供高品質(zhì)的生活享受。所以廣大地主紛紛離開農(nóng)村,選擇在城市居住并投資。農(nóng)村精英與資本的流失,國家制度供給能力的缺失,使農(nóng)村政治生態(tài)惡化,農(nóng)村金融枯竭,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成本提高;同時,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在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周期的影響下,于各種天災(zāi)人禍之外,又增加了一層不確定性。不斷惡化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條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資本的逃離。因此,在土地經(jīng)營方面,租佃制繼續(xù)占據(jù)著主導地位。地主階級以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方式,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剩余輸入城市與工商業(yè)部門。
總之,20世紀上半葉的城市化進程,抑制了地主制經(jīng)濟規(guī)模的擴張,但并未能促使其向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方向轉(zhuǎn)化。地主階級通過租佃制和高利貸剝奪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剩余,轉(zhuǎn)而投向城市部門。農(nóng)業(yè)部門缺乏積累與投入,技術(shù)進步停滯,生產(chǎn)方式落后,生產(chǎn)效率低下。這不僅削弱了農(nóng)業(yè)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也使廣大地主頑固地堅持租佃制經(jīng)營,反映出中國地主制經(jīng)濟與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發(fā)展之間的尖銳矛盾。實踐表明,只有徹底摧毀地主制經(jīng)濟,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才有發(fā)展的可能。
注釋:
① 李根蟠:《“封建地主制”理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大成果》,《河北學刊》2007年第1期;江太新:《對明清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史研究中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方行:《中國地主制經(jīng)濟的經(jīng)濟強制問題》,《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3年第1期;盛邦和:《中國土地權(quán)演化及地主租佃、小農(nóng)自耕模式的形成》,《中州學刊》2009年第1期;李德英:《民國時期成都平原的押租與押扣——兼與劉克祥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鄭振滿、鄭志章:《森正夫與傅衣凌、楊國楨先生論明清地主、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利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2009年第1期;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5頁。
④ 王宜昌:《從農(nóng)業(yè)來看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轉(zhuǎn)引自余霖:《介紹并批評王宜昌先生關(guān)于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底論著》,《中國農(nóng)村》1935年第1卷第8期;趙槑僧:《中國土地問題的本質(zhì)》,《中國農(nóng)村》1936年第2卷第6期;卜凱:《中國農(nóng)家經(jīng)濟》,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第四章”;白凱:《長江下游地區(qū)的地租、賦稅與農(nóng)民的反抗斗爭(1840—1950)》,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高王凌:《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討》,《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薛暮橋:《現(xiàn)階段的土地問題和土地政策》,《中國農(nóng)村》1939年第6卷第1期;孫冶方:《財政資本底統(tǒng)治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國農(nóng)村》1935年第1卷第12期;陶直夫:《中國農(nóng)村社會性質(zhì)與社會改造問題》,《中國農(nóng)村》1935年第1卷第11期;余霖:《中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關(guān)系底檢討》,《中國農(nóng)村》1935年第1卷第5期;余霖:《中國農(nóng)村社會性質(zhì)問答》,《中國農(nóng)村》1935年第1卷第12期。
⑥ 羅曉翔:《土地回報與資本流動——從善堂投資模式看清末南京城鄉(xiāng)經(jīng)濟關(guān)系變遷》,《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洪璞:《鄉(xiāng)居·鎮(zhèn)居·城居——清末民國江南地主日常活動社會和空間范圍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輯;安寶:《地權(quán)流轉(zhuǎn)·不在地主與鄉(xiāng)村社會——以20世紀前期的華北地區(qū)為例》,《東北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等。
⑦ 胡煥庸等:《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版,第261頁。
⑧{63}{70}{73}{75}{79} 德懷特·希爾德·珀金斯:《中國農(nóng)業(yè)發(fā)展(1368—1968)》,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115、129、118、117、231頁。
⑨ 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頁。
⑩{11}{18}{20}{23}{24}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9、48、47、53、40頁。
{12} 蔡云輝:《城鄉(xiāng)關(guān)系與近代中國的城市化問題》,《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13}{19} 費正清、劉廣京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頁。
{14}{15}{16}{17}{21}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1輯),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第54、55、56、57、960—961頁。
{22}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第3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814頁。
{25}{26}{27}{28}{29}{30}{31}{33}{34}{39}{51}? 章有義:《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2輯,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第464—465、637、637—639、640—642、639、639、639、639、639、320、305頁。
{32} 薛暮橋:《江南農(nóng)村衰落的一個縮影》,《新創(chuàng)造》1932年第2卷第1、2期。
{35}{48}{50}{54}{78}{81}{83}{86} 馮和法:《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資料》(上編),上海黎明書局1943年版,第234、201、40—41、120、176、176、22—23、22—23頁。
{36} 章開沅、羅福惠:《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xiàn)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頁。
{37}{67} 中國農(nóng)民銀行土地金融處:《中國各重要市縣地價調(diào)查報告》,中國農(nóng)民銀行土地金融處1944年印行;上述數(shù)據(jù)由本人利用Eviews軟件計算得出。
{38}{77}{80}{85}{95}{96} 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nóng)家經(jīng)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70、50、70—71、36、51頁。
{40} 千家駒:《救濟農(nóng)村偏枯與都市膨脹問題》,《新中華雜志》1933年第1卷第8期。
{41} 章有義:《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2輯),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第609頁;《荒旱災(zāi)互為因果之河南》,《農(nóng)業(yè)周報》1929年第2期;《陜?yōu)钠嬷亍罚掇r(nóng)業(yè)周報》1929年第2期;《吳縣被災(zāi)田畝統(tǒng)計》,《農(nóng)業(yè)周報》1929年第2期。
{42} 章有義:《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2輯),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第609頁;姜君辰:《一九三二年中國農(nóng)業(yè)恐慌底新姿態(tài)——豐收成災(zāi)》,《解放前的中國農(nóng)村》(第2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389頁。
{43} 卜凱:《中國土地利用》,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版,第674頁,“第二十四表·農(nóng)業(yè)情形”。
{44} 汝真:《目前農(nóng)民最困難之兩問題》,《農(nóng)業(yè)周報》1930年第14期。
{45}{46}{61} 《中國經(jīng)濟年鑒》,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版,第332、324、343頁。
{47} 李若虛:《大冶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1054頁。
{49}{66} 葉懋、潘鴻聲:《華陽縣農(nóng)村概況》,《民國時期社會調(diào)查叢編(二編)》(鄉(xiāng)村社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1、723頁。
{52} 《中國經(jīng)濟年鑒》(民國二十四年續(xù)編),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第G114—117頁。
{53}{90}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2—74、284,280頁。
{55}{56}{59} 土地委員會編:《全國土地調(diào)查報告綱要(1934年)》,中央土地專門委員會1937年刊行,第50、51、52頁。
{57} 《農(nóng)情報告》(1934年1月1日),中國經(jīng)濟情報社編:《中國經(jīng)濟論文集》(第2集),生活書店1935年版。
{58} 馮和法:《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資料》(上編),上海黎明書局1943年版,第7—8頁;《中國經(jīng)濟年鑒》,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版,第334頁;《昆山縣徐公橋鄉(xiāng)區(qū)社會狀況調(diào)查報告書》,《民國時期社會調(diào)查叢編(二編)》(鄉(xiāng)村社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頁;李樹青:《清華園附近農(nóng)村的借貸調(diào)查(1933年)》,《清華周刊》1933年第40卷第11、12期等。
{60} 《中國經(jīng)濟年鑒》,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版,第342—343頁;《云南農(nóng)村調(diào)查》,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版,第89頁;馮和法:《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資料》(上編),上海黎明書局1943年版,第162、163—164頁。
{62}{82}{88}{89}{93}{94} 白凱:《長江下游地區(qū)的地租、賦稅與農(nóng)民的反抗斗爭(1850—1950)》,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31、19、312、19—20、330頁。
{64}{87}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9、281頁。
{65}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246頁;黃宗智:《華北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8頁。
{68} 《浙江省農(nóng)村調(diào)查》,學海出版社1933年版,第28—77頁。
{69} 《浙江省農(nóng)村調(diào)查》,學海出版社1993年版,第8、138、182、24、22頁;《云南省農(nóng)村調(diào)查》,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版,第78、129頁;馮和法:《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資料》(上編),上海黎明書局1943年版,第58、211頁。
{71} 根據(jù)《全國土地調(diào)查報告綱要》(中央土地專門委員會1937年刊行)第32頁“第21表·每戶所有面積大小各組戶數(shù)及總面積之百分率”計算得出。
{72} 馮和法:《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資料》(上編),上海黎明書局1943年版,第238、44頁;薛暮橋:《江南農(nóng)村衰落的一個縮影》,《新創(chuàng)造》1932年第2卷第1、2期。
{74} 章有義:《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2輯),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第303頁;《中國經(jīng)濟年鑒》,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版,第337頁; 《浙江省農(nóng)村調(diào)查》(1933年),學海出版社1933年版,第7頁;馮和法:《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資料》(上編),上海黎明書局1943年版,第24頁;葉懋、潘鴻聲:《華陽縣農(nóng)村概況》,《民國時期社會調(diào)查叢編(二編)》(鄉(xiāng)村社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頁。
{76} 金陵大學農(nóng)學院農(nóng)經(jīng)系:《豫鄂皖贛四省之租佃制度》(1936年),金陵大學農(nóng)學院農(nóng)經(jīng)系1936年刊行,第77—79頁。
{84}{91} 杜贊奇:《文化、權(quán)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nóng)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3、160—167頁。
{92} 江國權(quán):《安徽省蕪湖縣第四區(qū)第三鄉(xiāng)農(nóng)村調(diào)查》,《民國時期社會調(diào)查叢編(二編)》(鄉(xiāng)村社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頁; 章有義:《近代中國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2輯),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第566—571頁;卜凱:《中國土地利用統(tǒng)計資料》,轉(zhuǎn)引自葉美蘭:《1912—1937年江蘇農(nóng)村地價的變遷》,《民國檔案》1999年第1期;《浙江省農(nóng)村調(diào)查》,學海出版社1933年版,第11—12頁。
作者簡介:李鐵強,華中師范大學經(jīng)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湖北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張衛(wèi)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