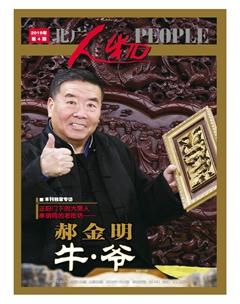查良鏞的遺憾(下)
(接上期)
那些曾追隨過他的員工們喜歡憶起他在《明報》時的往事。“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親自寫一份聘書給我。”潘耀明在還未辭去三聯書店職務的情況下就接下這份聘書。查良鏞不善言辭,在電梯里遇見人都羞于打招呼,對待下屬,他總希望下屬可以自己發現問題,來向他反映,而不是由他指出。假設問題實在嚴重到不行了,他便會遞一張紙條:某某兄,這個可否考慮這樣。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浙江大學的博士生無法適應他的“指導方式”。他不喜歡人家寫文章用成語,常講“用你自己的方式,淺白,不要故弄玄虛”。
1991年,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92年,傳媒業頹勢已現,查良鏞也到了退休的年紀,他決定找一個理想的接班人,便將明報集團控股權轉讓給商人于品海,套現了10億,辭去了明報企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職務。他希望繼續參與公司決策,在明報大樓仍保有辦公室。但到了1994年1月1日,他辭去了名譽主席,徹底切斷了與明報的聯系。
“后來(明報)有很多事情,查先生已經控制不了了,幾乎可以說是被架空了。他干脆辭掉了,那么對他心理上打擊也是蠻大的。”潘耀明回憶。離開了查良鏞的《明報》,從文字的水平、評論的角度,到新聞的采編水平.都變了味道,副刊更是不堪入目。大概10年前,張曉卿(明報現董事長)提到把明報交回給查良鏞來主導,查良鏞提出了一些嚴苛的條件,雙方沒有談妥。一位前下屬認為張曉卿做了錯誤的決策,因為查良鏞“懂得用人,會用人,懂得政治,他能夠妥協,而不出賣一些原則”。
生命最后的十幾年里,查良鏞從來不看《明報》。
查良鏞去世一周前,陶杰到醫院去探望他。人過九十,查良鏞想念家鄉,喜歡與幾個朋友講上海話,陶杰當時就用上海話,跟他匯報今天是幾月幾日,中美領導人最近的動向,貿易戰的最新形勢。喪失語言能力一年多,但聽到這些,查良鏞的眼神是亮的,“他非常關心的,嘴巴說不了,所以很慘。這么有思想的人,想象力這么豐富的人,到最后說不了話。”
陶杰感到很難過。近幾年,查良鏞的第三任夫人林樂怡擋掉了大部分訪客,朋友圈僅限于陶杰、倪匡、蔡瀾、李純恩和張敏儀等人。大家在一起,有時聊京劇,有時講上海話,聊《大公報》的往事、逝去的梁羽生、正宗的杭州菜—一查良鏞不喜歡吃小餛飩,認為那是給以前大戶人家的下人吃的。他仍喜歡看書,即使住院時也會看著書入睡。去電影公司看了《色·戒》,他很喜歡,也希望李安能來拍他的武俠。可惜,李安少年時代的臺灣,金庸小說仍是禁書,等到他拍過《臥虎藏龍》,也未再透露出拍武俠的想法,“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有緣無分,失之交臂。”陶杰說。
終其一生,查良鏞的本質是個熱愛自由的人,他不喜歡被人家管,但是熱愛自由的同時也一定要生存,因為不生存就沒法談自由。于是他學會了跟現實妥協,以極大的純真對現實抱有期待。少年喪父,中年喪子,可人死已不能復生。他非常有錢,也很有地位,盡管擁有了這些,他骨子里仍是個士大夫,愛人民、土地和文化,心系廟堂。“他的痛苦就在這兒……他覺得西方的民主不適合中國,但是有什么辦法,他又想不出來(別的)。”陶杰說。
他看重生存和身段,能忍,年輕時會把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寫進小說中:現實世界中,辦報紙被香港左派圍攻的孤獨和憤慨演變成《倚天厝龍記》里張無忌被八大門派圍攻光明頂和《天龍八部》中喬峰蕭峰契丹漢人兩面不是。一位友人說:“楊過、張無忌、喬峰、令狐沖、韋小寶都是他的不同的人格的折射,或者他理想的,他追求的……他怕人家看他的小說中毒,每個人都要做郭靖,所以弄出個韋小寶來,有時他又覺得這樣不太好,他自己也不確定,內心很多徘徊,掙扎。”
晚年時,種種遺憾涌上來,沒有寫成歷史小說,在浙江大學沒有當好博士生導師,在許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個學者,一生的心血《明報》最后背離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鏞如何與這些遺憾自處?在朋友們的描述里,他很糾結,一會兒是“他放不下”,“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一會兒是“很多都看破了,老實說看破了”,尋不到答案時,“就信佛啊”。
與陶杰的聊天在傍晚時分結束,他不斷感慨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很多人都走了,夏夢去世了,沒敢跟查先生講…… 在位于柴灣的明報工業大樓的一間辦公室中,掛著查良鏞的一幅字,字體干凈利落:看破、放下、自在……
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查良鏞還有一件放不下的事,他希望可以在老家海寧去世,但沒能如愿,他也想過死后可以安葬在澳洲,后來那里的房產被賣掉了,也不成。
11月13日,他的遺體在寶蓮寺火化,那里用的是柴火,整個過程要花8個小時。蔡瀾在給亦舒的信中寫道,“燃燒時發出濃煙,我們備得檀香木一塊,排隊走過火葬爐,把檀木扔進洞中。張敏儀因眼疾,要不斷滴眼藥水,這次也不顧煙熏痛楚,將整個禮儀行完。”查良鏞的骨灰被夫人帶回了家中。生前的種種遺憾,也隨著他一同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