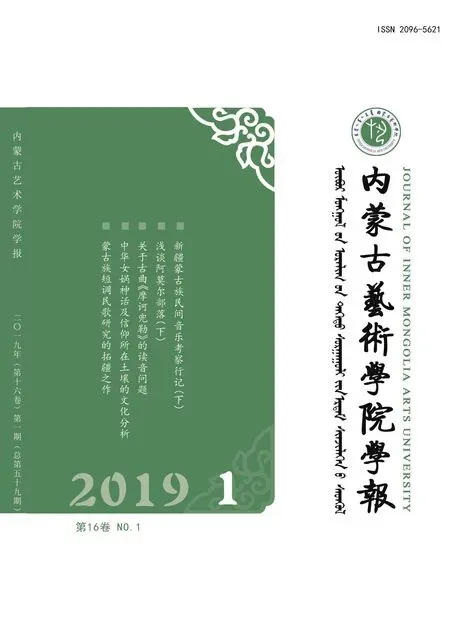5世紀晚期到6世紀早期中國藝術中的植物主題和卷草紋(上)
(美)蘇珊·布什 著,祁曉慶 譯,武志鵬 校
(1.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美國 波士頓 021382;2.敦煌研究院 甘肅省 敦煌市 736200;3.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公司 北京 100020)
最近在中國南方和北方發現的有關5世紀末到6世紀初的墓葬,使得藝術史家們可以在原本空白的藝術區域上標出明確的圖表。中國原本南北截然不同的區域性藝術風格現在可以更加精準地找到其對應的位置了,因為截然不同的獨特風格在墓葬或世俗裝飾中均有表現。去收集一個時期內具有平衡性的觀點也是可行的,迄今為止,對這一時期的藝術風格的認知主要通過北方石窟寺里保存的佛教造像。或許有樂觀主義者會認為各種形式藝術的影響力都可以以中國期刊發表的考古報告作為參照來加以描述。然而,如果我們能關注一些細節性的主題,那么可資利用的證據就 會變得更加具有說服力,例如彎曲的植物、風輪、放射狀、環繞的蓮花、卷曲葡萄藤狀的棕櫚葉和半棕櫚葉等。這么做的話,有人應該會將這種植物裝飾與超自然的創造物和飛翔的天神聯系在一起進行評論,這些植物紋飾裝點了貴族的車馬、宮殿、寺院和墓葬。
一、中國南方
南京和丹陽附近的南朝帝王陵墓的紀念碑上用來保衛“靈魂之路”的獸紋長期保存著最原始的藝術題材類型,這些藝術題材是從南朝首都發起的。1960年,在南京西善橋墓室中發現了“竹林七賢和榮啟期”題材的模塑磚。接著,1965~1968年,在丹陽縣發現胡橋墓和建山三個大型的石磚墓,這個區域埋葬有南齊宗族墓和梁天子墓。這批墓葬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發掘的胡橋墓,在保存最完好的墓室墻壁上有一幅“仙人戲虎圖”,非常引人注目。
南朝時期(420~589)在臨近南京和丹陽的帝王陵墓中長期保存著護衛“靈魂之路”的不朽石獸,這是由南朝首都發起的藝術類型原始的證據。到1960年,在南京西善橋墓墻邊發現的一塊刻有“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的模磚。[1]時代更近一點,到了1965和1968年,在丹陽胡橋挖掘出三塊大的墓室磚,這個地方是由南齊(479~501)宗族統治的區域,也是梁朝皇帝(502~557)的墓葬區域[2]。這個墓最著名的是1965年考古過程中在墓室西壁發現的一幅“仙人戲虎圖”。

圖1①
據《文物》1974年第2期刊載,這個墓葬習慣上被認為是齊成帝修安陵或者蕭道生陵墓。公元479年,在他死之后不久他弟弟也去世了。蕭道生的兒子,蕭鸞(459~498),也就是齊明帝,在11位王子為爭奪王位相繼離世后的494年即位。495年,他將他父母的墓移至帝后陵,并將他們的墓命名為修安陵。自從發現此墓葬為夫妻合葬墓,并且與惠安有關的文獻記載也與這個區域相符后,考古發掘報告的作者暫且接受了這一傳統觀點,并且根據墓室結構將墓葬的年代定為478年。[3]然而,與南方其他類型的墓葬相比,這個墓葬群規模較大,可能表明蕭道成在494年之后以帝陵的規格重新安葬其父母。無論如何,這種在墓道入口處放置石獸的方式被認為是南齊風格(圖1),就目前所看到的,在破損的出土物的配置或表面裝飾方面都與498年護衛蕭鸞的惠安陵不太相似。[4]

圖2,3
如果有人對比這些墓室當中的神獸和老虎,會看到它們頸部明顯的S曲線、具有動勢的毛發或小而卷曲的翅膀,這些都說明塑造者試圖在石頭上對已有的圖像設計的線條傳統進行再創造。然而,在胡橋墓壁畫中,老虎的這種瘦的、身體扭轉、翅膀像火焰一樣,并且向后傾斜的鬃毛和胡須都用不同的方式進行了刻畫。在這件作品中,白虎作為西面方位的動物,被其他神靈護送,它們代表了南方區域內一種折中的趣味和信仰。在老虎不遠處是道教仙人或卷發“羽人”,羽毛裝飾表明了他的超自然屬性。這件作品讓我們想到了漢代晚期或者漢代以前的模型。例如雕刻在沂南畫像磚上的3世紀時期的神仙與鹿的形象。[5]但是“羽人”現在已經穿上了束腰外衣與短褲,規則的頭部造型與他高而傾斜的前額和瘦肖的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圖2,3)。

圖4
翱翔于老虎背上方的是兩身名侍從,其形象截然不同,向上飄揚的綬帶強化描繪了它們瘦而彎曲的身體和右側腿部。正如天神或神仙,是一種中國的佛教飛天或飛仙,相似的形象還將出現在6世紀20年代的北朝石窟寺甬道、壁龕或天頂部位,方形頭部和瘦長型的身體與垂飾都是這個時期比較流行的特點。第二身手持淺盤的侍從似乎正在向空中散花或者珠寶(圖4),在他之后明顯有第三個形象正在演奏樂器,但是卻缺失了。[6]
這種扭轉的漩渦形植物讓我們想到佛教典籍中曾經提到的吉祥花雨,正如風吹云氣的紋樣表示蒸汽一樣,或者與漢代藝術中超自然王國有聯系。這些松散的草圖和點狀結構的云氣給人以書法的效果。這里的引導者是一名鳥人,他類似孔雀一樣的尾巴從衣服中伸出來,關于這種擁有西方天使翅膀一樣的鳥的最不平常的解釋,是認為它可能是緊那羅,即佛教凈土世界中的音樂神。[7]
雖然這件作品中的圖案被認為很可能具有西方來源,但是他們穿著具有中國風格的長袍,正如南方佛教最終融合到新道教思想中一樣。[8]也因為這件作品仍然具有漢代動物的保護和吉祥意義,所以僅有的極其微弱的有關佛教的元素只有他的飛翔姿態和后面的蓮花造型。在這里我們首次遇到用凌亂的植物造型填充壁面的做法,這最有可能說明它屬于南方風格。另外,位于墻壁更低一層的侍者形象的設計,只有“儀仗隊”展示了騎在馬背上的演奏者頭頂上有卷草紋樣,或許表明音樂的精神力量,也可能只是簡單地在人物形象上方起到填充空間的作用。通過與1968年發掘的南京丹陽墓室相比較,可以推測這種相似的地面裝飾毫無疑問也出現在已經殘缺的天神與獅子的設計中,或者名為特殊主題的畫像磚題記中。[9]

圖5
在“仙人戲虎圖”的底部發現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植物圖案。最流行的應該是可以稱之為“卷草”的紋樣,從蓮花的側面看,可以看到在不同階段隨著空氣流動的線條和隨風擺動的植物。仙人左側大約與腰部等高的位置下方是另一種由八瓣花葉環繞而成的圖案,樹葉和花朵從外環的八個邊伸出來(圖2)。如果這些葉片數量增加或者從一個方向轉動,它們將變成一種完全全新的“植物風車”樣式。這些圖案在當時被當做一種簡單的時尚以便很容易理解它們的組成部分。在之后出現的派生圖案中,它們逐漸變得復雜和松散。例如,1968年發現的兩個丹陽縣墓葬中的其中一座,雖然其護衛石獅拓片還沒有公開出版(圖5),但是可以看到這種卷草紋樣獲取了更多的植物拖尾,并且隨意地用氣體漩渦構思,甚至變成了打開的卷。[10]

圖6
這種復雜的版本接近裝飾了著名的鄧縣墓主題的卷草概念,在這里額外的植物紋樣已經被改造成了似乎可以快速旋轉的水波紋。而鄧縣墓的身形矯健的白虎與來自胡橋墓壁畫中的畏獸十分相似,這種植物填充物啟迪人們描繪出更復雜和更加簡化的樣式(圖6)。任何部分在品質上的不同都自然可以被地解釋為胡橋多室磚結構墓葬和寬度僅有15英寸的鄧縣單室墓葬在規模上的巨大差異。同時,鄧縣墓(圖7)的這幾種不同類型的植物風車造型證明了一種對繁茂和具有獨創性的植物形式的興趣。[11]然而任何有關鄧縣墓圖案與丹陽圖案設計之間關系的最終結論都必須延遲至對南方墓葬的其他類型裝飾題材的綜合考察之后。

圖7,8
胡橋墓中滿布的裝飾逐漸內收并趨向幾何形,最后提供了一系列更早時期的裝飾形式。裝飾的磚畫,占滿了沒有被使用的墻壁空間以及不太規則的邊界部分,最普通的裝飾是連續環繞的圓形蓮花。一對六瓣變體植物紋樣可以用來裝飾垂直磚塊的末端,或者將兩塊磚首尾相連形成一個規則的模型,在更高浮雕上面用來保持更大規模的八瓣蓮花形設計。[12]更早一點的最初版本的設計也出現在這里,是一對連接在一起的疊壓的長方形五銖錢。三排水平鋪砌的畫像磚與垂直放置的磚層交替出現。(這種典型的系統結構也證明在大型繪畫作品中,可能已經被設計者采用特定的規格尺寸。)這些水平方向磚塊指向一種疊加成鉆石形狀的恰當的十字形剖面,但是這種瘦長的框架被連續環繞的花形或者硬幣形分成更小的單元放置在每一個末端。中間一排被隨意地用一種構思更加自由的植物藤蔓裝飾,這種藤蔓裝飾更接近于在克孜爾看到的內部為植物的連續的橢圓形設計,[13]但是其中有一支花蕾指向一邊(圖8)。
除了上一種形式之外,這個墓葬的裝飾圖案顯示了典型的南京地區的本土特征。在首都附近的非帝國西晉墓已經生產出了與301和308年一致的模印磚。這種磚裝飾有幾何菱形和吉祥硬幣,以及最小畫幅的龍、虎、鹿和鳥等繪畫。[14]

圖9
畫面中更有趣的是東晉墓葬(萬壽村1號墓)中已經模印出了寫有公元348年紀年的銘文,正如拓片上看到的一樣;磚末端的龍可以由上述模制磚上的圖案加以印證。三塊垂直放置的磚末端被連接起來形成了四身坐著的非常寫實的彎腰駝背的老虎形象,每個角落各一只,傳達出“虎遨游在山上”的寓意[15]。在一個小規模墓葬中這些設計引領了南朝多室磚畫,在這種多室墓葬內的圖像被繪制成突起的浮雕線條和主題,如七賢,并標注了名字加以識別。348年墓葬中的其他類型的裝飾包括了面具、一種傳統形式的十字形對角線(圖9:1,4,5,6),以及報告中提到了但是沒有詳細闡釋的一種粗糙的不成熟的蓮瓣設計。后者是對植物圖案沒多大興趣這個區域中的部分線索之一,這種植物圖案變成了南朝裝飾紋樣的主要內容。與之并列的南京新寧1號工廠墓模制磚拓片闡釋了6世紀早期流行什么紋樣的問題(圖9:2,3,7,8)。一對頭向下嘴里銜著植物的龍和植物風車邊飾讓我們想到了鄧縣磚的設計。“從怪獸面具到植物裝飾”似乎顯示了南方風格的一種明顯的轉變。然而,這樣的推論很可能會誤導讀者,因為我們可以從3世紀沂南畫像磚墓的邊緣和臉部看到這種原本是怪獸面具,而如今轉變為蓮花圖案的例子,山東墓葬可以為這兩種幾何裝飾樣式和2個世紀之后的胡橋磚墓八瓣蓮花樣式提供一種便利的資源。[16]
可以肯定在4世紀晚期,植物圖案在南京地區站穩腳跟,這一點從刻有384年紀年的墓葬外部中山門上呆板的八瓣蓮花側面的兩根軸線可以判斷出來。[17]另外,幾何形在串聯的銀幣圖案的變異中處于優勢地位,這種串聯的銀幣圖案出現在象山墓王氏家族392年夏金虎墓中。[18]報告描述了一種環繞的八瓣設計,疊加在對角平分線上,作為一種花瓣樣式,但它不是南齊成熟的環繞蓮花的形式。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來自東晉墓葬,這個墓葬是1972年在湛江發現的,模印磚上面有398年銘文紀年,后來知道是金口,“首都口岸”,坐落于南京北部丹陽的揚子江畔。而更小的畫像磚是用較為平常的代表幸運的錢幣、動物或者菱形圖案設計的,更大的方形圖案被延伸至墓室墻壁之外,就如鄧城一樣。[19]與居住于Shan-baicbing的奇形怪狀的動物相比,這種主題在特征上顯得比較保守:僅描繪了漢代的四個方位動物,吉祥鳥神,怪獸等。[20]然而,用超自然神靈的方式進行構思是南朝風格的前兆,它特別強調從頭部到胸部之間瘦長的S形頸部所表現的奔跑姿勢。

圖10
值得注意的是那種植物裝飾在這里仍然是極少數,僅僅出現在固定的主題中:如同羽毛一樣的卷草圖案作為具有吉祥含義的鳥神的邊飾和松散彎卷的朱雀裝飾。對于這四個方位神獸,朱雀仍然以伸展的翅膀、抬起的腿,下垂的尾部為標志,但是白虎和與它配對的綠色的龍一樣,被設計雕刻成C形,使得它們伸長的身體看起來是作為整體處在一個方形或者矩形的格套中(圖10-1,2,3,4)。6世紀對龍圖像的使用呈下降趨勢,他們具有相似的身體特征:腿部瘦而且彎曲呈斜面展開,尾部交叉。而下方的這兩種鳥神作為一種奇怪的配對方式出現在520年北魏碑刻和朝鮮墓葬壁畫中。一般而言這些圖像沒有任何與佛教徒有關的元素,在這些墓葬裝飾中也沒有任何西方影響的蹤跡。
現存的第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具有外來卷草樣式的畫像磚來自南京地區,圖案中似乎應該有半棕葉形的波狀葡萄紋,和有著清晰明確的節點裝飾的西善橋墓中著名“七賢”作品。[21]這種類型的畫像磚首尾相連形成一幅連續的卷軸畫(圖11)。(兩行這種形式的磚與下方顛倒樣式形成一個雙層的半棕葉形的卷軸畫。)這個設計明顯受到來自西方物品的影響,[22]并且預示了這種花飾的統治地位。在一系列由帝王家族成員構成的南朝墓葬中,西善橋墓成為首選的研究對象。因為它的建筑和繪畫設計呼應了丹陽附近的南齊胡橋墓,它令人信服地構建了一個劉宋(420~479)統治下半個世紀或更早時期的裝飾風格,新出土的隨葬品無論如何都不會比五世紀中期晚。[23]著名的“七賢”畫像磚圖像代表了肖像畫作中的高峰時期,但這并不等于它們能被后來的帝王墓裝飾所采納。然而,這種植物裝飾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并不是佛教的花雨降落在新式道教的圣賢身上,除半棕櫚葉卷形外,傳統的銀幣和菱形樣式繼續裝飾其他的磚畫。然而,目前,南齊胡橋墓“仙人戲虎”壁畫首次說明這種發展了的植物主題在這個首都區域備受喜愛。
從1961到1962年在南京西善橋發掘的大墓判斷,后來南齊帝王墓的裝飾其實十分保守。因為它所在的位置和墓葬的規模,被認為很可能是陳獻帝。若果真如此,之后的近一個世紀,這種墓葬的內部裝飾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缺乏創新可能是時代萎縮的一個反映。
在入口處留存下來的僅有的這副獅子圖像也部分被破壞,它的后半部分與1968年發掘的大型丹陽墓葬里的獅子拓片非常相似,[24]但是空間設計明顯縮小了,因為卷曲的植物裝飾磚代替了它,并且空白區域填充了環繞蓮花主題。墻壁表面這些重復的六到八瓣的花兒整齊劃一的影響持續地被位于水平線磚層上的幾何交叉線的偏好所強調。
1971年到1972年在韓國光州宋山里發掘的公元525年的百濟武寧王和他妻子的合葬墓提供了這種聯系,說明這種形式的磚在6世紀時繼續被使用。這位韓國國王501年至523年在位,曾經于512年至521年之間送使者到健康并被梁武帝授予百濟大將軍的頭銜。墓葬墻壁上沒有出現畫像作品,墓葬的建筑也僅僅與南朝中國的墓葬模式近似。[25]但是畫像磚是以南齊的形式裝飾的,除了六瓣花朵外,似乎已經完全替代了五銖錢和植物樣式,而代之以八瓣花上的對角線設計(圖12)。然而這些改變一定既反映了梁代(502~556)的內部裝飾,也反映了韓國地方的偏好,但是如果將之與此時期中國南方其他地區繁復的植物主題進行比較就沒有什么必要了。

圖11,12,13
有更早的證據表明,湖南和云南地區從漢代一直到北朝,在蓮花形式方面仍然保持強烈的興趣。例如,長沙出土東漢墓畫像磚已經用一種可識別的四瓣花瓣圍繞的縱橫交錯的植物樣式進行裝飾。[26]位于云南省的東晉昭通后海子石墓非常有趣,時間大約是公元386年到394年之間,壁畫上繪有漢代六瓣和十二瓣花葉組成的呆板的蓮花,以及類似羅盤設計形式的卷云紋中的四個方位神(圖13)。這種原創性的藝術特征非常顯著,黑色龜背包裹的像一個手榴彈,旁邊還有像蛇一樣的蓮花,但是這種壁畫可能是目前在四川成都發現的一種形象化的區域性版本,在這里死去的霍彪首次被埋葬。[27]換句話說,有趣的是昭通附近發現的東漢墓幸運錢樹展示了幾種側面的蓮花輪廓。[28]但是這些例子也不能解釋植物裝飾圖案突然出現在5世紀末的原因。
長沙的劉氏家族墓的時代與499年的南朝2號墓葬一致,壁面水平磚層缺乏幾何形狀,并且與在丹陽發現的環繞蓮花主題一樣繪制得非常呆板。它們稱之為“花鬘”的卷曲的藤蔓裝飾紋樣從底部到天頂覆蓋了起來,非常具有裝飾特征。

圖14,15,16
畫像磚拓片[29]能夠使我們再一次看清卷曲的半棕櫚葉形狀,在棕櫚葉中間部分,每一片葉子都被延伸,尖端彎曲,與早期西善橋墓中的同種類型相比較而言,形式似乎變得更加細長。在右邊,以一種迂回蔓延卷曲的形式,十二片花瓣以來自古典遠東地區的忍冬紋相間隔,其中的棕櫚葉飾側面為兩片半棕櫚葉形,但卻并不是采用環繞藤蔓而彎曲的形式(圖14)。仔細觀察這些壁畫圖片[30],會發現當這種卷曲樣式水平延展時,在畫像磚的尾端會出現一種垂直型的不同的設計樣式:在這里,植物,包括棕櫚葉在內,兩側被兩片半棕櫚葉形上下輻射形成一個中間十二瓣的花形(圖15)。與此相似但是更小一些的設計類型出現在長沙北部偏東邊的湖北省武昌市郊區的一個南朝墓葬畫像磚的末端[31]。雖然這座武昌墓葬年代不明,但是奢華的花飾品味被武昌發掘出的485年編號為193的鑲嵌有多層蓮花瓣的陶器和兩簇半棕櫚葉卷曲形的墓碑復制了下來[32]。在年代未知的畫像磚拓片上,還可以看到一種不尋常的六瓣花飾,和包含有六瓣花飾變體的不同類型的卷曲裝飾(圖16)。這兩種新形式在520年的梁墓碑刻中也有發現[33],其中一個是棕櫚葉形藤蔓,另一個應該是一種沿著垂直方向重復的棕櫚葉形式附以藤蔓卷須從半棕櫚葉背面向下彎曲(圖17)。
后來對這種卷曲藤蔓的界定,母題更加自由并且傾向于不再具有連貫性。這一觀察符合來自南京附近的新寧工廠1號墓和鄧縣墓的設計(圖9:2,3,8)。在這種奢華的花飾成熟期,風車設計中從中間蓮花輻射出彎曲的植物的設計方式變得非常流行,并且花葉植物經常出現在邊緣。尤其是在鄧縣墓畫像磚上的奢華植物裝飾非常令人震驚[34]。但是可能它代表了從長沙南部到武昌這一地區的奢華裝飾傾向的高潮。例如,鄧縣墓的忍冬藤蔓(圖18:中心)、棕櫚葉和半棕櫚葉在稠密的垂直方向的葉形裝飾中顯得不再那么易于識別了。

圖17,18,19

圖20-1,2 圖21
位于墓室背面每一側用多重拼磚構成的鎮墓武士,大多數被有機構成的花葉形式交織的旋渦主題所圍繞,具有強烈的暗示性意味。這種設計(borrorvacui)預示著唐代旋渦形裝飾無處不在,但是它仍然是由獨特的單個元素,如植物、花瓶等組成,旋轉花葉不再正式融入到520年以后的波卷紋中(圖19)。在其他鄧縣墓拼磚結構中,某些植物樣式或者花葉邊沿有一個相對簡單的自然主義的特征,比如位于兩身歌唱永生的鳥神之間的植物以及位于一位仙人兩邊的植物(圖20-1,2)。然而,這些形式很顯然不是來源于自然,而是來自更早期的藝術形式,這可以從雕刻在江蘇蘄州漢墓和來自中國道教題材的帶翼麒麟或獨角獸和跪姿仙人的花紋輪廓中判斷出來(圖21)[35]。鄧縣墓拼磚既沒有這種植物也沒有彎曲的花紋邊沿,而是有夸張變形的早期曾被描繪過的像是被風吹彎的植物樣式。這種更加靜態的裝飾主題似乎成為520年梁朝“火紅花束”風格的前驅。
對這種程序的有限的討論還在持續開展著。這種特殊裝飾主題的分析自然不足以接近鄧縣墓拼磚的時代,因為歷史環境、墓葬結構和陶俑也必須作為和其他所有形式主題一樣來進行研究。這種綜合性方法已經被劉涵和安耐特·朱莉諾(Annette Juliano)的研究所采用:但是精確研究鄧縣墓的建造過程仍然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位于湖南邊界地區的南方政權控制之下,498年在北魏政權手中[36],甚至很難去給它安置一個時代標簽,因為它很顯然是南方風格,被認為屬于5世紀晚期南齊時代,那么與它同時代的丹陽相關材料的關系也必須進行解釋。正如已經被爭論的,刻有“仙人戲虎”圖像的胡橋墓的年代似乎更可能是495年左右,而且它的背景圖案顯示出“最早期”的花朵意向形式,這種樣式也同樣出現在鄧縣墓。因為較晚期的丹陽材料(圖5)更接近鄧縣墓主題風格,有研究認為這種裝飾紋樣進一步延續到了6世紀早期。另外,胡橋墓拼磚中的彎曲植物和植物風車的區別可能是接近這些主題本源的結果,南方首都的繪畫設計和帝王墓葬設計中的保守傾向,正如582年的鎮江墓一樣,可能甚至在諸如胡橋墓等更高級別的帝王墓裝飾設計中都已經成了固化的形式。當有更多的證據來證明這一結論的時候我們應該將諸如此類的考慮都放在腦海里仔細斟酌。如果鄧縣墓拼磚上這種類型的花飾比南齊丹陽墓“仙人戲虎”圖(圖2~4)和499年的長沙墓的例子(圖14)更發達一些,那么它的時代仍然不可能晚于6世紀早期,(這一點)從南京附近的梁墓遺跡之一的蕭弘(死于526年)墓石碑雕刻設計就可以判斷出來[37]。這種復雜結構的拓片中可以看到,一對飛身向下的龍面對石碑背面的洞,而上部位于蓮花基座上的蚩尤怪獸支撐著一個拱形頂,在它兩側兩身脅侍獸昂首闊步似乎要表達什么。這種擺動的姿勢在中國南北朝時期的520年和似乎是6世紀早期漢代類型的出土物中非常流行[38]。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還沒有出現在鄧縣墓的主題中。此外,這種主題可在地面看到,例如植物隨著葉片的紋路卷曲,似乎更加優美,比鄧縣墓中相互纏繞的設計或者丹陽墓類似的卷曲形式更加弱化。兩側面的植物伸向下方,到達三身飾有珠寶飾品的佛像兩旁,比鄧縣墓相對簡單的花葉植物更加復雜且細長。

圖22
在佛教文本中,疊加的蓮花植物作為普陀山石碑佛陀背光部分的裝飾[39]。但是蕭弘石碑的設計是基于單一的刻在不規則火焰紋末端的棕櫚葉和半棕櫚葉植物形式。與他們同時期的純粹的裝飾形式而存的金色放射性花紋可以與百濟武寧王帽子上的裝飾聯系起來(圖22)。這里,蓮花和棕櫚葉形式連接在一起形成一種非常漂亮而又時尚的風格,在韓國裝飾中,散落的黃金墜飾可能是模仿水滴的造型而形成的。這種創造反映了520年左右梁代朝廷的最新樣式,這個紀年雕刻在這座墓出土的一個銀手鐲上面[40]。無論如何,在蕭弘墓碑上這種放射紋是由規則和不規則線形作為豐富的植物主題。類似的不同類型的中國裝飾都毫無疑問位于不久后就被劫掠的南朝帝王墓中。不幸的是,武寧王的財富只是保留下來的其中一部分,它可以煥發南方裝飾藝術的異彩。在這一方面,最近在中國北部的的考古發現更進一步展現了出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