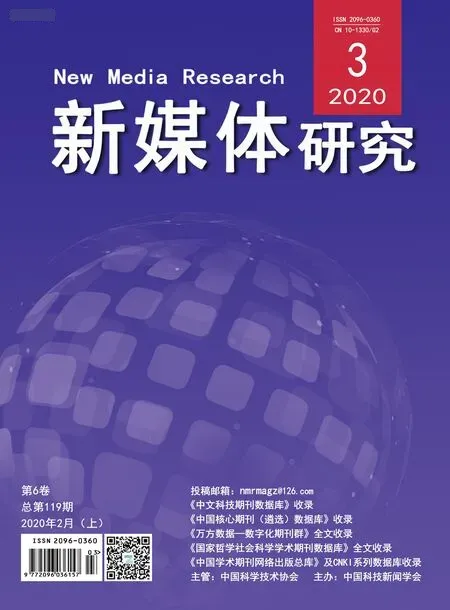網(wǎng)絡(luò)輿論“糾偏”的再認(rèn)知:基于“共識(shí)”視角下的反思
黃柄瑞
摘? 要? 伴隨著媒介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媒體格局的多元化趨勢(shì),網(wǎng)絡(luò)輿論作為當(dāng)下部分公民意見(jiàn)主要的集合體,在代表著公民新聞的自媒體和傳統(tǒng)權(quán)威的官方媒體之間的議題互動(dòng)形成的討論空間里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此引發(fā)了對(duì)輿論引導(dǎo)和糾偏、輿情治理的探討和反思。而輿論作為部分群體意見(jiàn)的結(jié)合體,必然體現(xiàn)了這一部分群體所包含的價(jià)值觀、世界觀的內(nèi)涵,當(dāng)看到了這個(gè)認(rèn)識(shí)機(jī)制下支撐觀點(diǎn)表述的核心所在,我們應(yīng)意識(shí)到:所謂的輿論的糾偏和引導(dǎo)是對(duì)一種共識(shí)機(jī)制的尋求和表達(dá)。基于此,對(duì)于新媒體下輿論生態(tài)的建構(gòu)成為了對(duì)共識(shí)實(shí)現(xiàn)途徑的探索和反思。
關(guān)鍵詞? 網(wǎng)絡(luò)輿論;媒體;議題互動(dòng);共識(shí)
中圖分類(lèi)號(hào)? G2?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 ? 文章編號(hào)? 2096-0360(2019)03-0017-03
輿論作為傳播研究的主體之一,在各種現(xiàn)實(shí)的環(huán)境影響因素下逐漸被賦予了新的內(nèi)涵,而網(wǎng)絡(luò)輿論作為我們社會(huì)的主流輿論[1],為我們豐富了表達(dá)渠道的同時(shí),也向我們提出了嚴(yán)峻的挑戰(zhàn)。在面對(duì)輿論“失范”對(duì)社會(huì)所造成的沖擊時(shí),大多數(shù)學(xué)者通過(guò)對(duì)輿論涉及的主體、生成機(jī)制以及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的分析提出了對(duì)輿論的引導(dǎo)和規(guī)范化治理。
在吸納了已有的輿論研究成果和觀點(diǎn)后,筆者認(rèn)為當(dāng)下輿論的治理方向在于對(duì)輿論生態(tài)的規(guī)范化建構(gòu),并且跳脫出傳統(tǒng)精英傳播的一元觀點(diǎn),通過(guò)傳播過(guò)程中出現(xiàn)的問(wèn)題的反思實(shí)現(xiàn)對(duì)“共識(shí)”進(jìn)行表達(dá)途徑的探索。這一探索目前主要針對(duì)以下三個(gè)層面:一是作為輿論主體的大眾,二是作為媒介的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三是作為整體傳播環(huán)境的媒介生態(tài)。
1? 輿論主體:明晰“共識(shí)”的核心碎片
媒介賦權(quán)下的網(wǎng)絡(luò)輿論傳播,主要呈現(xiàn)出了自由性與可控性、互動(dòng)性和即時(shí)性、豐富性與多元性、隱匿性與外顯性、情緒化與非理性、個(gè)性化與群體極化性等主要特性[2]。
而在對(duì)輿論的糾正性討論中,輿論主體所呈現(xiàn)出的情緒化與非理性成為了輿論治理的著力點(diǎn)之一,但如果籠統(tǒng)的將這些過(guò)錯(cuò)歸咎于“情緒化偏向”“非理性”“去專(zhuān)業(yè)化”似乎太過(guò)輕率。
從輿論主體的傳播層面來(lái)看,術(shù)語(yǔ)“公眾”向“大眾”的轉(zhuǎn)變暗示著文化由批判向消費(fèi)的轉(zhuǎn)向。而這與大眾傳播技術(shù)帶來(lái)的傳播手段的革新是分不開(kāi)的。科技的發(fā)展在傳播渠道上為我們提供了日益豐富的選擇,特別是從當(dāng)下各個(gè)媒體平臺(tái)的行動(dòng)上看,不難看出傳播科技與個(gè)人主義愈加糅合的趨勢(shì)。而作為傳播主體的“人”對(duì)于交流的渴望卻是由來(lái)已久的,人們通過(guò)交流和表達(dá)不僅為了溝通和促成社會(huì)行動(dòng),同時(shí)也是一種自我的表征(represent),這種欲望和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的碰撞產(chǎn)生的是更加多元的言論場(chǎng)域,同時(shí)也意味著更多的矛盾。傳播門(mén)檻的降低讓我們無(wú)時(shí)不刻的擁有一個(gè)“喇叭”,很多時(shí)候讓我們拿起“喇叭”的動(dòng)機(jī)并非是對(duì)一件事物進(jìn)行客觀、理性、全面的分析,而是看待事物的傳播欲望和共情效應(yīng)將人們聚集在一起。
所以對(duì)許多公民新聞進(jìn)行“新聞專(zhuān)業(yè)主義”層面的批判反而讓我們陷入了一種專(zhuān)業(yè)主義的怪圈:即媒介賦權(quán)下公民強(qiáng)烈的傳播欲望和由于媒介素養(yǎng)的不足導(dǎo)致的亂象之間的沖突,而對(duì)于“新聞專(zhuān)業(yè)主義”的極盡強(qiáng)調(diào)實(shí)際上站在了這種傳播欲的對(duì)立面,并未在這矛盾的二者之間開(kāi)辟出一條合適的道路。在意識(shí)到這是媒介技術(shù)進(jìn)程發(fā)展下所衍生的問(wèn)題時(shí),我們須以更加審慎且積極的態(tài)度去直面它的不足,而不是在媒介生態(tài)的劇烈變革中再以過(guò)去的框架去討論其發(fā)展。一味的強(qiáng)調(diào)(傳統(tǒng))“新聞專(zhuān)業(yè)主義”實(shí)際上是我們?cè)诿鎸?duì)新媒體賦權(quán)之下由于無(wú)力掌控輿論勢(shì)態(tài)的方向而做出的一種防御性回避,通過(guò)使用過(guò)去的框架將我們暫時(shí)束縛在一定的理想的可控范圍內(nèi),但這并非長(zhǎng)久之計(jì)。
回到輿論本身,其作為部分群體意見(jiàn)的結(jié)合體,必然體現(xiàn)了這一部分群體所包含的價(jià)值觀,世界觀的內(nèi)涵。輿論的偏向性并不等同于失范性的輿論,健康的輿論發(fā)展本身就包含著不同觀點(diǎn)的相互探討和佐證。而基于這種觀點(diǎn),所謂的輿論的糾偏和引導(dǎo)就成了把握潛藏在輿論表述之下的群體性“共識(shí)”的表達(dá)。通過(guò)拓寬公民言論表達(dá)的自由度,理性的看待建立在一種觀念認(rèn)同上的輿論主體,深度挖掘這一觀念的核心所在,避免由于偏見(jiàn)導(dǎo)致寬容度的不足,才能實(shí)現(xiàn)對(duì)“共識(shí)”的明晰和肯定。
2? 傳播媒體:議題互動(dòng)下把握“共識(shí)”的關(guān)鍵
在對(duì)網(wǎng)絡(luò)輿論的生成機(jī)制的研究中,無(wú)疑都將焦點(diǎn)指向了新媒體,這種指向來(lái)源于新媒體的出現(xiàn)本身打破了傳統(tǒng)大眾傳播的一元格局,它通過(guò)提供媒介技術(shù)來(lái)使得公眾可以從自身出發(fā)實(shí)現(xiàn)議程設(shè)置,并通過(guò)“共鳴”(轉(zhuǎn)發(fā)、評(píng)論、點(diǎn)贊等行為)來(lái)實(shí)現(xiàn)極大的傳播效果。而也正因如此,新媒體傳播在相當(dāng)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高度的自由化,突破了傳統(tǒng)媒體對(duì)于話語(yǔ)權(quán)的壟斷,當(dāng)這種自由化和傳播主體本身的傳播欲望高度重合時(shí),所展現(xiàn)出的便是輿論的多樣化和多極性。而在這樣程度上的多元化同時(shí)也將它自身所帶來(lái)的弊病以一種非常直觀的形式展現(xiàn)在了我們的面前,例如輿論導(dǎo)向的網(wǎng)絡(luò)暴力的產(chǎn)生,將討論上升為人身攻擊等。
在面臨著新媒體的沖擊和強(qiáng)大的輿論導(dǎo)向力所招致的輿論方向的“偏移”時(shí),代表著官方權(quán)威的傳統(tǒng)媒體必然需要在這一過(guò)程中發(fā)揮自身的積極作用,引導(dǎo)輿論朝著健康的方向發(fā)展。單純的將另一方視為核心都無(wú)法較為全面的去把握輿論生產(chǎn)語(yǔ)境的過(guò)程,需要站在一個(gè)更全面的視角審視二者的聯(lián)系: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通過(guò)“議程互動(dòng)”共同形成了輿論的生態(tài)體系,并且在這樣的互動(dòng)中通過(guò)對(duì)新聞生產(chǎn)方式的轉(zhuǎn)變,影響了輿論生成的語(yǔ)境的變化[3]。
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通過(guò)“議題互動(dòng)”(即“在報(bào)道議題方面形成的雙向交流與相互影響的過(guò)程”)實(shí)現(xiàn)了報(bào)道視角的拓寬和實(shí)現(xiàn)輿論的多方互動(dòng)。但在這樣的一種互動(dòng)過(guò)程中,傳統(tǒng)媒體出現(xiàn)的部分的“框架固化”和新媒體所展現(xiàn)出的情緒上的群體極化既有相互促進(jìn),也產(chǎn)生了較大的沖突。
通過(guò)對(duì)網(wǎng)絡(luò)輿論主體的劃分,可以更加直觀的分析這二者的矛盾和成因。網(wǎng)絡(luò)輿論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具有新聞媒體性質(zhì)的網(wǎng)絡(luò)新聞中所反映出來(lái)的輿論傾向,可稱(chēng)之為“網(wǎng)絡(luò)新聞?shì)浾摗?二是以BBS論壇、博客、各種社交網(wǎng)站和網(wǎng)上社區(qū)等為平臺(tái)而呈現(xiàn)出來(lái)的網(wǎng)民對(duì)社會(huì)上人和事的看法,可稱(chēng)之為“網(wǎng)民意見(jiàn)輿論”。在多媒體論述和學(xué)術(shù)探討語(yǔ)境下,網(wǎng)絡(luò)輿論更多地特指‘網(wǎng)民意見(jiàn)輿論[4]。
當(dāng)涉及新媒體和傳統(tǒng)媒體的“議題互動(dòng)”時(shí),“網(wǎng)絡(luò)新聞?shì)浾摗焙汀熬W(wǎng)民意見(jiàn)輿論”是相互促進(jìn)、不可分割的兩面。“網(wǎng)絡(luò)新聞?shì)浾摗睂?shí)際上是新媒體通過(guò)“公民新聞”來(lái)實(shí)現(xiàn)議程參與的重要渠道,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公民參與到新聞生產(chǎn)的過(guò)程中去,并通過(guò)和傳統(tǒng)媒體的“議題互動(dòng)”實(shí)現(xiàn)了傳播上的融合,但由于報(bào)道立場(chǎng)的不同、專(zhuān)業(yè)水平等差距的影響,導(dǎo)致了在這一融合過(guò)程中矛盾的凸顯,而這一凸顯則通過(guò)“網(wǎng)民意見(jiàn)輿論”的分化和偏向顯現(xiàn)出來(lái)。而僅僅將這種矛盾歸結(jié)于輿論情緒化對(duì)立的兩面未免失之偏頗,特別是在廣義的新聞的生產(chǎn)中,“網(wǎng)民意見(jiàn)輿論”所體現(xiàn)矛盾源于一種深度失衡(權(quán)利的不對(duì)等,階層的差異和表象上的不平衡)導(dǎo)致了這種內(nèi)心維持理性天平的崩塌。而這種不對(duì)等則是新媒體和傳統(tǒng)媒體在生產(chǎn)層面上的諸多差異所造成的,這就致使我們可以從二者間的互動(dòng)視角去重新審視新聞生產(chǎn)的過(guò)程。
較之以往傳統(tǒng)媒體有意識(shí)的選擇框架,當(dāng)下媒介賦權(quán)使得大眾更容易參與到新聞的討論當(dāng)中去,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輿論的指向往往容易成為大眾為媒介反向設(shè)置議程的動(dòng)力源,甚至在碎片化閱讀成為移動(dòng)客戶(hù)端的主流之下,信息的去專(zhuān)業(yè)化反而促進(jìn)了信息的傳播,強(qiáng)烈的情感宣泄和煽動(dòng)性的措辭極易激起浮在理智之上的“共情”機(jī)制。雖然新聞本身強(qiáng)調(diào)的是客觀與公正,特別是一種程序上、專(zhuān)業(yè)上的“客觀”,但在這里對(duì)于媒體來(lái)說(shuō),為了引導(dǎo)輿論的良性發(fā)展,不僅僅要在新聞內(nèi)容的呈現(xiàn)上極力訴諸新聞本身的客觀事實(shí),在新聞生產(chǎn)流程公開(kāi)化去尋求新聞的客觀公正,更重要的是,在認(rèn)識(shí)到了每個(gè)人無(wú)法避免的“前理解”之后,我們需要對(duì)客觀性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解讀。這一解讀是時(shí)下面臨著“信任危機(jī)”的媒介重塑自身“公信力”的過(guò)程中迫切需要回答的問(wèn)題:媒介是否值得相信?民眾是否相信媒介?[5]在當(dāng)下眾多主體的融合參與下,新聞不再僅僅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手段(方式)”,更重要的是,在飽含著人們的“公正”“客觀”等期待之下,新聞除了是一種信息傳播方式(更傾向于單向的模式),更是一種社會(huì)共識(shí)機(jī)制的表達(dá)(雙向的)。這對(duì)我們進(jìn)一步理解“共識(shí)”的概念是分不開(kāi)的。
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的“議題互動(dòng)”過(guò)程中,需要發(fā)揮各自的優(yōu)勢(shì),才能實(shí)現(xiàn)對(duì)輿論生態(tài)的良性建構(gòu),實(shí)現(xiàn)對(duì)“共識(shí)機(jī)制”的把握。對(duì)于新媒體來(lái)說(shuō),需要努力實(shí)現(xiàn)新聞生產(chǎn)過(guò)程中的規(guī)范化操作,朝著“社會(huì)性”的新聞生產(chǎn)作為實(shí)現(xiàn)“共識(shí)”的核心原則,在此基礎(chǔ)之上,利用新媒體技術(shù)的優(yōu)勢(shì),提供廣泛的事實(shí)供給核查,引導(dǎo)受眾朝著理性公正的認(rèn)識(shí)方向;通過(guò)信息傳遞的時(shí)效性及時(shí)對(duì)先前的錯(cuò)誤信息進(jìn)行更正,以期營(yíng)造一個(gè)健康的網(wǎng)絡(luò)輿論環(huán)境。
對(duì)于傳統(tǒng)媒體來(lái)說(shuō),提升輿論的引導(dǎo)力,更要做好公民這一原本的接收主體在新聞生產(chǎn)過(guò)程中的逐步滲透,甚至是以積極的態(tài)度去更好的接納與融合。相較于自媒體,傳統(tǒng)的官方媒體有一個(gè)巨大優(yōu)勢(shì)在于其資源的掌握,這里的資源有物質(zhì)性(資金、設(shè)備等)和非物質(zhì)性(聲望、對(duì)信息的搜集和獲取能力)的兩層含義。網(wǎng)絡(luò)傳播層面上的很多“溝通失效”在于媒體本身和大眾所擁有的資源不對(duì)等,這就導(dǎo)致了由于視角的原因?qū)е碌挠^念的錯(cuò)位,所以當(dāng)一味的強(qiáng)調(diào)“專(zhuān)業(yè)性、客觀性”而訴求無(wú)果的時(shí)候,媒體同樣也需要反思自身的立場(chǎng)和視角,如何更好的完善、補(bǔ)充事實(shí)從而實(shí)現(xiàn)“信息天平”的平衡,是對(duì)共識(shí)建構(gòu)的關(guān)鍵思路。正如美國(guó)西北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教授鮑比卡德2008年提出的參與體驗(yàn)理論,該理論針對(duì)大眾傳媒向互聯(lián)網(wǎng)和移動(dòng)傳媒變更,指出傳媒溝通的工作不僅僅是想方設(shè)法傳遞信息,還要讓受眾參與投入,讓受眾感覺(jué)到生活環(huán)境息息相關(guān)[6]。即通過(guò)提升公民的參與度將傳輸?shù)挠^念轉(zhuǎn)化為對(duì)共識(shí)的表達(dá)。
3? 傳播環(huán)境的規(guī)范化:維護(hù)“共識(shí)”的有力保障
如果將輿論引導(dǎo)視作一股“力”,那么,醞釀這股“力”則來(lái)源于我們對(duì)于良好的輿論環(huán)境的建構(gòu)。
首先,是采用高度的視角去看待輿論,“網(wǎng)絡(luò)輿情是對(duì)具備公共事務(wù)性質(zhì)的多種情緒和意見(jiàn)綜合,不應(yīng)將其視作帶偏見(jiàn)的極端情緒的不定期發(fā)泄。”共識(shí)構(gòu)建的基礎(chǔ)在于對(duì)輿論多樣性的保護(hù),輿論才能發(fā)揮它作為公共討論的意義所在,聽(tīng)取民意,共同尋求解決問(wèn)題的良好方式。
其次,提高對(duì)“失范性輿論”的管控能力和對(duì)網(wǎng)絡(luò)熱點(diǎn)輿論的監(jiān)測(cè)。由于網(wǎng)絡(luò)輿論的高度自由性,也導(dǎo)致其“惡性輿論”影響廣泛,即便是很小的群體也容易造成惡劣的影響,這有別于對(duì)輿論多樣性的保護(hù),也正因如此,對(duì)審核標(biāo)準(zhǔn)和技術(shù)層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熱點(diǎn)輿論的檢測(cè)上,則是將輿情視作社會(huì)的“皮膚”,監(jiān)測(cè)社會(huì)時(shí)事的“晴雨表”,亦即對(duì)共識(shí)的建立的落點(diǎn)不僅僅是放在嘴上,而是放在心里,落實(shí)到具體的事物上,才是提升傳統(tǒng)官方媒體的公信力的有力渠道。
綜上,對(duì)于輿論的“糾偏”在當(dāng)下復(fù)雜的媒介生態(tài)的實(shí)現(xiàn)途徑,轉(zhuǎn)變成了建立在良好的輿論環(huán)境基礎(chǔ)上的共識(shí)表達(dá)。而這樣的一種建構(gòu)離不開(kāi)社會(huì)每一個(gè)個(gè)體的努力。在觀念上我們不能對(duì)媒介傳播發(fā)展訴諸期望卻又在另一層面上對(duì)其所帶來(lái)的改變表現(xiàn)出一種消極和抗拒的姿態(tài)。網(wǎng)絡(luò)輿論所具有的多元性呈現(xiàn)出的是當(dāng)代社會(huì)多元利益競(jìng)爭(zhēng)的復(fù)合體,傳統(tǒng)的主流媒體固然在新聞傳播上秉承專(zhuān)業(yè)化的態(tài)度,通過(guò)其權(quán)威和影響力實(shí)現(xiàn)對(duì)話語(yǔ)權(quán)的把控,但其自身也受限于國(guó)家政治、利益集團(tuán)等外部因素對(duì)其獨(dú)立性和批判性造成的影響[7]。
在當(dāng)下復(fù)雜的媒介生態(tài)下,我們無(wú)法忽視代表著公民新聞的自媒體傳播在傳播影響力的作用,并且隨著大眾媒介素養(yǎng)的提升,傳統(tǒng)媒體的引導(dǎo)力不應(yīng)該被過(guò)分夸大,而是在這樣一個(gè)多元的環(huán)境下實(shí)現(xiàn)相互補(bǔ)充和完善。并且,不去刻意回避在傳播上“情感動(dòng)員”的威力,而應(yīng)該秉承對(duì)“專(zhuān)業(yè)性”的堅(jiān)守,去挖掘隱含在情緒之下支撐大眾的情感認(rèn)同的核心,這樣才能實(shí)現(xiàn)對(duì)傳播影響力的構(gòu)建,實(shí)現(xiàn)對(duì)共識(shí)的表達(dá)。現(xiàn)代新聞學(xué)將議題設(shè)置視作是媒介應(yīng)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8],既是對(duì)大眾傳媒業(yè)的公共屬性的肯定,同時(shí)也向其提出了更高的挑戰(zhàn),每個(gè)新聞機(jī)構(gòu)都應(yīng)該審慎考慮自身行為在引導(dǎo)社會(huì)輿論時(shí)或顯性或隱性的作用。誠(chéng)然在目前的環(huán)境下,企圖通過(guò)這樣一種多元化的互動(dòng)機(jī)制來(lái)實(shí)現(xiàn)觀點(diǎn)的相互補(bǔ)充論證和完善仍有一段很長(zhǎng)的路,我們不能對(duì)這種互動(dòng)完善的過(guò)程報(bào)以全盤(pán)托付的希望,但伴隨著傳媒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傳播渠道的開(kāi)放化和多元化,網(wǎng)絡(luò)讓“媒介融合”的概念成為了一個(gè)“新舊”媒介互動(dòng)的概念而不是替代性的概念,因此這仍不失為一種審視傳播格局“理想化”和實(shí)現(xiàn)傳播意義的關(guān)鍵要素之一。
參考文獻(xiàn)
[1]喻國(guó)明.網(wǎng)絡(luò)輿情治理的要素設(shè)計(jì)與操作關(guān)鍵[J].新聞與寫(xiě)作,2017(1):10-13.
[2]劉毅.略論網(wǎng)絡(luò)輿情的概念、特點(diǎn)、表達(dá)與傳播[J].理論界,2007(1):11-12.
[3]劉蓮蓮,常松.議題互動(dòng)、輿論生成與輿論偏向——新媒體時(shí)代傳統(tǒng)媒體輿論引導(dǎo)力的重建[J].學(xué)術(shù)界,2017:114-325.
[4]金兼斌.網(wǎng)絡(luò)輿論的演變機(jī)制[J].月度聚焦,2008(4):11-13.
[5]朱劍飛,邵靚.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媒介輿論引導(dǎo)力的建構(gòu)與強(qiáng)化[J].中國(guó)廣播電視學(xué)刊,2012(8):40-43.
[6]顧明毅,周忍偉.網(wǎng)絡(luò)輿情及社會(huì)性網(wǎng)絡(luò)信息傳播模式[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5):67-109.
[7]郭晴.媒介輿論:在各種權(quán)力與公眾之間——兼論公共輿論向媒介輿論的轉(zhuǎn)向[J].新聞界,2010(2):104-106.
[8]麥斯韋爾·麥考姆斯,顧曉方.制造輿論:新聞媒介的議題設(shè)置作用[J].國(guó)際新聞界,1997(5):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