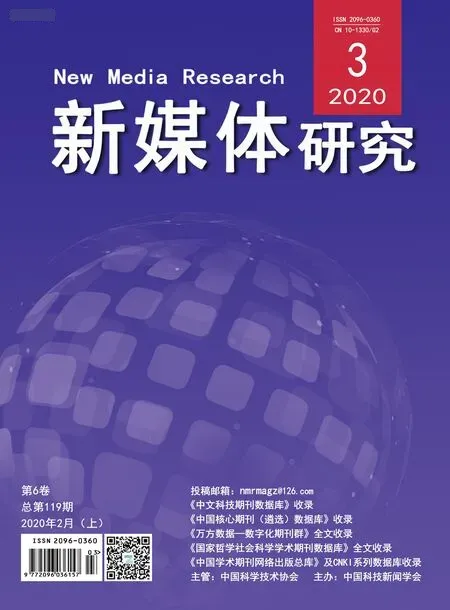“需求驅(qū)動(dòng)”新聞生產(chǎn)的價(jià)值邏輯審視
毛毅
摘? 要? 數(shù)據(jù)技術(shù)及算法邏輯的日益更新,愈加精細(xì)化的用戶行為數(shù)據(jù)為媒體提供了更為直觀的判斷依據(jù),這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新聞生產(chǎn)的“需求驅(qū)動(dòng)”特征。文章認(rèn)為,技術(shù)力量的加入使新聞生產(chǎn)癡迷于“滿足需求”,卻在算法數(shù)據(jù)中逐漸喪失了“人與社會(huì)”多維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的整體性理解,進(jìn)而把人的表象和人的本質(zhì)混為一談。鑒于此,有必要將現(xiàn)行的新聞生產(chǎn)邏輯放在多維視角下進(jìn)行價(jià)值邏輯審視,以此來厘清其中存在的各種現(xiàn)實(shí)悖謬。
關(guān)鍵詞? 新聞生產(chǎn);需求驅(qū)動(dòng);價(jià)值邏輯
中圖分類號(hào)? G2?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 ? 文章編號(hào)? 2096-0360(2019)03-0022-02
1? 屬人的需求與生產(chǎn)的需求
價(jià)值即事物對(duì)人類的意義或作用,是客體滿足主體生命意義的一種“效用”關(guān)系。價(jià)值的屬人性,決定了價(jià)值評(píng)價(jià)及判斷都須以人為本,以人的生活與社會(huì)發(fā)展為目標(biāo)。新聞生產(chǎn)活動(dòng)的基本原則是真實(shí)、客觀、公平、獨(dú)立地報(bào)道新聞事實(shí)以揭示事實(shí)的本質(zhì),其隱含核心價(jià)值內(nèi)涵是為社會(huì)公眾呈現(xiàn)“真”的事實(shí),并推動(dòng)社會(huì)及國家朝著“善”的目標(biāo)前進(jìn)。
在“需求驅(qū)動(dòng)”的生產(chǎn)邏輯中,媒體期望能切實(shí)把握個(gè)體的信息需求,從而為“個(gè)性化傳播”奠定基礎(chǔ)。技術(shù)的更新為媒體提供了這種可能性,通過對(duì)用戶行為分析,媒體獲得了更為直觀且能夠量化的“行為數(shù)據(jù)”。由此,媒體構(gòu)建起了“數(shù)據(jù)”與“用戶”之間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需求”數(shù)據(jù)成為了新聞生產(chǎn)的直接推力。從表面上看,“滿足需求”似乎體現(xiàn)了媒體的“公器”作用,實(shí)質(zhì)上,囿于技術(shù)的“先天缺陷”,媒體在“需求”判斷中,具有將生命個(gè)體分解為“行為片斷”的傾向,而出現(xiàn)平面化、匿名化、簡(jiǎn)約化的認(rèn)知問題。在這個(gè)過程中,屬人性的價(jià)值內(nèi)涵從新聞生產(chǎn)中剝離出來,而只剩下“為需求而生產(chǎn)”的屬物性邏輯。
鮑德里亞認(rèn)為,在物質(zhì)增長的社會(huì)里得到滿足的東西,以及隨著生產(chǎn)力的提高愈來愈得到滿足的東西,是生產(chǎn)范疇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人的“需求”[1]。在“需求驅(qū)動(dòng)”的新聞生產(chǎn)模式下,媒體選擇性地忽略了歷史與社會(huì)維度的宏觀意義建構(gòu),忽略了人的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與生命意義目標(biāo),導(dǎo)致了大量訴諸感官需求和低級(jí)需求的內(nèi)容充斥媒體,由此,媒體原本所具有的“求善”的價(jià)值內(nèi)涵在功利性的“求利”的生產(chǎn)需求中被解構(gòu)。
2? 正確的“標(biāo)準(zhǔn)”與平衡的“關(guān)系”
新聞生產(chǎn)的本質(zhì)是關(guān)系。在這個(gè)無形的關(guān)系構(gòu)架上,關(guān)系主體遵循相互承認(rèn)、相互尊重的交往原則進(jìn)行互動(dòng),以求最終實(shí)現(xiàn)人類及社會(huì)的良性發(fā)展。從關(guān)系維度來看,媒體與用戶都在尋求這種結(jié)構(gòu)中的平衡點(diǎn)。在這個(gè)結(jié)構(gòu)中,如何認(rèn)識(shí)對(duì)方,如何把握對(duì)方的需求和意愿,如何理解對(duì)于生活、幸福和發(fā)展的“核心價(jià)值觀”,這些均成為“新聞生產(chǎn)”的動(dòng)態(tài)制約因素。在倫理規(guī)范的作用下,既要肯定媒體“求利”的經(jīng)濟(jì)目的,也不能否定人的“求真”“求美”的生活意義訴求,更要為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求良”“求善”的發(fā)展目標(biāo)而奮斗。由此,新聞關(guān)系中的“平衡”狀態(tài),不僅可以視為判斷新聞價(jià)值的有力工具,更是檢驗(yàn)社會(huì)倫理認(rèn)知及文明發(fā)展程度的標(biāo)尺。
從倫理角度而言,“需求驅(qū)動(dòng)”新聞生產(chǎn)遵循的是一種功利主義的競(jìng)爭(zhēng)倫理觀念,只顧及利益和欲望,難以兼顧新聞關(guān)系中多元共生的生態(tài)結(jié)構(gòu)。在這種觀念下,媒體孜孜不倦地利用技術(shù)力量進(jìn)行用戶群體的特征畫像、價(jià)值評(píng)估、需求預(yù)測(cè),以實(shí)現(xiàn)流量、入口、留存、轉(zhuǎn)化等各項(xiàng)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提升。由此,用戶成為越來越有價(jià)值的商品,而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逐漸被各種“需求指標(biāo)”物化為“生產(chǎn)標(biāo)準(zhǔn)”。波茲曼認(rèn)為,技術(shù)以一種標(biāo)準(zhǔn)的、流水線式的生產(chǎn)模式逐步侵占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乃至于思想和行為的方方面面,這種趨勢(shì)使得個(gè)體逐步趨同,進(jìn)而影響文化的多元化[2]。一旦我們將“標(biāo)準(zhǔn)”納入用戶需求識(shí)別系統(tǒng),就必定會(huì)陷入將現(xiàn)實(shí)切成片段的傾向,而忽視了新聞倫理結(jié)構(gòu)中媒體與用戶、媒體與社會(huì)的多元?jiǎng)討B(tài)關(guān)系中的“平衡”訴求,這也會(huì)導(dǎo)致另一個(gè)嚴(yán)重的倫理錯(cuò)誤:借“標(biāo)準(zhǔn)化”的名義去侵占和剝奪其他人,甚至是社會(huì)的合理訴求。
3? 需求的靜態(tài)判斷與動(dòng)態(tài)生成
從認(rèn)識(shí)論維度來看,如何認(rèn)識(shí)“需求”,以及“需求的本質(zhì)是什么”這兩個(gè)問題,構(gòu)成了媒體認(rèn)識(shí)論的核心。技術(shù)為媒體的“需求判斷”提供了更為直觀的判斷途徑,讓生產(chǎn)的指向性更明確,在實(shí)踐中有一定積極作用,但“算法”背后的需求判斷卻存在明顯邏輯悖謬。首先,“科學(xué)性”的算法邏輯可能在數(shù)據(jù)處理中擬合度較高,但不意味算法與個(gè)體需求相符。其次,在行為數(shù)據(jù)分析上,大多數(shù)媒體的分析平臺(tái)僅僅能看一些較為宏觀的統(tǒng)計(jì)指標(biāo),而缺失了中觀層面的數(shù)據(jù)關(guān)聯(lián),很難說清用戶行為數(shù)據(jù)背后的實(shí)際價(jià)值。最后,用戶行為程度的不同,也致使平臺(tái)數(shù)據(jù)的涵蓋性有所欠缺。由此,數(shù)據(jù)的“需求”識(shí)別并不等于真正意義上“人的需求”,而只把這種多維、立體的需求結(jié)構(gòu)單維化、平面化、靜態(tài)化處理。
肇始于心理學(xué)與物理學(xué)的“信息需求”概念與哲學(xué)及社會(huì)學(xué)上的“人類需求”概念并不能劃等號(hào)。首先,拋開物質(zhì)需求或生理需求,人的需求非常個(gè)性化。新聞的滿足程度因人而異,因時(shí)而異。其次,從需求的滿足介質(zhì)來看,一般的人類需求,是有明確的需求對(duì)象的,是一種經(jīng)驗(yàn)的認(rèn)知,而信息需求卻難以用經(jīng)驗(yàn)的方式去評(píng)價(jià),是一種體驗(yàn)式的認(rèn)知。最后,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個(gè)體的自由度更大,也意味著需求的變動(dòng)程度也更強(qiáng),并且這種變動(dòng)也因用戶所處環(huán)境空間的不同而呈現(xiàn)出變動(dòng)的不同程度。由此,媒體根據(jù)用戶行為數(shù)據(jù)只能判斷信息是否到達(dá),卻無法獲知信息是否滿足需求,如果僅憑數(shù)據(jù)推斷用戶需求,而缺失社會(huì)個(gè)體存在的信息環(huán)境、心理狀態(tài)、社會(huì)關(guān)系、意義語境的綜合評(píng)價(jià),則會(huì)陷入歸納悖論而導(dǎo)致錯(cuò)誤的需求認(rèn)知。
4? 個(gè)體需求與共同價(jià)值
新聞生產(chǎn)使媒體、個(gè)體、社會(huì)共同構(gòu)成了一組基于信息的多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不同主體的目的訴求必然是異質(zhì)性的。同時(shí),共享的文化環(huán)境和對(duì)人類生命價(jià)值追求的普世倫理,又決定了這種多元訴求呈現(xiàn)出“和而不同”的特征,既有主體特質(zhì)性的現(xiàn)實(shí)性需要的滿足,又有著主體之間共同的價(jià)值訴求與目的期待。由此,新聞生產(chǎn)的目的預(yù)設(shè),不僅要考察個(gè)體及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需要”,更要基于融合文化的不同主體之間的意義互動(dòng)與傳播空間重構(gòu)的“共同價(jià)值空間”,理解個(gè)體及社會(huì)傳播目的的轉(zhuǎn)變。
在信息過載時(shí)代,信息量早已突破個(gè)體信息需求的臨界點(diǎn)。由此,用戶的信息需求必定會(huì)發(fā)生逆轉(zhuǎn),這種逆轉(zhuǎn)不僅是信息層面的一種去繁就簡(jiǎn),返雜歸真,更表現(xiàn)在對(duì)個(gè)體現(xiàn)實(shí)生活空間意義建構(gòu)上的關(guān)注。此種背景下,基于信息范式下的新聞生產(chǎn)注定無法滿足個(gè)體關(guān)于“生活意義”建構(gòu)的傳播訴求,也無法在“命運(yùn)共同體”的文化框架下滿足個(gè)人及社會(huì)的“共同價(jià)值”的訴求。它脫離了與人的現(xiàn)實(shí)而具體的意義牽涉,也違背了融合所蘊(yùn)含的人類“共同價(jià)值空間”的邏輯內(nèi)涵,即通過信息互動(dòng)、意義共享而回歸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善”的訴求。
融合時(shí)代的信息賦權(quán)肯定了個(gè)體表達(dá)真正屬于自己的人生意義的價(jià)值訴求。由此,新聞傳播的目的不在于指導(dǎo)個(gè)體如何生活,而是在于重新肯定“人性”,回歸人所生存的生活空間,幫助他們真實(shí)認(rèn)識(shí)生活的價(jià)值和意義。從這個(gè)意義上來看,新聞生產(chǎn)應(yīng)該給生活意義一個(gè)最大的釋放空間,它不僅是一個(gè)意象,而且也是一個(gè)聯(lián)結(jié)紐帶,個(gè)體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在共享意義空間中與它互動(dòng),與它對(duì)話。
5? 結(jié)束語
從發(fā)展來看,融合傳播環(huán)境是傳媒業(yè)必須面對(duì)的,要實(shí)現(xiàn)融合發(fā)展,就需要適應(yīng)融合文化的特征和價(jià)值內(nèi)涵。從本質(zhì)上看,“需求驅(qū)動(dòng)”的新聞生產(chǎn)活動(dòng)是無法滿足融合時(shí)代下生命個(gè)體關(guān)于生活意義的價(jià)值訴求的。一味肯定“需求”,只會(huì)日益加深媒體與社會(huì)、個(gè)人的意義分割,導(dǎo)致新聞媒體逐漸脫離社會(huì)共同觀念與共享價(jià)值的意義空間。
需要并非天然合理,這是客觀事實(shí),并不難理解。以滿足主體需要界定價(jià)值,是不科學(xué)的[3]。要拯救目前媒體新聞生產(chǎn)的困境,必須轉(zhuǎn)變“需求”指向的新聞生產(chǎn)模式,切實(shí)理解個(gè)體生活空間的存在,在提升新聞品格的基礎(chǔ)上,將新聞融入到個(gè)體性的生活空間意義互動(dòng)中來,推崇并引導(dǎo)共享的價(jià)值意識(shí)與倫理認(rèn)知形成,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媒介融合,進(jìn)而最終實(shí)現(xiàn)“善”的社會(huì)發(fā)展目標(biāo)。
參考文獻(xiàn)
[1]讓·鮑德里亞.消費(fèi)社會(huì)[M].劉成富,全志剛,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39.
[2]胡翼青.西方傳播學(xué)術(shù)史手冊(cè)[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252.
[3]王玉樑.評(píng)價(jià)值哲學(xué)中的滿足需要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7):6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