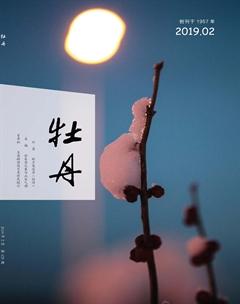“意象”背后的抑壓
馬巾晶
曹禺創作中的意象向來包含著豐富的含義,不同作品中的不同意象往往象征著作者最想要表達的主題思想。作為曹禺人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的《雪松》,其對于研究曹禺戲劇人生和人生戲劇具有重要的作用。
縱觀現代文學史,有這樣一顆璀璨奪目的明星,他的人生就像一個戲劇舞臺,他3歲即隨繼母輾轉各個戲院聽曲觀戲,從小內心便播下了戲劇的種子。入讀中國話劇運動的搖籃——南開中學時,他參加了南開新劇團,從而獲得了極為豐富的舞臺實踐經驗。在清華就讀時潛心鉆研戲劇,他廣泛閱讀從古希臘悲劇到莎士比亞戲劇及契訶夫、易卜生、奧尼爾的劇作。這讓他與中國的現代話劇運動建立起絲絲縷縷的聯系。他創作的《雷雨》《日出》《原野》等經典劇作,確立了中國現代話劇的劇場藝術,使中國的現代話劇走向成熟,這顆明星就是現代史上偉大的劇作家——曹禺。對于文壇和學界而言,目前他們將更多的目光關注于他的戲劇,可要對曹禺做透徹的了解少不了對他全息性的了解,人們忽略了他人生當中最后創作的一篇散文——《雪松》。
應《收獲》之約,曹禺于1991年9月28日在病房內完成散文《雪松》。這是歷經塵世滄桑的曹禺,對于他早年在《〈雷雨〉序》中所寫的“如神仙,如佛,如先知般”升華到“上帝的座”的自由奔放、神采飛揚的創作心情和態度的部分回歸:“其實,我這個人是極為歡樂的。我笑起來總是開懷暢笑,有時候一連串講起往事,也是找最愉快的事情講……”可細讀他的戲劇文本,細品他的人生,人們更多地看到的是曹禺的苦悶。田本相曾為他作傳采訪時,他就說:“你要寫我的傳,應該把我的心情苦悶寫出來。”還有日本的一位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曾著書《苦悶的象征》明言:“藝術是苦悶的表現,文藝是苦悶的象征。”如果說苦悶決定著藝術的創造或許略失偏頗,但對曹禺來說并非毫無道理。這苦悶在曹禺那里成了伴隨一生的抑壓,它是多重的,是豐富的,是漸變的,也是最終融合后升華成了渴求、規諫和反思。可這種情感的抑壓、社會的抑壓、人性的抑壓和生命的抑壓的表達在曹禺那里并非多么直白、明顯、強烈,僅僅單純地使用了五種意象:雪、玻璃翠、愛麗兒、孫悟空、雪松就表達得淋漓盡致。
一、雪:抑壓背后純樸地渴求
雪在人們的心中始終是圣潔純白的,令人格外歡喜的,在很多作家眼里也是如此。曹禺在《雪松》里這樣說:“一陣細細的涼風吹來,落在我頸上的是涼涼的雪粒。我多么喜愛這潔凈純樸的白雪,雪化開我的郁熱,散發我的沉悶。我忘記這三年來的疼痛,我要在雪地上走出我的腳印。我要用我心頭的熱來偎暖那些已逝去的朋友們,使我心痛的親人們。”這是曹禺的人性抑壓、社會抑壓、情感抑壓后產生的像“雪”一樣圣潔純樸的渴求。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城市資本主義興起的時期,他深刻地感受到現實的壓抑,紛繁復雜的社會里有著各種恐怖的人和事摧殘著他,折磨著他,讓他一刻都不得安寧。他看到了這個醉生夢死、燈紅酒綠的社會里藏匿的威逼與壓抑,所以他在揭露社會黑暗的同時又表達了他對社會純樸的渴望。這“雪”一樣的渴望也在他的人生態度里。曹禺的女兒萬方曾談及父親的遺愿時說到父親教育她如果要做一個偉大的作家,首先得有一個崇高的靈魂。人們要學會觀察和體會身邊的一切人和事,寫出他們的神態和生動的語言,不斷覺察和看見那些靈魂在文字間是如何發光的,這靈魂是像雪一樣圣潔的。所以,在曹禺的筆下,作為第一個意象的“雪”,是他抑壓背后對純凈文明的社會的渴求,也是對崇高圣潔的靈魂的寄予。
二、愛麗兒:抑壓背后雙重情感的寄托
莎士比亞被譽為人類最偉大的戲劇之才,他曾創作過一部戲劇《暴風雨》,講述了一位米蘭公爵被弟弟奪走爵位,攜帶襁褓中的女兒和魔術書籍流亡到荒島,并如何報仇最終奪回爵位的故事。在劇本里有一個可愛的精靈愛麗兒,愛麗兒效忠于主人,使出渾身解數幫助他。等到最后向主人提出要求:恢復原來的自己,重獲自由之身。這與孫悟空大不一樣,當修成了正果,被封為“斗戰圣佛”后,孫悟空就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來的猴身。曹禺在《雪松》中提到愛麗兒,這一鮮明的比較正深刻揭露了包括其自己在內的中國文化人,在新舊身份中是回歸以前還是坐享現在的自我迷失,這是曹禺在遭受了社會抑壓和人性抑壓后的情感寄托。
當然對于在愛麗兒身上體現的“人性”,曹禺極力地呼喚。莎士比亞筆下的愛麗兒十分善良,從那不勒斯王所乘坐的船遭受暴風雨開始,到后面的種種魔法的施力,幾乎全部都是愛麗兒這個精靈做的。她原本是島上的女巫西考拉克斯所驅使的仆人,但是由于本性善良無法服從邪惡的命令,遭到痛苦的幽禁。最后被普洛斯彼羅救出,此后為他效勞。愛麗兒作為一個善良溫順的精靈,她無法被邪惡的女巫所驅使,這正是一種超驗知識力量無法被邪惡所駕馭的一種表現,這是莎士比亞的一種人性的寄托,也是曹禺的一種寄予:“真正的理性就是美德。”
三、玻璃翠:抑壓背后破碎和美麗的映射
曹禺在《雪松》談玻璃翠:“這朵花是真的,真美,一點也不假。它亭亭玉立,細看看,不是孤單單的一朵,而是六七朵,每朵五瓣,濃紫色的花心,花瓣漸漸化淡,成了青蓮色的了。它微微蕩漾,使人心醉。”這種花是極美的,他渴望花一樣的美,也渴望像花一樣美的人性。這種美與他看到的這個社會的罪惡和污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看到了在這些污穢罪惡掩蓋下的美,但這種美的毀滅讓他心痛。與《雪松》相配套,1991年10月23日曹禺寫了短詩《玻璃翠》:“我不需要你說我美,/不稀罕你說我好看。/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濃濃的花心,淡淡的瓣兒。/你夸我是個寶,把我舉上了天。/我為你動了真心,/我是個直心眼。/半道兒你把握踩在腳底下,/說我就是賤。/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臉。/我怕你花言巧語,/更怕你說我好看。/我是個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騙。”經不起別人贊美而一再被利用、被欺騙、被拋棄的“玻璃翠”,是他為包括自己在內的一代讀書人,像孫悟空被封為“斗戰圣佛”后就再不想起自己的猴身那樣迷失自我的人生影劇和戲劇人生的傳神寫照。這是曹禺情感抑壓和人性抑壓后的映射,當然用“玻璃翠”來形容自己,像“玻璃翠”一樣柔弱中的感悟與執著,可以說是曹禺這一生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這一文一詩,曹禺無形中給自己“歧路彷徨”的戲劇人生和人生戲劇,圈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四、孫悟空:抑壓背后嚴肅的反思
對于孫悟空這個形象人們再熟悉不過,小時候的小人書,電視里的《西游記》,都有著他大鬧天宮和替天行道的兩大截情節。曹禺在《雪松》里不止一次提到孫悟空,他認為他的戲劇人生和人生戲劇與孫悟空一樣可以分為兩截。早期的曹禺,憑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野性,像孫悟空那樣在藝術的殿堂里大鬧天宮、自由地揮灑才華,充分地實現了他抒情詩人自居和以替天行道、神道設教的宗教先知的特權身份。等到他為了迎合和取得“學而優則仕”的世俗榮譽和官位,而把這種特權低頭折節地納入“存天理,滅人欲”的緊箍咒時,便只能像戴上緊箍咒的孫悟空一樣從事反貪官不反玉帝、反人欲不反天理的受招安的政治宣傳。
從嚴格意義上說,文藝學是人學,是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為表達而表達的獨立存在,藝術創作自我約束的邊界在于藝術家不應該以政治宣傳和政治權力為依附,藝術創作也不應該被用來包辦解決社會問題。例如,《日出》和《雷雨》等起自情色歸至宗教的為了表達而表達、為了藝術而藝術的經典作品是可以囊括豐富的政治宣傳和社會問題的。這樣說來,曹禺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喪失了為藝術而藝術、以人為本的價值,也沒有起到政治宣傳所需要的感動人心的效果,這是他對自我創作的反思,也是在社會抑壓和情感抑壓融合后給后來的讀書人嘔心瀝血的教訓的表達。
同時,以偉大的作家為出發點,改革開放后,歷史帶來了一次難得的創作契機,但曹禺感覺自己像斷臂的王佐:一切都明白了,人卻殘廢了。他渴望自由,渴望創造的夕陽之火,怎么也燃燒不起來,所以他想寫一部關于孫悟空的戲,寫他苦苦掙扎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可怎么也無力奮戰了,就這樣,他也帶著寫孫悟空的遺憾離開了。這是曹禺借孫悟空對自己一生的總結與反思,是借孫悟空對后人的一番規諫,也是借孫悟空實表自己創作的遺憾。
五、雪松:抑壓背后誠懇的規諫
“雪松”是散文里出現的最后一個意象,也是曹禺在五個意象中單單選中了它作為最后一篇文章的題目。曹禺曾說“雪松,勁直高昂,不屈不狂,經得起世情的冷淡,平實而奮發,充溢不懈不止的生命”,又說“雪松啊,是我再夢寐中不能忘記的精誠”。他渴望活成雪松的樣子,平實、奮發,不屈,也不狂,做一個正直真誠、努力向上的人。但曹禺也說:“在這三年的病痛里,我回憶起平生所遇見的許多人,他們就像眼前的雪松一樣,或者說他們就是雪松。”這足以表達了他對身邊的人的敬佩和思念。這是一種真摯的情感流露,他想用雪松的品質踱量自己,同樣在人生最后能創作的時間,他表達了對自己朋友和親人的懷念和感激。當然,也有著規諫,在曹禺離別時,他送給自己的女兒一首弘一法師的詩,同樣也送給我們:“水月不爭,/唯有虛影,/人生如是,/終莫之領。/為之驅驅,/被此真凈,/若能悟之,/超然獨醒。”
人忙活了一輩子,卻還是難懂水月不爭這個道理。等到什么時候悟參悟了這些道理,也就有了“超然獨醒”的人生態度了。
在人生的最后一截,曹禺依然在想著用自己的經驗規諫世人,也想把自己的創作經驗留給后人,甚至把做人做文的理也公之眾人,就是這樣一位有著傳奇的戲劇人生和人生戲劇的人物,用最簡單明了的五個意象將自己的人生表現得淋漓盡致,將自己的苦悶展現得酣暢淋漓,將自己的抑壓和期待凸顯得痛快淋漓。他最終并沒有倒下,而是在熬過一場又一場的劫難中得到了他應該得到的人生。他這一輩子,無論是在藝術創作的道路上,還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后都站成了一棵勁直高昂的雪松。
(延安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