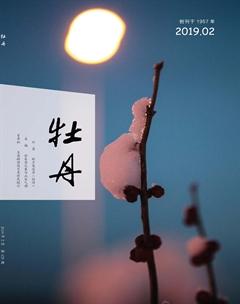論余華《第七天》中的聲音
余華的《第七天》涉及了很多種聲音,其在文本中分別表現為:人物的對話;非人的自然界及其社會上形形色色物品發出的聲音;作者直接發出的聲音和隱含的敘事者的聲音。它們召喚記憶,使人回顧生命,感悟生命的真善美,同時引導著情節的發展;它們暴露事實的真相,揭露現實的殘忍,以死的永生引人深思,同時表露作者的隱含心聲。
余華在其《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一書中向讀者透露了音樂對其寫作的影響,其在開篇寫道:“(對音樂的)無知構成了神秘,然后成為了召喚,我確實被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勾引出了我創作的欲望。”這種創作的欲望開始表現為在十五歲那年直接利用簡譜的形式進行音樂寫作,之后則表現為以“音樂的敘述”進行的文學創作。在該書結尾,他將文學的敘述和音樂的敘述類比,說:“文學的敘述也同樣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暫和安詳的敘述將會出現更加有力的震撼。”由此可見音樂對余華創作的影響。
莫言曾在《聲音帶給我的》中提到音樂影響了他的創作,同時他還提到:“聲音比音樂更大更豐富。聲音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是人類靈魂寄居的一個甲殼。聲音是人類與上帝溝通的手段,有許多人借著它的力量飛向了天國,飛向了相對的永恒。”由此可見聲音在創作中的重要性。
本文將要論及的《第七天》顯然反映了音樂對余華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為《第七天》中余華對紛繁聲音的描寫上。以下將從召喚之聲、萬物之聲、對比之聲三個方面來解讀文本中呈現的聲音,并由此揭示《第七天》中聲音的意義。
一、眾聲喧嘩的聲音:“聲音”的界定
在談論余華《第七天》中的聲音之前,先來界定這里所要談論的聲音。這里所論及的聲音有別于音樂上涉及音節、韻律的聲音,同時也有別于女性主義所說的涉及話語權的聲音。它是指文本中呈現的物理意義上由物體振動產生的聲波,以及精神層面傳達內心的思考的獨白和隱藏在文本中向讀者說話的敘述者。這些聲音在文本中分別表現為:人物的對話;非人的自然界及其社會上形形色色物品發出的聲音;作者直接發出的聲音和隱含的敘事者的聲音。筆者將這些聲音分為三大類,并結合文本進行分析。
二、紛至沓來的聲音:“聲音”的分析
余華的很多作品都涉及聲音,其中以《第七天》最為明顯。在《第七天》中,除了主人公楊飛和其他人的大量對話、他自己的內心獨白、自然界和社會上形形色色物品發出的聲音外,還存在著類似戲劇旁白的聲音和潛意識中召喚的聲音。
(一)召喚之聲
1.引導“我”走向記憶
毫無疑問,《第七天》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敘述整個故事的“我”——楊飛。他在死后的七天里,不斷地被不同的聲音召喚,那些聲音引導他走向生前的記憶,讓他回顧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
第一天,“昨夜響了一宵的倒塌的聲音”將永遠沉睡在生的世界里的“我”叫醒,它引導著“我”走向殯儀館,走向死亡的現場。“我行走在若隱若現的城市里,思緒在縱橫交錯的記憶路上尋找方向。我思忖應該找到生前最后的情景,這個最后的情景應該在記憶之路的盡頭,找到它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死亡時刻。我的思緒借助身體的行走穿越了很多像雪花一樣紛紛揚揚的情景之后,終于抵達了這一天。”“我”站在生和死的界限上,看著自己在那一天的經歷,眾人抗議暴力拆遷的聲音、小女孩的聲音、警察呼吁的聲音、電視里廣播的聲音和飯店老板譚家鑫的聲音像是一條聲音鏈將我的記憶附著在上面串聯起來,“隨即是一聲轟然巨響”,生的“我”在這聲巨響中消失,生前最后的記憶也就此中止。
在此后的六天里,不同的聲音引導“我”走進不同的記憶里。余華在《消失的意義》中說:“馬塞爾·普魯斯特說:‘我們把不可知給了名字。我的理解是一個人名或者是一個地名都在暗示著廣闊和豐富的經歷,他們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四十大盜的寶庫之門,一旦能夠走入這個名字所代表的經歷,那么就如打開了寶庫之門一樣,所要的一切就會近在眼前。”當一個陌生女人的聲音在呼喚“楊飛——”時,這聲音引導著“我”走向了與妻子李青在一起的記憶;火車在軌道上駛過的聲音引導著“我”走向了我的出生和成長的記憶;年輕女子詢問的聲音,帶我走入我搬進出租屋后的記憶……。“我”進入了死無葬身之地,在那里譚家鑫的聲音、李月珍的聲音將“我”帶到了“我”生前一直尋找的養父楊金彪的身邊。
2.作為“功能”的引導
縱觀《第七天》,我們會發現,在這七天中召喚著主人公楊飛的聲音實際上構成了一種引導整個故事情節發展的核心功能。胡亞敏在其《敘事學》中提到:“核心功能是故事中最基本的單位,是情節結構的既定部分,具有抉擇作用,引導情節向規定的方向發展。”
實際上,《第七天》中每一天的故事,都是在一個又一個不同的聲音召喚下進行敘述的,這些不同的聲音的作用在于引出對發生在主人公楊飛身上的事情的敘述——火車聲引出楊飛的出生及成長,陌生女人的聲音引出楊飛與李青的相戀過程等。
核心形成一些項數不多的有限的總體,受某一邏輯的制約,既是必需的,又是足夠的。這一框架形成以后,其他單位便根據原則上無限增生的方式來充實這一框架。在《第七天》中,七天引導楊飛的聲音雖然在形式上不同,但在實質上都是一樣的。一天之初召喚楊飛的聲音奠定了這一天將要敘述的內容,它在文本中每一天的開頭就制作了一個框架,而填充其中的故事只是在其基礎上不斷地變換。
作為“功能”的引導,使這些不同的聲音連在一起在無形中形成一條敘事線索。作者將這些聲音作為引導情節發生的核心功能,使得文本中雖眾聲喧嘩,卻又存在著一條明晰的聲音之索敘述楊飛生前死后的遭遇,傳達作者的心聲。
(二)萬物之聲
1.他們的聲音:揭示生的殘忍
“人的聲音是易變的、肉感的、復雜的,其聲音來自唇舌。”“自唇舌的聲音,正是長篇小說最初的聲音。”聲音傳達著信息,文本中不同人物的聲音揭開了被遮蓋的真相,它讓人們看到了生的虛偽與殘忍。
“我”在生和死的世界間穿行。當“我”走進生前的記憶,一些活著的人的聲音和“我”死后遇到的那些人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它們逐一地將生的殘忍袒露在“我”面前。
暴力拆遷砸死了很多人,新聞上在播放暴力拆遷事件時,同在飯館的陌生男子對“我”說:“他們說的話,我連標點符號都不信。”向李青求愛的人受辱后辭職,同事不僅不同情反而冷漠拒絕幫他,他們謊稱自己在忙,想讓他自己上來出丑;劉梅沖動之下說自己要自殺時,網友沒有勸解反而給她提供自殺的方式,當她站在鵬飛大廈的樓頂準備跳樓自殺時,圍觀的只是好奇她為什么自殺,并把自殺看作很平常的事情……
生的世界的殘忍、冷漠延續到殯儀館,在那里候燒者以身份為界分別劃到了貴賓區和普通區。當普通區的候燒者為買墓地而憂慮時,貴賓區的候燒者還驚訝于“一平米的墓地怎么住?”;當普通區的候燒者傷心地說“死也死不起啊!”,貴賓區的候燒者卻在考慮著死后的享樂。這些來自現實社會和殯儀館中他們的聲音,喧嘩不止,揭示了生的殘忍。
2.隱含作者的聲音:袒露所有的事實
小說作為敘事作品,理所應當地會有敘述主體,但“敘述主體不等于作者,而是指作品的敘述者和作品中的隱含作”。同時,布斯也提到:“‘敘述者通常指一部作品中的‘我,但這種‘我即使有也很少等同于藝術家的隱含形象。”在《第七天》中,敘述主體很明顯是“我”,即楊飛。但他并不能等同于作者,人們在文本中會聽到隱含作者的聲音,它們作為補充的聲音,比楊飛的敘述更加客觀冷靜,也更加接近真實。隱含作者的聲音有時候隱藏在文本中,而并非以人物對話的形式出現。它們作為補充的聲音,袒露所有的事實。
“我”在殯儀館侯燒時,因為市長要來,貴賓區和普通區都停止了叫號,貴賓區的候燒者抱怨不斷,但當市長來到時,“沙發那邊的貴賓們沒有了聲音,豪華貴賓室鎮住了沙發貴賓區,金錢在權力面前自慚形穢”。這樣隱含在敘事中的聲音,客觀冷靜地揭示了現實社會中人們向金錢、權力的屈服。在暴力拆遷現場,當走進不同暴力強拆事件的受害者中間時,“我”卻“覺得他們不像是在示威,像是在聚會”。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只會聚集、抱怨,他們沒有正確的途徑去解決問題,像是一群看客一樣,看著受苦難的人們和自己。當“我”為尋找父親而坐車回父親的村莊時,出租車突然停在了中斷的柏油路上,并向我解釋:鄉下的路是為了領導視察才修的,沒有領導來,路就在此中斷了。在這里,作者借助出租車司機來發聲,道出了鋪路的真正原因是敷衍視察,而不是為百姓著想。這樣沒有帶入司機的個人主觀感情的平靜語調,不僅反映了人們對這種現象的熟視,同時也揭示了政府機關中存在的唯上唯權等問題。
文本暗含作者沒有聲音、沒有直接的交流手段。作為補充的聲音存在的,除了作者借助他人之口隱含的傳達之外,文本中還有類似戲劇旁白一樣的語句,它們同樣冷靜客觀,作為敘述事件的補充,揭示被掩蓋的事實。被“我”視為母親的李月珍發現了醫院丟棄的死嬰,并傳達給記者,不久后車禍死亡,尸體和被她發現的二十七個死嬰放在一起。意外的塌陷使她和那二十七個死嬰的尸體突然消失。在這整個過程中,醫院辦公室主任、太平間的醫院勤工、市政府的官員和殯儀館的工作人員不斷地改口,最后矢口否認,將事實說成是謠言。補充在這個事件之后的話語——“這個醫院的勤工當天在自己的賬戶上存入了五千元”“這個月殯儀館員工拿到的獎金將是以往的兩倍以上”揭示了整個事件從事實變為謠言的過程,它讓人們看到金錢的“力量”,讓人們看到了人性中惡是怎樣遮蓋了善的面貌。
(三)對比之聲
1.此聲與彼聲的對比
《第七天》中很明顯地存在兩個世界——現實社會和死無葬身之地(此岸與彼岸)。剛剛死去的“我”在靈魂游蕩的七天里,穿行于這兩個世界,通過這兩個世界中的人發出的不同的聲音(此聲與彼聲),主人公“我”不禁發出:有墓地得到安息,沒墓地得到永生的感慨。
這里以《第七天》中“我”住在出租屋時的鄰居劉梅自殺前后的聲音為例。劉梅自殺前經常和男朋友伍超抱怨、吵架,兩個人經常惡語相向,雖然他們很愛彼此,但彼此說出來的話依然傷害了對方。在劉梅站上鵬飛大廈自殺時,站在樓下圍觀的人只是一種旁觀的姿態,他們關注的不是如何保全一個生命,而是想要窺探一個即將逝去的生命背后的故事。文中圍觀者有這樣一段對話:“有人問:‘為什么站在那里?有人說:‘自殺呀。‘為什么自殺?‘不想活了嘛。‘為什么不想活了呢?‘他媽的還用問嗎,這年月不想活的人多了去了。”言語中充滿了好奇和不耐煩,絲毫沒有惋惜自殺者生命的意味。
在劉梅死后進入死無葬身之地時,她向后來的人詢問男朋友伍超的消息,向“我”說伍超很愛她,肯定會想辦法給她買墓地,讓她安息的。聽到伍超為了給自己買墓地去賣腎后,她聲淚俱下。伍超進入死無葬身之地后,也和劉梅一樣一味地說自己的不好,檢討自己的過去,說自己讓劉梅受了委屈等。兩個人只記得彼此的好,后悔過去沒有好好的對待彼此。當死無葬身之地里的人得知劉梅有了墓地,可以得到安息的時候,大家都為她開心,他們給她凈身,幫她縫制衣服,真誠地稱贊她的美麗,并祝福她。正如那些慢慢變為骨骼的人所說的:死無葬身之地的人與人之間沒有親疏之分,這里對誰都很好。在死的世界里,每個人都愿意把愛無私地給予他人。
2.世聲與天籟的對比
除了現實世界和死無葬身之地中人聲的對比,《第七天》中還存在著兩個對比的聲音,即現實世界中除人聲之外的世聲和死無葬身之地中的天籟。開篇人們即可看到文本中關于現實世界房屋轟塌的聲音,汽車轟鳴聲、相撞聲。隨著主人公楊飛的回憶,人們還會聽到電視中掩蓋事實真相的新聞之聲,劉梅從樓上掉落時的沉悶之聲等,這些聲音有關破壞和毀滅,有關虛假和死亡,正如作者在文章開頭所寫,如同沸騰的水爆炸,迸濺在生活的每一個地方,使得現實世界更顯混亂無序、殘忍無情。
與此相對,死無葬身之地的天籟,流露出了更多的溫暖與愛。余華在《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中談道:“音樂一下子就讓我感受到了愛的力量,就像熾熱的陽光和涼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風雨似的來到了我的內心,我再一次發現人的內心其實總是敞開著的,如同敞開的土地,愿意接受陽光和月光的照耀,愿意接受風雪的降臨,接受一切所能抵達的事物,讓它們都滲透進來,而且消化它們。”《第七天》中對死無葬身之地的自然之聲的描寫正是如此。
當“我”坐在自我悼念者的聚集之地時,“寬廣的沉默暗暗涌動千言萬語”,我們不說話也沒有任何動作,只是坐在靜默里無聲地相視而笑,感受我們不是一個,而是一群。自然界的寂靜無聲中涌動著千言萬語,這種“此處無聲勝有聲”的聲音,將每一個自我悼念者的心聯系在一起,將我聚成我們,讓愛把孤獨驅散。“我”還聽到了火的聲音、水的聲音、草的聲音、樹的聲音、風的聲音和云的聲音,這些聲音使“我”回憶起生的苦難,“我”接受并且消化它們,它們從我的心中飛出,最后變成夜鶯般的歌聲重新飛回來。
生的孤獨與苦痛在自然之聲中得到凈化和升華,它讓游蕩在死無葬身之地的人們把生前的苦痛轉化為愛,把死的世界變得溫暖——“沒有貧賤也沒有富貴,沒有悲傷也沒有疼痛,沒有仇也沒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三、亙古流傳的聲音:聲音的意義
“聲音就是意義。”由上述分析可知,人們可以看到《第七天》呈現出的多種聲音,其中包含豐富的意義。這些意義不是單一的,它們是連貫的,一個引出一個,串聯在一起,是一個整體。在文本中,作為引導的聲音,主要是引導“我”走向生前的記憶,在記憶中回顧自己的一生,這種回顧不僅是一種對生命的總結,而且引導“我”走向生命的真諦——真善美。除此之外,這種引導的聲音作為一種核心功能,引導著情節的發展和文本的敘述。藝術的力量在于它可以由文本中的具體事件和人物個體上升為哲學的抽象和人類的整體,從而使讀者感受到一種普遍的力量。文本中作為引導的聲音,不僅在引導著情節和敘事,引導著“我”,同時也在引導無數的讀者。
當“我”在生的記憶和死的現實中來回游蕩時,人們的聲音和作為補充的聲音,不斷地揭示著生的痛苦、冷漠、孤獨和殘忍。這些聲音將被掩蓋在冠冕堂皇之下的真實揭露,將每一個死亡事件都剖析袒露在人們面前,使人們看到了生的荒誕與冰冷,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暫與虛空。接下來的對比聲音,從現實世界和死無葬身之地中的人聲和事物與自然之聲中,人們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兩個世界的不同。正如余華在《人類的正當研究便是人》中提到的《德意志安魂曲》歌詞所描述的那樣:“永恒的歡樂必定回到他們身上,使他們得到歡喜快樂,憂愁嘆息盡都逃避。”“死亡一定被得勝吞滅。”聚集在死無葬身之地的人們將生的憂愁拋卻,他們互相愛著,在死中得到了永生的歡樂。兩種對比的聲音,同時也傳達了作者的隱含心聲——希望現實世界能和死無葬身之地一樣,人與人之間充滿友愛,萬物之聲如同天籟。
“聲音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是人類靈魂寄居的一個甲殼。聲音是人類與上帝溝通的手段,有許多人借著它的力量飛向了天國,飛向了相對的永恒。”余華《第七天》中的聲音正是如此,它帶著許許多多的楊飛進入了沒有貧富貴賤、沒有悲傷疼痛、沒有仇和恨,人人死而平等的死無葬身之地。在那里,他們回顧一生,感悟到了生命的真諦——真善美;經歷了生的痛苦,所以每個人都能無私友愛;他們受到友愛之聲的洗禮,在歡樂中得到永恒。
《第七天》通過聲音,向人們傳達了現實社會的眾生百態。它們召喚記憶,使人回顧生命,感悟生命的真善美,同時引導著情節的發展;它們暴露事實的真相,揭露現實的殘忍,以死的永生引人深思,同時表露作者的隱含心聲。正如卡西爾在其《人論》中所言:“每一位作者似乎歸根到底都是被他自己關于人類生活的概念和評價所引導的。”作者余華以楊飛為主,向人們展示楊金彪、李梅、譚家鑫等人的人生,同時表達的對人生的見解和觀點——人生雖艱辛而苦難,但也要懷著溫暖而堅定的信念。“要認識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為以外,就沒有什么其他途徑。”而《第七天》正以一個死去的亡靈的角度,為人們“認識人”提供了一條別具一格的道路。
(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張坤坤(1992-),女,安徽阜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