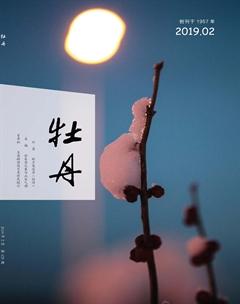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雙重角色
伊麗莎白·巴萊特·勃朗寧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女詩人。她的詩歌在英語文學史上頗負盛名。1856年,勃朗寧夫人完成了她的史詩巨著《奧羅拉·利》,并大獲成功。《奧羅拉·利》是勃朗寧夫人最長的一部詩集,也是她自認為最好的詩集。主人公奧羅拉·利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了自己和堂兄羅姆尼·利的愛情故事。全詩采用無韻詩的形式,共九本。一些評論家們曾對該詩的篇幅、體裁、語言、情節、人物塑造及對傳統的反叛方面頗有微詞。后來的研究主要從女性主義、神學、政治和藝術觀進行。中國學者對《奧羅拉·利》中的烏托邦構想、性別、婚姻觀、變盲的隱喻、女權主義者的歸宿等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不乏從女性主義視野進行的研究,但沒有說明《奧羅拉·利》中的姑姑既是父權社會的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從而揭示大多數女性在父權社會中扮演著雙重角色。本文將從姑姑對奧羅拉母親的厭惡、姑姑讓奧羅拉接受傳統淑女教育、姑姑對奧羅拉拒絕羅姆尼求婚的譴責三個方面來揭示姑姑深受父權社會侵蝕,在思想上認同女性從屬于男性。在自己扮演傳統女性角色時,她也極力主張身邊的人接受女性從屬地位。這一現象反映了女性既是父權社會的受害者又是維護者。
一
奧羅拉出生于佛羅倫薩,父親是一位英國學者,母親是意大利人。母親生下她之后身體極度虛弱,在奧羅拉四歲時去世。父親既當爹又當娘地將她撫養到十三歲時不幸去世,她被送回英國和終身未婚的姑姑生活在一起。經過漫長而無趣的長途跋涉之后,她終于到達了英格蘭。但是,在倫敦,她看到的只是姑姑如籠中之鳥的生活。姑姑是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代表,成千上萬的女性過著和她一樣的生活。
她活著
如籠中鳥般,在籠中出生
在籠中跳來跳去,
看上去比其他的鳥兒都生活得更加快樂。
天空啊,他們是多么的愚昧
羽翼豐滿,可悲地享受別人施舍的漿果!
年幼的奧羅拉就這樣被帶進了姑姑的“鳥籠”。第一次見到她時,奧羅拉渴望姑姑能夠給她的生活帶來一絲光亮。如此渴望與姑姑親近,一見面她就雙手摟住姑姑的脖子。姑姑將奧羅拉的手拿下,用犀利的雙眼尋找奧羅拉母親的影子。
姑姑愛奧羅拉的父親,也真真切切地討厭她的意大利母親。維多利亞時期,家中以男為尊,不論年齡,一家之主的妻子、孩子比待字閨中的姐妹們地位更高。不僅如此,父親因娶了異國的母親而被剝奪了繼承權。姑姑因此對母親十分不滿,然而這一切錯的不是母親而是社會制度。姑姑遭受的不公平對待,父親失去繼承權都被姑姑歸結罪母親。她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是父權社會造成的,而她的做法進一步支持了父權制社會對女性不公平對待的延續。
二
奧羅拉的姑姑是一位中產階級未婚女子,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老處女。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理想的家庭觀認為一個完美的、受人尊敬的女性地位應體現她在家庭中的位置,其自身價值體現在家庭中的犧牲精神和作為道德天使的角色中。按照當時中產階級的女性觀,這些女子未能通過婚姻實現自身價值,在社會上被歧視。為了讓奧羅拉將來能嫁給繼承人羅姆尼,不要像自己一樣遭受終身未嫁之苦,姑姑按照淑女標準對奧羅拉進行培養,繪畫、舞蹈、女德和女紅都被排進了奧羅拉的日程里。繪畫舞蹈是融入上流社會的必備技能,婦德奴化女性思想。在維多利亞時代,男人們夸夸其談,而女人則被要求認真傾聽并表現出十分欽佩。女性不能評價男性的言論,更別說發表自己的意見。姑姑總是喜歡女人要有女人的樣子,并自豪地宣稱英國女人是世界所有女人的模范。姑姑全盤接受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壓抑并按照維多利亞時社會期望的女子形象塑造奧羅拉。在姑姑的監護之下,女紅又是一門必修課。然而在奧羅拉看來,女人每天縫來縫去,戳破了手指,損壞了視力,制造出一雙拖鞋、馬桶墊、坐墊。然而,這些勞動成功大多數都被男權主導的社會忽視。
姑姑意將奧羅拉的培養成“家中的天使”。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仍然是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其主導信仰是,婦女低劣于男人,婦女地位低于男人。與男尊女卑的社會地位相對應的,此時大多數家庭都是父權制的,中產階級家庭也是如此,夫婦關系是夫尊妻卑,妻子附屬于丈夫,丈夫地位高于妻子。“家中的天使”同時也意味著妻子成為丈夫的附屬物,女性接受丈夫提供的舒適生活,同時家庭成為她們唯一可經營的事業。換而言之,女性不僅失去了在家庭中的平等權利,也失去了家庭之外的事業。姑姑對奧羅拉的培養正是要使她成為能被社會接受的女人,也就是從屬于男人的人。正是成千上萬的女性對年幼女孩的培養使女性從屬地位得以延續。
三
姑姑既是父權社會的受害者又是支持者。她無時無刻不向奧羅拉傳遞順從的觀念。好在奧羅拉意識到了成為順從的女人的悲哀,一次偶然,奧羅拉發現了父親藏書滿滿的圖書館,閱讀了大量書籍。她尤其癡迷于詩歌,并立志成為一位獨立自主的詩人。在她二十歲生日時,堂兄羅姆尼向她求婚并希望她放棄詩歌寫作,作為他的妻子幫助他完成社會主義追求。羅姆尼對女性寫詩的能力很懷疑,貶低女性詩人能為社會帶來的福利。他告訴奧羅拉女性沒有足夠的熱情、智力和自我救贖能力成為真正的詩人。他極力勸說奧羅拉放棄詩歌夢想和他結婚。對于羅姆尼來說,與其說需要的是一個妻子不如說是需要一個幫手幫他實現社會主義夢想。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國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她在著作《第二性》中寫道:“從傳統說來,社會賦予女人的命運是婚姻。大部分女人今日仍然是已婚的、結過婚的、準備結婚或者因沒有婚姻而苦惱。”在維多利亞時期,婚姻如同市場。大多數女性只有通過婚姻,才能獲得社會地位和經濟保障。如果從這些方面考慮,羅姆尼確實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然而,男人提供的保護和物質保障是以女性的順從為代價的。和羅姆尼結婚意味著放棄自己的才能,每日在家中處理既費時間又花精力卻不被丈夫和社會認可的家務。奧羅拉不愿拋卻自己的理想去過以輔助丈夫為生活中心的主婦生活,因而拒絕了羅姆尼的求婚。她清楚地明白羅姆尼需要的“并非妻子,而是助手”。
姑姑因奧羅拉拒絕羅姆尼的求婚嚴厲地指責她。可憐的奧羅拉因是意大利人的后代而被剝奪了繼承權,遠房堂兄羅姆尼成為家族合法繼承人。如果奧羅拉不與羅姆尼成婚,她將一無所有。姑姑不相信奧羅拉寫詩能養活自己,更不曾預料到十年奧羅拉的詩歌將會得到大家的認可。因而,姑姑要求奧羅拉為了生活保障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姑姑不懂得女性渴望的不只是社會地位和豐富的物質,還有情感與精神依托。盡管婚后羅姆尼會為奧羅拉提供舒適的生活,但是他們的結合也必然會給奧羅拉帶來更大的傷害,因為羅姆尼根本就不理解、不支持奧羅拉成為詩人的夢想。如果成為一位依附于丈夫的家庭主婦,奧羅拉就難以成為一位獨立的有自己思想的詩人。姑姑對奧羅拉拒絕羅姆尼的指責也是為了逼迫奧羅拉接受他的求婚,認為女人應該成為“家中的天使”。姑姑接受了女性從屬于男性的地位,并將這種思想傳遞給奧羅拉。這正是反映了父權社會中,女性不僅接受了自己從屬于男性的地位,而且通過培養下一代將這種思想一代代地傳遞。
四
姑姑就是在從小被灌輸女性環境之下成長的,女性從屬于男性的思想已是根深蒂固。當奧羅拉來到身邊時,她也極力將她培養成“家中的天使”,并期望她能與羅姆尼成婚。她的生活代表著千千萬萬維多利亞時期其他女性的生活,她們既是父權制社會受害者同時也是父權制社會的維護者。
(四川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作者簡介:曾海燕(1993-),女,重慶人,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